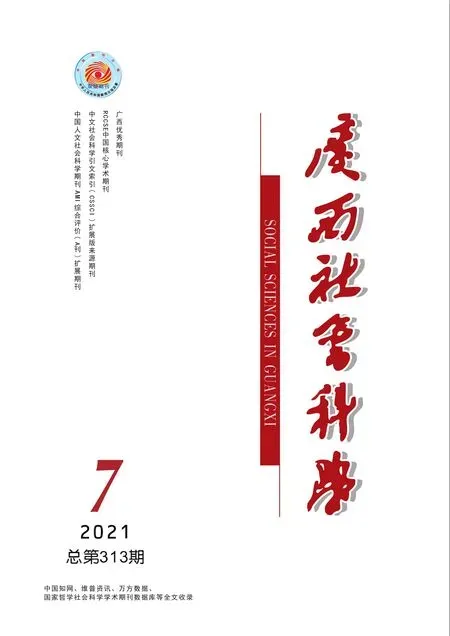共生、流衍与增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研究
2021-04-15杨刘秀子
杨刘秀子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2019年,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强调,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人文合作,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1]。“一带一路”博采文明之长,极大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文学是交流的方式之一,它能实现想象力、现实和创造力的共融共生,是作家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折射,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根据,助力与助兴于解码“世界是通的”①王义桅在书中强调“五通”所代表的互联互通,认为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是“通”的模式。参见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无独有偶,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文学是“通达”人类文明的桥梁。。文学跨越时间参数进入不同的场域,其生产与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共鸣,进而对“一带一路”科学把握“正和博弈”、走向共赢之路有所裨益——由此,文学便有了其所特有的属性——世界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与国之间有着深厚的共生基础及文化基因,可消除各种隔阂和壁垒,文学的传播方式与渠道也因此而更为多样。沿线国家文学在多元文学质态的交流互鉴中,构筑起自身的文学场域,将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共生基础
(一)对古丝绸之路文化基因的深耕
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2]。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文化和文学酝酿与生成,满足了沿线国家人民对异域国度的美好想象,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域,拉近了“过去—未来”的距离。经过长年历史与文化积淀,文学交流成为沿线人民的共同追求。文学不仅体现自身文本的意蕴,更是民族文化价值的体现。在经济贸易往来中,商品交换成为丝绸之路的主旋律,在频繁的物质交换之余促进了文学交流。早在公元前,“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两次持节出使,为日后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埋下了伏线,同时也带去了东方文学的赞歌。古丝绸之路串起中国与古希腊等各国之间的联系,《奥德赛》《乌孙公主歌》等作品成为文学交流中璀璨的明珠。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催生出富有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王传》,这些作品高唱出的英雄主义颂歌不乏古丝绸之路的文学基因。丝绸之路中的文学交流冲破了时空藩篱,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古希腊史诗《伊利昂记》中,希腊人骁勇善战,通过久战维护了集体的利益,如此宏大、连贯的叙事对后世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吾尔族史诗《江格尔》,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丝绸之路商品交换的背后是文化沟通。”[3]如此可见,古丝绸之路不单单止步于简单的物质交换和经贸往来,文学作品已然成为沿线国家人民的心灵依托和精神支柱,为广大人民带去良性的抚慰,或是奋斗精神,或是温暖启示,使读者镂之于心。刘大先在谈及丝路文学时提出:“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一直以来就有文学的相互传播。比如敦煌千佛洞里发现的大量唐代变文钞本,那些作品往往是渗透式的存在,而不是在现代文学学科经典化之后的所谓的经典文本。海上丝绸之路也存在大量的‘旅行文本’,比如宋元的南戏传到越南等地被本土化,然后又在明朝时候通过京族传入到中国,影响了壮侗语族的民间曲艺。也就是说,丝路文化交流是彼此渗透的,更多是浸润到了文学方方面面的影响。”[4]事实上,远不止古代的文学文本产生传播影响,报刊文学的出现也助力了文化的沟通。从表现形式来看,报刊本身就被近代社会视作“显学”。例如,我们从1906年6月22日《香港少年报》刊布的《各埠代理派报题名》中可知,其传播的影响范围不单限于香港,还有岭南的其他地区,甚至海外;无独有偶,岭南、上海、天津等地的报刊亦有相似的传播效用。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散发出耀眼光辉,有其独特的文学、文化审美意蕴,如今,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作品凭借着强大韧性和自信底气在文明交流过程中得以流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涵括
“一带一路”既承载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为沿线各国提供包罗万象的文学交流平台,形成多元交融的文学态势,又体现了全面、正面、通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内涵。其中,“全面”是指通过既往的文学交流范式阐释在共生中已取得的成绩、被发现的问题和可展望的未来,“正面”是指以文学交流为契机,为发展注入能够沟通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动脉的正能量,“通透”是指要把沿线国家通过文学交流的共生发展逻辑和规律找出来。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旨在借由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共生发展,构建包容互利的国际新秩序——这是习近平在审视中国自身发展道路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构建新的世界格局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以及我国各民族关系的行为准则,强调以“亲诚惠容”理念重塑周边环境,呼吁各国在全球范围加强合作共赢,构建一个和谐、开放、繁荣的国际环境[5]。
透过文学,我们能感受到更博大丰盛的文化人的“共同体”——“文学共同体”,其旨归是文明交流互鉴,摒弃文化霸权主义逻辑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以共赢取代对抗,以和平促进发展。“文学共同体”超越了个体的狭隘私欲——中国的“和合”文化基因正是最好的映衬,亦是沿线国家人民坚守和平的文化根基、共识愿想。对世界文化而言,合理有效的文化思维和文化发展战略是不可缺少的[6]。中国文学与沿线国家多元文学具有思想的共通性,儒家讲求兼收并蓄,文化间的交流不以征服、打压为目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交流史是最直接的见证。“和合”思想圆融精微,体现了对世界的辩证涵括,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共性。一方面,强调在差异与矛盾中寻求统一、异中求同;另一方面,注重聚同化异,强调对异质文化的差异性的认可。“和合”思想衍生出多样的价值追求,并深刻植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中国文学熔铸“和合”之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尊重彼此差异,坚持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以开放、欣赏的态度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不断推进“文学共同体”的构建,积极与各国开展文学文化交流互动。中华文化没有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又是中华精神文化的现代价值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为中国与各国的国际对话增添了介质,多元文化熔铸一炉、相互言说,通过国家间的优秀文学共享与传播,把握彼此文化精髓要义,使得文化在互学互鉴中真正做到共生。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演进
(一)不同文化质态的文学传播
在文化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式的交流不仅仅在汉文化圈中涌动,也在异质文化圈中有所延伸。汉文化圈在文化源流、语言传播形式等层面与中国文化有共同之处,相比于异质文化的文学传播,中国文学在汉文化圈的文学交流时间更为长远。早在秦朝时,汉文化就已传至越南。汉朝时期,汉字已在越南传播开来,在随后的2000多年间,汉字在越南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据统计,现代越南语中仍有70%以上的词汇是汉语借词,即汉越词[7]。汉字作为中国文学的语言载体,在文学跨国传播扮演着紧要的角色,是古汉文化圈得以促成的前提。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及以唐诗为代表的诗歌典籍在汉文化圈中大行其道,得到各国人民普遍认知和接受,并在汉文化圈的文化津润中起到促进作用。近代,传教士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的关注与译介,再次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加深。这种“加深”恰似催化剂,不但强化了中国故事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构建,而且使得部分学者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拥趸——这一切得益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科技革新、思想启蒙乃至社会心态变迁”[8]。16世纪处于繁荣顶峰的明代,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是印刷技术。“欧洲知识界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称羡的国家,那里司法得到良好的实施,百姓都富足和工作勤奋,还有和平及自我克制,艺术和工业发展到不容置疑的高度,甚至欧洲引以为傲的印刷术,被发现在中国早已有之。”[9]小说作品与刊刻技术相互观照,成为中国文学向异质文化圈传播的重大来源,促进异文化圈了解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程国赋总结道:“明代书坊刊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10]正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程度较高,在传播中甚至催生了“翻案”文学。小说大量涌入汉文化圈,传统训读及翻译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对原作进行“翻案”更符合汉文化圈读者的审美需求,于是掀起了一场中国小说的“翻案”热潮。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比邻而居,交流密切。在朝鲜世宗李祹尚未发明朝鲜文字之前,中国小说就已传入朝鲜王朝。15世纪,金时习的传奇小说集《金鳌新话》“翻案”自明清小说《剪灯新话》。17世纪,朝鲜半岛涌现了一批积极接受外来思想的知识分子,富有生活气息和哲理智慧的明清小说正契合了其吸收先进文化的需求。韩国闵宽东指出,已发掘的朝鲜王朝时期所传入的中国明清小说共有290部[11]。梁冬丽提到,《青楼义女传》翻案自《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题材、背景地点、托梦还愿、悲剧结局、主题思想都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脉相承。《彩凤感别曲》翻自《今古奇观》卷三十五《王娇鸾百年长恨》[12],不管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处处可窥见《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影子。文学是文明重要的承载体,文学交流促进文明对话。“翻案”文学在对中国文学变仿、增添、再造中进行文学创作,成为其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表达自身文学内蕴的同时,也展现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是跨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体现。
不同文化质态的文学传播还包括了教材中的文本传播[13]。古代韩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汉文教育成为主流。《世宗实录》卷二十三写道:“高丽设汉语都监及司译尚书房,专习华语。其时汉人来寓本国者甚多。”[14]世宗五年即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成宗下旨:“夫始肆华诸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两书,以为学语之阶梯。”[15]其中,“老乞大”是“老契丹”的转音而来,意为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人,该书采用对话的体式讲述了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的故事。另一著名汉语教材《训世评话》由李边撰写,采用中国评话的形式、文白对照的体例。由此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可追溯的,并早已在不同的阶段形成了多种可资参照的交流路径。
(二)多元文化的统合
文学巨擘鲁迅、伤感派小说代表郁达夫、专以报刊小品文学牖导社会的郑贯公等都曾留学日本,日本文学及中国文学相互影响,产生了共振关联。在新文化兴起前,中国民间文学及传统古典文学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部分华人和知识分子迁居东南亚,并带去了中国文学。以中国文学为基础的近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文学得以生长、壮大。茅盾、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在东南亚国家传播甚广,不少现代中国作家的经典文本更是被选入教科书。许多中国文学的作品素材直接取于东南亚的社会风貌,展示了东南亚的人情世态、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及精神文化境界,比如许地山的《命命鸟》、许杰的《椰子与榴莲》。东南亚国家的现代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观念上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其中“同”是既对道德观念的强调,也对民族气节的拔高。因此,中国文学作品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1936年,泰国曼谷还举行了全国性的鲁迅纪念活动。
随着世界各国紧密联系,我国开始对东欧、阿拉伯等异文化圈的文学作品做译介工作。在社会历史语境下,东欧的红色作品译作、黎巴嫩文学史家乔治·宰丹、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等作品大量涌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很大,即使一些国家同为汉文化圈,其文化也存在差异。因为崇奉信仰的不同,也许会造成文化曲解和文化摩擦——是文学交流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但正因为“一带一路”是一条“海纳百川”的道路,绝不能因矛盾存在而遏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本交流实践,更不能停止借用文学文本还原文化高度丰富性和高度复杂性的脚步。近代中国文学与沿线各国文学已逐步找到彼此文化契合点,成为许多文学译著者阐释和分析文学文本的重点之源。而沿线各国文学作品并非单单停留在地域文化视域中的本民族文化生产,在统合沿线各国不同地域、场域文化非均质化的风貌下,文学文本和文体风格各具特色,中国和沿线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再过度局限于本民族文化,而是突破流于地域、场域文化的僵化机械套用,真正实现文化互补共鉴及多元文化相容共生。从中华文化历史底蕴中获得深沉持久的力量,能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文化圈相适应,进而产生世界价值和永恒意义——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固根基,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
(三)文学价值意蕴的探寻
优秀文学作品因人类对艺术及生命本质的价值探寻而得以跨越地域、纵横古今及突破语言的隔阂。关注各国文学的民族个性,彰显人类对生命、情感、自由的审美及价值判断。各国由于发达的农业文明带来了思维思量上的相近性,善于用整体性思维、经验性倾向来分析事物,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为彼此交融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交流需要突破当前沟通障碍,通过交流对国与国形象的认识认知进行编码再造。“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文学交流,应关注于沿线国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解释和发掘。沿线各国文学的深入交流,促使各国文学冲破国与国的边界,迈向世界性的深化沟通,片面狭隘的民族局限性将得到逐渐消解,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作品合力打造世界文学的态势将得以形成,并演变成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新的审美现实。文学的“世界性”强调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传播将常态化,对文学价值意蕴的探寻将常规化。中国古代文学在“丝绸之路”上熠熠生辉,当代中国文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出了更广阔的书写空间,为丝绸文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图景和文化魅力。“汉语热”的掀起,如孔子学院的人才派驻、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助力了中国文学的传播传颂;我国文学作家斩获了不少国际性的文学大奖,作家莫言于201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一个世界性、文学性事件,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良机。《红高粱》《酒国》等作品得到各国不少读者的青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文学译介发展的助力,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文学与各国文学没有抵牾之处。莫言深挖高密东北乡的文化传统,创设出了符合各民族审美心理的文学样式,在艺术创作中显露了民族文化、体现了时代精神,创作出了一个既属于中国,又表现“人类共同体”的文学作品。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学在多渠道的文化传播中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传播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三、“一带一路”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增殖路径
(一)文学交流在互鉴中形成文化合力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作家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股新的力量[16],这将有益于推进跨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获取的整合反应。数字化信息时代,多元信息渠道为文学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范式,世界文学成了新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的文学交流,超越空间、国家的视野,以世界文学的高度重新探索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人类学对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17],沿线国家文学亦是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着力助推“数字丝绸之路”的搭建,促进了文学共同体为价值趋向的构建。文学既能表现人类普遍的共性,又带有自身的民族特性,因为社会环境及历史语境的不同,各国文学存在差异,因此在交流过程中需要对焦各国文化,不是刻意追逐文化趋同,而是在文学译介和交流传播中凸显文化张力,并在碰撞中彰示合力,从而使传播内容产生裂变效应——而“变”的前提毋庸置疑是“合”。由于沿线国家不同群体对中国文学接受度有所不同,文学交流传播中应注重差别化,并培植开放、包容的环境土壤,在与不同国家文学交流中对国家的风土人情、国家发展、审美取向及文化趣味进行细致探察,从而探索为该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播路径及方法,实现中国文学与沿线国家文学的精准对接,展现中国文化交流的诚意、善意,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部分负面舆情。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中,各国主体要深深植根于自身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保有自身的民族初心和特性,匡正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处理好国际视野下本国文化及他国文化的关系,既不能停留于对他者文学外在形式的机械模仿、空流于形式,在迷途中丢失自我,也不能故步自封,而应以兼收并蓄的胸怀接受批判。
(二)文化传承与出跳中凝聚智慧
“文化全球化是既成事实,是一种存在的现实。”[18]面对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化,“一带一路”的文学交流作为新时代国家文学交流的样态,沿线各国须品析融聚古今民族文化的精粹,结合当前时代的精神风貌,在民族文化中创新话语表述方式——这是“一带一路”文学交流“合”与“变”的意旨,也是对民族文化优秀基因的传承与进化、升华,更是各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的当代实践显现。中国文学作为“一带一路”文学交流的倡导者,在交流中注重如何对中华文化丰饶性和广延性进行深度开拓是必要的。中华文化的精粹出跳于历史局限,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创建新的发展境界,能够为当代国际关系处理生发出有价值的认知图示。
“一带一路”文学交流过程是对本国文化创新传承的过程,能够促进文化内省与理性思辨。精准切入新时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判断和文学创作实践,探知世界交往的诉求,赋予本民族文化以新内涵与外延,并在承接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实现新时代转换——“一带一路”视域下文学的创作及传播,不是单一的本民族文学的追寻与复归,而是在“一带一路”语境下使文学理论与实践舞台实现转化,呈现出文学传播的新样式。“一带一路”的文学交流须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路标中,也须从本民族文化历史架构中实现未来文学创新的智慧凝聚,是民族文化精神在新时代转换的探索重点。“一带一路”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为丰富文学和本国文化本身而存在的。因此,在与沿线国家文学交流过程中切忌游离于本国文化之外,避免文学交流变成对枯燥文学文本、国家史料的堆砌,而应转换思维,集中力量,激发沿线各国文学的生命力,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可始终保持以本国文化为源,拓展文学交流的格局。
(三)多元赋能促进文化价值的全球传播
随着各国经济、政治力量的崛起,“一带一路”的相关建设在国际话语权中开拓了新的面向,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创建沿线各国文化成为一个时代话题。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如果对个体的文学文本解读与阐释不能从客观、普遍意义上取得共识化,认知偏见视角的切入难免会存在对作家内在富厚的精神世界限缩、简化和苛减,甚至偏离、遮蔽作家文学生命的本质。差异性个体由于对不同的国家存在刻板记忆,难以在文学作品中了解作家作品想象、构建的共性联结点,从个体经验中很难抽象出文学作品的“世界性”价值。为了减少文学交流中读者偏见所造成的文学价值曲解,不能仅仅将文学交流限缩于品读文学经典作品样本,极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文学交流的宏观视野中,通过经济、政治等多维度、宽领域的合作,在新信息宣传渠道中严格检视并多元赋能,从而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的活力。
不得不承认,当下文学的传播与国家实力紧密相连。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跻身世界前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研究与日俱增。当前,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的交往有效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世界文学传播的历史轨迹证明,一国文学影响力与国家综合国力、世界影响力是呈正态比例的。中国文学见证了中国的长足发展,国力的提升、经济的崛起、权力话语的构建助推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学与沿线各国的交流愈加频繁,中国文学的主题、形式和内容方面更为多样,已培育出一大批兼具民族特性及世界视野的文学家。沿线各国加强在经济、政策等多领域的合作,借助文化来表现民族的风貌,以国家形象增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在增强民族向心力的同时,促成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对话。在媒介融合下,传媒产业壁垒逐渐消解,传播内容形态和组织方式趋向多媒体数字化,传播渠道相互连通又互为补充,为“一带一路”的文学交流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数字化信息、有声化媒体背景下,文化传播渠道更为多元,文化作品成为各国形象的展示载体,是人们接触异国文化的紧要存在。他国文学、他国民族元素在各国的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国家形象在各国的文学作品中频频显明。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的文化声气相应、走向世界创设了一个国际化的舞台,为世界认知各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其所呈现的是民族与世界的交互与统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超越以往群体无意识的传承与传播形式,经过系列文学交流实践的洗礼与文化合作实践的烛照,能够进一步打开走向世界文化的大门,使文学在价值塑造、精神凝聚中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实现“人类共同体”福祉最大化的可贵实践,沿线各国的文学原生价值得以丰富与再认识,借助技术赋能将对具有某种共通性或差异性的文本加以分类和区别,加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再认识和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