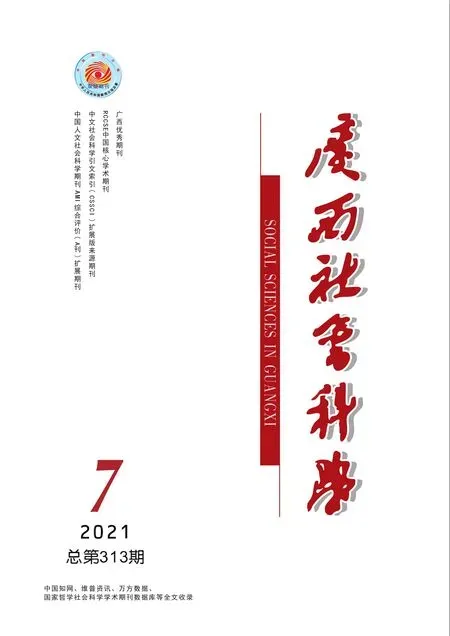远古至春秋时期的情报问题探析
2021-04-15黄朴民刘进有
黄朴民,刘进有
(1.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2.重庆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16)
情报一般指被用于传递的知识或事实,具体而言是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所需要的一种信息。相关人员对这种试图获取的信息投入大量有效的工作与活动,希望从获得的信息中汲取有效内容,并据此进行决策。《辞海》对情报的含义分类进行了解释:“获得的他方有关情况以及对其分析研究的成果。按内容和性质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等。”[1]由此概念界定,本文所谓的情报主要包含政治情报、军事情报两个方面。由于军事与情报的关系似乎更为紧密,本文亦会对军事情报方面的阐述略有侧重。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情报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甚至是在经济领域中,情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以往情报活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侧重于军事情报思想理论的研究;另一种注重对间谍活动的研究,且多集中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情报活动。总的来说,学界对先秦情报研究方面仍然关注较少,且缺乏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就远古至春秋时期情报问题的起源、一些具体的情报活动及情报理论作一系统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情报问题的缘起
(一)远古情报活动的起源
情报活动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早期的情报非常简单原始,主要传递有关饮食、起居与生存安全方面的基本情况与信息。如众人配合围捕猎物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情报传递的内容也扩展到政治、军事等领域。根据先秦典籍可知,在氏族部落时代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情报活动。
《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黄帝因著《占梦经》十一卷。”[2]当时,黄帝姬姓部落地处西北,蚩尤为东部及南部部分部落的联盟首领,两大部落联盟斗争日趋激烈。为了赢得最终胜利,双方各自拉拢或征服周边部落,至于派往四方打探各地情报的人员自不在少数。黄帝部落派往东部地区与南部地区的情报人员应当发现了部落首领风后、力牧的能力以及所领导部落的重要性,并将此事告知于黄帝。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3],说明黄帝通过允诺二人高官厚禄,最后使两人及其部落归顺黄帝。这应该是较早的关于情报工作的记载。帝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众人举荐舜为其接班人,帝尧“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4]。换言之,帝尧为了考察舜的能力与品行,便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私下的品行,以“九男”与其相处共事来观察其治邦理政的才能。通过这种方式,帝尧将舜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直至最后方将帝位传之于舜。《逸周书·史记解》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昔谷平之君愎类无亲,破国弗克,业形用国,外内相援,谷平以亡……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5]也就是说,有果氏曾帮助少康中兴,之后日益骄纵、不听王令,且喜欢以新易旧,因此导致国家内乱,夏王趁机收买一些有果氏的国内大臣,最终在内忧外患下,有果氏走向灭亡。谷平之君残忍暴戾,打败他国却不灭之,最终敌国利用谷平国内的反对者,大量搜集谷平国内部情报,趁谷平君不备之机消灭了谷平国。绩阳国四处征讨,重丘国不堪其扰,遂以美女为间谍,献于绩阳国,蛊惑其君,使其不理国事,同时绩阳国内政被女间谍告知重丘国,终使绩阳国一分为二,重丘国也在强国压境的局面中得以存活下来。通过此处三个案例可以看出,间谍已经在早期的邦国斗争中产生,并成为各国获取政治情报与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者。《国语·晋语》记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韦昭注:“伊尹,汤相伊挚也,自夏适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6]《吕氏春秋·慎大览》曰:“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7]由此可知,伊尹以商汤谋臣的身份潜入夏朝内部,同时亦和妹喜勾结,窃取夏王朝情报,为商汤灭夏作了大量工作。
(二)殷周之际的情报活动
殷周鼎革之际,周人一方面臣服于大邑商,另一方面又为积极翦商做准备,打入殷商内部、搜集情报便是文王翦商、武王伐纣活动中的重要举措。早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已经开始为起兵伐商做好舆论准备,而这一舆论引导是通过“太姒之梦”来实现的。清华简《程寤》有载:
太姒梦见商廷惟棘,廼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币告宗祊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8]。
来自殷商的贵族女子太姒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个梦是大有寓意的:商王的庭院中不成材的荆棘预示着商朝朝纲混乱,将要走向衰败。太子发移栽梓树于商廷,梓树成佳木说明周人将要取代殷人拥有天下。同时,周文王让神巫给自己、太姒、太子发祓灾,并使梦成为吉利的梦,表示已经从皇上帝处接受了商王朝的“命”。当时的周部落尚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刚脱离母系社会不久,女性地位较高。《诗经·大明》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9]太姒乃来自殷商的大邦之女,貌若天仙,地位尊贵,文王亲自到渭河边迎娶,可知太姒在周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且她为殷商贵族,对商朝内政十分熟悉,通过“太姒之梦”预言商朝将要灭亡,这一预言在周人中更有信服力,也更能团结周人及其联盟。由“太姒之梦”可见,周人十分肯定商王朝处于政治衰败、穷兵黩武的局面,以及周革殷命将会在太子发领导下完成。此类信息皆能说明,周人已经掌握商人的内政、外交、军事等情况。殷商后期,帝乙、帝辛(纣王)父子深陷征伐东南夷的泥潭无法自拔,朝歌空虚。周武王通过情报人员得知商军主力移师东南,王畿空虚,多次观兵孟津,一方面是消灭、威慑殷商周边的部落方国,另一方面是伺机进攻殷商防守空虚的都城朝歌,并凭借情报在第三次观兵之际一举克商。
商末,社会矛盾丛生,帝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得罪王朝内部的一大批元老,引起众多贵族的反对。这些人员便成为周人拉拢的对象,甚至成为周人获取商王朝内政的重要情报源。《国语·晋语》有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韦昭注:“胶鬲,殷贤臣也,自殷适周,佐武王以亡殷也。”[10]帝辛“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最终“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11]。也就是说,胶鬲原本为殷商大臣,最终叛商归周,甚至连太师疵、少师强这种地位较高的贵族也投奔于周,将商的军国情报尽告于周。这些人即便不是周人的间谍,也是周人利用商王朝内部的矛盾长期离间商人的工具。这便为获取殷商情报消息提供了便利。帝辛是一代雄主,“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12],然而他被周人栽赃污蔑,最终成为暴君的象征。在遍读中国史书的毛泽东看来,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接着,他又对帝辛地位及其周人利用情报灭商作了客观描述:“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13]可知,周人所从事的情报工作为其灭商作出重大贡献。故而孙子对用间与情报在商人与周人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有所阐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4]
(三)春秋时期的情报活动
周王室东迁后,天子无力掌控诸侯,诸夏纷争的时代也由此开始。由于利益纷争与斗争的加剧,各国与各阶层之间相互使用间谍以及获取情报的活动日益增多,且多种多样。
春秋时期,各国来往频繁、战事不断,各国甚至一国之内的不同统治集团相互遣送间谍更是常见之事。譬如《周礼·秋官·士师》记载的邦贼、邦汋、邦谍与《左传·成公二年》中的候正,这意味着春秋时期间谍已成为各国的专业情报人员。《左传·桓公二年》云:“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杜预注:“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师为曲沃伯。”[15]曲沃桓叔在晋国威望甚高、实力雄厚,晋昭侯十分畏惧,故而将桓叔封于曲沃以分散其在国都中的势力。即便如此,晋都的大夫潘父与身在曲沃的桓叔暗通款曲、传送情报,并“作为内应,发动政变”。《诗经·唐风·扬之水》的作者是个知情者,“他跟从桓叔去了曲沃,但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通过诗歌的形式委婉地告了密”[16]。当时晋国的局面是晋王室衰弱而曲沃强盛,“国人将叛而归沃”,作者还以诗歌“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17]的形式偷偷告密,希望这场密谋政变能为晋君知晓,由此断定作者当是晋君派出跟随桓叔的间谍。双方为了完全掌控晋国,各自搜集对方情报,最终潘父弑晋昭侯并欲迎立桓叔,国人击退桓叔,暂时保存晋国大宗。情报与间谍在这场政治、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18],这里的“觇宋者”便是潜藏于宋国的情报员,意思是晋国谍报人员侦查完宋国情况后,将情报信息报之于晋侯。《左传·桓公十二年》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19]伐绞战役中,罗国人伯嘉潜入楚军营地,数清了楚军的人数,为罗人攻楚提供了重要情报。楚国令尹子元伐郑,“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20]楚国的军队攻郑,郑人害怕欲奔他处,间谍侦查到楚营上方有乌鸦,便将楚军已退的情报告知郑国。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卫国将伐邢,礼至说道:“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21]因而,礼至与昆弟前往邢国作了武士,实则作为间谍向卫国传送情报,卫人借此情报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22],邢国因此灭亡。
郑武公欲伐胡国,以女嫁胡君以堕其志,并询问众人:“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说:“胡可伐。”郑武公怒而杀之,并说道:“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于是,胡君以为郑人亲己,不再防备郑国,“郑人袭胡,取之”[23]。郑武公通过嫁女使得胡君错误以为郑国欲同其交好,杀掉主伐胡国的大夫不过是郑武公为麻痹胡君释放的一个虚假情报,胡君不辨情报真假,致使国家灭亡。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卒,出殡之际,灵柩内“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并说:“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杜预注:“声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闻秦密谋,故因柩声以正众心。”[24]之后,果然如晋人所预测的一样,为郑国守城的杞子送情报于秦,说:“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25]秦穆公派大军出师郑国,及至滑地,正要去周都做生意的郑商人弦高遇到秦军,探知其欲伐郑国的企图后,“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言:“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26]弦高欺骗秦人,说郑君让他在此先以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慰劳秦军,并将伐郑告知于下人,使其将秦军入侵一事快速传达给郑国。秦人以为郑国有备而来,故放弃伐郑,转而灭掉滑国,回师途中为晋军全歼。在此过程中,秦国通过杞子的情报便仓促起兵。晋国的情报人员获得秦打算越过晋国边境伐郑的消息,晋大夫利用晋文公灵柩制造声音,说这是文公之灵发出的军令,不久之后秦军会越过晋国边境,出击定会大获全胜。秦军越过晋国边境却不告知晋国,秦人又对晋国的战略意图一概不知。而晋人对秦国的动机了若指掌,又知秦军将骄兵逸,故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秦兵出动,保密工作做得不够,面对郑国商人,秦人又未能及时控制,对弦高的虚假信息不加分析,为其所误导。郑人又能根据半路截取的情报详加利用,快速做出反应,避免亡国之祸。由此可见,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及时掌控情报与利用好情报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与战争胜利具有重要作用,而对情报的简单利用、错误利用则会造成覆军杀将的危险。
春秋时期各国关系错综复杂,掌握他国内政情报对于处理本国内政、外交具有重大意义。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六卿专政、内斗不已;面对吴国的咄咄攻势,楚国疲于奔命、处处挨打。此时,晋国执政者赵文子根据楚国和齐国的内政情报,指出弭兵(罢兵休战)的可能性:“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27]宋向戌与赵文子友善,又与楚令尹子木交好,“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28],向戌通过多年的外交经历,打探各国有关外交举措的情报信息,得出诸侯皆厌兵,促使诸侯“弭兵”的机会来了,而他正是实现诸侯休兵的桥梁,这不仅能成就美名,而且还能为各小国尤其是宋国免除战争之苦。晋楚争霸,郑国首当其冲。在弭兵前后,郑大夫子产探知“晋楚将平,诸侯将和”的情报后,针对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国讨伐郑国一事,子产认为:“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29]建议不做抵抗以满足楚王的虚荣心,结果正如子产所料,楚王率军队耀武扬威一番后班师归国,一场大战就此化解。数年后,楚令尹公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筑城三座,郑人恐慌,子产对楚国内政也十分了解,通过情报人员调查得知公子围欲夺取王位,筑城以转移国内矛盾。故子产安慰国人道:“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公子黑肱、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30]果不其然,次年冬,公子围绞杀楚王郏敖而自立。郑国是楚国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的必经之地,郑国亦屡遭兵祸,子产正是掌握了楚国政治动向及其相关情报才能使郑国一次次化险为夷。
二、情报思维与情报理论
就目前而言,《逸周书》是最早涉及情报理论的典籍。《逸周书·大明武解》中曾记载有“三疑”“间书”,朱右曾注:“三疑,一、虚者实之,二、实者虚之,三、虚虚实实,皆使敌人疑而莫测。间书,遗之书以离间之。”[31]此处强调了使用疑惑之法来打乱敌人的认知,使敌人对情报信息真假莫辨。同时利用虚假的情报信息离间敌人,使敌人内部瓦解。《文政解》记载的“九慝”,即九种罪恶之事,其中便有“外有内通”之罪,陈逢衡云:“外有内通,奸人潜结左右也。”[32]其意指收买对方人员以为己用,通过这些内线探知敌方内情,获取自己想要的情报。《武纪解》曰:“伐国有六时、五动、四顺。间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约。”陈逢衡注:“间其疏,谓间彼疏远之臣,使为我用。薄其疑,薄,迫也,敌有所疑,则多方以误之。”[33]这里强调了在征伐敌国的战争中,利用重金、美色以及高官厚禄瓦解敌人、拉拢敌方不受重用之人,并借虚假情报误导敌人,使对手难以有正确的取舍与判断。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期,周人已对情报问题十分重视,并有一定的理论总结,但所涉情报问题十分散乱简略,这种理论总结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技巧,尚未形成一套系统严密的情报理论。
《司马法》记载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军事理念,且含有较丰富的情报思想。第一,强调情报是战争能否开展与取胜的先决条件。《司马法·仁本》记载:“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刘仲平注:“‘知终’即知战争的必胜,‘知始’即知战争的可用。”[34]此处的“智”指先知先觉,即掌握战争必胜的条件以及战争可用的要素,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知彼知己”。只有充分掌握了对方的各种情报信息,并作一对比,才得出战争进行的可能性与胜算。《司马法》的《定爵》篇中提道“见物应卒,是谓行豫”[35],即观察敌情、伺机而动,在军事行动前一定要有所安排。第二,情报是军事行动中的行动指南。《定爵》篇曰:“凡战:间远,观迩,因时,因财,贵信,恶疑……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36]换言之,凡作战,皆需派遣间谍探知远方的敌情,又要侦查近处敌情的动向。同时也要利用好天时气象的变化和敌人的资财,这也是间谍在行动中需要掌握的情报。“刃上察”说的是在战斗中,明察敌情也是杀敌自卫的重要保障。《司马法》的《用众》篇云:“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37]此处强调的是在战争中靠战斗实践去获取敌人情报信息的重要性。战时,己方通过示敌以众或示敌以寡来观察敌情变化;用进攻与撤退来观察敌阵是否牢固;用迫敌以危殆来观察敌人是否畏惧;以安静来判断敌人是否懈怠;以疑兵看敌人是否疑惑;用偷袭看敌人的治军方法。通过上述方法,利用收集的情报掌握敌方军队的治理、士气和队形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与敌军交战时便可直击对方命脉。第三,做好情报防护工作。“龟胜微行,是谓有天”[38],说的是占卜到胜利的征兆后,大军开拔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这便是顺应天时;进入敌境后要断绝对外联系,大战前夕要“书亲绝”[39],即不能与亲人通信,这便避免了军情泄露的可能。可见,《司马法》中对作战的保密性与防侦查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认知。
《孙子兵法》中阐述了一套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其有关情报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十三篇的“用间”。正如钮先钟所言:“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次,实为孙子思想体系中的最大特点。而其全书在结构上是以计划(《计篇》)为起点,以情报(《用间篇》)为终点,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基础。”[40]可见,情报工作是孙子军事思想中的重中之重,以下就其情报理念简要胪列。
其一,孙子对情报的认知。第一,情报的客观存在性,即情报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取决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五事”即“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41]。“道”指政治条件,“天”指天气情况,“地”指地理条件,“将”指将帅素质,“法”指军纪法制;“七计”则要了解对手的政治手段、将帅能力、天时地利、法令通行、军器装备、兵卒训练、赏罚规范:“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42]这些情况是战争中必须考虑的要素,也成了情报必须涉及的对象。第二,情报的可获取性以及人有利用情报的主观能动性。《孙子兵法》中的情报思想以“知”为核心,全书出现七十九次,即明“知”方能获得情报。所谓“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43],《始计》篇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44]。简言之,若无“先知”也就没有“庙算”,全部理论不免流于空谈。人能通过各种方法与途径去获得敌方情报。如通过兽骇、尘起、树动、鸟飞以及敌使言辞、敌军内部行动等各种征候判断敌情的“相敌法”;“策之”“作之”“形之”“角之”[45]的“动敌法”。
其二,搜集情报的思想。除战前的“五事七计”外,孙子的情报搜集思想主要体现为“快”与“全”。所谓“快”,如《孙子兵法》之《九地篇》所云,“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46],在战斗中要迅速察知敌方的战略意图,快速对敌情做出分析,做到智战、巧战。“全”体现在:在整个大的战争中要搜集有关敌方统治者的战略意图、战场地理环境、向导的情报。如《孙子兵法》之《军争篇》言:“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47]就具体的战斗而言,孙子认为情报搜集工作一定要细致,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都有可能关乎作战行动的成败。亦如《孙子兵法》之《用间篇》提及的“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48],在孙子看来,城池守将及其身边左右等亲信下属的信息都需要掌握。此外,孙子十分重视战场中的“相敌”(掌握敌人动向)之法。“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三十三种的具体相敌之法。其中包括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敌之作战意图,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意向,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劳逸、虚实、士气以及后勤补给等情况”[49]。这些细微之处皆隐含着重要的情报信息,是全面考虑战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保证“快”与“全”,及时、全面、完整与准确的情报才能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所掌握,才能使情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其三,孙子的反情报思想。对于情报的保密工作,孙子主张先从己方着手,通过“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50]的方法,严格控制己方情报散播的范围,把情报泄露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样便做到了“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51]。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事莫密于间”[52];“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53]。由此可见孙子对情报保密十分看重,对泄密者更是严惩不贷。在用兵过程中,孙子主张“兵以诈立”,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这要求进攻方既要搜集敌方情报,又要对敌以“诡诈”待之,并采取严密的防间保密举措。只有明白“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的道理,方能做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54],即把己方之形藏得一丝不露,似鬼神一般在暗中制敌之命。在战略上,要学会利用虚假信息,用欺诈的方式,“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55]。在战斗中,要根据不同的对手、任务、阶段、地理环境,制造和释放虚假的情报,给敌人以假象,使其形成错误的情报分析结果。孙子主张“五间并起”,“五间”即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其中以“反间”为主,这也是应对敌方人员窃取情报的重要举措。
三、结语
原始社会时期,早期的情报因先民为了相互告知有关饮食起居以及生活必须问题而产生。氏族社会后期,黄帝、尧帝等部落首领在征服其他部落或者在部落联盟内选择继承人时往往会使用自己的耳目去搜罗相关情报信息。之后,各个方国的斗争乃至夏商易代,皆利用搜集情报的方式来为消灭对手做准备。殷周鼎革之际,周人不断利用内线人员来窃取商廷内政情报,并不断瓦解殷商贵族,在获知商军东伐淮夷的情报后,一举克商。春秋时期,诸夏纷争不断,各国专门设置间谍以获取情报,这些间谍已经是十分专业的情报人员。为了生存发展,各国甚至一国内不同统治集团为获取政治或军事情报可谓是不择手段,同时利用虚假情报乃至使用反间的举措也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逸周书》中体现的情报思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情报理念,但略显散乱简略。《司马法》中的情报已经较为详细,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春秋后期的《孙子兵法》对情报问题有颇多的论述,可见孙子在对情报的认知、搜集以及反情报等方面皆有深刻的见解,这也标志着早期情报理论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