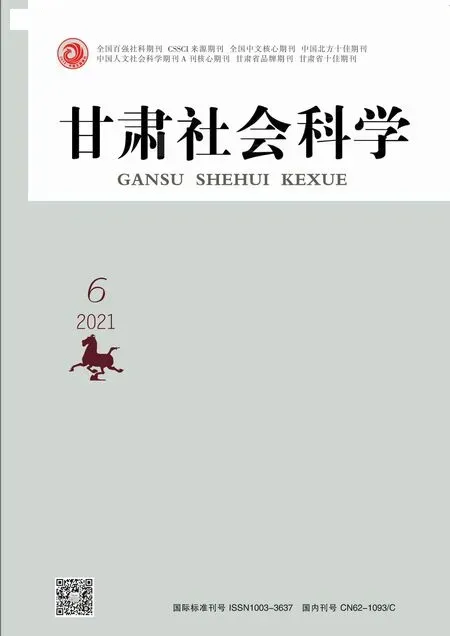敦煌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独特性探析
2021-04-15黑晓佛杨利民
黑晓佛 杨利民
(1.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民族宗教教研部,兰州 730070;2.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兰州 730070)
提要: 敦煌哲学是中国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又有自己的独特性。敦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性格,使敦煌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形态、思维方式等,都表现出了相应的独特性。敦煌哲学的性质既是哲学的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又是敦煌学的,它是中国哲学特殊的呈现形态和表达方式,是以形象和思想的双重融合、哲学与宗教的无碍融通和艺术与生活的高度契合来呈现一种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思维方式。敦煌哲学是自成一体的哲学,其关注点更多的是现实社会,是人的生存与生活;其存在样态既有典型的理论样态,又有现实生活化的存在样态;其思维的表现形态既有理论形态的表达,又有非理论形态的表达;其问题的展开方式既以观念文化的方式展开,又以日常行为的方式展开。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在历史上有“华戎所交一都市”之称。4至14世纪约一千年间,东西方不同文明因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而齐集敦煌,交流交融,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文化形态。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1]“千余年来,中西方各种文明在敦煌汇聚、融合,创造出了具有敦煌气派、敦煌风格、敦煌特色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敦煌独特的文化性格、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2]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它“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2]。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3]因此,从精神层面和哲学意义上对敦煌文化进行发掘和揭示,是深入认识、理解、提升、拓展敦煌文化总体风貌、文化传统、精神内质和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敦煌文化——一种文化的属人世界进行深度阐释的现实课题。
一、敦煌哲学为何?何为?
对敦煌哲学的理解,敦煌哲学的倡导者、探索者、拓荒者早在2013年就已作了奠基性的理论阐释,即“我们所理解的敦煌哲学,就是以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问题,进而探索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4]。这一表述既是对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同时也初步明确了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领域、价值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敦煌哲学”概念的提出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随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呼应①。从2011年敦煌哲学概念的提出、2013年甘肃敦煌哲学学会的成立至今,敦煌哲学已经走过了“十年创意”与“八年创业”的历程,期间虽取得了一些成果,却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敦煌哲学的整体面貌及其“敦煌性”的把握还不十分清晰,敦煌哲学的研究方法及具体进路还略显生硬等。所有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界对于敦煌哲学“合法性”或“合理性”的质疑。上述问题以及敦煌哲学“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行”等一些具有“元哲学”意义的理论问题既是敦煌哲学的先行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又是敦煌哲学的研究者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同时更是“敦煌哲学”在更高层面被提出并引发学界再次关注之际,所有敦煌哲学学人都应进一步回顾、梳理、思考的问题。我们提出“敦煌哲学”的概念、探索“敦煌哲学”的相关问题,并不是文化“本土主义”的“一厢情愿”,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作秀,而是试图以我们的努力揭示敦煌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让其中蕴含的智慧与品质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力量,同时也是回眸盛大辉煌的敦煌文化的陇上学子油然而生的时代使命。
关于“什么是哲学”以及“中国有没有哲学”等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而且都有各自的道理,此处不再赘述。在这些讨论中,牟宗三先生从“文化构成”的视角所做的论述颇具启发意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开篇,先生即澄清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并提出了“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5]3的精彩论断。随后,他进一步从“文化要素”的层面对中国哲学的存在问题进行了肯定回答,他指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问题是在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5]3牟宗三先生这段话真可谓真知灼见,发人深省,非常透彻地回答了“什么是哲学”以及“中国有没有哲学”等问题。笔者以为,牟宗三先生精彩且透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对敦煌哲学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先生的论述其实也同时澄清了“敦煌有没有哲学”或“有没有敦煌哲学”等一系列问题。
哲学这一学科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哲学”的定义。而且,即使“西方哲学”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物,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概念范畴及术语系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哲学概念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规定和理解。特别是随着20世纪以来哲学的现代转向,人们对于“哲学”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更趋多元。贝奈戴托·克罗齐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当他认识到那种自19世纪以来的经验论哲学已经不能“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加以解答”的时候,便对那种“古老的、顽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及其种种“先入为主之见、倾向和习惯”等表现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由此提出了一种“作为方法论的哲学”,以及他对这一哲学的理解——“一切有利于增加指导性概念的宝库、增进我们对于现实历史的理解及帮助我们构成那我们生活其中的思想实体的也都是哲学”②。这一观点为我们在更深层次及更广领域去认识和理解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或关于历史以及历史文化的哲学)提供了可能。
哲学从来没有一种普遍的、为所有哲学家所能接受的、固定不变的哲学定义,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形态。杨海文先生就曾指出:“哲学在终极意义上应该是不会有文字或定义的,也没有不变的‘哲学形态’——哲学正是因其在本质上无定义而显得千姿百态。”[6]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那些“千姿百态”的、特殊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那些“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牟宗三先生从哲学形态的共相与殊相之关系层面对此也有透彻的论述,他说:“哲学虽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有其特殊性,故有中国的哲学也有西方的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均要承认。”[7]因为“道是完整的,它是个全。由于人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8]。因此,任何具体的哲学形态都仅仅只能展示“道”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层面。因此在牟宗三先生看来,“道术将为天下裂”乃是一种必然。哲学是普遍的和相通的,但哲学的表现形式却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因此,如赵景林先生所说:“就哲学的普遍性而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甚至每个人的哲学都是哲学;就特殊性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每个人的哲学又各不相同。”[9]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以及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着某种特殊性。因此,敦煌哲学与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都同样只是“哲学之一种”而已。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探寻敦煌哲学合理的诠释方法和表述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哲学话语、哲学问题等,从而创建出能够真正体现敦煌(文化)精神的“敦煌的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在敦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是促使我们在更深层面对敦煌哲学的“敦煌性”进行揭示与追问,是对敦煌哲学学科的可能建构与方法理念的深入探索。笔者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部分”的敦煌哲学,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从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③。因此,对于敦煌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一问题本身,而已经延伸到对敦煌历史文化思想自觉表达的讨论。我们对“敦煌哲学”的理解是一种历史的理解,但同时更是一种文化的理解——敦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是体现敦煌文化或历史上敦煌民众精神生活及其生活方式的哲学论说。我们讨论敦煌哲学的合法性,就是要把对敦煌哲学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外在关注,通过我们的“重新理解”或范式的转换,转化为对敦煌哲学主体与时代、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命间的内在关注。此外,在此过程中通过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深度解读和透彻理解,去探询蕴含其中的独具个性的人类性生存智慧和特殊的生活旨趣,从而发掘出一些具有某种参照和启迪意义的文化价值、意义资源和精神理念。
二、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化及其文化世界
在《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一文中我们曾明确提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学和敦煌文化,敦煌学是直接的研究对象,而敦煌文化则是间接的研究对象。”[4]范鹏先生在《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一文中对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与前文大体一致,但却对“敦煌学”能否成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一问题“还可以讨论”,随即笔锋一转重点讨论并阐述了敦煌哲学研究对象“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④。笔者以为,敦煌学既是我们了解敦煌文化、进入敦煌文化世界的中介,同时也是开启敦煌哲学研究的钥匙。只有从敦煌学的成果入手“接着讲”,才能真正把握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敦煌文化。因此,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文化,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敦煌文化”,是公元4至14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敦煌这一特定地域,由历史上敦煌民众自己创造的,一种在中古时代人类文化中具有一定独创性、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文明互鉴中具有典型包容性的文化。这一特性,使其文化在总体格局上表现出“既多元开放,又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和主导”[10]420的特点。
第二,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敦煌文化”,是一个有着完整生命和主体性存在的文明样式或文化类型。在《敦煌哲学的独特性、问题域及研究范式》一文中,笔者初次提到“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以敦煌为空间范围而存在的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割的整体”[11]。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都是历史上敦煌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劳动创造,是“这种劳动创造和体现与承载的敦煌地区居民那一千年间的精神活动及其物化表现”[10]6。由于这三个方面共生共存于“敦煌”这一共同空间范围,使三者成为“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一种被其他文化割裂、肢解的零散材料和文化碎片。
第三,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敦煌文化”,是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古文化现象的存在本身及其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品格、身份、资格而存在的根本所在,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敦煌文化的“敦煌性”本身,而不在于敦煌文化之外的任何东西。离开敦煌文化土壤的任何阐释,只是对某种其他经验的简单移植或嫁接,是一种简单的、没有意义的发掘。
第四,作为敦煌哲学研究对象的“敦煌文化”,主要集中体现在四类“文本”之中。(1)敦煌遗书中各种公私文书(如敦煌文献中的各类典籍、类书等,各种法事活动的应用文,如造像记、写经题记、发愿文、施舍疏、偈赞歌辞,敦煌数术文献及敦煌具注历,敦煌石窟图像以及敦煌社会流行的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俗赋、俚曲、因缘、儿郎伟、话本、词文、故事赋、小说、书抄、书仪、梦书、葬书、天文历法等等),也都蕴含着历史上敦煌民众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历史等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特定历史时期敦煌民众对宇宙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是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思维与存在等重大关系问题”的思索和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觉解”。(2)宗教文献(如大量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尤其是古逸经典)特别是在敦煌社会广为流传并被敦煌化了的宗教文献以及疑伪经,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中古敦煌社会中现实的思想和独特的观念;官方及民间各种信仰活动所反映的思想及观念,也是获取对古代敦煌社会生存方式超越性和理想性维度把握的重要路径。(3)各种信仰活动(以“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活动,以宗教场所为中心的各种法事活动,世俗宗教信徒的各种功德活动,民间的其他文娱活动以及术数技术的广泛流行和运用等),都是敦煌哲学重要的考察对象。(4)敦煌石窟遗存(以石窟为主体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建筑、木版画、粉本等遗存和遗物)所反映的思想及观念,也是敦煌哲学必须关注的方面。所有这些大众活动以及通俗读物的流行,其背后都蕴含着某种观念、秩序和精神,都不同程度地表现或反映着敦煌民众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世界的理解和叙述以及历史上敦煌民众获得生命力量、思想方向和智慧光芒的价值源泉和精神营养。对该类“文本”的解读,也就是对历史上敦煌民众生活方式和宗教精神传统的“再度发现”和“重新思考”。
敦煌哲学的研究除了要全面观照敦煌文化之外,还应同时重视宏大而深邃的通过历史上敦煌民众的创造性活动而构建起来的敦煌的属人的“文化世界”,它同样是敦煌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目前我们对它的理解还并不清晰。这个文化的世界,或者是如姜伯勤先生所言之“四至十四世纪以敦煌石窟艺术及石窟所出文书等载体所显现的中国文化繁盛时期的心灵的历程,一个大时代的心灵提升的轨辙”[12]2;或者是“敦煌所见的唐代前后的艺术、宗教和礼乐中所显示的思想超越性、所显示的人文精神和对于中国智慧的追求”[12]2;或者是历史上敦煌民众内在精神的提升与追求实践智慧的历程……无论如何,这个世界都将是一种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综合存在;是一个包括人的所有创造谋划和所有实践创新活动的属人世界;是由人的文化活动所创建的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这个文化世界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众社会活动的精神生产的实际前提和行为基础。这里有历史上敦煌民众当下直接体验的人生之道,有他们安身立命的宇宙大道,有诸多需要内在理解、深层体悟的由历史上所有敦煌人分享的信念、价值和习俗。这个文化世界就是历史上敦煌民众生活体系的一切观念和精神细节之总和。这样一个属人的“文化世界”,既是敦煌哲学研究的对象,又是敦煌哲学建立及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敦煌哲学是中国哲学特殊的呈现形态和表达方式
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哲学形态必然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固有形态,而只能是中国哲学一种特殊的呈现形态,是以形象和思想的双重融合、哲学与宗教的无碍融通和艺术与生活的高度契合来呈现一种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思维方式。
(一)敦煌哲学既是哲学的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又是敦煌学的
“敦煌哲学”这一概念是“敦煌”(文化本土性)与“哲学”(智慧普遍性)的统一,它既具有人类哲学智慧的普遍性,又具有敦煌文化情结的特殊性。敦煌哲学既存在于敦煌文化千年延续万世传流的脉络中,又表达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性的哲学精神。我们既要善于从特殊中追寻一般,以悟宇宙人生根本之道,也要美美与共,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中坚守敦煌独具魅力的个性智慧。敦煌哲学是以具有敦煌特色的艺术呈现、知识框架、话语体系来表达关于人类普遍关注的宇宙、社会、人生根本问题的系统理论。从敦煌独特的文化形态中挖掘、开拓出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哲学精神,这是敦煌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通过普遍的现象来揭晓特殊的价值同样不可或缺。
(二)敦煌哲学是自成一体的哲学
敦煌哲学既是敦煌文化的思想基础,又是对其文化精神的升华与概括,是中古时期四大文明交流交汇交融中形成的时代精神之精华。敦煌哲学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思维特点、特有范畴和时代特征,它既不是“哲学在敦煌”,更不是某种哲学原理或理论与敦煌文化的简单结合,而是既具有鲜明的敦煌性,同时具备深刻的哲学性的敦煌的哲学。
第一,敦煌哲学的存在样态既有典型的理论样态又有现实(日常)生活化的存在样态。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相互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13]如前所述,敦煌哲学的文本,概括地说主要有三大类,即敦煌出土文献、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亦即具有敦煌性的文字、图画和文物。这类“文本”中确实不乏学术性的、纯粹、直接的哲学“文本”,如敦煌遗书中儒、释、道诸家典籍。该类典籍绝大多数与中原地区传世典籍并无多大区别,其所蕴含的思想与其他传世文本中的思想也是大同小异,似乎并无太多的独特性或敦煌性。这些经典数量极大,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应忽视。倒是那些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哲学“文本”需要我们予以特别关注和深入发掘,如各种流行于历史时期敦煌社会的名目繁多的日常经济、法事活动的文书遗存(如社邑文、愿文),岁时节庆以及宗教的、世俗的各类礼俗、仪式,天文历法医卜等文献(如历书、宅经、葬经、医药方、卜筮文书等)及其技术的流行与运用,社会大众的各类信仰实践以及大众通俗读物(如诗文、词文、转变、俗讲、因缘、故事赋、小说等)的传播,等等。这些文献具有鲜明的综合性、融汇性的特征,它所承载的知识、思想以及活动的广泛传播与普遍流行,其实都是已化为日常生活且又标识着大众知识、社会思想、艺术理念和宗教信仰的非典型形态的哲学存在,都是某种观念或精神的外化和表现。这些文本“所涵包的许多内容虽不属于纯粹哲学的范畴,但却仍然包含着哲学的思考,蕴含着哲学的意味,是一种以特殊形式展开的哲学创作”[11]。
第二,敦煌哲学思维的表现形态既有理论形态的表达,又有非理论形态的表达。敦煌哲学思想并不仅仅是甚至大多不是哲学家个人个性化的思想体系,而更多的是敦煌民众和敦煌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不是沉思与言说的结果,而更多是来自社会实践之中的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体现在衣食住行等人伦日用之中,是一种非理论形态的哲学表达。因此,这种哲学思想并不是如其他哲学那样存在于哲学家的著作中,而更多的存在于敦煌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艺术创作和宗教信仰之中。敦煌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其传统中虽无哲学之名,但却并不缺乏哲学的意识、哲学的思维以及哲学的精神。历史上敦煌民众所接触和探讨的有关哲学的问题,也都是敦煌现实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以及敦煌自身历史变迁变革中的一系列与人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而绝少哲学自身发展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也就使敦煌哲学思想往往“隐身”于敦煌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同其文化思想完全混同在一起,而显得有点“支离破碎”和“面目全非”。正因如此,才使敦煌哲学在思考与讨论纷繁复杂的现实具体问题时,还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对于终极性的关切。因此,对敦煌哲学的理解不能抛开敦煌哲学思维特殊的表达形态,而削足适履地去寻觅形上世界的哲思与思辨以及抽象的概念与范畴的演绎,而是要追问那些直接来自敦煌文化历史的提问及其思考,要走入历史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深处,进而从生命理念的层面,从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的层面,从敦煌历史文化思想为人所能够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方面,去理解和体悟其中蕴含的生命与生活之道,以此凸显敦煌文化的气质和根性,拓展敦煌文化的思维空间。
第三,敦煌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既以观念文化的方式展开,又以日常行为的方式展开。敦煌哲学既有终极精神层面的超越性,又有非常世俗化的现实性,它不是或不仅仅是纯粹精神的存在,而往往与具体的现实问题缠绕在一起,更多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与人伦日用之中,以历史时期敦煌民众的日常行为表达着对“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某些层次和多个侧面的理解。因此,对敦煌哲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纯精神层面,而应延伸到历史上敦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的生存生产生活以及洞窟中精神世界各个层面。敦煌独特的历史文化及其特殊的存在形态,展现了历史上敦煌民众对现实生活以及对天道与人道、宇宙与人生、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当下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等关系的思索和理解。作为佛教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的哲学,它仍然具有印度佛教哲学的出世特色;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流交汇交融的产物,它又具备一定程度的入世情怀;作为中古时代中华文明的特殊成果,它必有既出世又入世的中国之道的特质。敦煌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敦煌地域文化、人类文明的特定成果与哲学思维的有机融合。即便是宗教思想(如佛教思想及壁画、彩塑艺术),经由敦煌社会的世俗化之后,其中所表现的也往往都是敦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是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现实生活的某种观念与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既不完全是精英的思想,也不完全是民间的观念,而是精英与民间思想观念互动的结果。这种思想同时也反映并影响着敦煌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
敦煌哲学存在样态、思维表现形态及问题展开方式的多样性,要求我们既要突破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狭隘视野,面向敦煌多姿多彩的人的文化生活去探索其中蕴含的宇宙大道、生活之道和交融之道,更要深度发掘敦煌文化和敦煌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精神和文明模式。唯此,我们对敦煌哲学的诠释和理解,才可能真正地既是哲学的,也是敦煌的。
敦煌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条件、知识传承和文化生态,它是一个有着自己完整生命、独立价值的主体性存在。同时,敦煌文化又是一个有着无限丰富可解释潜质的文化世界和知识体系。站在当今时代,转变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我们一定可以重新认识、发现蕴藏着无限文化瑰宝的敦煌文化中未被发现的哲学思想、时代精神和人生智慧。“敦煌哲学”是以敦煌文化独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它的形态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应该是一种既坚持敦煌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与世界(人类)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哲学建构活动。我们最终的理想,是形成敦煌哲学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四、敦煌哲学的关注点主要是生存与生活
与中国哲学一样,敦煌哲学也是以社会为起点,以“人”为中心,其关注点更多的是现实社会,是人的生存与生活。敦煌特定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性格决定了敦煌哲学的基本风貌或价值取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与文化建构中,敦煌民众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正是在这种现实环境(现实世界)与理想状态(理想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形成了敦煌社会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即更加重视实践活动中的创造性和探索性,而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似乎并未给予太多关注。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就是对现实生存和生活问题的关注。从哲学层面讲,实际上就是把“生存”问题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或者说,它所理解的“本体”始终都在人间,始终都是生存和生活问题。敦煌哲学的这一基本风貌或价值取向,在数量众多的敦煌大众读物及大大小小的各类洞窟中都有相当的反映与体现。如《敦煌变文集》收录的句道兴本《搜神记》一卷中,有一节孔子与一位老人的对话颇有意味,兹引述如下:
“昔孔子游行,见一老人在路,吟歌而行。孔子问曰:‘脸有饥色,有何乐哉?’老人答曰:‘吾众事己毕,何不乐乎?’孔子曰:‘何名众事毕也?’老人报曰:‘黄金已藏,五马与绊,滞货已尽,是以毕也。’孔子曰:‘请解其语。’老人报曰:‘父母生时供养,死得葬埋,此名黄金已藏。男已娶妇,此名五马与绊。女并嫁尽,此名滞货已尽。’孔子叹曰:‘善哉!善哉!此皆是也。’”[14]
对话中的“老人”及其故事在敦煌社会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在这位老人看来,孝养父母,死得安葬;子已娶,女嫁尽,为人已尽责——这是敦煌社会普遍的伦理、中国老百姓的人生大事。故老人虽“脸有饥色”但仍“吟歌而行”。这位老人的看法也正是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生活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观念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关怀。这则对话,通过对“代表其所处文化的‘特性角色’”——生动、形象的“老人”的凸显,使“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化了的存在”[15]。这既是古人的生活经验,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以哲理或片段性的哲学观念的形态隐身于故事之中。这些观念也正是由于通过诸多“特性角色”的具体叙事才使其经验得以传播和传承,由此而成为一定社会的一种精神资源和精神传统。
此一时期敦煌洞窟的营造、壁画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都体现了关注生存与生活的特点,这在莫高窟第98、100、108、256、61、55、454、261、146、152、133、53、22等大窟及同时代诸多石窟中都有充分、直观的体现。此时,人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佛,此岸世界的重要性也已经超过了彼岸世界的重要性。莫高窟第98窟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洞窟中供养人像数量众多、造型生动、服饰艳丽、高大鲜活、位置醒目且详列世俗职务及头衔,极富生活气息。这一时期的“佛窟”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窟”。洞窟中所呈现的所有这些景象,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的价值观念,而且更强调着这些价值观念寓于其中的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及其价值、追求与愿望。再如,这一时期以“弥勒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大量增加⑤,且情节更丰富,描绘也更为细腻生动。如莫高窟第445窟北壁所绘弥勒经变画内容详尽,画面复杂,其中许多情景都是依据经文发挥想象创制而成。经中曾说道:“有一翅头城,庄严清净,人民皆有福德。此国稼禾滋茂,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寒暑自用;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16]所有这些表现特定故事的壁画内容在一段时期的流行,其实早已成为反映敦煌社会一般社会价值或观念的图像代码的一部分,或哲学思想具象化的表现形式。
由于敦煌民众以信仰的方式去对待“生存”与“生活”,所以在这种信仰中,文化形式可能多样,“生存”与“生活”的出发点也可能多样,但其目的性追求却始终如一。在此我们不必说敦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即使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的信仰中也有着直观、全面地反映。至少在公元3至10世纪的敦煌社会,佛教及其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敦煌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等思想创作的方方面面。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及其文化已经是完全实现了本土化,并由此表现出了显著的世俗化、大众化、生活化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之下,敦煌社会僧俗之所以信仰佛教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为了“通过佛法智慧之桨,驾驭佛教信仰之舟”,以了悟“生死轮回”之道,达到“寂静涅槃”妙境,而更多地则是为了“‘乘佛愿力’,使所求有托,所愿得偿,达到营生有助、事业有成的目的”[17]。敦煌遗书S.530v《斋仪摘抄》中有一组莫高窟僧人为世俗信仰者所写愿文、唁词的愿文文范,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世俗大众的普遍愿望,谨录数句如下:
“……谦[谦]君子,洛下英才。常怀三义之心,每有断金之美……伏愿……伏愿碧山与寿,红树增春,心期镂玉之获,展星河之庆……常居翠柳之年,永镇芙蓉之帐。伏愿青丝不变,红粉争春;德齐岩下之松,寿等月中之桂。伏愿绿眉状月,长分八字之鲜;玉貌如春,独占春之色。朗君子,伏愿文摇五彩之笔,高视洪流;觉(学)富九经之书,低看鲍谢;折东堂之仙桂,香发子中;驰儒之曲(典)坟,名传海内。禄(绿)萼相暎,玉树莲芳,同礼移庭,长光膝下……伏愿浩海常流,资景福而逾远;寿山耸峻,等群岳而转高……金璋永耀,紫绶长荣,财盈四海之珍,福五侯之俸。事清吉,荣禄日新;所谋长,遂於宿心……门荣(石杂)碎(翠)柳,光益宗枝,四德传芳,耀荣九族……秉文秉武,为紫府之良才;尽中(忠)尽贞,作元戎之心腹……德光金简,为世上之股肱;声振玉阶,显名彰於日下……金紫与日月而争辉,福寿比山河而永固……”[18]
这些溢美之词,是敦煌社会群体思想活动具体而生动的展现,是当时敦煌社会上自归义军节度使、世家大族,下至僧众、工匠等普通民众普遍的人生理想的生动反映。人们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实现的愿望,以“愿文”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希望通过自己对佛、菩萨虔诚的信仰使自己所求、所愿能够如愿以偿。在上述文范中,佛教所描绘的彼岸世界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遗忘,而却不厌其烦地凸显和强化着对此岸现实世界生存及生活的理想与憧憬。在此,敦煌社会民众包括僧人,对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的赞美、热爱和追求的情怀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此外,敦煌文书中大量的愿文、碑铭、题记等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敦煌民众的喜好、审美、愿望以及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风尚等。这些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时期敦煌民众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生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人的自我意识与生活态度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的看法亦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一定的哲学形态……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19]敦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性格,使敦煌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形态、思维方式等,表现出了相应的独特性。
余 论
敦煌哲学既传递着时代的呼吁,又积淀着时代的精华。我们提出并探讨敦煌哲学并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对历史上某种思想遗迹进行某种凭吊,而是要通过对敦煌文化及其历史遗存的发掘,阐发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以在更深层次及更广领域丰富中华民族智慧,促进人类文明深度对话。这个过程是一个用时代眼光、参照现代哲学学术体例对蕴含在敦煌历史文化中的思想资源进行发掘和梳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与“建构”交互作用的过程,在“发现”中“建构”,在“建构”中“发现”。这个过程既是从现代反思传统,又是以传统关照现代;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对敦煌哲学的探讨要始终坚守敦煌文化遗产之灵性而悟透其崇德唯美、向善守正、开放包容、通而不统、和合共生之道,从哲学的视角考察由敦煌民众的创造性活动而建构起来的敦煌的文化世界,关照敦煌的现在,瞭望敦煌以及敦煌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此外,还要回答、解读、传播发端于敦煌、扩散于世界的“丝路”精神,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注 释:
①2011年范鹏先生在《敦煌哲学引论》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敦煌哲学”这一概念,当时只是提出了问题、抛出了概念。2013年1月19日,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成立,成立大会上多位学者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就“敦煌哲学”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拙文《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和范鹏教授提交的论文《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发表后,《新华文摘》2013年第16期作为封面重点文章,将其纳入“新华观察”栏目全文转载,引起了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之后,又有两篇研究敦煌哲学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②贝奈戴托·克罗齐直接把哲学定义为“方法论”,并认为“这样一种哲学正是把哲学作为历史(因而是把历史作为哲学),是哲学阶段在纯范畴和方法论阶段中的规定”。详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9-129页。
③俞吾金先生主张,要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该具备的合理的形式(学术规范、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上来肯定西方哲学已经做出的贡献,而并不主张在内容上照搬西方哲学家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因为,只有从学科应有的形式出发来探讨其合法性问题时,这个问题才可能获得其实质性的意义。参见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④范鹏先生认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有重大而广大的历史文献、宗教经典和艺术精品……但同时也有断片碎页、只言片语、残垣断壁和细沙一般的微观细节……”。详见范鹏:《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⑤莫高窟第23窟窟顶西披,第33窟南壁,第91窟北壁,第109窟南壁,第113窟北壁,第116窟北壁,第123窟北壁,第148窟南壁龛上,第180窟西壁龛内,第208窟北壁,第15窟南壁,第218窟北壁,第445窟北壁,第446窟北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