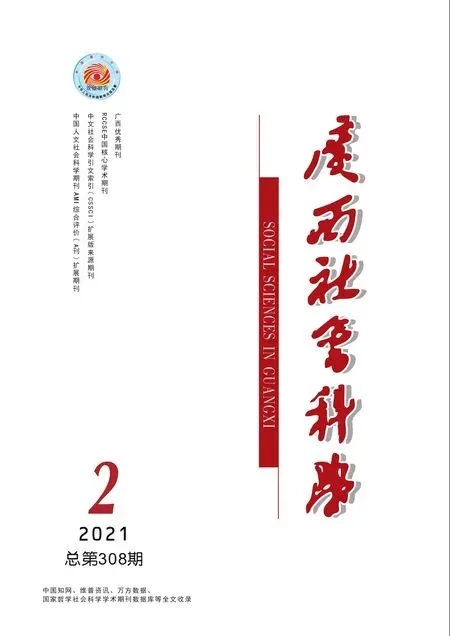现代社会“绿色生存”的制度理性逻辑及价值构序实践
2021-04-15马瑞科袁祖社
马瑞科,袁祖社
(1.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现代社会“绿色生存”价值信念的确立与“美好生活”的实践证成,遭遇和面向的是一个病理化的危机场域。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布展,生态危机愈益成为现代人所遭遇的最为紧迫且复杂的公共性生存论危机之一,“危机型”生态场域的生成与持续扩展,从价值本体的深度揭示着启蒙现代性文化所证成和辩护的“资本占有型”进步主义发展逻辑的内在悖谬。在知识社会学和“后发展”的意义上,一种足以超越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优良生存价值观的培育与生成,吁求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绿色生存”信念的整体性出场和持续性在场。由“美德伦理”向“规范伦理”的现代性范式转换为此种优良生存信念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性的观念史语境。立足文明转型的新时代,一种合乎伦理规范的理性制度观念及制度实践的确立,为生态型“绿色生存”价值信念得以可能构筑起了坚实的价值—实践前提,制度理性的生态转向所着力证成并深刻阐扬的是一种彰显文明时代所应有的“绿色生存”的伦理自觉和“绿色发展”的实践理性。由此,在生态文明与制度文明价值共契的意义中,制度理性的生态转向将为“美丽中国”的创获构建一条切实可行的价值关切与实践规制之道。
一、异化生存的制度性超越: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制度理性批判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理论发展,始终贯穿着一条基于“制度性批判”的价值—实践反思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共构的话语实践场域内,马克思系统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迁史,深刻剖析了所属时代“非人性”和“反生态”的“制度困境”,由此创生出具有鲜明生态旨趣和超越性理论品格的新哲学理论。新哲学以现实感性的人的生产—生活历史实践为地平,以一种真正“属人的”和“人属的”新制度质态的阐释、探求和创获为价值—实践旨归,在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异化生存的现实”,并在“改变世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宣言的引领下,实质性地促成了西方哲学观的现实性、历史性、实践性和生态性转向。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话语的理论特质在于:以变革资本主义“旧制度”、创生共产主义“新制度”作为新哲学“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使命。正是这一诉诸生产—生活实践的制度性反思、批判和变革的价值—实践品格,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全部生态价值旨趣和实践立场。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是工业资本主义由地域性走向世界性的时代,工业文明展示出其强大的物质财富创造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当一个时代普遍沉浸在物质的甜美幻象之中时,马克思冷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制度性悖歧”所最终导致的异化现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
在马克思制度性批判的话语逻辑中,资本主义是一种建制化的制度设计理念,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制度性背反是诱发生态—生存论危机的现实根源。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制度,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前提,在割裂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互关联的同时,也解构了通过劳动实践所构建起的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在资本逐利逻辑和扩张本性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制度“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此种“制度性短视”的内在缺陷概括为由资本创建的“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正是在这种以“普遍有用性”为终极旨归的功利化制度实践视野中,人之绿色生存的价值信念被财富占有、被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偏狭的生存法则替代,自然与人自身的内在自足性被解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4]。在强大的资本逻辑的裹挟中,“效用主义”和“金钱崇拜”实质性地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性价值原则。“金钱拜物教”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形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性价值尺度,“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5]。作为一种世俗化的神学隐喻,“金钱”变身为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神”,成为一切存在确证自身的至上尺度;而“效用主义”的根本价值旨趣仅仅在于:“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6]进而,在以“效用”和“金钱”为终极价值的制度场域中,人与自然丧失其自足性的内在价值规定,仅在单纯“实用理性”的限度内,被资产阶级赋予有限的“工具性”价值。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藐视和实际的贬低。”[7]自然被窄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原料库”,工人则蜕变成资本家谋利的“物役性”工具,由此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异化性”交往关系格局——“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之间、“制度的异化”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化”之间有一种辩证统一的关联。“自然的异化”和“制度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内在否定性社会关系结构的表征,在根本上体现着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非人化”和“反生态”的生存论困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现象的考察,始终以制度性地扬弃与超越“双重异化现实”为价值—实践旨归。在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逻辑架构内,异化生存的最终超越,必须走出思辨形而上学纯粹抽象的逻辑论证,进而以历史性、实践性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形态为前提,通过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打破私有财产、资本逻辑、金钱效用原则对社会结构以及自然生态的整体性形塑和钳制,从而实践性地创生一种“人与人的和解”同“人与自然的和解”高度契合的理想型生态共同体制度样态——共产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理想社会制度创生的逻辑视域中,作为一种饱含生态伦理关切的理想型制度实践,“共产主义”在价值实践超越性的意义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规制下的私有财产及人与自然的异化性在场的整全性扬弃,从而促进了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合理性复归。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因此,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9]。“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0]。
“生活在极盛现代性的世界,便是生活在机遇与风险的氛围中。而机遇和风险又是为适应自然支配和对历史的反身性建构而形成的某种特殊体系的必然伴生物。”[11]吉登斯的辨识向现代人揭示出此起彼伏的风险和危机的叠加出场,构成现代性挥之不去的宿命——与物质财富积累同步到来的,还有被人类长期忽视的各种极为复杂的否定性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持续进展和资本空间生产逻辑的全球性布展,“启蒙主体性”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绝对地位,人们愈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人类个体是价值的终极支座和真理的终极法官”[12]。也正是此种片面的、褊狭的绝对主体性意识的僭越,促使全球性生态危机超越认识论和知识论的限度,具有了生存论的意蕴,进而强化了人类理性的超越诉求。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看来,现代性生态危机的有效克服“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13]。乌尔里希·贝尔同样认为:“工业生产中看不见的副作用变换为一触即发的全球生态问题的导火线,严格地说……是一种工业现代性(‘反思现代化’)首要的(国家的)深层次的制度危机。”[14]现实的、世俗的生活的残缺与不完满,总是促使人们观念性地或实践性地想象、寻求和建构一种理想化的替代性生活空间。制度理性的有效介入为现代社会“绿色生存”价值信念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实践反思视角。
二、优良生存方式的变革与制度理性的塑培:现代生态治理的范式转换
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彰显着一个文明时代所应有的价值担当和实践理性。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制度是人自主性地运用主体理性,对人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各种复杂交往关系的慎思明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稳定的、外在的、系统性的协调、规制和范导机制;制度文明阐扬着时代精神,同时塑造着主体理性,进而规约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和特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践。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制度构成人类生存的现实历史—文化境遇,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现代理性意义上的“制度”范式的出场,是西方近代以来比较晚近的现象。前现代社会虽有广泛而丰富的“制度性”(规范性)智识,然而制度在社会治理中并不居于优先地位。不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中所涉及的共同体正义和社会秩序都是依托一种由等级身份、宗法血缘和宗教神学构成的美德伦理或先验价值。前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本质上是“法律化的道德”或“制度化的伦理”,即伦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法制的角色,具有内外结合的约束性。在前现代伦理本位的社会中,良好的生态秩序主要依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伦理法则加以规制,在农耕文明中自然被赋予超验的价值属性,形成一种万物有灵的朴素生态伦理,人与自然之间始终保持着由文化、神话、宗教、传统、习俗内含的伦理规则所塑造的神秘间距。由此,前现代社会的“绿色生存”是一种生态伦理基础上的伦理化生存信念。
启蒙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人摆脱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裹挟,通过制度理性实现主体性自治的历史。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换,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由“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制度性转型实践,是人类社会从“德操”到“致富”(亚当·斯密)、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卢梭)、从“家庭”到“市民社会”(黑格尔)、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马克思)、从“身份”到“契约”(梅因)、从“共同体”到“社会”(滕尼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迪尔凯姆)、从“共同体化”到“社会化”(韦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费孝通)的复杂转型过程。
伴随现代性转型而来的,是社会整体性价值标尺的重构。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运作机制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伦理生活方式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由等级身份、宗法伦理所造成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平等、自由为价值取向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确立。正因如此,由传统伦理原则维系的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朴素生态伦理信念被打破。在科技理性大肆征服、掠夺和控制自然的现代性“祛魅”实践中,理性主体性的凯旋,强化了现代人的独立、自治的主体意识,自然沦为理性主体自我确证的手段和工具,“控制自然”在认识论意义上被予以强化。此时,制度作为人类理性自主谋划和设计的现代性规范建制,取代了前现代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维系、利益分配、行为规制的主导性治理范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制度”一词颇为流行,致使“制度”成为学术焦点,主要是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现代性的进展,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共同秩序的维护从“美德伦理”向“制度理性”转变。西方制度学派的创立,使得“制度”范式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制度、法律、历史、社会、道德、伦理等“非经济”或“非市场”的规范性因素替代了传统经济学派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抽象演绎(“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反思话语。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5]这里的“规则”和“制约”更多地指向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规范性原则;在社会政治领域,休·E.S.克劳福德(Sue E.S.Crawford)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or Ostrom)赋予制度“均衡”“规范”和“规则”三重政治内涵[16];人类学者则在更为宏大的视域内,把制度理解为“一个业已建立的、社会公认的规范,或关于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行为模式”[17]。
由上可知,多学科的有效介入丰富和加深着现代人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然而,此种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层面的实证性研究,其本位价值取向依然偏执于政治—认同型、经济—效率型、社会—秩序型的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此种研究一方面从社会治理工具论的层面上理解制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治理后果论的层面上评价制度,制度的伦理关切及制度本身的伦理正当性被“悬置”。由此,一种“好制度”仅仅被规约为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治理绩效最大化的手段。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分化和社会治理技术的改善,“高效的”“稳定的”“复杂的”制度化建制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得以有效治理的规范性前提。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生态理性和“绿色生存”的价值视域中,现代社会遭遇的“制度性困局”是:当现代社会被事无巨细的制度性规范所限定,从而构筑起无所不包的制度性“铁笼”时;当现代性制度实践的程序合法性与形式合理性替代了实质合理性与伦理正当性时,不但现代人所遭遇的生态—生存论危机似乎并未被化解,而且现代人自身的自由与发展也被设定在制度理性的限度内。大卫·库尔珀曾对此展开过颇有见地的批判:在现代社会中“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具有了优先性……在实质合理性的情形中,有一些价值观是被当作纯然真实的价值观而被接受的,而且这些价值观与被如此接受的这一世界图景也很切合。现代性并不只是动摇了这种传统,而且颠覆了这种传统。对效率和一致性的考虑将不再受到一套给定的实质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制约。而这些规范自身,反过来还要根据其在达成已选定目标和意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效率和一致性来加以判定”[18]。换言之,当实质合理性的生态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倘若现代性制度实践依然无法摆脱对资本逻辑、功利主义、进步神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偏执,抑或是甘愿以财富占有和欲望满足的世俗功利主义为其合法性根基,不论其诉诸怎样严苛的程序合法性或自洽性的形式合理性(即“效率”和“一致性”),在实然层面上都必然会在制度与资本结盟所建构起的“占有型共同体”中,充当资本牟利和控制自然的强有力手段,无法从根本上破解现代性生态危机。
基于文明转型新时代人类美好生存的价值期待,当现代人重新反思生态危机的时代性症候、运作机理和治理出路时,制度性的审视是切实可行的重要切入视角。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生存论危机,由西方启蒙现代性所形塑的制度实践却依然偏执于现世的、区域性的、功利的“收益”,“制度”的自我放逐使其丧失了应有的生态伦理担当。而置身于此种制度境遇中的现代人,在潜移默化之中被规训、模塑出一种“占有型”的现代性人格特征。“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权力的追求。”[19]在“占有型”生存方式中,“我同世界的关系乃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要使每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20]。由此,毫无节制的财富占有和虚假消费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世俗依托。“绿色生存”作为一种优良的生存伦理信念,其合理性在于阐扬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21]的价值取向,在“绿色生存”的价值信念之中,“好制度”应当是一种涵括了生态伦理关切,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共生、共在、共享的公共性生态化制度实践。此种生态型制度实践以“生态人格”的塑培为旨归,以“绿色生存”的生态本位价值为主导性制度治理取向。在广义关系论的意义上,即在人、自然和共同体良序共生的关系格局内,实现并践履一种包容、共享、和谐、可持续的生态化制度实践。
三、现代制度实践的生态化转向:“绿色生存”的制度性创制逻辑
作为一种新质的价值—实践叙事话语,“绿色生存”本位价值信念的出场,开启了“后发展时代”中国社会总体性发展的价值—实践新转向——从“富裕社会”到“美好社会”的范式转换。所谓“后发展”并非一味地摒弃和拒斥发展,而是在“超越性”的意义上,扬弃启蒙现代性主导的褊狭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单向度的经济发展——重构一种涵括人学关切的整全性、本真性的有机发展理念。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制度性创新实践始终围绕着“民生本位”的优良品质和美好生活价值正题的吁求、证成和公共性享有而展开。在范式创新和话语逻辑变革的深层意义上,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制度性变迁提升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促使中国民众的生存—生活共同体质态经历了由“政治生活共同体”“经济生活共同体”到“生态生活共同体”的演变[22]。此演进历程的价值本体旨归在于对“绿色生存”信念的制度性证成和践履。
在“政治生活共同体”的语境中,“政治—秩序型”的价值取向成为制度性实践的本位价值,生态理性难以成为现实制度设置的主导性价值关切,个体理性被严格限定在政治话语的整体性框架内,对自然内在价值和生态伦理很难形成主体性的自觉。
在“经济生活共同体”的场域中,社会整体性的制度实践以“经济—效率型”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经商致富的世俗价值从政治秩序中脱离而出,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合法性价值取向。在利己本性和功利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在整体性的工业化、市场化实践中,社会制度的生态关切稀缺,民众的生态自律意识匮乏,生态问题日渐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愈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民众对生态幸福的价值期待,生态治理成为中国制度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议题。“整全性的生态生活共同体”时代以“生态—福利型”的价值理念为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实践归宿。“生态—福利型”发展理念所阐扬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容型、共享型和可持续型公共性价值信念,其所极力证成的是一种超越“财富占有型”世俗功利伦理的“生态幸福”新伦理信念。党的十六大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制度创新的重要指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核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订出台,“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的陆续实施,更是从整体上使得“绿色生存”和“生态幸福”的价值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新篇章。
有效的制度性治理实践是一个由多元交互主体共建、共享的复杂性治理实践。制度规范作为重要的治理载体,其本身的日趋完善是制度性治理的前置性条件。然而,仅仅寄希望于制度规范的广包性,难以自足创生一个清明世界和正派社会。尤其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作为外在规范的制度实践从来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选择,其背后所隐匿的各种根由与中国传统社会“重人情、轻法理”的人文传统不无瓜葛。在学者卢现祥看来,受制于传统人伦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日渐形成了一种“非理性”制度观[23],由此加重了中国生态治理的“制度悖论”。
立足文明转型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制度化建制、转型和创新证成生态幸福的绿色生存信念,从来不是纯粹的、外在的、单一向度的制度建构问题。在现代性生态—生存论危机极度复杂的内在运作场域中,在足以可能引领、形塑现代国人智识化生存方式根本变革的意义上,“绿色生存”作为一种合乎人性、合乎公共善、合乎自然法则的优良生存信念的确立,内在地涵括了个体人格秩序的再塑、共同体质态的提升以及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
一是现代个体人格秩序的生态化再塑:从“占有型人格”走向“生态型人格”的新伦理自觉。人格秩序是人之内在的价值本体。一切外在的制度性实践,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体现着某种人格预设的价值立场,并现实性地塑造着与之相应的新人格取向。现代性的价值—实践原则造就了现代人同质化、单向度、排他性的“占有型人格”,现代“占有型主体”将永无节制的财富占有和随心所欲的欲望表达视为自我同一性的终极原则,由此造成人与自然、人与共同体、人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实质性疏离,进而构成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由此,现代性生态危机的深层治理,必须对现代个体人格秩序中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加以合理化规制。立足人格再塑的价值—实践高度,“绿色生存”的生态本位价值信念内在地吁求一种“生态型人格”的出场,而此种生态型“新人格”的培塑与养成,要求现代人悬置“生态冷漠”,给予生态—生存论危机足够自觉的价值关切,把生态伦理视为安身立命之“道德律令”,在康德“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24]的启迪中,在交互共生、意义共契和价值共享的意义上,努力提升现代个体的人格境界和生态伦理自律意识,积极践行一种多元主体共生、共在、共享的优良公共性“绿色生存”之道,为现代社会生态治理培植内在的伦理新认同。
二是现代共同体质态的生态型转换:从“资本共同体”走向“生态共同体”的新生存论自觉。与前现代社会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的先在性自然共同体(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不同,现代社会基于共同的目标、利益、认同和归属感建构起多元异质的共同体形态。受技术、资本和市场机制引导的现代性公共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片面的公共生活样态。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共同偏好所结成的“资本共同体”,在财富与伦理的深度疏离的背反性境遇中,践行着一种“金钱至上”之狭隘的现代性生存信条。“绿色生存”的生态本位价值信念的确立,迫切期待一种整全性的优良公共性生存空间的开显。在面向将来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现代社会公共生活样态从“资本共同体”向“生态共同体”的转换,为“绿色生存”的优良生存信仰的践履创生出现实的生存场域。在现代文明演进的意义上,“生态共同体”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超越性品格与永远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理想;其以生态正义为共同目标,以多元主体的共生互惠为认识论共识,在充分认肯与守护地球家园与生命意义的价值—实践视域内,培育与生成一种敬畏生命、珍视自然的公共理性自觉。
三是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生态性转型:走向个体生态美德自律与共同体生态制度规范内在共契的多元治理模式。现代个体人格秩序的生态化再塑为“绿色生存”的价值信念的养成提供了基于现代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认同机制,现代共同体质态的生态型转换为“绿色生存”的价值信念的践履创生出现实的公共性空间。除此之外,一种走向个体生态美德自律与共同体生态制度规范内在共契的多元治理格局的建构,是有效克服中国民众“制度理性”不及与“生态理性”不足的二元困境的现实出路。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的生态治理延续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政府作为主导型治理主体,在共同体生态制度规范的建构与完善中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并承担着部分本应由社会与个体所履行的生态义务。这造成社会生态关切乏力和个体生态自律不足的问题。作为一种优良的生存信念,“绿色生存”的生态本位价值信念的确立,一则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生态制度规范的约束与引导;二则需要社会总体性的制度理性的培育;三则有赖于个体生态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生态自律品格的养成。唯有在一种涵括国家、社会与个体在内的多元治理格局中,“绿色生存”才能落定为现代人的生存信念。
总之,对作为现代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价值导向和实践规约的“绿色生存”信念的认同与践履,必将在自然、人文和心灵秩序的总体性生态化攀升的努力中,以反思、矫正与超越由启蒙现代性文明引导和造就的成问题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为价值—实践旨归,进而创制、模塑和证立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人类生存的新伦理信念。现代性生态危机的有效克服,最终要诉诸“绿色生存”价值—实践信念的整体性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