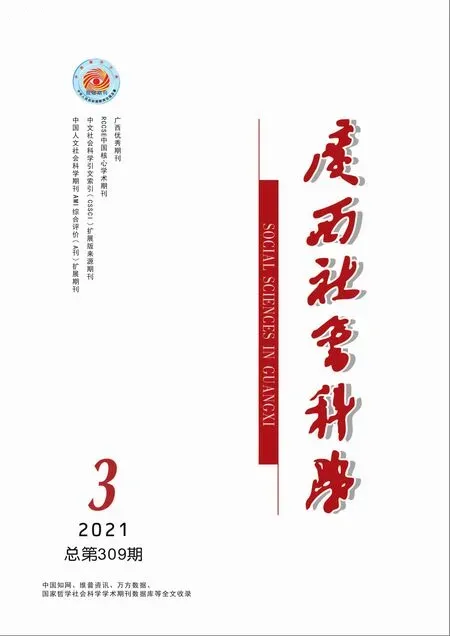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学研究范围探析
——以张楚《直到宇宙尽头》为例
2021-04-15尼莎
尼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作为一种发生于中国本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近年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目前学界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大体可以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类着重于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和阐发,另一类研究则倾向于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方法研究特定的作家作品。本文试在吸收学理性的基础上,以当代作家张楚的小说《直到宇宙尽头》为例,在依然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从作者设置的伦理语境、人物的伦理选择以及作品中透露的伦理价值三个层面,明确伦理学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适用范围。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学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通常被认为是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就其含义而言,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判方法[1]。此一研究方法由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提出,其要点在于将文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进行折叠,视道德为文学作品产生的源头,认为文学就本质而言是关于伦理的艺术。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伦理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者认为,由作家所建构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社会同样是对作家所处现实社会的高度虚拟和提炼,其中几乎涵盖了伦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它能够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丰富及典型的研究对象。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看来,伦理学除研究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及各类道德活动、现象之外,也可以研究艺术中虚构的社会问题及道德活动。
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入手,文学伦理学批评致力于把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以作品中内含的道德现象作为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同时发掘作家的创作意识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在聂珍钊教授看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文本内容的诠释角度看,注重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伦理及道德因素的分析,主张在历史而不是当下的语境中分析作品及人物的伦理选择;其二,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角度看,聚焦于作品与现实社会中道德现象的关系,阐释文学作品对现实社会的道德教化作用;其三,从作家与创作的关系角度看,研究作者的道德倾向及这一倾向与作品道德观念间的联系;其四,从读者与作品的关系角度看,研究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中反映的道德观念的接受对作者及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倾向的伦理评价[2]。这些同样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区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特征。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学”的界定
传统的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风俗或道德(德性)的学科,关注的起点是个体道德,注重对自我德性的完善。随着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以及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伦理学的关注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需要正视自己的公共生活实践,需要致力于为公共生活实践寻求合理性方向与途径[3]。文学批评这时便能够充分发挥其针砭时弊的社会性价值,由于其内容涵括广泛,也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从伦理学角度对社会公共生活中重大问题给予价值关注、寻求现实解决方法的渠道。
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学”,在界定其概念之先,须厘清“文学伦理学”这一概念。学界通常将其与传统伦理学间的不同集中于现实性与虚构性的差异:“它(文学伦理)主要指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中存在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4]认为文学伦理学主要立足于文本中虚构的道德关系,而伦理学关注的则通常是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和问题。
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西方语境中,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是道德哲学,或者关于道德、道德问题和道德判断的哲学思考”[5]。但在中国文化里,文史哲三科间的界限很多时候并不明晰。如《史记》中很多人物传记亦可作文学作品观之。篇末“太史公曰”部分又多流露出作者的认识论与人生观。如此我们很难以西方学科划定来简单地为我们所要研究的人物、作品进行归类。同时,2010年左右国内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潮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在不排斥作家个人性的同时,力求书写现实世界的复杂矛盾和问题[6]。寻求文学写作与时代共振的非虚构写作为达到社会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的尝试,是文学文本突破虚构性的最好证明。
从文化传统的差异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伦理学的意涵要大得多,甚至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本身即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其他文化形式往往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西方哲学有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划分,而在中国,古人对于天人、力命、心物关系的思索都是在伦理框架下展开的。中国的政治、律法等其他文化形式亦然,文学创作自然也无法摆脱伦理教化的功能。同时,就伦理关系自身而言,它有别于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关系。这种非实体性的关系是在实存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因人的反思和评价而存在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并非具体的社会实体间实实在在的物质性交往关系,而是基于这种物质性交往关系而延伸出的观念性关系,并因人们的评价而存在[7]。作为非实体性关系的伦理关系既然可以诉诸反思和评价,自然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因此,以虚构与现实与否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传统伦理学研究的区分标准,其合理性似可商榷。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就目前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兼涉文学与伦理学两类学科,但学界普遍认同其为借鉴了某些伦理学研究手段的文学研究方法。如何在保证文学性的同时,适当扩大伦理学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适用性,进一步深化同伦理学学科的结合程度,是我们可以探讨的问题。那么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伦理学如何更好地进入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而扩大自己在这一研究中的话语呢?
(一)了解当代伦理批评有别于传统文学伦理批评的特征和需要
在中西方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文学作品的伦理批评都囿于时代呼声下的文以载道的操守,以及忧愤刺世的德性意识和道德行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才开始发出重建伦理批评体系的呼声,还有学者提出文学理论“伦理转向”的号召[8]。无疑,针对当代文学文本的新伦理批评不该再仅仅局限于宣传一种道德观念并为之说教的刻板方式,而是应更加注重于阐释文学背后的脉络,察识伦理以怎样复杂的方式参与甚至操控文学话语的产生。也就是说,文学中蕴含的伦理批评不仅应关注文本内的历史语境,同时也应关注文本的写作者所处的现实环境,关注隐藏在文本之外的、代表不同阶层作家价值取向的价值秩序以及基于作家与读者内在情感体验的伦理判断。
(二)发掘文学与伦理学的深层共性
对于好生活的追寻是伦理学研究的广泛议题。一个好的生活通常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愉快的感受和重要目标的实现,也有人将其概括为主观的满足和客观价值的实现。人类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两方面的圆满,而促成这种圆满的,就是人类的善[9]。作为作家意识活动产物的文学作品,也是作家对好生活向往的一种内心映射。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类戏剧小说历来有一种大团圆的书写传统。这种与现实结局或多或少存在偏差的文人结局,正是作家内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投射。弗洛伊德把文学创作的动机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想象活动,他认为孩童在游戏时“用一种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他那个世界的事物,来使自己得到满足”[10]。这种他“付出全部热情”的创作自然是他内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反映。这一文学与伦理学的共性为我们深化两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论土壤。
(三)设立开放的对话式的学科边界,使学科之间拥有灵活转换的空间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曾多次批判“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的观念,指出这种思维赋予实体以高于关系的特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障碍。进而,布尔迪厄将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归功于其关系性思维,并将关系性思维视作所有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真实的东西就是相互关联的东西”(the real is relational)[11]。在学科之间的边界层面,布尔迪厄非常强调学科间的关系性。在关系性中,各个学科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由此,他把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伦理共置于同一个话语空间之中,大大拓宽了研究主体的思考向度和研究视域。布尔迪厄的观点给我们扩展学科边界、促进学科理论融合带来很大启发。在《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一个方法论的讨论》一文中,姚新中教授提出,比较哲学的方法可以通过让来自不同传统或具有不同风格的哲学观点进行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辨析出其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最终达到视域融合的效果[12]。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处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与伦理学间的关系。加强对话与沟通,能够有效突破学科之间的限制,进一步丰富研究设想的空间。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学的应用
《直到宇宙尽头》是当代青年作家张楚最新写就的一则短篇小说。小说借女主人公的故事描写现代社会伦理秩序失措对当代人心理造成的异化;同时通过对宇宙意向的书写,又在更深的层面肯定了人的存在和精神。作品呈现出众多的伦理问题亟待人们反思。笔者试就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伦理语境、构造的伦理结构、揭示的伦理价值,来明确伦理学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适用范围。
(一)《直到宇宙尽头》的伦理语境
伦理语境(ethical context)是指伦理环境中的语境,即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人物的观念、意识和语言交流的伦理环境。伦理环境形成文学作品的历史空间,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通常对于作品的道德评价不应超过其特定的伦理环境[13]。但若我们跳出文本中特定的伦理环境,以规范伦理学的视角审视文本,那么将得出许多超越文本内容的问题,如何为作者心中的善?人物角色的道德选择应当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从伦理环境看,宇宙意向在小说中得到了多层次的渲染。现代西方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将宇宙视为由各种现实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摄入而不断生成的现实过程。任何现实存在,不管是实体性的山川星辰,还是非实体性的精神意识等,只有在不断生成的现实过程中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个不断生成的宇宙出现在《直到宇宙尽头》的书写中。小说对宇宙的描写通过侧写展开:宇宙深植于女主人公姜欣的脑海之中,是她逃离现实的秘境,也是与她的精神救赎。宇宙大多数时候是安静的,悄无声息地隐匿于姜欣的意识中;有时与她的身心融为一体。只有在某些非理性状态下,宇宙才会从她口中脱口而出。讽刺的是,此时的宇宙却同现实中姜欣周围人群构成巨大的张力,造成她无处容身的孤独。
生活环境的贴近,使得张楚作品中的伦理环境与当代社会伦理现状有着十分广泛的重合度,其作品中的道德困境亦能在现实环境中寻找到影子。埃米尔·涂尔干曾将道德准则作用于人身的情况比作“想象的墙”(imaginary wall),在这堵墙的阻隔下,人类的激情及欲望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就会消退。但如果这道屏障在某一时刻减弱,此前那些受到约束的力量就会蜂拥而出,一旦这些力量遭到释放,它们就找不到任何可以停止的极限[14]。这用来形容当代社会伦理困境十分恰当。《直到宇宙尽头》中姜欣因丈夫外遇而对其进行的一系列自毁性报复,正是作者对传统社会伦理秩序遭到冲击而新的伦理规范又未建立之时,人们抛弃伦理身份而进入伦理选择的错乱状态、最终导致人生痛苦不堪的叙写。小说所描述的特定伦理语境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作者对当今现实中存在的家庭与社会伦理失范现象的忧虑。
(二)《直到宇宙尽头》的伦理结构
伦理结构(ethical structure)是指文本中依据人物思想与行动建构起来的文本结构。构成作品伦理结构的因素有四个:人物关系、思维活动(包含意识结构和表达结构)、行为和规范[15]。伦理结构由伦理结和伦理线交织而成。伦理结(ethical knots)是文学文本结构中矛盾冲突的突出点。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展示作品中的基本伦理问题。伦理线(ethical line)是文学文本的线性结构,其作用在于将作品中若干个伦理结串联起来,形成完整而复杂的伦理结构。
小说《直到宇宙尽头中》以姜欣同韦礼安、安炜、贺医生三段性关系谋篇,设置悬念,引导读者思索其不合理行为背后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段性关系的描写中,作者的用笔是分层和不断变化着的。在同韦礼安的互动中,作者运用了冷静笔调对二人的性行为进行了大量白描式的客观叙写,这时宇宙潜隐在女主角头脑中,几乎未曾出现;同时以“蜥蜴”“河马”等动物的描写暗示了主人公身上的兽性因子(即人的动物性本能)。此时是姜欣复仇的初期阶段,也是复仇意识最强的阶段。在姜欣和安炜的性关系描写上作者隐晦了许多,同时宇宙开始以脑文本(即以人的大脑为介质保存的记忆)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此时主人公对于自己的形容从动物发展为人形玩偶(废弃的塑料交警玩偶),“人”的意识开始萌生。最后一段性关系的重点在精神层面展开,读者终于明白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姜欣行为的动机,宇宙开始成为姜欣现实中的呼唤。与此同时,姜欣的复仇思想开始产生动摇,人性因子(即人的理性意志)的作用开始凸显。她和王瑜山的互动是一段未开始即已中断的复仇。人的理性的回归促使姜欣中止了对王瑜生的陷害。至此在作者笔下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从动物的非理性向人的理性转变的伦理选择。
(三)《直到宇宙尽头》的伦理价值
伦理价值(ethical value)指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与警示价值,它是正面道德价值和反面道德价值的总称[16]。在从传统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与往昔田园诗般的生活挥手作别,随之失去的还有往日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与伦理规范。这一缺失反映在部分现代人身上,便是人格和心理上的异化。《直到宇宙尽头》中无爱之性在作者漠然的笔下成为苦闷的牢网:“在墙上那面碎了一角的镜子里,她看到两头黄昏时分从水族馆爬出来的河马:又老又笨,瞪着干涸的眼”[17]。在都市中,许多人道德感降低,金钱成为衡量爱情的标杆,爱在功利挤压下变得虚伪且暧昧。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现代人虽身处都市,却形同穿行旷野。
对现代性过程中这一痛点,小说中隐含着作家的价值关怀。正如作家对少女时期姜欣经历的描写——双脚只能陷进牲畜的排泄物里,内心却渴望头顶上神秘高贵的星空——那样,成年后的姜欣虽然在内心会将自己异化为“又老又笨的河马”“仓库里废弃的塑料交警”,但宇宙自始至终内化于她的心中。作者赋予姜欣阅读科普读物这一喜好,如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彭罗斯的《通向实在之路》等,因为“只有在这些冷静的、没有任何色泽的文字里,她才能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渺小。是的,渺小的、可笑的、粗鄙的但又不乏高贵的‘人’”[18]。康德将人视为生活在目的王国中的、自己立法并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
《直到宇宙尽头》中对宇宙星空与污浊现实的着笔,最终依然落脚于人类理性意识的求真与求善。“她仿佛就坐在宇宙尽头,等待那个无限热、无限密集的点在上帝之手的拨弄下,以超越光速的速度爆炸开去……她安抚着下身无比沮丧地想,时间,终于诞生了。”[19]小说末尾以姜欣一人坐在幽暗楼道中的意识流动作结。按照时下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时间产生了宇宙大爆炸之后。由她自导自演的复仇行为的消息爆炸之后,今后的人生应如何继续呢?对于姜欣的失婚及复仇,作家没有轻率地作出道德评价。悲剧本身就有净化人心的作用,小说集中留白之处更深化了这一思考。在后记《虚无与沉默》中,张楚引用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你们都是星尘”作为该书尾声:“我们就是星尘,我们,也是时光本身。所有诞生并存在过的,都会在沉默中等待着与时光融为一体。这一切,无比美妙却不自知。”[20]康德将宇宙中亘古不变的道德律令比作我们头顶的永恒星空,作者于此亦将理性的存在同宇宙星空等同起来,对于理性的肯定是人类无尽的追逐。
在《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指出,好的小说应同时包含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21]。对《直到宇宙尽头》而言,对宇宙的关注与书写直指时间,而潜隐在冷静叙事下对人类理性与善的肯定,则是对价值生活的关照。亚里士多德曾将善视为我们所有活动的唯一目的,声称善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满的善是独立自足的,这种自足并非指远离人群的孤独生活,而是“一事物仅凭其自身的存在便使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22]。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就是这样的事物。姜欣虽身处无法挣脱的泥淖之中,但在生活的片刻之间,意识却独立自足地飘荡在宇宙星辰之间,依然保有独立思想的姜欣是幸福的。女主人公这一或可慰藉的幸福,也是创作者价值观念的展现。
综上,文学的重要特征是虚构,但也反映现实生活;伦理学的主要面向是现实生活,但伦理关系本身又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关系。伍尔夫曾这样评价小说中的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既然小说与真实生活如此紧密相连,那小说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真实生活的价值所在”[23]。自五四运动开始,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何找到思想和艺术无缝对接的方式,思想如何转化为合宜的文学表达,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因此文学伦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文学文本层面的考察,还要把握时代精神,关注当代社会,从现实关怀出发对文学文本中的伦理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相信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断获得发展的今天,深入挖掘其中的伦理学研究视角,会为此研究赢得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