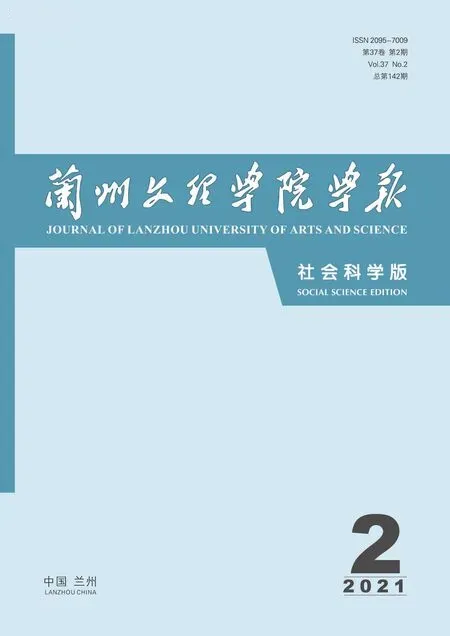论上古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联系
——兼论《文始》“壬”族
2021-04-15陈晓强
陈晓强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系统是若干要素相互联系并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有机整体。认识系统的首要工作,是找到系统要素并对系统中要素的功能有正确的理解。汉语词族系统的要素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词族系统的要素当然是词。这种认识不能说错误,但汉语词族系统中词的要素功能何在?词以什么样的状态在系统中存在?词与词如何在系统中联系并区别?这些问题,如果简单地从词表层的音、义中考察,无法得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在对系统的元素和环境的不多的研究中,一般都具有两个基本缺陷,一是直观性,如把元素简单地说成是组成系统的基本成分,把环境说成是周围的情况。……第二个缺陷是这种直观定义不能体现系统研究方法与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区别。……这种对系统元素和环境范畴理解的直观性和模糊性不仅在理论上不科学,在实践上亦引起许多混乱。”[1]简单地从词表层的音、义角度观察汉语词族系统的要素,问题即出在“理解的直观性和模糊性”。因此,需要摆脱词表层音、义的束缚,在词和词深层的联系中思考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存在方式。
下面,本文以《文始》“壬”族①为基础语料,对上古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存在与联系方式进行分析。
一、从词源意义的联系看词族系统要素
《文始》“壬”族中系联了“廷”声、“巠”声②诸词:
“挺生为本义,……(壬)变易为莛,莖也。又为莖,枝柱也。”[2]“挺生则直,故诸壬声字义多近直。梃者,一枚也。筳者,繀丝筦也。桯及桱者,床前几也,臣锴曰:‘勁挺之貌也。’珽者,大圭也,《周礼》注曰:‘无所屈也。’脛者,胻也。脛旁转阳则为胻,脛端也。頸者,头莖也。經者,织从丝也。徑者,步道也。廷者,朝中也。庭者,宫中也。《释诂》曰:‘庭,直也。’凡此数者皆直,并孳乳于壬。……颋,狭头颋也。《释诂》:‘颋,直也。’曰侹,长貌。曰娙,长好也。曰勁,强也。曰呈,平也。”[2]300-301
以上“壬”族诸词的联系,显然不是词的表层使用意义。例如,“莖”是莖秆,“脛”是小腿,“頸”是脖頸,“徑”是步道,“經”是纵线。以上诸词各有所指,使用意义没有关联。那么,《文始》根据什么线索将以上诸词系联在一起?“音近义通”是汉语词源学的基础理论,也是系联汉语同源词的基本方法。以上诸词,用同声符形声字记录,自然满足“音近”条件。“义通”之“义”,既然与词的使用意义无关,那么,汉语词族系统中词与词“义通”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呢?《文始》认为“壬”族诸词的关系为:“义多近直”“凡此数者皆直”。可见,“莖、脛、頸、徑、經”等词的“义通”之“义”是直义。直义在以上诸词中是如何存在和显现的呢?很明显,直义不是以上诸词共同的使用意义,而是隐藏在诸词词义内部的相通的词源意义。因此,词族系统中词的联系,不是使用意义的联系,而是词源意义的联系。王宁先生认为:“词义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词的表层使用意义,另一种是词的深层词源意义。”[3]摆脱词表层使用意义的束缚,在词的深层词源意义中则能清晰地看到词族系统中词与词的相互关联。
下面,以形声字声符“廷”和“巠”为线索,对《文始》“壬”族中词源意义为“直”的同源词进行扩展系联,以展示词族系统中词与词的联系与区别。
(一)“廷”声“挺直”义的系联
侹:《说文》:“侹,长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后文简称《段注》):“与挺音义略同。”[5]
莛:《说文》:“莛,莖也。”《张注》:“莛之言挺,谓挺然直出也。”[4]188
梃:《说文》:“梃,一枚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下文‘材,木梃也’,《竹部》‘竿,竹梃也’,但指其干,不兼枝叶而言。”[6]按,“莛”为挺直的草本植物茎秆,“梃”为挺直的木本植物茎秆。引申之,“梃”则有“一枚”义,用于做挺直之物的量词。《张注》:“徐锴曰:‘梃者,独也。梃然劲直之皃也。’舜徽按:梃之言壬也。本书‘壬’下云:‘象物出地挺生也。’故凡从壬声之字,多有直义。大圭为珽,艸茎为莛,繀丝筦为筳,女出病为娗,皆此音义。”[4]1409
珽:《说文》:“珽,大圭。长三尺,抒上,终葵首。”《张注》:“大圭长三尺而形挺直,故谓之珽。”[4]57
筳:《说文》:“筳,繀丝筦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筳,所以络丝者,苏俗谓之籰头。筳即其四周挺如栅者。”[7]《张注》:“筳之言挺也,谓其挺直也。”[4]1119
颋:《说文》:“颋,狭头颋也。”《尔雅·释诂》:“颋,直也。”“颋”本义为头挺直貌,引申则为正直。
脡:挺直的长条干肉。《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高子执箪食与四脡脯。”何休注:“屈曰胊,申曰脡。”《礼记·曲礼下》“鲜鱼曰脡祭”,郑玄注:“脡,直也。”
娗:《说文》:“娗,女出病也。”《段注》:“疑娗、婷同字。长好皃。”[5]2501按,《说文》:“娙,长好也。”“娗”同“娙”,谓女子身材修长挺直。《文始》:“娗为女出病,即《千金》诸方所云阴挺出也。”[2]300《张注》:“此医经所谓阴器挺出,即今语所称子宫脱出也。”[4]3096挺出意象与挺直意象不同,《文始》《张注》观点可能有误。存疑。
涏:《集韵·迥韵》:“涏,波直皃。”又,《径韵》:“涏,波流直皃。”
綎:《说文》:“綎,系绶也。”殷寄明《汉语同源词大典·上》:“系佩玉的丝带,垂直而长者。”[8]按,“廷”声之挺直意象能否泛化为垂直意象,“綎”之词源意象是否为垂直,有待商榷。
(二)“巠”声“直而长”义的系联
坙:《说文》:“坙,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一曰水冥坙也。”《张注》:“水脉为坙,谓其行之直也。坙从壬省声,壬象物出地挺生,有直义。坙即从壬得声得义也。《广韵·十五青》‘坙’下云:‘直波为坙。’是坙本有直义矣。水行直谓之坙,犹织纵丝谓之經耳。”[4]2810按,“巠”金文作“”,学界多认为“巠”为“經”的初文。清·吴大澄《说文古籀补·川部》:“巠,古文以为經字。”郭沫若《金文丛考》:“余意巠盖經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均象织机之纵线形。从糸作之經,字之稍后起者也。”[9]
經:《说文》:“經,织也。”經为织机上的纵线,其特征是直而长。
涇:《说文》:“涇,水。出安定涇阳幵头山,东南入渭。雝州之川也。”亦指直流的水波。《释名·释水》:“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
莖:《说文》:“莖,枝柱也。”草木的主干部分,特征是长而直。引申之亦可指器物之柄。皆直而长之物。
頸:《说文》:“頸,头莖也。”
鋞:《说文》:“鋞,温器也。圜直上。”《张注》:“徐灏曰:‘《急就篇》颜注云:鋞,温器,圜而直上。’即本于《说文》。又云:‘鋞或作钘。许则分为二义也。’舜徽按,鋞、钘音同,故古人多视为一字。器之长頸者,与器之圜而直上者声义并与莖、脛同原也。”[4]3419
娙:《说文》:“娙,长好也。”《段注》:“体长之好也,故其字从巠。”[5]2471
脛:《说文》:“脛,胻也。”《段注》:“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载物。”[5]679
牼:《说文》:“牼,牛厀下骨也。”《张注》:“牼之为言脛也。在人曰脛,在牛则曰牼。《释名·释形体》:‘脛,莖也,直而长似物莖也。’”[4]2810
桱:《说文》:“桱,桱桯也,东方谓之荡。”《张注》:“徐锴曰:‘桯即横木也。桱,挺直之皃也。’舜徽按,木之勁挺者为桱,犹胻谓之脛,头莖谓之頸,艸木干谓之莖,织纵丝谓之經,牛厀下骨谓之牼耳。”[4]1444按,“桱”为床前几,其特征是长而直。
徑:《说文》:“徑,步道也。”《张注》:“戴侗曰:小道徑达,故因之有徑直之义。”[4]429按,“徑”为直而长的便捷小道。
陘:《说文》:“陘,山绝坎也。”《段注》:“凡巠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两山中隔以成隘道也。”[5]2933《张注》:“山绝谓之陘,犹断头谓之刭,亦谓之刑,刑、陘双声,语原同也。”[4]3553按,段、张二说,从形声字声符“巠”的示源系统考察,段说更佳。
(三)词族系统要素的联系与区别
根据中国古代训释材料的实际、中国古人重视分类和习惯一分为二的思维特点,王宁先生把词义内部结构分析为两个部分。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王宁先生把这两个部分中体现词义类别的部分称作“类义素”,体现词义特点的部分称作“源义素”或“核义素”,并指出:“同源词的类义素是各不相同的,而核义素是完全相同或相关的。”[3]105根据王宁先生提出的义素分析法对上文所系联“廷”声、“巠”声诸词进行分析,能很容易地从“廷”声诸词中归纳出共同的源义素“挺直”、从“巠”声诸词中归纳出共同的源义素“直而长”。同时,也能在不同词中提取出不同的类义素。如:
挺、侹:人身体+挺直
娗:女人身材+挺直
莛、梃:莖秆+挺直
珽:大圭+挺直
筳:纺丝工具+挺直
颋:头+挺直
脡:长条干肉+挺直
坙、經:經线+直而长
莖:莖秆+直而长
脛、牼:小腿+直而长
桱:横木+直而长
徑:步道+直而长
陘:隘道+直而长
頸:頸项+直而长
鋞:温器+(頸)直而长
要素只有在相互联系和区别中才能在系统中有其存身位置,才能在系统中发挥其功能。以上诸词,或在源义素“挺直”下发生联系,或在源义素“直而长”下发生联系;同时,每个词又在不同的类义素下产生区别。由此,我们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系联得出两个词族系统。系统具有层次性,“廷”声“挺直”义词族系统与“巠”声“直而长”义词族系统只是更大词族系统的子系统。那么,这两个子系统是否属于同一词族系统?如果属于同一词族系统,那这两个子系统又成为更大词族系统的要素,它们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呢?
二、从子系统的关联看词族系统要素
(一)字族系统的关联
系统具有层次性,上文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所系联词族,只是“壬”族直义子系统的一部分。对该子系统进一步考察,则又能解析出“廷”声、“巠”声等不同子系统。这种解析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由此,上古汉语单音节词族系统的子系统与以形声字声符为核心的字族系统发生密切关系。一方面,字族系统作为词族系统的子系统,不同字族系统中的词,自然具有词源意义的共性联系,例如“廷”声字族和“巠”声字族的词,词源意义都具有直的意象。另一方面,汉字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一词族中的不同字族的词在词源意义上往往有其个性特征。形声字声符的字形造意是探求汉语语根意象的重要线索,不同字族中的声符,其字形造意的不同往往能够间接反映字族的个性特征。例如,“廷”西周金文“”“”象人挺直站立在庭前之形,“壬”甲骨文“”“”象人挺直站立地面之形,“壬”在“廷”中兼有表义、示源的双重功能。与“廷”之字形造意关联,“廷”声字族的直义,多具有挺直的意象。“巠”西周金文“”“”象织布机上直而长的经线,与该字形造意关联,“巠”声字族的直义,多具有直而长的意象。挺直的意象与直而长的意象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从语音角度考察,“廷”“巠”韵母都在耕部,但声母有别:“廷”为透纽,“巠”为见纽。语音在相近基础上的微殊,进一步让我们注意到“廷”声字族和“巠”声字族的不同个性。这也促使我们深思:“廷”族与“巠”族在语根上是否同族?
挺直的意象与直而长的意象有相通之处,如草茎笔直、人挺直等的特征既是直而长,又是挺直,如《说文》:“莛,莖也。”细长的草茎,同时也具有挺直的特点,故草莖既曰“莖”、又曰“莛”,例如《楚辞·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汉书·东方朔传》:“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又如《说文》:“娙,长好也。”《段注》“娗”:“疑娗、婷同字。长好皃。”[5]2933《说文》:“侹,长皃。”《张注》:“侹之言挺也。谓挺然直立也,故训长皃。”[4]1928
从以上材料中,能感受到“廷”族与“巠”族的密切关联。因此,《文始》将“廷”“巠”归入一族有其合理性。但是,挺直的事物不见得直而长,直而长的事物也不见得挺直,例如“徑”“涇”“陘”等事物,就不具有挺直意象。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在词族的初度系联时,把“廷”之字族与“巠”之字族分属于不同词族更稳妥一些。另一方面,面对“廷”族与“巠”族关联密切的事实,我们需要在初度系联的基础上对“廷”族与“巠”族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通过多角度的考察,我们认为:语根上“廷”“巠”很有可能同出一源,它们共同的语根意象为直;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为了分化不同的形状的直,“廷”“巠”逐渐有了语音和意象上的微殊,进而又繁衍出关系密切但又有微殊的“廷”族和“巠”族。战国文字“巠”或作“”(郭.唐.19),《说文》“巠”之古文为“”。这些文字中“巠”为“壬”声,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形声字分化高峰时期,“壬”“廷”和“巠”的语音已接近。挺直意象和直而长意象相通,再加上“廷”和“巠”语音接近,春秋战国之后,“廷”族和“巠”族的意象逐渐混同。例如《集韵·径韵》:“涏,波流直皃。”《玉篇·目部》:“,直视也。”波流之“直”,当然不是挺直;直视之“直”,也不是直而长。“涏”“”的声符意象,只是泛化的直义。
(二)词源意义运动变化中形成的词族子系统
由于意义的运动变化,词族系统中的词源意义往往是多层、多向的。例如,上文所析“巠”声,既有直义,又有坚硬、刚劲义:
勁:《说文》:“勁,强也。”“勁”为强劲有力。
痙:《说文》:“痙,强急也。”《段注》:“体强急,难用屈伸也。”[5]1403“痙”为风强病,也称痉挛,其特征是身体僵直而难曲伸。
硜:《六书故·地理二》:“硜,小石坚介,扣其声硜硜然。”“硜”为刚劲有力的击石声。《史记·乐书》:“石声硜,硜以立别,别以致死。”裴骃集解引王肃曰:“声果劲。”
桱:《玉篇·木部》:“桱,木名。”《广韵·徑韵》:“桱,桱木,似杉而硬。”④
由此,以形声字声符“巠”为线索系联得出的词族系统又可分为两个子系统:以直义为词源意义的子系统和以坚硬、刚劲义为词源意义的子系统。直的意象与硬的意象相通,直、硬的意象又与刚、劲的意象相通。词源意义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传统小学常用术语“义通”来说明这种现象。词族系统的子系统因词源意义的相通而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到字族系统中,则是同声符形声字的相通现象及不同声符形声字之间的互通现象。[10]“巠”声系统中的义通关系,也表现在“吉”声、“臤”声等声符系统中。《文始》“壬”族将“吉”声与“巠”声、“廷”声关联:“壬读如徑、經、勁、娙,次对转至则孳乳为吉。从吉声者有桔,一曰直木也;有颉,直项也;有佶,正也。桔孳乳于梃,颉孳乳于頸,佶孳乳于颋勁。”[2]301下文以“吉”声与“巠”声的互证为例,进一步说明词源意义运动变化所形成的词族子系统。
1.“吉”声坚硬、刚劲义的系联
硈:《说文》:“硈,石坚也。”“吉石”之“吉”分化,则为“硈”。
黠:《说文》:“黠,坚黑也。”《段注》:“黑之坚者也。”[5]1951

鲒:《说文》:“鲒,蚌也。”《张注》:“蚌又名鲒者,鲒之言坚也,谓其外介质坚也。”[4]2875
结、髻:《说文》:“结,缔也。”“髻,緫发也。古通用结。”《张注》“结”下:“结之言坚也。谓坚固不易解也。”[4]3181按,今语“结实”,仍反映“结”之坚实义。
劼:《说文》:“劼,愼也。”《张注》:“其本义自谓用力坚定不轻略也。”[4]3394
2.“吉”声直义的系联
颉:《说文》:“颉,直项也。”《张注》:“凡从吉得声之字,亦多有直义。直项为颉,犹直木为桔,正人为佶耳。又多有坚义,如齿坚为,石坚为硈,坚黑为黠,蚌壳为鲒。直与坚,义实相成。颉从吉声,吉即坚之入声,是借吉为坚耳。故凡从吉声之字而有直义、坚义者,固皆义通于坚。颉训直项,乃谓人之颈项能直不能屈者,即今所称硬颈根也。”[4]2173
桔:《说文》:“桔,桔梗,药名。一曰直木。”
佶:《说文》:“佶,正也。《诗》曰:既佶且闲。”
诘:《说文》:“诘,问也。”按,“吉”声之直义由具象变为抽象,“佶”即人正直,“诘”即直白地问。
三、从意义、字形线索看词族系统要素的联系
(一)意义的联系
对词义的认识,学界多从词表层的使用意义角度理解,例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12]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指出: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基本联系方式,是词和词通过词源意义发生联系。因此,上古汉语词族研究,要摆脱人们对词义固有认识的束缚,要摆脱词表层使用意义的影响。有学者从词表层使用意义角度系联上古汉语同源词,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很多错误。例如,章太炎《文始》:“(辡)引伸为辡论,今以辩为之。孳乳为谝,便巧言也。为譬,谕也。”[2]220利用形声字声符线索,可看出:“辡、辩、瓣、辨”等词同源,词源意义为“分辨”;“谝、媥、翩”等词同源,词源意义为“轻巧”;“譬、僻、避、癖、臂”等词同源,词源意义为“偏旁、旁边”。“辩”“谝”“譬”尽管词义都与言语有关,但词源意义上却没有相通关系。章太炎先生将“辩”“谝”“譬”作为同源词系联在一起,存在问题。再如,王力《同源字典》认为“言”“语”同源[13]。《说文解字》:“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段注》:“郑注《大司乐》曰:‘发端曰言,答难曰语。’注《杂记》曰:‘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汉·东方朔《七谏·初放》:“言语讷譅兮。”注:“出口曰言,相答曰语。”“言”“语”意义相近,但词义特点却不同:“言”与“唁”同源,“唁”是吊唁,只能是倾诉而不可能是言语的交流,由此可知“言”是主动地说,故前人有“直言曰言”“发端曰言”“出口曰言”“言己事”等训释;“语”与“牾”同源,“牾”为抵牾,具有互动地特征,“语”为两人或多人的互动之语,故前人有“论难曰语”“答难曰语”“相答曰语”“为人说”等训释。王力先生认为“言”“语”同源,问题出在将词表层的使用意义与深层的词源意义混同。
章太炎《文始》和王力《同源字典》在汉语词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两部著作中以词的使用意义代词源意义的问题不少。这些问题的根本,即在对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义”的联系方式的错误认识。从直观角度而言,词族系统的要素是词;但是,不能简单地从词表层的使用意义角度来理解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联系。
(二)字形的联系
词族系统中联系最紧密的词,是词源意义相同且在字形上有共同声符的词,如上文所析“廷”声“挺直”义、“巠”声“直而长”义下类聚的词。系联上古汉语同源词,要高度重视对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利用。但是,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语同源词的系联也要注意避开汉字字形的干扰。词族有不同的形成途径,有些词族,形声字声符线索的作用很明显,如本文所析“壬”族。有些词族,形声字声符的线索并不明显。例如,《文始》“酉”族系联了一组以“祷告”为词源意义的词:“祷,告事求福也。祷又孳乳为祝,祭主赞词者也。引伸之义则祷与祝同。又变易为,祝也。为,詶也。为诪,詶也。为詶,诪也。……其别事为祷,则有禂,祷牲马祭也。”[2]390这一组词的同源关系,很多学者认同,如王力《同源字典》认为“祝”“詶”“诪”“”同源[13]309。《张注》认为:“缓言之则为祝,急言之则为,实一义耳。”[4]29“诪之或体作詶。”[4]578“禂之或体从寿得声,与祷实一字耳。”[4]34“祷”“祝”“”“”“诪”“詶”“禂”等词同源,但它们在字形上只有“祷”和“诪”有关联。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如果过于依赖词族要素的字形关联来系联汉语同源词,必然会导致大量同源词的遗漏。
由汉语词汇派生和汉字形声孳乳相伴而行的客观事实决定,汉语词族系统中经常可以看到多个以形声字声符为核心的字族系统,如“壬”族系统中包含“廷”声、“巠”声、“吉”声等多个字族系统。因为在字形上有形声字声符的关联,字族系统中词与词的联系非常直观。这种直观的联系,表象是声符的关联,实质是词源意义的相同或相通。词族子系统中的词,不是字形上同声符词的类聚,而是相同词源意义下词的类聚。因此,形声字声符只是系联同源词的线索,但切不可机械地认为形声字声符是词族系统要素联系的关键。例如,同样是“巠”声,如果机械地将词源意义为刚劲的“勁”“硜”等词与词源意义为直而长的“經”“莖”等词关联在一起,词族系统中词的关联不仅不能在形声字声符线索中得到提示,相反,杂乱无章的形声字的类聚,会掩盖词族系统中词与词的联系。
结语
要素在相互联系中构成系统,如果不能对要素的联系方式有正确认识,系统要素就只能以散沙状的方式呈现。进而,对系统结构、功能等问题的讨论也很难深入。汉语词族系统中要素的联系有共性的规律,如要素通过词源意义发生联系、词源意义运动变化生成多个子系统。不同词族系统中要素的联系又有个性的特征,如有些词族系统中形声字声符线索的作用非常明显,词族与字族关系密切,有些词族系统中词和词的字形联系却很少。就词族中具体的词而言,词和词因词源意义的联系而具有共性的特征,但每个词的表层使用意义,却有各自的个性;词表层使用意义与深层词源意义的融合,才是对词义的完整理解。因此,对汉语词族系统要素的考察,要注重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的结合。
上古汉语词族系统的要素联系,学界长期存在误以词的使用意义为词源意义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从词的表层使用意义角度来理解词义是很多学者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上古汉语语根的特性、词源意义的运动、汉语词族的形成、汉语词族的系统性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王宁先生曾经预言:“汉语词源学这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凭着它自身的生命力和它日渐强大的队伍,将在21世纪有巨大的发展。”[14]本文的一点粗浅认识,希望对汉语词源学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为了便于指称,本文以《文始》“初文”为相关词族的名称。
②为了便于显现同声符形声字之间的字形关系,本文所讨论“巠”声字采用繁体。
③《说文》:“聖,通也。从耳呈声。”(呈,从口壬声。壬声与呈声有互通关系。)“逞,通也。从辵呈声。”“,空也。从穴巠聲。”从《说文》的这些训释材料中,即可感受到“壬”族的通彻意象。
④“桱”既有直而长的特征,又有质地坚硬的特征。故“桱”在“巠”声的直义、坚义两个子系统中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