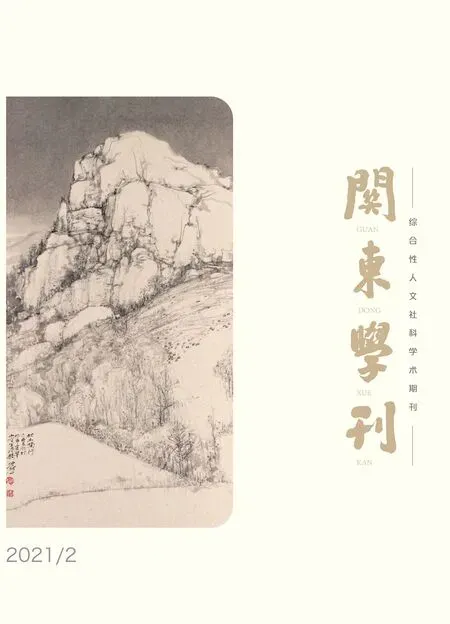跨文化交际障碍与翻译伦理
2021-04-14于辉
于 辉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国家之间广泛接触。作为交际最重要的语言,在各自的词汇史上都留下很深的印记。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人群进行交际的必要手段,自然也就被重视起来。不过,由于翻译者母语与第二语言——被翻译语之间的熟稔程度不同,以及不同文化、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常常会造成一些翻译乱象,或者更学术地说是跨文化交际障碍(barriers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障碍的现象虽然是世界各语种之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中文圈里表现得尤其强烈一些,这是翻译界不争的事实和文化界的普遍共识。书评人乔纳森就曾指出,“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不能让人满意”(1)乔纳森:《谈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的翻译质量》,《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25日,第15版。;媒体人乔苏也提出,“欧美的翻译出版”“总体上质量要比中文翻译更可靠”(2)乔苏:《我对翻译作品有警觉之心》,《新京报》2012年3月28日,第C02版。。每当翻译乱象频出并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的社会热议时,翻译伦理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学术界重视起来。
关于翻译伦理,虽然早在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Antoine Berman首次提出时并没有引起翻译界多大反响,但这一理论倡导在当下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Pym(1997、2000、2001、2012)、Chesterman(1997、2001)、Venuti(1998、2013)、Arrojo(1997、2005)等都有过理论贡献;国内也产生了《翻译伦理》(张景华)(3)张景华:《翻译伦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翻译与翻译伦理》(王大智)(4)王大智:《翻译与翻译伦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翻译伦理学》(彭萍)(5)彭萍:《翻译伦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等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在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中,2001年芬兰翻译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 根据当时存在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沟通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循规伦理(norm-based ethics),提出这些模式在一些方面不兼容,且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因而提供另外一种思路,补上第五种可能的模式: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构成翻译伦理五模式,(6)Andrew Chesterman,“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The Translator,2001,(2).影响很大。其中再现伦理、沟通伦理和承诺伦理,对解读和研究中国近些年翻译界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一、再现伦理与翻译“失真”
再现伦理是Schleiermacher、Berman、Venuti和Newmark等人比较推崇的翻译理论。Chesterman曾解释说:“再现伦理源自忠实译员的理想和精准传译文本的神圣感。要求译者必须准确地表达源文本、原作者的意图,不能有任何添加、省略或改变。”(7)Andrew Chesterman,“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The Translator,2001,(2).“再现伦理”追求的精准,就是严复所言“信达雅”中的“信”,而且具有文学和绘画理论中的超写实主义特点,即重视原文到“真”(truth)的程度。关于“真”(truth),Newmark进一步指出,遵守“翻译职业道德”的译者,要力求做到“五个真”:事实真(factual truth)、逻辑真(logical truth)、审美真(aesthetic truth)、道德真(moral truth)和语言真(linguistic truth)。(8)Peter Newmark 1994.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In C.Picken(ed.).Quality-Assurance,Management and Control,Proceedings III Conference 7.London: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pp.113-122.
再现伦理之所以被提出,显然针对的是翻译界出现的“不再现”“不真”的现象,本文在这里再次重申,也是因为中国翻译界出现大量翻译“失真”的问题。比如学者朱正2015年曾针对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主持翻译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简称《选编》)(9)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一卷中发表的长篇文章,指出其中存在翻译“失真”问题。其中他举例说:
其一,《选编》78页的《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档案中,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为此朱正纠正说:“当时并没有‘秘密警察局’一说。这里的‘秘密警察局’显然应该译为‘保密局’。”证据是“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改组,公开的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秘密核心部分组建为郑介民任局长的保密局”。(10)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73页。
其二,《选编》112页的《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档案中写:“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把军队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朱正纠正说:“这里的‘民主联盟’”“应该都是‘民主同盟’”;“这里的‘国家议院’应该译作‘国民大会’”。证据是“民主同盟”这个组织“1941年2月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叫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该书的《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部分就写着周恩来说:“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2)……”(11)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73-174页。
类似这种错误的还有将“内政部”译为“内务部”,将“国防部次长”译为“国防部副部长”,将“军队国家话”译为“军队国有化”,将“中国农民银行”译为“农业银行”,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译为“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将“民主社会党”译为“社会民主党”,将“政学系”译为“政治学派”,将赛珍珠的英文名“珀尔·布克”译为“比尔·巴克”等。(12)朱正:《解“解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的误译》,《领导者》2015年第6期。
所有这些“失真”的翻译,不能说完全错误,因为译者是根据俄文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表面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即便是对应语言翻译没有问题而实质上却有大问题,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秘密警察局”“民主联盟”“国家议院”以及“内务部”“副部长”等专有名词,这违背了Newmark“五真”中的“事实真”和“语言真”,也会让学界迷惑不解或贻笑大方。
如果说这类因为翻译不符合历史实情的“失真”多少还值得原谅的话,那么接下来朱正指出的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的翻译错误就不能再宽容下去了。比如:
其三,《选编》343页的《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档案中:“我们在西康省的无线电台好久没有广播。而现在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每天找我们的人了解中共有哪些指示。”朱正纠正说:“那时共产党在刘文辉那里设置了一个秘密电台供联络之用,并不是广播电台。这‘好久没有广播’应该说‘好久没有发报’了。”(13)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79页。
其四,《选编》425页的《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档案中关于“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所加的注释中写道:“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朱正纠正说:“一看就知道:这一条注释和正文衔接不起来。第一正文说的是蒋介石和外国签订的条约,而这个1922年的‘九国公约’却是徐世昌大总统任内签订的,为功为过,都和蒋介石毫无关系。”(14)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80页。
类似这种错误的还有将“《华商报》”译为“《华乡报》”,将“潍县”译为“万县”,将《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译为“金任”,将东北九省省政府主席“徐箴”译为“徐减哉”、“吴翰涛”译为“吴潮涛”、“韩骏杰”译为“韩俊杰”,等等。
至于一些说不清是误译还是校对中出现的错误,如将内战时期的国共和谈“三人小组”的张群、周恩来、马歇尔译为“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的三人小组”、将“(不)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译为“没收大地主的资产”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有这些错误的翻译,已经不必套用什么翻译伦理的“五真”说法,简直可以判定译者是一个只懂语言而不懂历史的门外汉或史盲。如此之明显错译,足可见沈志华教授翻译团队中一部分人的水平还是差强人意。其中也可见其翻译团队成员在外语教育方面有先天不足的缺憾,这也是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培养的一个典型特征,即只注重语言本身而忽视其他学科知识的修养。这种病症,甚至都不属于跨文化交际障碍,而仅仅用跨学科交际障碍来界定就可以了。
二、沟通伦理与翻译实践
关于沟通伦理,作为理论代表人物的Pym(2001)认为:“译者主要是在两个或多个文化的交织或交叉点工作,而不是在一种文化里工作”(15)Pym,A.The return to Ethics,Manchester:St.Jerome.2001,pp.129-138.,这就是翻译的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Chesterman解释说:“在Pym看来,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实现互惠互利,沟通伦理引导下翻译的目标是促进互为“他者”的各方之间的跨文化合作。因此,一个秉持沟通伦理的译者,会通过翻译优化这种合作。”“沟通伦理强调的不是再现‘他者’,而是与‘他人’沟通。”(16)Andrew Chesterman,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The Translator,2001,(2).两位学者的观点,总结来说就是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对等翻译,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交际中应该充分理解对方的文化,这样才能做到沟通无障碍,并进而实现翻译的最佳状态。
然而,译者在跨文化之间进行交际是有前提的,就是译者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语言和文化,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需要认真准备功课的,否则就会出很多笑话。比如文学界著名的吴福辉先生就在编辑、译注《梁遇春散文全编》时出现了重大错误。在《泪与笑》作为“附”的《论麻雀及扑克》一文中,针对原文“若使像Ella同Bridgetel一样play for love那是一种游戏,已经不是赌钱”一句做注说:“Ella和Bridgetel为一般人名,这里泛指一男一女。”(17)梁遇春著,吴福辉编:《梁遇春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实际情形如何呢?原文中这两个英文实际上是Elia和Bridget的拼写或印刷错误。Elia和Bridget也不是“一般人名,泛指一男一女”,而是兰姆自己和堂姐勃莉吉特。
如果说这一处的错误,是因不够细心、严谨造成的,那么第二处将“play for love”“译为:做爱”,就实实在在是望文生义和胡乱想象了。因为根据原文:“when I am in sickness,or not in the best spirits,I sometimes call for the cards,and play a game at piquet for love with my cousin Bridget—Bridge Elia”的上下文来看,兰姆的意思就是自己生了病,或心情不太好时,跟堂姐玩一会儿牌,消磨时光,怎么会和“做爱”联系起来呢?其实不用看原文,就单纯的“play a game at picture for love”这一英语短语来说,也不能直接翻译成“做爱”,而是“(打牌)打着玩玩”的意思。但是,经这么一注释,就成了把做爱当游戏或姐弟乱伦了。
这样重大的误译必须指出来,否则读者真的会以为小品文家兰姆不但如此“不检点”地做出那样的乱伦之事,还写成文章“不知廉耻”地四处招摇,尤其是在道德家和流言家遍地的儒家中国,这个问题简直比天都大。
更严重的是,虽然不确定吴福辉先生是不是始作俑者,但后来的涉及梁遇春这个作品的其他选本中,比如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醉中人生》(18)宋文华选编:《论麻雀与扑克·醉中人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200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梁遇春散文》(19)吴福辉编:《论麻雀与扑克·梁遇春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2009年华夏出版社的《泪与笑》(20)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论麻雀与扑克·泪与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页。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毋忘草》(21)梁遇春:《论麻雀与扑克·毋忘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0页。、201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天真与经验——梁遇春散文》(22)梁遇春:《论麻雀与扑克·天真与经验——梁遇春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2015年,第147页。等,都使用或沿用了这一谬误,可谓贻害无穷。另外要说的是,《春醪集:权威插图典藏版》虽没有跟风错下去,但却将“play for love”译注成了“谈情说爱”。顺便说,该选本将原文的出处《语丝》121期写成“21期”。(23)梁遇春:《春醪集:权威插图典藏版》,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好在梁遇春的作品没有被广泛阅读,也好在没几个人注意这个问题,所以错误就悄无声息地寂寞在书中二十多年,没有产生什么文坛波澜,否则可能官司缠身了。
与上述诸位编者不谙英国文化形成反差的恰好是梁遇春。这位年轻的翻译家不但在32年生命中靠有限的几年时间,翻译了200多万字的作品,还凭借非常具有特色的译上加注备受学界重视。不妨示例:艾迪生的OntheExcessiveCareofHealth,梁遇春将其译为《论健康之过虑——虚弱者之来信》。为何译为“虚弱者”呢?梁遇春加注说:“指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而自己心里却老以为有好多杯弓蛇影,自寻烦恼的地方,所以或者不过属于一种ill habit of mind。”(24)[英]约瑟夫·艾迪生著,梁遇春译注:《论健康之过虑——虚弱者之来信》,《英国小品文选·译者序》,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20-21页。这个注释非常有助于对译词的理解。再如哥尔德史密斯的《快乐多半靠着性质》中有一句:“Dick Wildgoose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快乐的傻家伙。”梁遇春加注说:“Wildgoose此字译意是‘野鹅’,英国人以为鹅是傻的东西,这位先生又是野性难驯的,所以这个名字实在有意义的。”(25)[英]哥尔德斯密斯著,梁玉春译注:《快乐多半是靠着性质》,《小品文选》,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62页。这样一个注释,将主人公狄克·魏尔德戈斯的性格和形象非常鲜活地揭示出来。再如加德纳的AFellowTraveller中有一句:“我戴上了黑帽子。”(英文原文:I assume the black cap.)如果单纯看原文和译文,都无法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梁遇春在此加注补充说:“英国法官判决死刑的时候,就戴起黑帽子来,所以‘戴黑帽子’就是宣告死刑的意思。”(26)[英]加德纳著,梁遇春译注:《一个旅伴》,《小品文选》,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168-169页。
简单的几个范例,就可以看出梁遇春在了解英国文化方面,是有用心和专业准备的,尤其是对比前面诸多学者和编者的“误译”,二者间的差距更加明显了。
关于译者的跨文化知识积累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家傅雷曾说过一段有道理的话:“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烈热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27)傅雷:《论翻译书》,《读书》1979年第3期。类似的话,王佐良在1984年时也说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28)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事实也确实如此,翻译工作看上去简单,实则相当有难度,如果不了解对方文化而进行“硬译”,也难以在沟通伦理和跨文化交际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承诺伦理与翻译实践
Chesterman的“承诺伦理”与Newmark的“翻译职业道德”及Pym的“译者专业责任”有些类似。Chesterman说:“我把承诺作为黏合剂,把从业者与实践的价值结合起来。因此,这也是一种美德,支持追求卓越,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译者。承诺往往是公开的,类似于婚礼上的许诺或宣誓。”他进一步指出,译者的承诺,主要包括译文真实、文字清晰、容易理解、值得信赖等伦理内涵。为了贯彻翻译的承诺伦理,Chesterman特别强调翻译的职业化,将其视为一种承诺,因为“职业(profession)、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词源都是professing(声称;表明信仰)”,意思是“以公开宣誓的形式公开肯定某事”,与医学界的“神圣誓言”相当。(29)Andrew Chesterman,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The Translator,2001(2),pp.147-149.
Chesterman的意思说到底就是翻译近似一种神圣事业和信仰,不能随便应付、一译了之,但是这样的看法和操守对于中国很多翻译者来说,实在近乎耳旁风或对牛弹琴,因为深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学术界,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表达,因此无论过往还是当下,翻译都没有行业准入机制,流行的现象是只要会一门外语人人都可以翻译,专业化、职业化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这也是为何中国翻译界乱象和笑话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妨示例: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奇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30)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现此书已被出版社全部收回。)中,把英文资料中的很多词汇误译,包括期刊、书名、出版地和出版社等,造成了新世纪以来堪称最大笑话的翻译乱象。比如其中他把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实际应是蒋介石),把J.K.Fairband(正确拼法为John King Fairbank)译成费尔班德(实际是费正清),把 Immanuel C.Y.Hsü译为苏春月、苏埃曼纽尔、苏依姆(实际是徐中约),把Ch'Tung-tsu译为楮东苏(实际是瞿同祖),把Jonathan D.Spence译为斯宾塞(实际是史景迁),把T.C.Lin译成林T.C.(实际是林同济),把T.A.Hsia译成赫萨(实际是夏济安)等一共15处明显的人名错译。(31)高山杉:《“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游戏的风雅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93-197页。
王奇教授为何如此大规模地、明显地或甚至近乎滑天下之大稽地错译这些文史学界的名人呢?首先是因为他想当然地按照音译原则进行翻译的结果,他并不知道Chiang为“蒋”的威妥玛拼音,Kai-shek为“介石”的粤语译音,所以把中国人或历史学者最熟悉的历史人物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
如果仅仅是因为知识盲区造成错误,也因为不了解出身文学专业后来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史又一直在海外工作的夏济安教授,还有心可原,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哪怕就是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者,起码也应该了解同是历史学家的费正清、徐中约、瞿同祖、史景迁、林同济吧?书中所引述他们的著作名称,起码也应该有所目睹耳闻吧?然而,王奇教授就是以一个超乎任何学者、译者想象的方式上演了这一出翻译界、学术界的闹剧。
这样的翻译乱象和闹剧,并非是首次上演,1998年,由胡宗泽和赵力涛翻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校对的安东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英语: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在三联书店出版。其中在第三章第3节中有这样一句话:“门修斯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32)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9页。初看这句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一核对原文就会发现大问题了,因为作者吉登斯引用的这句话,源自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的英译本“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英译本书名中的1928应是1926的错写)。吉登斯著作中的英文原句是Mencius quoted Confucius as saying,结果译者不但将孔子的格言(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当成了孟子的格言,然后将这句格言望文生义地译为“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而且还将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人物Mencius(孟子)译成“门修斯”。这短短五个英文单词译成汉语就出现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错译,足见译者、校对者和出版社编辑多么不负责任,因为但凡其中有人有些许文化,认真核对一下,就不会出现如此荒唐的翻译乱象,这也就难怪目前翻译界特别为那些人名译错的现象命名为“门修斯”了。
从门修斯到常凯申的翻译乱象、怪象,不是仅有的两个例子,而是家常便饭,比如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将SunTzu的OnTheArtofWar(孙武或孙子的《孙子兵法》)译为“桑卒《战争艺术》”(3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比如网络上戏称的将Sun Yat-sen University译为双鸭山大学(实际是中山大学)。这样的案例实在多得不胜枚举。
更有甚者,还有人假借翻译拼贴文章,靠主观臆测搬弄是非。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2015年7月5日《上海书评》的《阿克顿与陈世骧》一文。文章基本是在Harold Acton的两本回忆录《唯美者之忆》(MemoirsofanAesthete,1948)和《唯美者续忆》(MoreMemoirsofanAesthete,1970)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和转述,然而不但未忠实于原著,还不断地诱导说Harold Acton(阿克顿,实际该译为艾克敦)是“著名的同性恋,据说最喜欢年轻的中国小伙”,学生陈世骧“比其他同学更大胆”,“勇敢地”接受阿克顿“回校与他同住”的邀请。又说晚年陈世骧“与妻子姚锦新离婚不久”,阿克顿就跑到伯克利与他“合译《桃花扇》”,两人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校园。阿克顿还建议陈世骧将“情”字译为“ordeal”,意思是“试炼/煎熬”。对于二人将“离别削弱一般的情感,但是会给伟大的恋情火上浇油,犹如风吹灭蜡烛,却能助燃大火”译为:Absence weakens ordinary passions, but inflames great ones, as the wind extinguishes a candle,but fans a fire,译者更是欲语还休地解读为“应是有过切身体会”。(34)冯洁音:《阿克顿与陈世骧》,《上海书评》2015年7月5日。
关于艾克敦自己使用Aesthete(爱美者)(35)包探案在《〈阿克顿与陈世骧〉之误》(《上海书评》2015年7月26日)中指出,此说系“旁人调侃的称呼,自王尔德之后,这个词在英国尤其是在文化人中已有同性恋的暗示。艾克敦自号不讳”。作为回忆录的标题,以及关于他本身对待同性恋的看法固然会引发人们联想,但是正如包探案在《〈阿克顿与陈世骧〉之误》所指出的,陈世骧是因为老家河北滦县受到战事影响,生活无着落,艾克敦知道情形后才发出邀请的,忽略这一历史背景,之后的各种叙事都变得暧昧不清。至于最后那个“ordeal”和那句具有“切身体会”的翻译,真实的情况是,前者是二人翻译陆机《文赋》时,将“情”译为“ordeal”,意思分别是:“自己写文章时,更能体悟到他人创作的甘苦”和“既有创作时尝试锤炼表达这层含义,又体现了写作者个人情绪上的感应”,“这个‘情’与私情无关”;后者的情况更糟糕,因为那句话是艾克敦转引17世纪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公爵(Françoisde La Rochefoucauld)的话,译者不但将省略号去掉,将passions误译为“恋情”,而且还去掉了后半句:“and absence had inflamed my passion for Italy.”(离别燃起了我对意大利的激情)(36)包探案:《〈阿克顿与陈世骧〉之误》,《上海书评》2015年7月26日。
如此不负责任地翻译和拼贴文章,如此无德地移花接木、捕风捉影地叙事,读者难免不被蒙骗而浮想联翩,就是陈世骧本人在世、且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这时再谈什么承诺伦理,什么翻译清晰、卓越、优秀、美德和神圣,简直是不知从何说起了。不过,如果受害人的家属提起诉讼,怕是译者要有大麻烦了。
从晚清至今,中文翻译已经走过一百多年,按理说翻译事业应该步入轨道,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也应该取得应有的进步,但是部分中国译者不时地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以及翻译伦理考核成绩不佳等问题,实在是需要认真对待并很好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