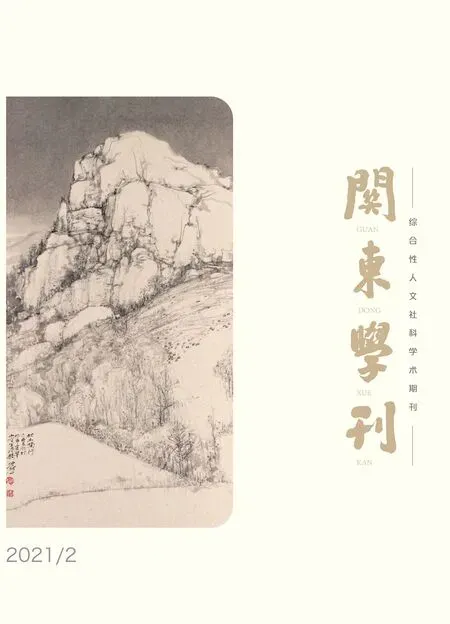人在哪里?
——张志扬对“天人合一”结构的拆解
2021-04-14程平源
程平源
一、成为一个人
对我而言,张志扬哲学的全部意义在于:成为一个人!个体的自由昭示着在虚无、孤独、荒谬、断裂、苦痛、有限、罪性之中,成为一个面向生命的属己存在,超越生存的挤压、他者化与边缘化、伟大的独断信条,担当起活着的重负,“挺身而为一自由人”。
个体性的成长意味着与类脱节,与千年的文化脱节,清理自身“道德的渊薮”,在虚无中寻唤着存在的力量,好像里尔克体验到的,“此刻有谁在世上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存在意味着与自身拼搏,好像“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同另一个分离”。
对个体而言,博大精深的文化渊薮确实令人苦痛,活着就意味着死去,没有人在意一个卑微灵魂的呻吟,只要你不处在“修齐治平”的优势地位,在价值上就几近被抛,只要你不在“天人合一”的道德结构中上升为“大丈夫”、为他人立命的总体人、普遍本质,就只能失语。可人总得活下去呀!宁静逍遥能够遗忘于一时,却不能把遗忘也遗忘了,那深伏的生死焦虑依然在对立的冲突中不能抹平虚无的底色,在喊叫着“痛”。
为此,张志扬不断重申“个人的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个人是怎样的,能是怎样的。”在绝对和虚无之间,个体安顿于“个人的自律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张志扬哲学在于恢复个体的自由。“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
在张志扬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哲思追问中可以映现个体自由的五个维度:一、面对人生苦痛时的生命感知力;二、个体生命从类归属中出离;三、面对虚无的勇气;四、仰望:个体生命的成长;五、划界: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
二、问题意识的起点: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
罪恶与苦难,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的生活。不管有多好的理由,例如“爱上帝”,人们也要爱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心从不发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之后”,不但任何死的理由都不能面对死的事实,连幸存者的活也失去了恒常的意义,除非它能背负无端死的罪责与欠疚,就像人人背负着“十字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初是为“真理”而战的,就像中世纪是为“上帝”而战的一样,交战的任何一方都恪守着“颠扑不破的真理”……
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1)张志扬:《创伤记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8、41页。
由以上的思考张志扬提出问题:“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
下面以《缺席的权利》为例来梳理“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的问题史:
1.文化质疑:“性爱的类归属。”(2)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0页。
2.电影阅读:“如果卡密是‘我’,‘你’是谁?‘它’是谁?”(3)张志扬:《E弦上的咏叹调》,《缺席的权利》,第41页。
“个人归属于阶级,阶级体现于政党,政党集中于领袖……”(4)张志扬:《找一个理由就能活》,《缺席的权利》,第47页。
3.文化结构:天人合一的结构中没有“个人”,“而是体现于天道伦常的承担者,不如说他是指合天人为一的圣者的‘人称’(Person)。”(5)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61页。
4.“十字架”:“道德罪”“宗教罪”,“它启示着既可超出有限又不可达到绝对的自律信仰的中立特征。”(6)张志扬:《“忏悔”的皈依》,《缺席的权利》,第63、161、171、196页。
“任何个人都获得不了普遍的立场,也根本没有这种立场,而且个人作为个人,首要的规定是同他人的区别,他们只能以各自的差异与缺欠相互存在。那种以为自己就是普遍者而肆意取代他人,不管是善意的欺骗还是恶意的剥夺……”(7)张志扬:《重复“十字架”与“圆”》,《缺席的权利》,第192页。
5.“本体论差异”:“僭越”/“人必须放下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武器。他只有权过自己选择的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8)张志扬:《痛苦、智慧、信仰》,《缺席的权利》,第73页。
6.“知识分子”议题:“中国历来不容个人,知识分子尤其害怕个人。谁敢头上不顶着‘天理人伦’呢?”“按理,知识分子应该是自我意识着的个人,然而,知识的传统形式因追求普遍必然的同一性又使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普遍者。”(9)张志扬:《拯救专名的荣誉》,《缺席的权利》,第80、85页。
7.启蒙之蒙(批评形而上学史、语言的两不性):“道德主体”/“……把个人从为圣为王的伦理共性中解放出来,使‘臣民’或‘子民’变成‘公民’,至少是启蒙的一个最切近的目标。”(10)张志扬:《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缺席的权利》,第116页。
8.“理想”议题(对形而上学命题的逻辑质疑):“经验归纳上升不到普遍命题。”(11)张志扬:《理想的膨胀与坍塌》,《缺席的权利》,第133页。
“‘缺席权利’,来自归根到底的不确定性,使个人免遭要求认同共识的善良意志的保护性剥夺。”(12)张志扬:《理想的膨胀与坍塌》,《缺席的权利》,第137页。
9.汉语言(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中国的道德……上封于祖宗神的天道伦常,排斥了非认同的超验的上帝;下封于家族,排斥了个人。……语言的自然既与的类比性、象征性覆盖了、幽闭了语言的逻辑再生的结构性、陈述性。……”(13)张志扬:《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缺席的权利》,第150页。
10.语言哲学:(语言的两不性):“任何哲学提供的形而上学本体的终极证明是徒劳的……把它变成权力话语所强制的思想一律,更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所以,个人作为个人,至少在思想上天然地拥有……缺席的权利,即不认同、不共识。”(14)张志扬:《交谈一:缺席》,《缺席的权利》,第209页。
以上十个方面的批判性言说,从“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个体消失于类,隐匿于“天人合一”所建构的文化传统的各个层面进行了解析,言说仿佛是个体在苦痛的生命体验中生成性的哲思。
三、天人合一:儒家形上学的根基
儒家形上学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面对人在文化中的处境,张志扬追问“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展开了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清理。通观整个“天人合一”结构,张志扬从四个方面展示了对儒家“天人合一”结构拆解的论证。首先,作为个体的小我被大我勾销,代天立言的道德理想主义畅行其道,有限的人以至于上升为无限;其次,有限的人达不到普遍真理,结果“伪”“讳”就成了“天人合一”结构的伴随物;再次,儒家语式建立在自明性的类比上,不是逻辑演绎,而是独断的权力话语建构的经验定式;最后,借助意识现象学还原,在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层面,君臣父子与三纲五常的类比推论式建构遽尔脆断。
(论证一)问题:主体的僭越
其实“人是有限的”
天人合一的道德主体,表达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达者兼济天下
为天地立心……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人合一即小我与大我合一:“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之一……”(金岳霖)(15)张志扬:《创伤记忆》,第17页。
如果有一个人在重建他的道德主体时体悟到,他的小我就是大我,二者“天人合一”得足够的广大,以致广大到万众一心的地步……真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即使改变了权力的政治形式,也还有权力的话语形式……(16)张志扬:《交谈四:道德主体》,《缺席的权利》,第245页。
意即,“个人可以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存在”“朕即圣王”“予一人”“人神不分”“个别即普遍”。
主体的僭越:
问题:
A.人能成为上帝吗?
B.人能代表真理吗?
C.人凭什么支配他人?
D.人在什么限度内不受他人支配?(17)张志扬:《创伤记忆》,第62页。
要害在于这种人性至善论一开始就掩盖了人永远也至善不了的有限性。
人不能实指至善,正如人不能僭越神的位格一样,圣人也不行。然而,“天人合一”使僭越成为合理,成为“独权”“一教”的合法性基础。圣人用“人伦”之教把“天理”掩盖起来,从而用“至善”掩盖了“至罪”。这一维的缺失从根本上导致了“君权”及其“伦理”的“无法无天”。(18)墨哲兰(张志扬):《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人终究是人,不能把他的有限生命许诺的那么不着边际的遥远。理论上没有这种许诺的能力。……如果天真有启示,真有“好生之德”,它的“天谴”警示我们,谁也不能盗用“天”之名行善以营私。(19)张志扬:《创伤记忆》,第21页。
“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人不是上帝。……这种否定性,至少杜绝了人对“上帝”或“真理”的独断论妄想症,……即个人作为类与上帝或真理的等同。(20)张志扬:《创伤记忆》,第62-63页。
一个人要凭借真理成为他人的主宰,首先他必须同样凭借真理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即自己领悟到真理的自我对仍然拖着沉重肉身的另一个自我进行主宰。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对他人的支配就会沦为纯粹的暴力专制和道德欺骗。事实上,他做不到这一点。第一,他并不能确定真理为何物。第二,他不能完全减除自己的肉身而纯化为真理的形象……(21)张志扬:《创伤记忆》,第63页。
再问:
A.一个普通人凭什么整人以至于死而心安理得?
B.一个知识分子凭什么剥夺他人知识或思想以至于无知无思而心安理得?(22)张志扬:《创伤记忆》,第134页。
“所以,他打人其实不是他打人,是他所属的普遍本质在打人。”(23)张志扬:《禁止与引诱》,《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是奉命(宪章、最高指示、领导指示、文化、诫命)打人。
这个人并不自知其为有限的个人,他生下来就获得了“类”的认同。父母、导师、领袖,接踵而至,于是他在宗祠、帮会、集团、教派、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中获得了超出自身有限的普遍性,并视为高于自己存在的本质问题:谁是审判者?谁有审判的权利?
“在世界上,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审判?这个人作为个人有审判的权利与尺度吗?”(24)张志扬:《禁止与引诱》,《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第5页。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志扬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在形而上学层面,天人合一彰显的是主体的僭越;在政治哲学层面君权独尊必然导致膨胀的权力性与独断性;止于至善的人性论必然导致“伪”与“讳”;三纲五常的伦理学借助天道下贯只能建立一个等级社会秩序;德主刑辅的社会控制思想需要借助教化与律例维持主奴辩证法的循环,最终的结果就是建设一个去个体性的弱民社会。图示如下:
儒学思想体系的大厦(图示)
天人合一(形而上学)→僭越
‖
君权独尊(政治哲学)→权力性
‖
止于至善(人性论)→“伪”“讳”
‖
三纲五常(伦理学)→天道下贯
等级社会秩序
‖
德主刑辅(教化罚学)→主奴辩证法
社会控制
‖
弱民社会(人成了工具)→去个体性
(论证二)结果:“伪”“讳”“伪科学性”“权力性”
理想罪
“伪”“讳”是“天人合一”的“至善论”不得不与生俱来的伴随物。愈是在上位的君子愈是不得不“伪”而“讳”。小人做不到,可顺其自然,反正是小人。君子就不同了,一个是他要争当君子,尽量做成君子的样子,做不像只有“伪”了;一个是他俨然以君子自命,本来应是君子的样子,做不像,只有“讳”了。
从本原动机过程到结果皆“善道一以贯之”,与“恶”“罪”不相干,至少从头到尾都排除在外,即“尽己”“慎独”时就已“存天理,灭人欲”了。(25)墨哲兰(张志扬):《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另参张志扬:《创伤记忆》,第47、57页。
“在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前提的制度里,每个人都只有过高尚道德生活的义务,而没有选择过低下道德生活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是隐形(匿名)的圣(人)化生活的被要求者。(这种要求是不能违规的,否则后果就是自绝于人民大众——被民意论的道德社会清理出门,被社会抛弃、被边缘化。)在这种残酷的游戏规则下,产生了大量的伪善者……”(26)程平源:《人比我想象的要自由得多》,《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4期。
原来总以为“理想”是“善”的,甚至是“至善”的,它正是“人心本善”或“人性本善”的终极对应物,否则,何以能调动千军万马,何以被人结党为公以营其私呢?事实上,损人利己的直接罪行,有法律就够了。然而最难的还是那些用善良的愿望或理想铺成的罪恶之路,历史长期对此不警觉,无意识。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走出自己创造历史也创造灾难的不幸阴影,因而对罪恶的体验与反省和对幸福的渴求与向往总是不可分割地根置于人的动机结构中。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理想也有它的罪恶。
“理想”作为观念形态的理想“主义”,其“理想罪”是隐形的。只有当理想“主义”演变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时,其“理想罪”才以超现在时的僭越与剥夺形式表现出罪恶,即向上僭越剥夺以代上帝,向下僭越以代万民。因为只有在僭越与剥夺中,理想的将来时限度才得以暴露其理想完善化(向上)的“虚假性”,以及它在自我实现时的权力化(向下)的“非法性”。
总之,对现在时与个体性的僭越与剥夺乃是“理想罪”的基本形式。(27)张志扬:《创伤记忆》,第136-140页。
(论证三)自证其是:儒学的自明性语式“类比”的“次第学”
一义性
自然性(28)张志扬:《创伤记忆》,第48页。
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丙、“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乙、丙句属“定义、释义、关联、推论合而为一”的典型儒学语式,几乎代表了中国正统思想家的思想方法。孔门儒学不说“逻辑”而说“次第”,只有按此“次第”,才“违道不远”,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近道的先后次第看,乙和丙是一样的:“格物而后知至”。但说法不一样:乙句是倒推法,丙句是顺推法。
顺推、倒推始终如一而不改其意者,在孔圣人的“次第学”看来则是普遍必然命题无疑。孔学门人包括老百姓也对此坚信不疑,想必是用自己的日常经验有意识无意识地做了经验证明和逻辑补充,才使得孔圣人的经验命题在万能归纳的意义上变成了“万世师表”的“永恒真理”。
然而,只要任何一个经验环节在经验世界脱落,比如“格物”不等于“修身”,“修身”不等于“齐家”,“齐家”不等于“治国”,孔圣人的普遍必然的“永恒真理”顷刻像多米诺骨牌倒塌。
孔圣人的“次第学”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经验命题充其量只是或然的、模态的,“格物”可以“修身”,但不一定就能“修身”,“齐家”可以“治国”,但不一定能够“治国”,如此等等。
孔圣人以降的“语录”体文本,“家训”也好,“国训”也好,这样的用或然冒充必然、用经验冒充先验或超验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比比皆是。所以服人的,不是如此次第“违道不远”,而是权力与伦理习俗的互为再生产造就了人的经验定式,历史的惰性也在其中了。
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代表的儒学正统,充斥了这样的伦理语式特征,那就是,“命题与论证合一的自明性语式”,“定义、释义、关联、推论合一的封闭性语式”等等。这种儒家语式结构特征,正是儒家思维封闭性、保守性、综合性、类比性、独断性的自我表现与自我禁锢。(29)墨哲兰(张志扬):《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论证四)意识现象学还原
之一:政治哲学(君臣父子)
之二:社会伦理(三纲五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结构:“君为臣纲、父为子本”。
“作为超越形态的精神主要是‘天人合一’的伦理形而上学或道德本体论。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范畴的嬗变中照样维持‘原先被接受的’‘天人合一’的价值信仰。这种历来如此,不假思索到无意识的前提自明性即价值信仰。”(30)张志扬:《创伤记忆》,第44页。
“由父子而君臣……在家事‘孝’——‘父为子本’,在国事‘忠’——‘君为臣纲’……‘天地君亲师’,天道下贯如此,尊卑有序定矣。
但是,真正起直观证明作用的,不过父子的自然血缘性。它在身上、在心中,亲情体认,由此心性而上达天命,整个支撑起了‘天人合一’观,即合了时间中后出(君臣、天道),实为逻辑之先导的‘辩证法’。这是从经验现象抽象出超验本质的传统手法。然后抽象出的超验本质不过是想当然的名份,只在信仰中,并不在事实中,尤其不在永恒的实体中。……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君臣’‘天道’,而在于人自身。你只有这样的意向能力,也只配这样的意向对象,而且用自身的‘直观性’‘自明性’给予它,使一个完全不同的类比如‘君臣’获得了‘护身符’。
换句话说,从父子的亲情体认,几乎是当下直观到‘君臣’‘天道’,其间的巨大空间的跨度,完全是靠人为的信仰意向联结的。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意识的意向能力所以为自明的自明性,恰恰是自我非自明的限度,它本身还是一个问题。由此观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自明性命题’的‘自明性’,全部维系在‘父与子’的自然‘类比’上。
一个‘类比’,竟支撑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传统的深远与脆弱,都在这里。”(31)张志扬:《创伤记忆》,第49-50页。
家-国伦理观念的建构:“忠孝仁义礼智信”。
“中国的道德有一个通则,上限为‘国’,下限为‘家’,属社会伦理的类道德。由此上封于祖宗神的天道伦常,排斥了非认同的超验的上帝;下封于家族,排斥了个人。”(32)张志扬:《创伤记忆》,第47页。
“究竟是家规定人,还是人规定家,在当时,中国人的意识无论如何不能从‘家’中走出来直观到个人自身。‘天命’尚不能下贯到伦常性的‘家’以下彻底到自然性的‘个人’。”(33)张志扬:《创伤记忆》,第51页。
回到问题意识起点的结论:
单子似的个人,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个人只能作为共同体的“国”(族)、“家”的一分子而存在,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以“国”(族)、“家”为其存在区间或存在本质的“个人”,其意向能力自然会在“父子”身上直观到“君臣”“天道”。否则……“禽兽不如”。(34)张志扬:《创伤记忆》,第50页。
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被删除了。
四、暂停:思考一个问题
个体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怎样的处境?如果将张志扬的问题下行到社会理论层面,我们可以将个体的“人”置于以下五组关键词来思考这个问题:国家/权力;等级/秩序;人性/斗争;道德/关系结构;个体/社会性。
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利维坦,在社会冲突中个体的卑微和屈服,中国历史中个体“人”的命运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
社会不平等是儒法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文化将“人”框定在结构中,每个朝代的律例大多残酷地规定了不同社会等级的秩序,以及法律对这个制度的维护。
中国人性与斗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梳理旨在解释人性善的假设与残酷的政治(人际与人性)斗争之间的关系,解释道德理想主义导致的理想罪如何撕裂人性,展开斗争。
“道德”建构的“关系”将不平等内化,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普遍认同,所以对特权和不平等的追求反而吊诡地建构了社会合法性。
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个体原子化、社会冷漠与看客心理的形成需要从个体的主体性上得到解释。社会团结何以可能或不可能?
通过考察个体“人”的哲学与历史处境,辨析在这五组权力框架下个体“人”的命运,需要张志扬式原创哲学或者说个体“我在”言说的力量,需要深入到历史隧道的深处捕获这个已经脱体的暴力幽灵,追溯逃逸出潘多拉之盒的罪恶之源,在它无穷的变体和幻象中识别出它来,是理性的刑侦技术给当代学术的任务。我们需要尝试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和当代问题之间找到关联,在对断裂、碎片、失衡的复原中探索一条贯穿时空的隧道。
后记:缘起
2018年4月20-22日由《优教育》杂志社主办的“张志扬哲学思想与我”恳谈会在南京伊顿学园举行,邀请函交代了这次思想聚会的初衷: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国内不多的几位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思想家之一,张志扬老师尽管因其“自甘边缘”的立场而少有人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35)刘小枫:《已开第七秩,勤笔仍慎思》,贾冬阳编:《思想的临界——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张志扬老师的哲学思想中“原创性的和生命感的力量奇大”,数十年来,其影响已经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各人文领域,深深改造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国内的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崭新的灵感与话题。
江南春暖花开之时,多年深受张老师哲学思想惠泽的追随者将从海角天涯齐聚一堂,分享各人的阅读体会和思考,并当面向张老师请益,且以此纪念每个人的八九十年代。
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盼望我们和张老师的相聚能够焕发一点八九十年代的气息,并留下生命中珍贵而美好的记忆!
对这次思想聚会,张志扬老师答曰:想起自己在学术界近四十年,穿行于“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比较古典学会”“科学哲学概念帮”,从来不属于体制内的“官哲”或“洋哲”,也从来不申报国家课题从来不担任任何国家或社会名份的头衔名号,始终保持“逆向夜行”的距离,自居民间布衣,直到退休。所以,这次恳谈会对我来说“实至名归”“名副其实”。我也非常认真地写好了发言稿“答谢友人”,如实地介绍了我的思想轨迹。
时值春暖花开,四面八方的友人带着八九十年代思想激越的记忆汇聚在仑山湖畔,既为庆祝张老师八十华诞,也为纪念那个逝去的思想激越的时代。
在给伊顿学员推荐阅读《幽僻处可有人行》的导读语中记有: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张志扬似乎不为人知又广为人知,现在又被称为哲学界的“大隐”“秘密教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
张志扬的意义在于他从此在的残缺和命运的虚无开始的个体言说。个人从天命、宗法、宗祠、帮会、集团、教派、政党、父母、导师、领袖等等的类归属中获得解放,正如哈耶克强调:“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36)[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恢复人的基本尊严,使个人主义成为现代文明的奠基,这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张志扬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在于,他的哲学言述纯粹是个体性的,对于个体从类归属的重负中获得个人自由殊有启迪。
本书是结集出版的三本散文集,包括他个人曲折的生命历程和遭遇的事件,以及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解读,在哲思中彰显了他个人独特的生命气质,对生命的追问和幽僻难隐的心绪贯穿于字里行间,堪称汉语思想界难得一见的个体行传。
为了欢迎张志扬老师的到来,受邀者中很多人用文字回忆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张志扬老师的哲思著述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对张老师哲思进程的理解。
本人将张志扬老师的哲学著述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早期:八十年代开始的著述,以《风从两山间吹过》《门》等为代表。
(一)读书笔记-哲思-生命体验-对生命和意义的追问(以文学、电影、西方哲学等的阅读思考为基础)
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唤醒(文字见于《风从两山间吹过》《门》《幽僻处可有人行》)
引导词:“虚无”“孤独”“受苦”“意义”“断裂”……(参《禁止与引诱》)
可概括为《哲思的张力——张志扬哲学的语式力量》
思想的脚力:1.从一切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主义话语中返身追问它的合法性;2.个体在漂泊(断裂、孤独、虚无)中追寻(敞开)超验之维;3.对民族苦难、个体创伤的文化结构进行意识现象学清理。
批判的力量:1.“为”生民立命的意识形态话语,大话,不知“我”是谁;2.“关于”的学问——譬如做一个“人头”——翻译、介绍、六经注我的“研究”——没有自身的问题意识;3.个体生命的阙如导致只能是类归属的评价指标,从大话到空话的叙事。
(二)对人的有限性、罪性的体悟与思辨
禁止与引诱——追问“原罪”之源
——由此,从存在论上追问文革以及人类苦难的根源
在救赎面前的个体选择
(三)从“人的有限性”“罪性”出发对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结构的质疑、诘问、辩难
到“理想罪”概念的提出。
二、中期:九十年代以后的著述,以《缺席的权利》《创伤记忆》等为代表。
经生命体验的问题意识抽象为哲学问题,在学理上推进为原创性的哲学体系:
(一)哲思中累积的问题意识
(二)思想者的个性
(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
(四)思想的工具——意识现象学
三、后期:2000年以后的著述,以《西学中夜行》《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阴影之谷”》等为代表。
随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进,开始审视西方启蒙理性、技术理性甚至民主自由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
上文即是对张志扬早期哲思第三部分的梳理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