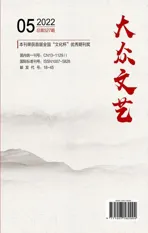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瘟疫叙事*
2021-04-14李佳颖申屠思盈
李佳颖 申屠思盈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绍兴 312028)
16至17世纪,伦敦经历了多次瘟疫。1563年,莎士比亚出生前一年,伦敦爆发严重瘟疫,夺去约四分之一伦敦人的生命,一年后,瘟疫蔓延到莎士比亚的家乡。1593年,伦敦大瘟疫,死亡人数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剧院也随之关闭,在这期间莎士比亚写了很多首十四行诗。直到1595年,伦敦剧院重新开放,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再次登上舞台。不久前的那场瘟疫以别样的形式出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1603年,瘟疫卷土重来,约有三万伦敦人死亡,剧院再次关闭,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等作品。“‘plague’一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出现98次”,它作为情节元素,意象,诅咒语等多种形式出现在莎翁作品中。但学界相关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与充分探讨。莎士比亚敏感地注意到了麻风病、鼠疫和梅毒等瘟疫流行病与当时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将瘟疫作为对当时整体社会解释的一部分展示在作品中。
一、瘟疫的表现形式
瘟疫文学是指“那些主题与一些有传染性的或是致命的身体疾病以及与社会或心理导致的疾病相联系的文学”,它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在描写灾难的同时,让人们看到灾难背后蕴藏的人性善恶、叵测命运与生死劫难,又为现实寻找可能突破的路径。《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莎士比亚的代表作,被更多关注的是其追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主义的爱情悲剧主题和人文主义思想,但少有人注意的是,它也是一部在瘟疫横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作品,瘟疫意象暗藏其中,并且是导致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的元凶之一。在1597年出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第一版中,莎士比亚用的是“A poxe[梅毒]o’both your houses”,两年后,莎士比亚在新校正、补遗和修改的第二版中特别用“plague[瘟疫]”取代了梅毒,明显是为了突出“瘟疫”。
“瘟疫”或类似的词语,作为一种情感宣泄混杂在人物愤怒或厌恶的话语中,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瘟疫作为诅咒语出现:茂丘西奥替罗密欧应战提伯尔特,被刺中要害,他在临死前既怨且怒称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两个家族是“两家倒霉的人家”,而且不止一次地哀号咒骂两家为“倒霉的人家”。单看中译版也许无法理解茂丘西奥咒骂“倒霉的人家”的深意,但在原文中“A plague o’both your houses!”可以理解为“遭瘟的人家”,联系戏剧上演的时间,正是在瘟疫爆发之后,可见这句咒骂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最为恶毒的诅咒,整个伦敦都笼罩在瘟疫的恐怖阴影之下,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瘟疫作为戏剧情节直接展露出来的场景是劳伦斯神父派约翰送信给罗密欧。瘟疫不仅在城中肆意蔓延,也蔓延到了人们心中:巡逻人因疑心他们走进染了瘟疫的人家把他们锁起来。在听到约翰疑似染病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拿那封信,导致罗密欧和朱丽叶双双死去。即使莎士比亚没有提到瘟疫的具体病症,但是刺激了人们对瘟疫的恐惧感知,在演员表演戏剧片段时,唤起观众的瘟疫记忆与瘟疫想象,将之生动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瘟疫的人性隐喻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瘟疫患者被封闭在房子里,密切接触者也被隔离起来。当时伦敦政府对治瘟疫的主要措施的确是隔离。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隔离都是处理瘟疫的一个主要手段,但不同于现在的是,过去的隔离尚不具备适时的医疗救治手段,隔离往往造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牺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视线渐渐看向人的自身,疾病渐渐褪去了神秘的衣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很多缺乏文明意识的人物形象隐含了莎士比亚从神性看向人性,愿理性代替愚昧,用科学和药物来治疗瘟疫的期盼。
瘟疫给伦敦当时带来的影响有很多。伦敦人每日都在惶恐中度过,心理压力倍增。一些记录清晰地说明了这种痛苦和恐惧,“当他们看见身边的人死去、当他们听到他们身边每一栋房子里面都传出的哭声和呻吟时,着实令人恐惧”。“病人的遗嘱、痛苦的呻吟、寡妇的恸哭、孩子的哭喊、孤儿的嚎叫,所有这些在每条街道都彻夜不息”。而隔离措施的实行更加剧了社会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因为害怕被传染,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交流,社会关系变得冷漠。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邻里之间,还出现在朋友之间,在城镇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个家族的仆人因为恩怨而发生械斗,市民在发现之后却并没有进行劝阻反而持枪棍加入械斗,怒喊“打倒凯普莱特!打倒蒙太古!”这一场混乱的械斗也可能是人们负面情绪的一种发泄。
瘟疫的降临打破了以往和谐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邻里关系,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人性中自私、暴戾的一面被恶疾与恐慌激发出来。罗密欧被放逐,即便约翰带着信成功走出维洛那城,就一定能把信顺利送到罗密欧手中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毁灭式结局看似由一系列偶然性情节构成,实则埋藏着必然因素。在瘟疫肆虐的历史语境中,主人公个体不懈抗争,但其间最后的一根稻草——信,必定无法送到罗密欧手中。
三、瘟疫的空间隐喻
隔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出现过多次,莎士比亚通过设置不同的场所,形成了各种空间上的隔离。比如:石头的果园围墙,劳伦斯神父的密室,朱丽叶的衣柜、坟墓;蒙太古说道罗密欧有心事时,“我那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的儿子,就逃避了光明,溜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了门躲在房间里,闭紧了窗子,把大好的阳光锁在外面,为他自己造成了一个人工的黑夜。”罗密欧认为自己深受束缚犹如被隔离:“我没有疯,可是比疯人更不自由,关在牢狱里不进饮食,挨受着鞭挞和酷刑”,“……我只有一个铅一样重的灵魂,把我的身体紧紧地钉在地上,使我的脚步不能移动。”这些都是隔离的一种隐喻,不仅影射了当时政府对抗瘟疫采用的隔离手段,也影射了男女主人公自我心灵上的束缚和隔离,暗含了随处潜伏的死亡和跌入深渊的危险。在当时社会,这种对瘟疫单一的认知和处理方法,充满了悲剧性,也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相呼应。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有与之相反的情节,罗密欧在舞会结束后来到了花园和朱丽叶见面:“……花园的墙这么高,不是容易爬得上的……”,“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阻隔的”;罗密欧被判放逐时,神父给他指导:“去吧,晚安!你的命运在此一举:你必须在巡逻者没有开始查缉以前脱身,否则就得在黎明时候化装逃走”。无论怎样,罗密欧都能冲破束缚和隔离,这种空间上的紊乱暗示着瘟疫并不能够通过隔离来解决,无论怎么封闭,它都能够冲破牢笼。这种混乱状况是戏剧中维洛那的混乱,也是当时的伦敦在瘟疫笼罩下政治生活的混乱和灾难。
四、瘟疫的爱情隐喻
在瘟疫肆虐的背景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展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在所有人身体和内心被隔离的情况下,可怕的瘟疫却变成了爱情的毒药,他们选择内心热烈的情感,正视自己的人性和爱情,以肉体的欢愉打败了对瘟疫的恐惧。他们的爱情就像瘟疫一般来得迅猛而热烈,彼此互诉衷肠,倾吐爱意,超越了世家仇恨的高墙,展现爱情的甜蜜和忠贞。同时,他们爱情的悲剧命运也像感染瘟疫一样惨烈而痛苦。罗密欧决然地喝下毒药,朱丽叶用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死就像瘟疫一样轰轰烈烈却又悄无声息。因此从人性和爱情角度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真挚地道出了全世界青年男女的心声”,虽然全剧以主人公的双双死亡作结,但两族的世仇因此而得以消弭,它因此更“是一本讴歌爱情至上的喜剧”。莎士比亚通过简短的话语侧面反映了当时伦敦政府和人民尚没有重视科学防疫与救治,导致瘟疫频发。莎士比亚借用瘟疫这一意象,融入戏剧中,发挥它的隐喻作用,影响剧情的发展,通过探索瘟疫与人的关系来表现自己对教会禁欲主义、神权束缚的反对,也展现了对理性和科学、人性解放与自由的追求。
五、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爆炸,莎士比亚关注到文学与疾病之间的深刻联系。《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报还一报》《雅典的泰门》等作品中多次出现瘟疫叙事。他对疾病病症的摹写甚至早于许多医学文本,他展现人类在危险环境中的生存境况,通过文学叙事舒缓心灵,消解死亡焦虑,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特殊关怀。同时,莎士比亚观察瘟疫对社会、心理和物质因素的综合影响,思考人类流行病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救赎。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瘟疫不再仅仅是文学叙事的写作对象,更是作为一种文化催化剂,启迪人类深刻理解我们与流行病相遇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流行病与技术变革、思想革新之间的历史关系等诸多问题,是构建英国早期现代“瘟疫诗学”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