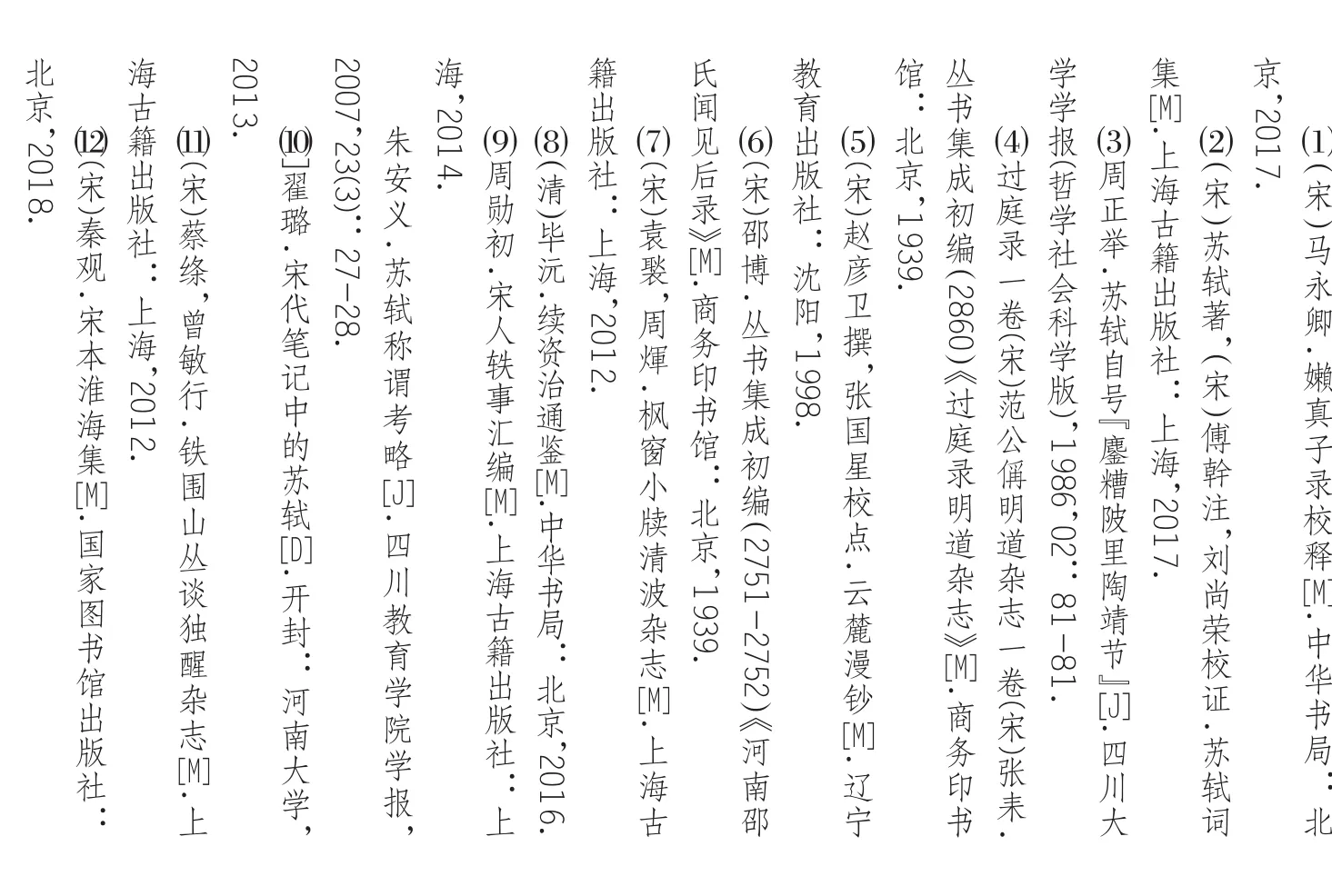北宋人物称呼探究
——以苏轼为例
2021-04-12王沛轩
□王沛轩
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方法多种多样,而称呼与个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国家给予的身份证明有可能被定期改变,不能像称呼一样与人一生成为终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当人们死后,他人在记忆中仍然保留的是对于我们的称呼。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总是认为人们生前所用的称呼和死后相同,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尤其自宋代开始,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在其生涯中被人们用不同的简称在不同的场合来称呼。人名称呼系统在北宋这一时期也延续了唐代不断变化的形式,但是北宋时期却与唐代又有差异,苏轼的称呼问题就反映出了这种现象,因此本文将具有代表性人物的所有称呼进行分析,借此展示北宋时期称呼的真实内涵。
一、北宋时期的人物称呼
历史上,人名称呼系统经历了几次变化,演化至唐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了近现代以前的称呼系统。汉代基本完成了『姓』与『氏』之间的区别消融,形成了如今意义的『姓』,而平民如果能上升到社会上层也能够获得字和谥。精英阶层为自己初生的孩子取名称之为『小名』或『小字』,上学后另外取的名字称之为『名』或『讳』加以区别。至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将行第和辈分加入『名』中成为新的特点,而这些信息在以前是由『字』来传达给他人,这表明『名』与『字』区别的逐渐模糊,『号』的使用在文人中更加广泛,平民模仿精英家族在名字中也采用行第的顺序字。
北宋时期独特的人物称呼是由多种方面组成而展示出来的。姓氏的高度集中至北宋时期越发明显,人们所认定某些姓更为优质的习俗已经深入人心,从西汉的《急就篇》至南朝时期的《百家谱》再到北宋时期的《百家姓》,姓氏向几个大姓集中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北宋与唐代贵族制度相比,人群更加分散,因此出现了宗族和家族制度的再造,宗族联系越来越强,宗族组织也越发普遍,为了将拥有共同父系曾祖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而影响了人名称呼系统,平民的数字名流行了起来,普通人在名字中采用唐代已有的『行第』取名或采用存在已久的旧时方式取名,但是他们采用『行第』并不是作为常规人名的补充,而是将其当成唯一的名字,这种数字将伴随他们一生,因此数字作为名字成为那些从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名字的核心,除非是在其社会地位提升之后,会另外取一个文雅的名字。『小字』和『小名』更加受人重视,在北宋时期马永卿的《嬾真子》录卷之四中,记载了他看到进士《同年小录》中同时收录了他们的『小名』和『小字』,而南宋时期一一四八年和一二五六年保留下来的同年录中也是如此。『字』仍延续与『名』意思相近,它的构建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将表示长幼的字和对男子尊称合并组成,另一种方式则是用一个表示出生顺序的字加上一个与名意思相近的字,还有一种便是将名字中的一个字或者是与名有关的某个字在其后加上『之』一类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而组成。『别名』在这一时期发展完成,一直延续至帝制结束,它是文人士大夫使用的不同种类的别名、附加名和特殊名号,一般通称为『号』,而『号』又分『自号』与『赠号』,『自号』通常表示了文人的思想寄托和某种姿态,自北宋起一个人一生中取几个号或是更多的号是常见的,而在此之前人们通常会满足仅仅有一个号。绰号在北宋时期贯穿各个阶层,它由周围的人给起的补充名,不仅包括了正面的赞美,也通常包含其他许多负面的东西,如『黑旋风』李逵便是从其外貌称之。出于礼貌在对地位显要的人还须用一些间接的方式来称呼,最常见的便是用姓加上官衔或是供职地和用姓加上籍贯两种方式。还有所谓『谥』,谥多为精英阶层死后依照生前的品行、事迹和特点等方面因素被朝廷所给予的,这通常是称呼前人的方法。『庙号』与『尊号』则是运用在统治阶级身上,而我们往往能够记住的也是他们的这种称呼。
二、苏轼的称呼
苏轼是北宋年间颇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从他获得的成就,还是其平生经历都让他在这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不同的称呼。关于苏轼的称呼,在宋人笔记中多有提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其自己所称中所获得;二是由家中长辈给予或从家庭结构出发所被赋予的;三是随着官爵不断变化而得来的称呼,既有自己所取,也有他人所起;四是任职处于不同地方所得。结合已经面世的宋人笔记和某些史书记载,苏轼所用称呼和当时北宋时期主流人名称呼系统吻合,故用苏轼为例来探讨。
从自身层次出发。有时苏轼自称『居士先生』,如其《满庭芳·三十三年》:『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或自称『居士』。苏轼《如梦令·春思》:『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也有自称『东坡翁』,其《游白水书付过》的署名即是『东坡翁』。苏轼曾被改姓『胡』,如文同诗题《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四首》,因苏轼牵扯党争,为避祸而改之。『髯』一字多用来形容多须或须长的人,苏轼既是这样的人,『髯苏』一称呼苏轼亦用作自称,其《客位假寐》诗:『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苏。』又苏轼在神宗年间被贬黄州曾和王定国多次交流,有一封信中说,他『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因其十分敬重陶渊明。
以苏轼家庭层次方面出发。苏轼字有『子瞻』、『和仲』和『子平』三种,前两种被我们所熟知,而当时著名画家文同也是苏轼所敬重的表兄,经常称之为『子平』。文同诗写到『子平一见初动心』、『子平谓我同所嗜』,且注有:『子平即子瞻也』。苏二则是以在家中排行称苏轼,苏轼虽然有一兄但却夭折,故称之,黄庭坚《避暑李氏园二首其一》有『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中的『苏二』正是指苏轼。大苏算是苏轼的俗称,与其弟弟相对,魏学浄《核舟记》『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又称『大苏公』,《明道杂志》载:『范蜀公不信佛说,大苏公尝与公论佛法。』因其排行,又有人称其两兄弟『长公』和『少公』,张耒评价苏轼两兄弟时写道:『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也称苏长公,宋李孟传谓:『本朝欧文忠、王荆公、苏长公、曾南丰诸宗公,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也有以姓氏而称『苏氏』,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这些宋人笔记中提到了苏轼以其家庭背景出发的称呼,可见当时称呼的多样性。
以苏轼社会地位层次出发,称『苏贤良』。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陈希亮……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贤良』一称呼符合苏轼的人物性格和品行,故被人如此称呼。元祐七年,苏轼仕途到达巅峰,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等职,由此得『端明』一称,苏辙为纪念苏轼时所作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周煇《清波杂志》记载了这样的情景:苏轼在常州病逝时,好友维琳方丈对其说道:『端明宜勿忘西方。』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元年九月丁卯条:『以中书舍人苏轼为翰林学士。』在担任翰林学士时就演化出了三种称呼,一为『翰林』或『苏翰林』,秦观的《南柯子·霭霭迷春态》写道:『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和《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中写道:『文与可每为人写竹竟,辄属曰:「无令着语,俟苏翰林来。」』二为『苏内翰』『内翰』之称呼,《王直方诗话》也写过:『东坡初得颍,有颍人在座云:「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三为『翰林公』。黄庭坚《题子瞻石竹》:『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尚书一职是苏轼职位的顶点,在其任职时故有『礼部苏尚书公』『苏尚书』的称呼,李廌《师友谈记》记录了这样的情况:『礼部苏尚书为言:「顷石参政中立为馆阁时,亦赐绯,仍系银带。」』曾敏行《独醒杂志》:『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宋孝宗乾道六年苏轼被追谥为『文忠』,所以有称『苏文忠』或是『苏文忠公』等。这些均是苏轼在担任某些职务时,被赋予的称呼,但我们可以看出,某些称呼并不是对于一个人特定或是独有的,这些称呼往往根据被称呼人的处境变化而改变。
以苏轼有关的地理因素出发。苏轼家在眉山,根据其家族籍贯,就有了不同的几种称呼,有称之为『眉山公』,晁补之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还称『眉阳』,《淮海集》:『梁国张公、涑水司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阳』。苏轼熙宁七年徐州,获『苏徐州』『徐州』等称呼,秦观作诗云『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因新党执政在绍圣元年贬至惠州时,称之为『苏惠州』,《明道杂志》:『苏惠州尝以作诗下狱』。『东坡』这一自号是我们所熟知的,一般认为,元丰二年苏轼被贬黄州后,因其耕种的土地位于黄州城东面山坡,便有了『东坡居士』。至此有『东坡』又衍生了许多称呼,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一有载以『坡公』称之,『孙公素畏内,众所共知。尝求坡公书扇』。又称为『东坡先生』。《师友谈记》:『东坡先生常谓某曰』。或称『东坡老』,苏轼作自称,其《真一酒》一诗自嘲道:『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还称『老坡』,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引朱弁《风月堂诗话》『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又称『大坡』,时人将苏轼幼子苏过称为『小坡』。《宋史·苏过传》:『苏过有《斜川集》二十卷……
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或称为『东坡公』。费兖的《梁溪漫志》『然东坡公之名节,固自万事不磨矣。』又称为『东坡道人』。胡仔引黄庭坚语:『东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可见,随着身处地方的不同,苏轼的称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在某些地方的称呼也不尽相同。
三、结语
本文探究了北宋时期人物称呼的有关情况,通过对苏轼现存的称呼进行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在命名方式上,字辈命名法等随着时间变化对传统的影响愈发明显;『号』运用的逐渐增多代表了北宋人对人一生阶段性的升华。人的正式称呼大多是被他人赋予的,极少数的是在成年后自己选择。名字的起法即带有随性,也有限制。帝制时代以宗法制为纽带,同宗常用辈谱字取名,其影响直至近代。每个时期都有流行的名和字,而北宋时期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风气便是多用老态意蕴的名或字,一方面这受到当时盛行崇尚老成持重的社会心理影响,因此形成了不同于五代时期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