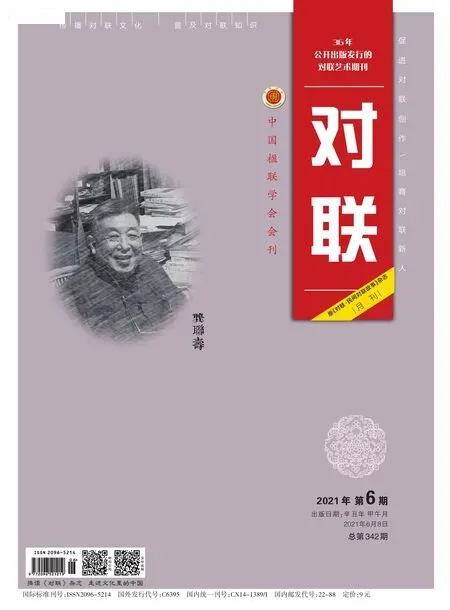论吴均游侠诗中的『不遇情结』
2021-04-12谢莹
□谢莹
在吴均现存的一百四十余首完整诗歌作品中,异于时风的表现游侠题材的二十余首游侠诗让人印象深刻。诗人在这些诗篇中歌咏游侠高尚品质,向往其行侠报国;自比游侠,折射其怀才不遇、功业难成的现实际遇,将对恩遇难求的失望与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难以消解的情感蓄积成了其诗中的『不遇情结』。
一、『不遇情结』的渊源
『不遇情结』与游侠诗擦出火花,要追溯到『游侠』这一角色进入文学特别是诗歌进而形成感叹不遇的文学现象了。游侠诗即以游侠行为或精神为表现对象的诗歌。『游侠』这一概念最早出自《韩非子·五蠹》中的『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其『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典型形象和品质特征是由太史公书写的。游侠以『不轨于正义』之身入世,想要为社会所容,自然倾其所有寻求建功立业的机缘,并渴求为人知遇,以期实现自我价值,立足于社会,被大众认可。而文人多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态,也希望博取功名而得君主恩幸,在本质上,这与游侠仗剑拼杀、立功扬名的希冀一致。诗人笔下游侠诗中便『常有某些功名不遂激愤至极的变态心理微妙地暗伏其中,津津乐道于……
侠风义胆的诗人们,实质上也在暗示或表白』。他们羡慕侠士能够以命相酬知遇之人,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君主、为知己舍生忘死,他们急切呼唤、渴求机遇,却一次次被恩遇难求的现实沉重打击,便有了『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的感慨,不遇之悲积郁于胸,难以释怀,随着『往日侠风血勇被流光溢彩地点染再现,深深地烙上了文化中主体意志、人格的鲜明印记』。
长期积淀,游侠诗中的不遇之悲成为了『一种典型或者反复出现的意象』,具有了『原型』的意义。『不遇情结』在游侠诗中频频出现,经常使人联想到理想、不平等多层含义。但魏晋以来诗人多作乐府来表现这一主题,尚处于偶一为之的阶段,吴均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状况。
二、吴均游侠诗中『不遇情结』的内涵
『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生死报君恩,谁能孤恩眄。』(《雉子斑》)游侠舍生忘死,建功立业以报知遇之恩的品质被吴均推而广之,重视非常,无论是边城将士,还是仗剑少年,身上无不闪耀着这一游侠本色。『轻躯如未殡,终当厚报君。』(《边城将诗四首其一》)『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结客少年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未免粗陋直率,但有着激荡人心的感染力。诗人极度渲染游侠身上的忠与义,甚至将游侠抬升至『握兰登建礼,拖玉入舍晖』(《结客少年场》)这样被皇帝赏识的崇高地位,很明显是出于对游侠的快意人生和豪侠禀性的强烈向往。理想世界中的吴均才华横溢,可登台拜相,胸有沟壑,能勒马杀敌;现实世界中的吴均怀才不遇,空有抱负,一腔热血难以报国,正如《行路难其二》中游侠少年一片挚诚,愿为知己肝脑涂地,只求机遇一展抱负,但结果却是『复闻梁王好学问,轻弃剑客如埃尘』的结局。游侠的立功热情越是高涨,不遇的现实越是血淋淋地刺痛游侠的心,这股悲愤、不平越是挥之不去,最终也只能发出『大才大辩尚如此,何况我辈轻薄人』的无力叹息,吴均以游侠之口代言己身抱负。
梁代偏安一隅的君主听不见边关呼啸的北风,看不见尸横遍野的战场,更对边境百姓流离失所的哀恸少有怜悯,可胸中仍存热血的诗人听得到、看得到,奈何武帝一句『天子今在,关西安在焉?』使他的豪言壮语成为笑谈。军功难立,仕途不顺,诗人对现实已经极尽失望与绝望,他在诗中迫切地找寻一个人去替他实现抱负,建功立业。狂傲不平的吴均在同样出身低微但渴求赏识的游侠身上找到了与自身契合之处,其诗中常见类似『仆本幽并儿』(《赠别新林诗》)『纷吾少驰骋』(《赠任黄门诗二首其二》)的诗句。
有时诗人托物寄兴也渗透着不遇心态。韩非子将『游侠』与『私剑』并称,『剑作为「武」的象征,很早就引起文人的高度重视』。在吴均的游侠诗中,游侠剑不离身,『剑尾掣流星』(《入关》)『剑光夜挥电』(《古意诗二首其二》),以剑的精致锋利象征持剑侠客的勇武豪气。更有代表性的是《咏宝剑》中诗人以切玉如泥的宝剑自比,自荐光华。英雄求主,怀宝待沽,这样一把利剑却无缘上阵杀敌,只能在匣中悲鸣;这样的人才却迟迟没有明主赏识,只能自怜自伤,悲叹怀才不遇。
三、吴均游侠诗中『不遇情结』的形成原因
游侠诗中『不遇情结』的豪迈气节、理想色彩、不遇之悲等多重内涵,在吴均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体现。吴均借游侠诗抒发内心怀才不遇的悲伤,塑造知恩图报、豪迈仗义的游侠形象以作心理补偿,是其抒情言志的需要,其原因自然离不开吴均个人的审美倾向,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个人经历和个性有难以分割的关系。
首先,时代的风云变幻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命运。当时南北战乱频繁,朝代更替频繁,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权不稳,人民流离失所。吴均『家世寒贱』,前后历经刘宋、萧齐、萧梁三朝,可想其命运与浮萍无异。面对如此世道,如吴均这般敏感的文人不由对人生无常、命运脆弱多发慨叹,有着希望为国家献身、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豪情壮志。『为君意气重,无功终不归』(《战城南》)是他的理想豪言。但时代的命运始终握在士族手中,尽管寒门庶族有机会登上政坛,也不过是『恩悻』,寒士的努力终是蚍蜉撼树,仕途对大有抱负而心有傲骨的寒士吴均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其次,南朝地处富庶秀丽的江南,帝王偏安一隅,少有收复失地的雄心。而从吴均诗中『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古意诗二首其一》)『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胡无人行》)等句中不难看出吴均对建立军功之热忱。吴均渴望以军功见擢,也从军去过战争前线,结局竟是『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赠别新林诗》),不得不有『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战城南》)的悲叹。吴均曾得临川王萧宏举荐给梁武帝,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可见其并非没有机会得到君王恩遇。事实上,吴均入仕后多次在官场应酬中惹皇帝不快,又因私撰《齐春秋》,实录未避尊者讳而被罢官。无论是靠军功、凭文采、走门路,吴均的仕途都不是很顺利,因此,『岁暮竟无成』『积恨满东西』的积郁难平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隋朝王通的《中说·事君篇》评吴均为『古之狂者』,其友人萧子云眼中的吴均是『欲知健少年,本来最轻黠。绿沉弓项纵,紫艾刀横拔』(《赠吴均诗》),一副放肆豪迈的游侠做派。吴均也自言『小来意气重,学剑不学文』(《战城南》)。可见,吴均欣赏游侠、自扮游侠,有其自身性格与游侠这一角色契合的原因。吴均如此耿介、正直、孤傲的文人风骨,也是其怀才不遇、功业难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吴均游侠诗中的『不遇情结』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个人难以避免的悲叹。在世人沉湎于一时安定、歌舞升平的假象时,在文坛深陷绮靡华丽的宫体诗时,诗人吴均以游侠诗承载『不遇情结』,让后人听到了齐梁诗坛久违了的对建功立业的激情与渴望,对怀才不遇的喟叹与不平,如孤星般闪耀于黑夜,上承曹鲍乐府,下启唐咏侠诗潮,在蔚为大观的游侠诗域算是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值得后来者驻足欣赏。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