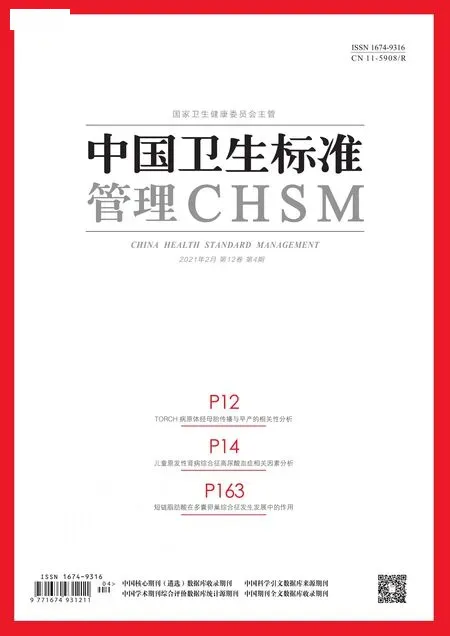中医在消化微生态调整中的应用进展
2021-04-03姚晶晶吴勇王菀彭继升
姚晶晶 吴勇 王菀 彭继升
肠道微生态系统又称肠道菌群,是人体一个重要的“功能器官”,其具有复杂、个体差异且动态平衡的特点[1],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大量现代医学研究显示[2],肠道菌群失衡与肝病、消化道疾病、感染、免疫及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肠道微生态制剂能够有效调节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衡,在疾病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对肠道微生态认识的不断深入,许多中医药学者结合理论和实践,积极探索中医与肠道微生态的关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治疗肠道微生态失衡开辟了新的思路,本文就近年来年中医在消化道微生态领域的应用研究做一综述。
1 中医基础理论与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
近年来的中医理论研究主要指出从整体观念、正邪学说、阴阳学说、藏象学说的角度去认识肠道微生态。
1.1 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旨在阐释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性和统一性。人类是宇宙中的一员,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环境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同时,人体本身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肠道微生态系统由正常的肠道菌群及其生活环境共同组成,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统一体系。现代微生态学认为,一切微生物与环境之间、微生物与宿主之间都是一个整体,宿主的一切表现包括其内在微生物群的表现都是不可能以单独存在的。肠道内的各种微生物共同参与了消化、免疫、代谢等过程,当有些菌属发生数量、比例、移位等变化时,机体的健康状态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可出现病理状态;同时,当人体健康的大环境发生变化时,肠道微生态也会受到影响,饮食结构、生活环境、地域、季节、宿主的社会行为如运动、服用药物等均可影响菌群结构。并且近年大量研究发现消化道内的肠道菌群与生理应激、心理应激引起的心身疾病有密切关系。肠道微生态系统像是存在于人体内的一个小宇宙,与机体本身、环境、社会共同参与健康与疾病的发生发展。
1.2 正邪学说
《素问·评热病论》所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旨在表明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本是正气不足或者降低,发病的外在条件是邪气侵袭。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这两股力量不断地进行斗争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发生消长盛衰的变化过程。
正常生理情况下,机体选择性地让某些微生物定植于肠道,并为其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和营养,而这些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人体内发挥生物屏障功能、参与免疫系统成熟和免疫应答的调节,并对机体内多种生理代谢起着重要作用。现代微生态研究发现,人体内肠道微生态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当机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菌群发生种类、数量、定位、分布、比例等方面的变化,或部分菌群产生对机体有害的代谢产物,或者外来菌侵袭机体免疫系统,破坏了这种相对平衡状态,导致生物屏障功能及免疫调节作用产生一定障碍,继而产生相应疾病。正如明·张景岳所著《类经》云:“气得其和则为正气而生物, 犯其变则为邪气而伤物。”《素问·六微旨大论》云:“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逆则变生,变则病。”这种肠道微生态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即属于“正气”的范畴,失衡的肠道菌群则属于“邪气”的范畴,肠道菌群组成改变、代谢活性变化或分布变化的过程即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过程,通过分析正邪的消长盛衰变化,可判断肠道微生态对发病、病程及预后的影响[2]。
1.3 阴阳学说
中医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释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病理变化过程,并指导疾病诊断和防治。阴与阳之间是通过对立制约来维持协调平衡的状态,当其中一方过于亢盛或者过于虚弱,则另一方会相对不足或偏盛,继而出现疾病状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肠道微生态是机体内的一个生理性组合系统,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的菌群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相互排斥,并始终维持着动态平衡。“阴阳贵和”,肠道内的需氧菌和厌氧菌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布,它们互相作用、互相依赖而生存,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同菌群之间这种互资互用的关系遭到破坏[3],就会出现“阴损及阳”或“阳损及阴”的病理变化,当肠道菌群之间的病理变化超过了机体自我调节的范围,疾病就发生了,通过运用调节肠道菌群的治疗手段,使失去平衡的肠道微生态回归到平衡,即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机体则可恢复健康。
1.4 藏象学说
“藏象”首载于《素问·六节藏象论》,是运用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方法去认识和把握内在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从而探寻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临床把握病机的重要理论基础。藏象学说可运用于解读肠道微生态失衡致病的病机和论治方面。
现代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相关疾病的发病与脾胃密切相关,同时与心和肝有关。《医旨绪余·宗气营气卫气》说:“卫气者,为言护卫周身……不使外邪侵犯也。”脾胃为后天之本,化生水谷精微,其中剽悍滑利之卫气具有防御外邪的作用,而肠道菌群构成了机体的生物屏障,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活动与发育,与卫气卫外功能相近。同时,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受损,则气机升降失调而生病,脾胃病机传变与肠道菌群失衡均为机体自稳机制失常而导致的健康和疾病的演变趋势。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4]消化道内的菌群与生理应激、心理应激引起的心身疾病密切相关,李波等指出负性情绪可以引起肠道菌群紊乱导致机体炎症增加和免疫力下降,即涉及心主神明及肝主疏泄的功能。辨证论治方面。吴佳佳等[1]对肠道微生态与中医证候相关性进行综述,近年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脾虚证、肝脾不调证、湿热证、脾虚湿盛证。
2 中医在消化微生态调整中的应用
近年多项研究表明消化系统疾病如腹泻、便秘、肠易激综合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与肠道微生态失衡关系密切,中医药治疗这些疾病的作用机制与调整肠道微生态的相关性也成为研究热点,以下主要从中医证候的角度进行整理。
2.1 湿热证
湿热证是指湿邪和热邪搏结而蕴于体内,导致脏腑气血经络运行受阻,以出现全身湿热症状为主的重要证型。湿属阴邪,具有重浊、黏滞、趋下的特性,致病易伤阳气、阻遏气机,以头身困、四肢酸楚、胸腹痞闷、排泄黏滞不爽为主要临床表现。热为阳邪,燔灼趋上,易伤津耗气、生风动血,以发热、咽干舌燥、烦躁、小便短赤、大便秘结、各种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肠道微生态相关消化道疾病的湿热证主要包括脾胃湿热证、肝胆湿热证和大肠湿热证。
2.1.1 脾胃湿热证 多因过食肥甘、嗜烟好酒、恣食生冷,酿生湿热,内蕴于脾胃,或因感受湿热之邪,阻滞于中焦而致病。临床常以胃脘痞胀、嗳腐吞酸、口干黏腻、大便不调,舌红苔黄腻,脉弦滑为主要表现,与现代医学的腹泻、便秘、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及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症状相似。现代研究显示腹泻、便秘、IBS及UC由多因素致病,但多项研究表明其发病均与肠道内环境紊乱有密切关系[5]。研究发现双歧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在功能性便秘脾胃湿热型患者粪便中数量显著减少,肠球菌数量显著增多;治疗方面,研究得出不论是单味还是复方的苦寒类中药均可调节肠道菌群结构。郭思嘉等[5]研究发现大黄可改善便秘实证患者,其机制可能是抑制致病菌过度生长、减少肠道细菌移位。
2.1.2 肝胆湿热证 多由感受湿热病邪,或嗜食肥甘而化生湿热,或脾胃纳运受损,湿浊内生,熏蒸肝胆所致,临床以身目发黄、胁肋胀痛、口苦、厌腻等肝胆疏泄失常症状与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等湿热症状共见。相关疾病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在临床中多表现为该证型。CHB与NAFLD为国内外最常见慢性肝病,近年多项研究发现肠道微生态失衡在肝脏损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8],可能机制与菌群比例及多样性改变、内毒素升高、细菌移位、肠道黏膜通透性增高有关[9],故调节肠道菌群使其恢复稳态成为了当前治疗慢性肝病新的重要策略,而中医药在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衡方面展现出一定优势。黄连素是从中草药中提取出的一种典型具有抗菌活性的成分,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其可通过减少免疫毒素、增加抗炎因子,对肠道菌群可进行双向调节,从而对NAFLD发挥疗效,其他中草药活性成分如白藜芦醇、槲皮素均可减少肝脏脂肪含量、修复肠道菌群紊乱[10]。刘福妍[11]通过临床试验发现茵陈四苓散可有效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湿热型患者血浆内毒素的水平,同时可增加有益菌的数量,而降低革兰阴性有害菌种的数量。李自辉等[12]进行动物实验研究发现茵陈蒿汤显著升高双歧杆菌属、冷杆菌属等益生菌的数量,减少会产生致病性肠毒素的葡萄球菌属与链球菌属数量,通过双向调节在治疗NAFLD的过程中对肝脏起到保护作用。
2.1.3 大肠湿热证 多因饮食不洁,湿热蕴肠,或时令暑湿热毒侵袭大肠,伤及肠道气血所致。临床多表现为腹痛腹泻,或暴注下泻,色黄味臭,或下痢赤白脓血,里急后重等大肠传导失常的症状,同时伴有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濡数等湿热之征象。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以结肠黏膜连续性、弥漫性炎症改变为特点,腹泻、黏液脓血便为其最常见症状[13]。现代医学尚未明确UC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广泛开展,遗传、感染、免疫、环境、肠黏膜屏障功能等因素被视为UC发病的主要因素及发病机制[14]。其中肠道微生态与机体免疫机制密切相关,近年来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量研究证实,UC患者存在肠道菌群失调,主要表现为菌群多样性的减少及优势菌群丰度的变化,导致肠道机械屏障障碍、免疫失衡而引发疾病。目前,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柳氮磺吡啶等规范化的治疗药物可有效缓解UC的发作,但面临诸如服药周期长、不良反应多和患者依从性下降等问题,而中医在缓解症状、减少复发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且近年较多研究指出中医药在调节肠道菌群方面显示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在动物实验中黄芩汤[15]可能通过增加肠黏膜屏障标志性蛋白的表达量,调节UC模型小鼠的肠道菌群组成结构和丰度,发挥治疗大肠湿热型UC的作用。
2.2 虚证
虚证指以人体气血、阴阳、津液、精髓等正气亏虚,以“不足、松弛、衰退”为主要症状特征的证。虚证的形成可由先天禀赋不足导致,但主要由于饮食失调、情志所伤、房事不节、久病失治误治等后天因素造成。由于虚损程度不同及影响脏腑差异,虚证的具体表现也各不相同。肠道微生态相关消化道疾病的虚证主要包括脾虚证和肾阳虚证。
2.2.1 脾虚证 多因饮食不节,或忧思日久,或劳倦过度,或久病耗伤、调养失慎,或禀赋不足、素体脾虚,或年老体衰等导致脾气亏虚,日久逐渐发展为脾虚气陷、脾阳虚证。脾虚则运化失职,主要表现为纳呆、脘腹坠胀、便溏等,同时具有气虚或阳虚的症状。现代研究认为,从脾虚论治慢性腹泻、慢性便秘和IBS疗效甚佳。UC常反复迁延不愈,损伤脾胃而形成脾虚型慢性UC,曹莞婷等[16]提出“脾-肠-菌”轴功能紊乱是慢性UC的发病机制,而肠道菌群是该轴的枢纽,健脾方药能够调节菌群失衡,提高益生菌/致病菌的比例,促进“脾-肠-菌”轴功能复常而使大肠黏膜愈合。基于腹泻、便秘、IBS及UC的发生与肠道菌群失调密切相关,多项研究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对中医健脾方剂治疗上述疾病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发现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可增加肠道菌群失衡模型小鼠肠道内有益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的数量[17]。补中益气汤治疗脾虚型慢性腹泻及IBS疗效显著[18]。还有一些单味健脾药物,如黄芪、党参、白术中的多糖、皂苷等均可通过多靶点、多途径调节肠道菌群比例[19],从而可以治疗肠道菌群紊乱。
2.2.2 肾阳虚证 多由素体阳虚,或房劳过度,或久病伤阳,或年高肾亏等所致。肾为先天之本,是推动和调控脏腑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的源动力。当腹泻、IBS及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日久不愈,则可损及肾阳,临床除表现脾阳亏虚之症状之外,还有腰膝酸冷、性欲减退、夜尿多等肾阳虚的症状。有临床试验观察自拟温肾健脾汤治疗ICU抗生素相关性腹泻脾肾阳虚证患者的疗效,发现温肾健脾汤组治疗前后大便杆/球比值变化明显优于对照组[20]。有研究发现温阳法[21]不仅可以治疗脾肾阳虚型IBD患者,还可以降低大肠杆菌、肠球菌有害菌数量,增加双歧杆菌与乳酸杆菌有益菌数量,达到促进黏膜愈合的目的。肾主下焦,司二便,肾精亏虚导致大肠失润或无力鼓动时,则可见排便艰涩,常见于老年人便秘。研究发现济川煎[22]可治疗老年慢性功能性便秘,研究发现治疗组肠道厌氧菌群数量明显增加,需氧菌群数量明显降低,进而改善患者便秘症状,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综上所述,肠道微生态失衡成为许多消化道疾病发病原因和机制研究的热点,改善肠道菌群结构和丰度也成为了治疗消化道疾病的新思路,而中医药不仅能够从基础理论很好的解释肠道微生态失衡在消化道疾病中的病机,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衡的疗效也被大量研究证实。同时,肠道微生态可从一定角度为中医辨证的科学内涵提供参考。中医药疗效与肠道微生态相关性的研究还需更进一步的深入,有很好的研究和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