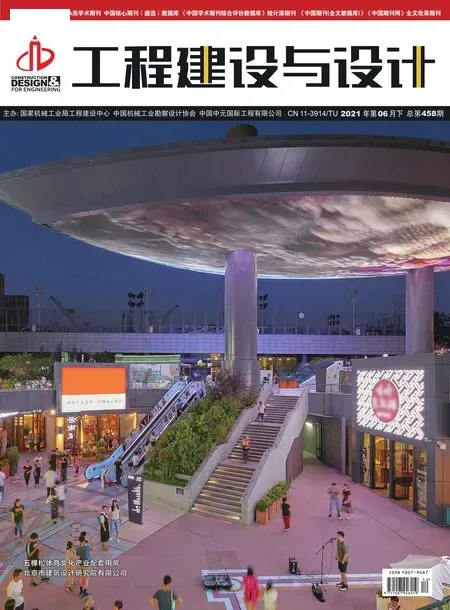差别化用地政策与全要素统筹逻辑梳理
——以兰州市未利用地“一减三增”为例
2021-04-01郭紫镤张祥德
郭紫镤,张祥德
(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 730100)
1 兰州市未利用地开发探索历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我国将土地用途基本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3 类,农用地与建设用地均有较为具体的用途,未利用地更多的是自然保留地或未明确开发利用的其他用地。
兰州市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占市域土地面积20%以上的未利用地与生态脆弱区高度重合,主要为其他草地(93%),是分布在黄土梁峁沟壑丘陵区的矮半灌木荒漠草原。
2012 年,兰州被确定为低丘缓坡开发试点区,兰州新区与主城北部是探索未利用地综合整治模式的重点区域。2017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有关工作意见的函》发布,未利用地综合整治工作停滞。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合理增加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地开发建设指标”,使未利用地再次成为兰州市破解保护和发展矛盾的政策红利区和空间统筹弹性区。
2 兰州市保护与发展的核心矛盾
2.1 生态本底脆弱与生态建设需求迫切的矛盾
兰州市黄土梁峁丘陵区占土地面积约65%,海拔1 800~2 300 m,地表破碎,是全域主要的水土流失区域。
黄土梁峁沟壑区是黄土高原因自然变迁、环境变化、风力吹扬的粉砂和尘埃沉降堆积,经风蚀、水蚀形成低丘峁梁地貌,最高坡度可达40°。主要成分为石英(50%~60%),富含碳酸钙(7%~30%),粒径为0.01~0.05 mm(相较于其他地区土质更为疏松,多孔隙粉状且具有较强湿陷性),含水量一般在10%以下,对水非常敏感,含水量增加时极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遇水易形成空洞,有湿陷性特质[1]。
兰州自解放初期就开始坚持不懈地进行生态建设,从20世纪50 年代背冰上山开始,南北两山绿化面积从1999 年的1.4×105亩(1 亩≈666.67 m2)增加至2019 年的6×105亩,已成为主城区重要的生态屏障。2019 年年底,全市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51.07%,但黄土梁峁区立地条件差、坡度较陡、管护成本高,因降雨量少,绿化依靠提灌,兰州部分区域亩均造林成本达到2 000 元/亩,而国家天保工程、三北工程造林亩均投资标准为500 元/亩。生态建设工作推进艰难,表现在空间上就是生态斑块规模小而散,除2 处自然保护区外,全域林草空间大多小面积散布,各生态斑块之间缺少生态廊道的联系,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高。
兰州是祁连山—秦岭以及黄河两大国家级生态廊道的交界点,其生态建设是国家西部战略和黄河战略落实的有效保障,也是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泄压阀。但生态本底脆弱,自然因素影响大、水土资源不匹配、植被少而不均、承载力低、修复能力弱也是兰州生态的基本特征,生态建设难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国家重要生态资源祁连山、黄河的保护。新时代重新思索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创新黄土梁峁区生态建设模式,是兰州优化水土过程、保护重要生态资源、增加碳汇能力、提升生态服务能力的主要路径。
2.2 有限的盆地河谷与各级战略投放的矛盾
受自然地理约束,占全域约15%河谷盆地是兰州开发建设的集中区域,兰州历次空间拓展呈现出跳跃式、大跨度、远距离特征,与特殊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兰州集聚了全省约1/3 的常住人口,提供了全省1/4 的就业岗位,却挤在兰州盆地内狭小的主城4 区,其中,安宁区和城关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分别达到46%、39%,远高于全域平均土地开发强度5.78%。2000 年以来,在全国人口“东南飞”的背景下,兰州市人口增长约占全省的50%,具有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兰州是全省发展绩效、潜力、综合承载力最强的城市,是未来全省城镇化的主领地,2035 年,兰州市将成为人口规模超500 万人的I 型大城市。2020 年,兰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81.04%,人口持续向河谷集聚挤压,国家功能、省级功能和本地功能无法合理统筹,各种要素导致的城镇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仍在加剧。
2.3 土地紧约束下人粮争地的矛盾
长期以来,兰州市耕地质量等级较低(13~14 等),以旱地为主,相对优质的水浇地(9 等)主要集中在河谷盆地。近10年,全域耕地从2009 年的2 896 km2减少至2018 年的2 804 km2,主要影响因素是秦王川盆地设立兰州新区以及周边河谷的建设发展。
平坦且水资源相对充裕的盆地河谷十分有限,兰州又是各级战略重点投放的省会城市,未来,随着人口流入和城市各级功能的完善,河谷盆地内的建设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在已知地理条件作用下,盆地外的耕地多以枝状分布在黄土梁峁区的沟岔内,地质条件复杂、水资源匮乏、水利工程建设难度大,成本高,不适宜规模化现代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十分有限。
3 新时代未利用地统筹使用方向
兰州市水蚀风险处于中度侵蚀以上,北部靠近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是风蚀灾害较重区。通过多种方法模拟土壤侵蚀与坡度关系表明,随着坡度的增加,相应的土壤侵蚀速率也逐渐上升[2],同时,土壤分离能力也随之增强。土壤颗粒从土壤基质中分离和迁移,会破坏土壤团聚体结构,引起土壤中氮、磷、钾的损失以及地表破碎和植被退化,陡坡土壤侵蚀强、土壤养分被迁移至缓坡,不利于大型植物的生长[3]。在坡度为25°、持续降雨达到约17 min 时,泥沙流失量最高,而在坡度约为5°时,泥沙流失量最少,且随着降雨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大[4]。随着植被覆盖度提高,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逐渐上升,当植被覆盖度达50%时,水土流失可减少50%[5],植被覆盖率一旦超过60%,土壤风力侵蚀基本停止[6]。
3.1 生态优先,统筹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
兰州应进一步锚固生态基底,以保障黄河安全、优化水土过程为根本目的,增补市级生态走廊、绿带、生态保育区以建立和完善生态网络,实施差异化管控,加强生态空间的保育、修复和拓展。
从流域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支流为骨架,沟道小流域为单元推进基底网络建设。加强侵蚀沟道治理、沟头防护、雨水集蓄工程建设,梳理并加强生态脆弱区重要的沟道系统建立,完善与黄河干支流的联通性;考虑沟道季节性特点,形成有时空关系的生态廊道,维护“从山到河”生态网络完整性。
从提升生态服务能力的角度出发,优化“山、河、城”的关系,建设山地公园体系,增加游憩空间,统筹林田草分布。
3.2 化零为整,实现耕地提质增量
立足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城市生态安全,以“坡改梯”与老旧梯田提质改造为主,分类分区统筹农业发展与水土流失治理:
1)榆中北山在原有梯田模式上提质改造,加强沟壑塬面加固除险与保护工程建设。
2)新区—皋兰—永登区域创新“坡改梯”模式,以50~100 hm2为单元、坡度5°为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枝状耕地与未利用地集中整理,促进耕地集中连片。以此为基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灌溉、排水和降渍能力,稳定主要农产品生产空间,提升水土保持能力。
原则上未利用地优先开发为农用地,开发为耕地的,经县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共同认定,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审查,省自然资源厅复核确认后,应纳入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库。
3.3 精用适用,优化未利用地使用
位置好、成本低,短暂的国家试点政策与扁平化的动力牵引模式下,造成低丘未利用地开发一度成为“兰州热点”。2010—2018 年,全市未利用地面积减少70.78 km2,目前,兰州市未利用地综合整治模式以点状分布的单一用途转化为主。
新时代大规模“低成本”未利用地开发是“高成本”的发展行为,未来兰州市未利用地应在做足生态本底建设、保障农业空间安全的基础上,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角度,适度适量转化建设用地,纳入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管理。
4 结语
兰州市生态本底脆弱,是全国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区,占全域土地面积50%以上的黄土梁峁区,是长期以来未利用地分布的主要区域。特殊的战略地位与地理格局使得兰州长期面临3 个核心的空间治理矛盾:本底脆弱与生态建设需求迫切的矛盾、有限的盆地河谷与各级战略投放的矛盾、土地紧约束下人粮争地的矛盾。2012 年起,兰州结合国家土地政策试点进行了2 轮小范围的未利用地综合治理探索。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立新格局与黄河战略的提出,使未利用地再次成为兰州市破解保护和发展矛盾的政策红利区和空间统筹弹性区。
紧扣3 个核心矛盾,结合本轮国土空间规划,兰州提出“一减三增”的全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模式:“减”水土流失严重且生态服务能力有限的未利用地,优先系统化“增”建生态空间,锚固生态基底;“增”农业空间,统筹耕地提质增量,推动农业空间从破碎化零散分布到集中连片;适量“增”建设用地,保障用地弹性和战略需求,优化用地结构。
从另一个角度讲,“一减三增”是新时代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创新,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分区分类统筹空间治理:(1)从流域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支流为骨架小流域为单元,推进“从山到河”生态网络的完整性;(2)以现代化“坡改梯”与老旧梯田提质改造为主,将农业发展与水土流失治理统筹起来;(3)与城镇空间密切相关区域构建蓝绿网络,建设山地公园体系,增加游憩空间,缓解建设矛盾,提升生态服务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兰州生态本底脆弱的现实条件和保护黄河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兰州的未利用地使用必须以系统化生态建设为前提,未来须抓住水土流失治理这一核心任务,遵循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优化空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