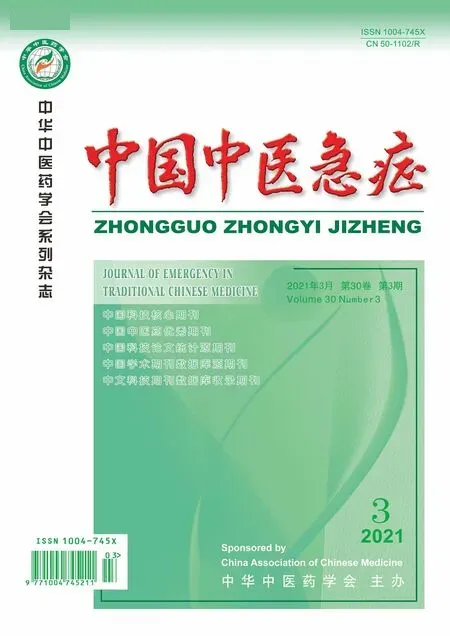张永康教授中医治疗冠心病思路浅探*
2021-03-28牛金宁仪荣荣徐斗富李晓敏指导张永康
牛金宁 仪荣荣 徐斗富 李晓敏 康 静 指导 张永康
(1.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省人民医院,山西 太原 030012)
目前,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呈逐步上升趋势,2018年心血管统计报告显示心血管病患者数量高达2.9亿,其中冠心病患者数量1 100万,占比人数仍居首位[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致使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坏死的一系列临床病理生理综合征,占心脏病死亡率的50%~70%,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2]。冠心病患者,血管通透性下降,心脏射血功能减退,致使心脏负荷过重,心肌缺血,甚至出现梗死,表现气喘、胸闷、水肿等心功能严重受损症状,常引发心衰。目前,治疗上多主张早期干预治疗,常规西医治疗配合中医四诊理化合参辨证,在此基础上,张永康教授擅从药物性味、归经、配伍方面入手,对应不同病证辨证分型治疗,如从性味、归经方面分析红参味苦但起到补益作用的机理,并探讨具有补益作用的药物性味分布规律,进而探究其临床用药规律。
张永康教授为硕士生导师,第6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原明忠学术经验继承人。其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吕仁和国医大师肖承悰、首都国医名师侯振民教授,精研中医理论,习众医家之经验为己所用,对心血管疾病、老年病、疑难病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吾有幸跟师学习,深有体会,受益匪浅。现将个人体会介绍如下。
1 中医理论的冠心病病因病机认识
1.1 病因 年老体弱本虚生,痰瘀气滞标实存。冠心病的致病因素总体可概括为虚(气血阴阳亏虚、年老体虚)和实(气滞、痰饮、瘀血)两大类,以虚为本,以实为标。翁维良教授指出气虚和阴虚是本虚的重要方面,冠心病、心力衰竭等与心气不足关系密切[3],对此,张教授持主张从“虚”而论,认为心气虚、心阳虚是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原因,血瘀是引发疾病的关键因素,对冠心病的治疗注重虚瘀同调。冠心病发病群体中老年居多,而如今年轻化趋势渐明显,不良的生活习惯、嗜食肥甘厚味、情志因素等均会增加冠心病患病风险。现代医学认为,高血压为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性因素,与脂代谢紊乱也有着密切联系,尤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值的升高较为重要。现代研究表明,血液黏稠度增高,引起血小板聚集是导致老年冠心患者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阻塞的重要因素[4]。人至中年,脾胃功能开始减退,脾胃之气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全身气血、津液的运行皆依赖于其运化功能,若中气亏虚,水液、血液运化无权则形成痰饮、瘀血等物阻碍气血运行,则冠脉斑块形成。
1.2 病机 气血异常血脉阻,脏腑传变并病走。冠心病归属于中医学“胸痹”“心痛”范畴,其病位在心,可涉及他脏,寒邪、情志、体虚等内外邪因素皆可致病[5],从痰、瘀、虚方面[6]论治可概括为“心脉痹阻”“阳微阴弦”8字,胸中阳微不运,久则阴承阳位而为痹结,属本虚标实之证。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滞,气虚之甚演变为阳微,虚而生瘀,虚实夹杂[7],痰饮、瘀血、气滞等痹阻心脉,均可发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亦明确表示“阳微阴弦,胸痹心痛,责其极虚”,故虚为其本质,痰、瘀等病理因素为其标实,初始因素则可归因于心肾阳虚、脾气虚弱、肝失调达。冠心病患者长期患病,心气不足为其根本,气虚日久损耗心阳,心阳失于温煦,心脉瘀滞,脉络痹阻;气虚运行水液不利,则聚而成痰;痰浊之气随气体自由升降,阻碍气机,气血运行受阻,内生瘀血,则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心气虚极日久,加之浊毒之邪内生便形成体虚标实之象。现代研究表明,痰、瘀作为冠心病发病的重要病机之一,郁而化热可衍生多种疾病[8],如心脏、血管等的病变。冠心病致病因子除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外,炎症因子、病原微生物等亦能引起和加重冠心病[9],这些不同病理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夹杂,最终演变成复杂的临床症状(如脾肾阳虚、痰瘀内结等)和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张教授临床诊治冠心患者主张早期干预,适时因人而异把握病机,权衡标本。
2 张永康教授临床治疗思维
2.1 红参味苦补为主,药性配伍参辨证 张教授善于分析总结药物性味归经方面异同点,如红参味甘微苦,性温,苦性药物多以泻为主,而红参却以补为主。红参“以苦为补”,更多是以“引经”作用发挥其效果,苦入心经,一方面可助红参温通脉络功能直达心经,另一方面尚具引其他药物入心经的作用,增强疗效。王淑仙等研究表明小鼠心肌的ATP含量和耐氧能力对小红参提取物Ⅱ-A反应强烈;而这种提取物还可减轻犬冠脉外周阻力,增加冠脉血流量,有效保护犬缺血心肌,显著减轻心肌损伤,减少心肌梗死面积[10-11],可认为红参能有效保护心肌和血管。临床冠心病患者心阳虚瘀致病者多见,心阳虚温煦血液能力减弱,冠状动脉血流缓慢,心肌受损缺血,瘀血阻滞,故出现胸闷、胸痛等典型心肌缺血的症状,多以温阳益气活血之品为要,心肌轻度受损者,可服用红参破壁饮片,但若心肌受损严重,则首选汤剂,药物选择上多加用养血益气,活血通脉之品,重在活血不伤正,补益不壅滞。
张教授善研药理,认为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别,故明药性,通五味,辨升降浮沉为临床辨证用药前提,辨证准确的基础上明辨药性配伍,在药物的选择应用上结合药物补泻作用,做到补中有泻,散中又收,寓通于补,方可对症下药,祛除病邪。人们经长期医学观察,将药物作用于人体发生的反应归纳出“寒、热、温、凉”4种药性,如冠心病患者手足不温,冷汗自出,面色苍白,辨为寒证,治宜温阳散寒,以桂枝、细辛、当归等温性药物为主;但若患者出现深寒肢冷,气短喘息,脉沉微等症状时,体内阴寒之邪极盛,心功能渐减弱,应加强温性药物使用,以乌头赤石脂丸加高良姜、细辛等为宜,所以,药性不同,对应治疗疾病的症状深浅亦不相同。药物性味之苦味,寒性居多,常结合其他药性,如苦温、苦平等,《医学启源·用药备旨》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12]。从药物五味论,苦味药物多有沉降、疏散之意,一般视为沉降类药物,用于实证攻积治疗[13],碍于其沉降之性,可断定苦性属阴,主泄,且降泄、润燥。苦甘温或苦平药物多为补益药,用于虚证,可归入五脏,适用于五脏气血阴阳虚损[14]。红参虽苦,但其性温,入心经,可温补心阳,兼通肺脾肾,味甘微苦,甘入脾,可滋补、缓和脾脏功能;苦入心,虽多以泄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可通经活络,增强其通行气血,改善心肌功能的作用,在治疗心气虚、心阳衰竭方面起到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作用。红参作为苦味药中少见具有补益作用的药物,补而不滞,活不伤正,甘苦合化阴气,滋补阴血,燥不伤阴,滋而不腻,可在保护心肌、血管以及改善心功能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即“甘得苦不致呆滞,苦得甘而不刚燥,合而成功也”之理。纳西族民间,人们曾使用小红参50 g,水煎服,白酒为引治疗胸痹心痛证(冠心病心绞痛),而且红参乙酸乙酯部位具有抗心肌缺血的作用,临床使用小红参注射液治疗心绞痛有效率可达90%,其效果显著[15],此结论尚可对红参保护心肌及改善血管提供理论支持。
2.2 以通为补心为主,通补结合他脏辅 五脏六腑皆可致病,血脉痹阻为其主要致病原因,冠心病患者发病不单一,病症繁多,致病因素也较多,比如高血压患者常伴随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不同疾病不同脏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便转为高危。张教授临证用药坚持以通为主,以补为辅原则,常以丹参、赤芍、红花、川芎等行气化瘀活血,疏通心脉心络,心痛甚者,加延胡索、乳香、没药等活血止痛。张教授认为通补结合可化其瘀血,补其气血,但五脏六腑皆可致病,非独心也,虽本在心,致病因素却与肺、脾、肝、肾相关。张教授治疗善通心脉、益心气、温心阳,通补结合兼顾他脏。另外,他特别强调运用化瘀通脉药的同时要谨慎考虑气血之间的关系,注重气血调和,用药常选用木香、郁金等行气化瘀药,使气行血行,共奏疏通心脉之效。
张教授临床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常坚持“通”法和“补”法两大原则,“通”法包括芳香温通法、宣痹通阳法、活血通络法。临床广泛应用芳香温通法治疗胸痹心痛,其中,芳香温通药物所制中成药还被列为临床急救常备之品[16],如速效救心丸、麝香保心丸等。宣痹通阳法常以瓜蒌、薤白、枳实、桂枝等药为主;活血通络法则以血府逐瘀汤、丹参饮等化瘀行气为主,临证治疗可加用益母草、当归等养血活血药,使活血不伤正,还要注意鸡血藤、皂角刺等藤类药物的使用,以增强通络之效。“补”法以补气血阴阳为主,多选用当归、熟地黄、芍药、川芎等以补血活血,淫羊藿、仙茅、补骨脂以温补肾阳,墨旱莲、牛膝等以滋补肾阴。全国名老中医原明忠大师临证常以益气通脉汤和温阳通脉汤为主,认为气、阴、阳虚为本,瘀血为标,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其经验方:益气通脉汤,温阳通脉汤[17]。张教授师承原老经验方,亦坚持补虚为主,祛瘀为辅理念,认为通法与补法是治疗冠心病不可分割的两大原则,无论单一病还是合并病均应通补结合,或通法和补法交替使用。
2.3 活血散瘀兼通阳,芳香温通顾夹杂 张教授认为活血化瘀贯穿冠心病治疗的始终,为重要治疗途径,但切不可一味地活血化瘀,临床治疗应注意根据伴随症状辨证施治,配伍以养阴益气、化痰理气之品,临证活血化瘀药用量较大,视病情轻重用量15~30 g不等,取其药力峻猛之效直达病所,并且善用对药治疗,强调对药根据中药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反的特性,将不同药性的中药组合可起到协调作用,如五灵脂与蒲黄配伍,五灵脂善于活血行血,化瘀不动血,蒲黄止血力量强,使活血而不动血。张教授认为冠心病常多种疾病并发,且伴多种兼夹证,临床治疗善辨证配伍用药,在活血化瘀基础上佐以养阴益气、化痰理气药物,活血化瘀药临床上常选用丹参、鸡血藤、当归、赤芍等养血活血,乳香、没药、三棱、水蛭等破血活血,选用破血药物时强调切不可一味化瘀止痛,而遗忘其峻烈之性,伤及正气。
《类证治裁·胸痹》云“胸痹之脉,阳微阴弦,阳微知在上焦,阴弦则为心痛,以《金匮》《千金》均以通阳主治也”[18]。寒邪内闭,阳微阴弦为胸痹发作重要病机,在冠心病轻、中、重不同程度的中医治疗中张教授常加用桂心、干姜、吴茱萸、麝香等芳香走窜、温通行气类中药,并配合常规中西医疗法四诊理化合参辨证分型论治。芳香温通法同样为临床常用治法之一,主要以芳香辛散,温通经脉药为主,现代研究表明芳香温通类药含有成分挥发油,可解除冠脉痉挛,增加冠脉血流,减少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供血,血液流变性以及心肌收缩力[19],故可认为芳香温通药在治疗寒邪内侵,阳气不通所致诸痛证有效。此外,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注重抓主症,兼顾夹杂,标本同治,对于阳虚欲脱者,多以四逆加人参汤以回阳救逆固脱;对于兼顾肾阳虚者,则多以真武汤加黄芪、汉防己、猪苓、车前子温阳利水,顾护他脏。
3 冠心病帕金森案
患某,男性,77岁,于2017年5月28日就诊。主诉:心脏支架术后间断胸闷2个月,加重半月。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憋胸闷,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遂行心脏支架术,共植入支架3枚,术后仍间断胸闷。现症见:胸闷、心悸,症状持续约1~2 min,经休息后可缓解,头晕,进食后突发心烦后意识丧失约10 min,意识恢复后呕吐痰液,伴恶心,时精神差,眠可,饮食尚可,大小便正常,舌淡滞苔白,脉沉涩。伴高血压、糖尿病15年,帕金森7年。辅助检查:视频脑电图示,轻度异常脑电图;心脏彩超显示,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动态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偶发室性早搏,成对室性早搏;头颅CT示,左侧丘脑、左侧基底节区及半卵圆形中心多发腔隙性脑梗死,中医诊断为胸痹,辨证为气虚血瘀、阴虚阳亢。治以补气活血、滋阴潜阳,予自拟益气通脉汤加减:党参20 g,麦冬20 g,五味子20 g,丹参20 g,红参 6 g,黄芪 30 g,黄精 20 g,桑椹30 g,菖蒲20 g,郁金15 g,细辛3 g,续断30 g,益智仁20 g,钩藤20 g,当归15 g,川芎10 g,何首乌20 g。6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二诊(2017年6月3日):胸闷、心悸减,头晕稍减,睡眠可,舌质较前有所改善,继服上方,接续服用血府逐瘀口服液、通心络胶囊、多巴丝肼片、左氨氯地平片等药物治疗。
按语:该患者冠心病伴帕金森、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植入支架3枚,仍间断胸闷、心悸,临床辨证要素为气虚、阴虚、瘀血,处以自拟方益气通脉汤加减。益气通脉汤由生脉饮合膈下逐瘀汤相合而成,系原明忠老中医多年临床实践所创,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等的治疗。方中所用参类药物本为人参,有时考虑患者体质因素,选用红参,现多以党参代替。红参苦温之性,一方面起到温通心脉作用,另一方面利用其“苦可入心”机理,可引诸药直达心经,更好发挥行气活血之效。党参、麦冬、五味子补心气养心阴,郁金疏理气机,消散瘀血,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与川芎、丹参化瘀药同用,可助疏心之脉络,通脉之气血。另外,祛瘀活血药配伍行气药尚可缓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医学认为帕金森多因肝肾亏虚,阴不制阳所致,加之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多年,故用黄精、桑葚、续断滋阴补肾,何首乌补益肝肾,菖蒲、益智仁醒神益智,钩藤平肝潜阳通络,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通脉、醒神益智之效。
4 结 语
冠心病为临床常见心血管系疾病,同时也是危险系数较高的疾病之一,易伴随多种并发症。张永康教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强调分期分型论治,活血化瘀法贯穿冠心病患者治疗始终,用药方面不同于其他医家,活血化瘀药用量偏大,意在取其药力峻猛直达病所之效。阴升阳降,阴平阳秘为中医治病之根本,对生理功能平衡有很大作用[20],张教授对于冠心病及多发病善于协调阴阳平衡,气虚多兼痰瘀,药物使用上注重在活血化瘀基础上加用养阴益气,化痰温阳之品。红参,味甘微苦温,可入心经,一方面可加强其本身温通脉络之效,另一方面可引其他益气活血药物归入心经,增强疗效。笔者通过药性方面探索辨证辨病用药规律,活血化瘀基础上合理配伍益气温阳、复脉固脱、化痰祛瘀之品,以兼顾夹杂证,标本同治,以上仅为张永康教授诊治冠心病部分辨证用药思路,尚有不足之处,需在以后跟师学习中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