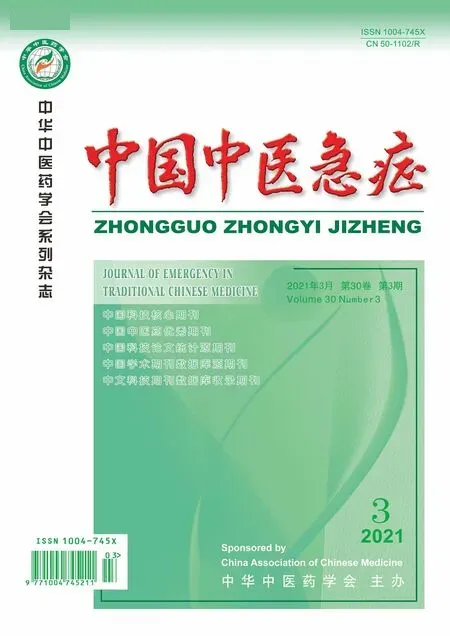《医学衷中参西录》张锡纯论治心病理论探析*
2021-03-28陈会君赵御凯
陈会君 赵御凯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张锡纯为清末民初贯通中西医学的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参西而不背中,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堪称理论结合实践的经典之作。其在心病领域,立足于中医经典理论,展望西人之学,诠释心之神明、君相二火、不归原及枢机等原理,为后世医者在领悟中西医学心病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笔者深受张氏医术渲染,多次拜读其作,感悟深刻,于记之。
1 心与神明诠
张氏在神明论中曾驳西人“神明在脑”的时间起源,曰“自神明在脑之说倡于西人,近今讲科学者鲜不谓其说至精至奥……吾中华医学早先西人数千百年而发明之”,并且张氏认为,中医学的“神明在脑之说”早于西人千年之久[1-2]。张氏认为神明并非只发充于脑,脑只是神明的所藏之处,而将之展现出来的为心,即发露于心,故有“盖言神明虽藏于脑,而用时实发露于心”之说,这更加诠释了心在机体中的重要地位。《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头颅只为脑的外壳,脑为外壳内的中心点,为神明所藏之处,而脑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用时必须经过心表达出来。《丹经》认为忧思及心,而忧思就是通过心脑贯通才以成形。又如《六书精蕴》云“元神何宅,心为之宅,元神何门,囟为之门”。进一步印证了张氏学说的神明发于心,藏于脑,其又认为神明为纯阳之物,脑藏之,脑不畏寒,心发之,因此心恒温,心与神明是有直接的关系,而上升至现代中医心病的理论实践中[3]。脑藏之,心不发之,多因心阳不振、阴寒凝结所致,故而神明与心断隔,病证多见胸痹、心痛等症,病因多杂,但寒邪、阳虚为重中之重,临症其人心胸憋闷,四肢厥冷,多伴神志不宁,舌淡胖,脉多涩沉细。治法首以温心阳不振之法,心之得畅,神明才能展现,病情预后则会较好。若上升至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其病多见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室上性早搏或室性早搏)等症,但总体不外乎强心、扩管、复律、稳心等治法[4]。无论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对于此种疾病的预后都是以神明得畅为主[5]。张氏更以心与神明理论领悟养生之道,云“凡人之享大年者,下元必常温暖,气血必常充足,人之神明固可由脑至心”[2],长寿者,下焦多温暖,气血多充足,气血充足则可上灌注于心,心之气血充足,则神明自然明亮,真气也就凝聚,即神气充足,丹田温暖,寿命之根自然壮固。可见人体精神之气的旺盛,是与心的温煦功能分不开,故在诊治心病方面,应多倡导稳固心阳之法[6]。
2 论人身君火、相火有先后之分
张氏在谈及君、相二火,以道家学说、《黄帝内经》入手,避开先后,只论及两者的微妙关系。又云“道家以丹田元阳为君火……是以《内经》论六气,止有少阳之火,而未尝言命门之火”[2],故道家以“丹田之火”作为心之火,而《黄帝内经》以胆中之火作为相火,说法不同,但其出发点、落脚点却为一致。《黄帝内经》论六气,君、相二火只作少阳,以足少阳胆经为主,心在上,胆在下,心阳临照中焦脾土,中焦熏蒸上元君水,故此张氏将上中焦失衡病机引入临床,用实践说明两者关系,其将经典方“《金匮》苓桂术甘汤”加减应用于上元不足,饮食不化病证中,下元不足,上元失去温煦,久致寒痰凌心,君相二火不通,故而脾土亏虚,饮食不化,辨证配伍巧妙细微,又不伤及上下元气,可谓理、法、方、药展现得淋漓尽致。曰“盖心为太阳之火,如日丽中天,临照下土……至胃中之食,则又赖上焦之心火,中焦之火化之”[2],提出应温煦上元,下照中焦,脾气充足,既能熏蒸上元,又化饮食。因此,张氏未提及君、相先后之分,只谈临证两者的相关性,更加体现出人、自然、阴阳、五行之间的整体性。而在中医心病的临证论治方面,将君相二火巧妙地运用实践,以脾土不运,相火亏损,上元不足,则君火虚弱,作为两者失衡的重要病因,脾土得畅,上元得畅,心病自安,病机相互夹杂,相互转换,更加体现出张氏所说的君相之火未有先后之分的道理,因此,诊治心病应多整体辨治,深思心与五脏的密切联系,重视并发症,才可能全面认知心病[7]。
3 论火不归原治法
首先,张氏批评方书中将“下焦之火”命为“阴分之火”或者为“龙雷之火”的概述,曰“谓下焦之火生于命门,名为阴分之火,又谓之龙雷之火,实肤浅之论也……下焦之火为先天之元阳,气海之形,如倒悬鸡冠花,纯系脂膜护绕搏结而成”[2]。认为“下焦之火”起源气海,为先天元阳,可以萦绕周身之气,因其在下焦,故其比喻为“倒悬鸡冠花”。火不归原,即气海元阳浮越,多夹杂中医心病的临床表现,治法各有所宜,张氏一一罗列[1]:1)其病,头晕目眩,面目潮红,心悸怔忡兼见气息鼻贲,则为气海虚,无从固摄下焦气化,导致元阳浮越,脉象浮大无根,治法多予山药、山茱萸肉、人参温补,赭石力专下行,佐龙骨、牡蛎潜阳,补而敛之,镇而安之;2)其病,口苦舌干,咳喘不断,心间时有灼热,多为下焦真阴亏损,元阳无所恋,上浮之;3)其病,上热下凉,为上阳分微弱,下阴分既虚,两者无交集,治以“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多用下焦滋补之药,药效平和,且不伤中气;4)或其病,上部燥热,心中不安,时有时无,下部自觉凉意浓浓,甚至作泻,因元阳大虚,下焦积寒日久,脉多弦迟细弱,或两寸浮而看似有力。治法多用芍药,解上焦之热,结合山药、人参敛元阳之气,下归其宅;5)其病,胸部满闷不适,时时作呃,多吐痰涎,为冲气或胃气上逆,元阳浮越,胃火夹痰火,症似心病疾病,治以冲胃之气下降,诸病自除;6)其病,忧心忡忡,心中烦躁,易怒疑人,自觉热于肋下,散在周身,脉多滑数之象,兼寸关有力,为伤心后生热,引动少阳之火,多数上越,因此以心病症状多见,治以芒硝、臭剥(溴化钾)解心经,化热痰,山药健脾胃,滋周身,取寒凉之药节制相火上浮,重用山药加以滋补周身,防止元气大伤,故为取济相顾之道;7)其病,头晕耳鸣,周身发热,短气咳喘兼心前区闷热,只思食水果,但食后腹胀不适,脉多弦迟细弱,此为上中二焦阳虚之病,多有寒饮停滞中焦,溢于膈上,迫使心肺脾胃之阳上越,从临床症状来看,兼有外越之嫌,治以张氏“理饮汤加减”,干姜、桂枝助心阳,生白术、茯苓、甘草理脾胃湿气,兼杭芍、橘红、厚朴等药加减,助君臣之药降虚火、平肝胆、利痰饮。
上述陈列不归原之证,张氏追其病原皆不同,但均为内伤之证,症似心病,或兼有心病表现,但究其根源,不外乎虚、实之证。张氏在临床辨病中,辨证根源,配方加减,为治疗心病、心病夹杂病及相关鉴别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思想,同时也为后世医者在中医心病临证辨治方面打下坚实的临床基础。
4 论枢机亢进
心,血脉循环枢机也,动一发,周身皆动之。张氏论治心病首先以心机的亢进为切入点,多从阳明胃腑及三焦、元神及气血等方面的相互关联性来论证,因此,本文从以上两点深度剖析。
4.1 由阳明胃腑引病三焦论治心病 论及心病,张氏先谈心机亢进之证。有外感热邪导致阳明胃腑上蒸以致亢进,有燥粪内留不通而致心机亢进,总归多以阳明胃腑谈论之,但实则病因为下焦阴分损伤,上下无法维系。譬如,心病不寐门中,一人年愈六十,多食易饥,暗伤中焦胃腑,诉其心中自觉发热,胃脘发胀,导致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张氏认为中焦得热,火升心神则无法平降,加之病患年愈六十,病而久之肾精、肾气自损,以致阴阳无法交融,故而不寐。在本病的治则及方药配伍上,其多采用滋肾潜阳,降胃镇肝,用药多以大剂量山药滋补下焦,加之大甘枸杞、玄参、北沙参共补肝肾之气阴,降心间虚火,重用赭石,其色赤、质重,治疗阳明胃腑燥热,从而使心阳得降,佐龙骨、牡蛎、酸枣仁收敛之品,保护神魂安定,方可稳睡[8]。
张氏的心机亢进阳明胃腑思想其涉及中焦,但理论是以阳明为证候,从下焦引至上焦,病机的关键在于下焦,而治疗的根本在于消除本证,本证消除标证自安,在配伍用药方面,简洁明了,看似以阳明论治,但实以补肾之精气,再重降阳明,收敛并用。
4.2 由元神、气血双损论治心病 元神藏于脑,发于心,思虑过多其心必热,热则亢进,故病患多迷惑,也就是西人常说的注意力不集中,张氏认为思虑所生之热多与痰涎相关,但最终的结局是损伤周身气血。故曰“心机亢进之甚者,其鼓血上行之力大,能使脑部血管破裂,气与血并走上而大厥也”[2]。所以说,由于思虑过多而导致的心机亢进,首先是以元神受损,其初始症状多见头脑作响,间觉晕眩,肢体无力等症,其病机愈久涉及气血,会产生心悸,心中跳动不安为多见[9]。治法上,张氏以自拟名方“建瓴汤”引血下行如建瓴之水,醍醐灌顶,及时止损,使元神得安,元神安定方可重补气血,以山茱萸肉、酸枣仁、山药诸药保其气,龙眼肉、熟地黄、柏子仁养其血,朱砂、龙骨、牡蛎安神定志,倘若心房狭小者,多考虑瘀滞,去朱砂、龙骨、牡蛎加菖蒲、远志开窍化滞,远志含有稀盐酸,两药合用可以调节心脏功能,后用红糖水送服,助其血脉通畅。
张氏在心机亢进中表达的元神、气血思想是以神损牵致气血双损,心主血脉,若单单只补气血,导致气血不受元神控制,血脉逆乱,势必心病频发,重者逆于上充血破裂,治疗原则以安定元神,再补行气血,主次分明,辨证加减。
5 论枢机麻痹
如有心机亢进者久而不愈,多以病因、病机标本失治,延至日久,则为心机麻痹。心机麻痹病因多端、治法各异,有素体阳虚,以致寒邪叨扰,心脏之阳麻痹更甚者,故曰“至心脏麻痹之原因,亦有多端,而究其原因,实亦心体虚弱所致”[2],因此,张氏衷中参西,自拟名方理饮汤以复心脏之阳的同时,还首次提出可服西药斯独落仿斯(毒毛花苷)及实答里斯(洋地黄),可谓强壮心脏之良药。如有邪毒侵扰,充塞六脉以致心神不宁,心机麻痹者,其自拟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扫毒菌、利心脏,同时投以西药臭剥(溴化钾)等,可救一时之困,故曰“有心脏为传染之毒菌充塞以至于麻痹者,霍乱证之六脉皆闭者是也,自当与扫除毒菌之药并用”[2]。因此,本文从本体阳弱、邪毒惊扰神明这两方面展开深度挖掘。
5.1 本体阳弱 素体阳虚者,心脏之阳本身薄弱,加之胃部寒邪凌逼膈上,以致心脏阳虚与寒邪交滞,为重症,其心肺脾胃皆为阳虚,脉象异常微弱,曰“心脏本体之阳薄弱,多兼胃中积有寒饮溢于膈上,凌逼心脏之阳,不能用事”[2]。而临床症状则以心、肺尤为突出,多见喘气、满闷、咳吐痰涎等症。张氏认为此种心脏麻痹者,主治心肺,心肺得畅,周身之气才可通利,以致脾胃功能正常运行,可解心脏之寒阳,其自拟名方理饮汤,以干姜、桂枝为主,助心肺之阳宣通,再以白术、茯苓、甘草淡渗脾胃湿气,厚朴、橘红、生杭芍破气利痰,潜热敛润。若有素体阳虚者,受外感之邪,多由表入里,转至阳明,心脏为热所伤,最终成为麻痹重症。张氏认为此证应以大剂量人参汤破心脉,激活心脏搏动功能,再给予毒毛花苷,其性质温和,可改善心肌炎症,从而中西医结合诊治,疗效显著,曰“至西药斯独落仿斯为强壮心脏之良药,而其性又和平易用,诚为至良之药”[2]。
张氏对心病素体阳虚之人的诊治,从表、里两方面致病因素着手。表证者,心脏受热邪损伤,多中西结合,补气以激活心脏舒张及收缩功能,再以西药强心剂改善炎症。里证者,所有寒邪均在机体内部,加之阳虚寒邪交滞,心脏受寒邪损伤,多以温热之药,通上焦心、肺之阳,再利脾胃,通达周身,以缓心脏麻痹。
5.2 邪毒惊扰神明 外感病症多有邪毒,体质亏虚者,毒菌侵袭六脉,以致心脏麻痹。张氏在本病治疗原则上主要以兴奋心脏、清扫毒邪为主,自拟名方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其中樟脑、冰片为激活心脏功能之品,朱砂、薄荷冰均为清扫邪毒之品,方药配伍简单,治则治法明了,且两方对凉热邪毒均有效果。而对本病的继发症状,张氏另辟新境,如麻痹者,六脉皆闭,神明不安,常出现惊悸症状,并且这种症状恰好与邪毒所致心脏麻痹症相反,病机多虚实夹杂,故曰“心中神明不得宁静,有若失其凭依,而常惊悸者,此象多杂,与麻痹相反”[2],而对于此症状者的虚实辨证及用药上,灵活加减,治本换标。虚者,脉微弱无力,多以黄芪、白术、党参重补气为主,生地黄、玄参滋阴,以防重补太过生热,佐以酸枣仁、山茱萸肉凝神收敛之功。实者,脉数兼滑,多以生地黄、玄参泻热为主,龙眼肉、熟地黄补虚,以防泻其太过,佐以龙骨、牡蛎保神镇魄。张氏认为此症状如若服用溴化钾,只能缓解一时之效。因此,西药在处理心脏麻痹并发症上效果并不突出,应当四诊合参、整体论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作用。
若基于现代医学的构架,张氏认为的传染毒菌使心脏麻痹之证,可与病毒性心肌炎相互贯通,而对于后续治疗上出现的惊悸等症,他也给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对后续医者在中西医领域诊治心脏麻痹症或者病毒性心肌炎,甚至预防继发疾病,如惊悸、不寐等症,提供了新思路、新疗法,真可谓融贯中西。
6 结 语
品味张锡纯的医学思想,不仅是研读古今文化的碰撞,更是中医学领域的一次大升华。能立足中医,不改其道,对中医所倡导的整体观念,能巧妙地结合五脏六腑,形神气血,详细阐明了外在的“真象”与“假象”临床表现,对于现代中医心病学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创新[10-11]。其在心病领域,辨证论治,方药考究,具有自己独特的领会,在中药的运用上能够抓住药物的药理学属性,师古而不沉拘于古,中西合用,相得益彰,西药用在局部,缓其标,中药求因,重其本,给后世医者展现了一次真正的中西医实践与理论的大结合[12]。并且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就是要立足中医,以中医为本,辨证看待医学临床中遇到的问题[13-14]。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诊疗,我们都必须时刻保持中医思维,结合现代医学观,这一点对提高临床疗效很重要。
自西医东渐,锡纯先生在面对西医学的广泛兴起中,能衷中参西,汇通新旧,追求医学界的尽善尽美,无偏私之见存于心,实为清末民初中医学的大家[15]。其次,成书《医学衷中参西录》记录了张锡纯在论治心病方面,细审病机,辨证施治,见解精进独到,方药灵巧多变[16],为临床诊治心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实为中华医学之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