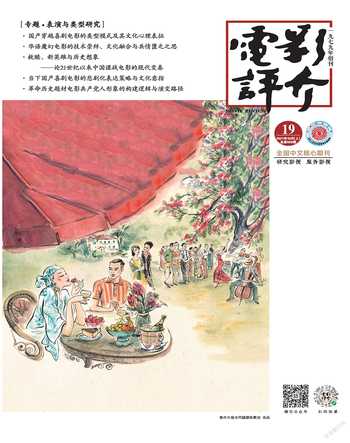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兰心大剧院》:镜像改编与类型重塑
2021-03-27张燕冉与郭
张燕 冉与郭
2021年9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顺利举办,作为评委会主席的巩俐成为焦点人物,不仅有其主演的多部经典影片特别展映,更适时推出了由她主演、娄烨导演的新片《兰心大剧院》,在银幕上演绎了一段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内错综复杂的谍战风云故事,颇具关注度与影响力。
对于此前已拍摄《春风沉醉的夜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多部现代戏的娄烨导演来说,《兰心大剧院》这部电影并不仅是一部改编自小说、追求娱乐视听、自觉推进商业创作的谍战类型片,更是一部意识强烈、情怀浓烈、影响深远的作品,因为影片“是在真实的兰心大戏院拍的……回到原来我待的地方,在侧幕、灯光台上,在那里等父亲下班。那一段经历还是比较有影响的,不光影响这部影片,对我整个工作的影响都大”。因此,导演在二度创作中除了把脉小说的故事与神韵之外,还自觉注入导演自身深刻的成长记忆与生命体验,运用极具个人风格的镜头语言和简约的黑白色调,解构了传统类型叙事,在银幕上创造出了“既是作者记忆,也是客观的小说故事”①改编的虚实互文、折射时代的作者电影。
一、叙事互文的镜像改编
影片主体上改编自虹影小说《上海之死》,但又部分嫁接了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情节,从文学到电影的二度创作转化中,实际上是交汇了历史与当下、中国与日本、真实与虚构的一次探索实践。
(一)“戏中戏”的叙事编排
就叙事编排而言,影片基本沿袭了《上海之死》的故事脉络。原小说突出的特点就是“戏中戏”的架构,以紧凑的线性时间为叙事推进,讲述了一个舞台内外的悬疑复杂、精彩纷呈的谍战故事:1941年12月初,著名女演员于堇应谭呐导演之邀从香港返回上海,排练出演即将在兰心大剧院展演的舞台剧《狐步上海》,但事实上于堇回沪的主要目的不是演戏或营救被汪伪76号关押的丈夫倪则仁,作为盟军特工的她旨在获取日本人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情报,为此她周旋博弈于汪伪、日军、军统等多种政治势力之间,奔波于居住的国际饭店与兰心大剧院,最终她为了内心纠结的使命而跳楼自尽。电影在改编时巧妙地取文学之筋骨,尊重原著继承保留“戏中戏”的叙事走向,以华懋饭店、兰心大剧院两个主要的上海都市空间为场景,将主人公于堇回沪入住华懋饭店的现实生活、明面上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戏剧排练、暗面上的设法接近日本人套取情报的间谍任务等多条内在交叉的线索交错推进,在紧凑的时间推演中展开惊心动魄的谍战行动,有效地构筑成相互对抗,但又有内在驱动的核心叙事情节。事实上,编导进一步浓缩了故事时间,提纯了叙事浓度,影片在开篇抛出一个统摄全片的问题悬念“于堇回来只是为了演戏吗?”。随后将全部内容浓缩在于堇抵沪后的一周内,迷雾般并置了主人公生活在饭店、排练在剧院、为使命穿梭在刀尖的三种虚实交互的生存状况,不时又分解出于堇营救丈夫、于堇结识白云裳、于堇与谭呐的情感纠葛、于堇刻意靠拢古谷三郎等相互间关联、却似乎并不紧密的多重悬念,如同步步紧逼、逆序推减的危机动力,叙事在紧凑的时间线上一路推进。
更值得关注的是,编导调用严密的现实逻辑与心理动机,对小说《上海之死》进行了精心择选,在多个关键处对人物走向与关系搭建进行整合,精心打磨桥段细节与心理内因,有效夯实了故事的内在肌理,并改写了情节布局,促使影片兼具理性之美、感性之情。影片以于堇为核心人物,其真实的间谍身份与表面的演员身份混淆共存,同时又穿梭于虚构的舞台与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她的生命经历与情感走向左右着整体叙事布局,也影响到该片的叙事基调与审美接受。原小说中,于堇为免于日本人纠缠,在获得情报后选择跳楼自杀,这样的悲剧桥段牵引出休伯特自杀、夏皮罗被暗杀、谭呐被活埋等一系列悲剧事件。相比较而言,影片的重心不在于事件冲突,而着力于以情为核,在小说仅止于使命与演出的强戏剧冲突的叙事结构中,全新植入于堇与谭呐经受时空历练、但深藏其内的真挚爱情,延展出一条足以转变后半部分叙事主调的情感动因。尽管于堇最终逃脱不了死局,但她浸润于美好爱情的坚定信仰和挚爱男友的温暖怀抱,影片结尾在揭示人物难逃悲情命运的同时,也赋予了独具一格的叙事开放、审美延宕与情感共鸣效应。此外,编导部分借用横光利一小说《上海》五卅运动后的上海描写,赋予戏里戏外的于堇作为工厂罢工运动骨干的政治成长背景与中国人身份,这种刻意强化补充的乱世之中以国家民族、穷苦大众利益为重的进步意识,可以说源头上充實了人物内在的身份认同与心理动因,也才能合理解释作为盟军间谍的于堇为何刻意隐瞒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导致美国舰队遭受重创后影响二战战局的叙事发展。可以说,这一笔虽然篇幅很少,但确实精妙重要。
(二)人物创新性改写
编导不拘一格地策略性强化戏剧冲突、铺陈叙事谜障,而且更在看似谍战类型的模式套路与旧中国旧上海的都市空间中,尤其在对主要人物与人物关系进行创新性改写的过程中,自觉融入现代性的理性思维,展现出令人着迷的理论思辨与人文哲思。
以于堇为中心,原小说关联出与多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迷般布局的孤岛时期政治博弈关系网,每个人物均有其特定的形象建构与精妙的叙事功能。但撇除文字的抽象,为了银幕上戏剧冲突的浓缩聚焦与具像呈现,导演以心灵契合与情感共鸣作为创作中心,对影片中具有复杂背景与多重身份的部分人物进行了巧妙的整合与改写,着力挖掘相关人物的情感化与立体性,强化开掘叙事之下的人性深度。比如莫之因的文学作家与舞台剧《狐步上海》编剧身份被过滤,主要凸显出其借助戏剧制作人身份,同时作为汉奸执行汪伪政权特务机关76号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具有对于堇、白云裳的情欲诉求以及对好友谭呐的情感,这就演化成后半部其与白云裳的欲望对决与血腥决绝;还有埋伏抓捕于堇时担心谭呐,由此这个人物的叙事推进功能与形象塑造更为立体丰富,富有了多重的人性层次与深度阐述。再比如,白云裳在小说中的身份更为复杂,她既是于堇丈夫倪则仁的情妇,也是日本特务机关管制汪伪76号莫之因的上级和重庆军统内部调查人员,但电影为了更明晰这个人物的焦点功能,将她主要简化为重庆军统间谍、被莫之因交易拉拢以及热爱戏剧、崇拜于堇、满怀成为明星欲望的女人,同时强化赋予了其凄苦成长的孤儿情结与灼热浓烈的戏剧热情,通过简化与发展,实际上意图将这个人物塑造成于堇的部分舞台“分身”,与特工的镜像存在,这样顺理成章演化成她被设计成能代替于堇演出的棋子,并作为叙事中转激化推进莫之因偷听其向谭呐传达的消息后告密抓捕于堇的高潮戏。再有小说中的日本海军武官府古谷三郎是在舞会上认识于堇而后被套出情报,但电影将纯类型化的色诱桥段进行情感性转化,将其发展成为因为深爱失踪的妻子而被貌似其妻的演员于堇催眠套出情报,由此将这个机器般存在的角色赋予了真实可信的人性内涵。
(三)女性的电影与主体建构
诚如娄烨导演受访时说“我没有把这部电影作为间谍片来拍,我更愿意把它拍成一个人物的电影、女性的电影”①,女性人物的真实性、丰富性与深刻性是这部影片的创作根本与亮色,也是影片脱俗于常规间谍片的关键点。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小说文本与电影改编之间的人物塑造特点,可知主人公于堇具有着虚实相生、真假交错的多重角色,这既是20世纪40年代初孤岛时期上海乱局下多股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胶着对抗的银幕策略性描写,更是影片自觉建构主体性的理论实践。拉康的镜像凝视理论的提出,观众观看是想象性的建构机制,同时亦区别于客观凝视的主体建构机制,即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在电影角色人物身上融入自身的权力欲望,呈现出分阶段、分层次的主体性想象建构,通过观众自身与银幕上角色虚像混合而形成一定的认同,进而指涉银幕角色是理想的自我,而后在混淆真实与虚构、欲望与想象的过程中,实现将自我想象为他人、将他人指认为自我的主体建构。影片自觉应用凝视理论,通过“戏中戏”的多重形式,实现了丰富的故事内人物与银幕外观众、舞台内外的人物之间的多层面主体性建构。就故事内外而言,银幕上的于堇作为一个美丽女性、影剧明星、智慧特工与巾帼民族英雄,在特定历史时期寄托了理想女性的全部想象,同时亦与当下现代社会职场理想女性的想象期待相通,观众通过自我与角色的影像置换,实现了女性主体价值的理想化建构。而就舞台内外的于堇与白云裳而言,现实生活中返沪受到追捧、影剧成就斐然的女明星于堇,是白云裳梦寐以求的成名欲望的理想投射与坚强成长、孤独共鸣的情感慰藉,反之白云裳身上充溢出的戏剧热情、同病相怜的孤儿情结甚至是伪饰的影迷身份、沉浮于乱世的特定政治身份等,莫不是叠加在明星生活与间谍身份、演员真实与虚构角色的于堇自我主体的多重镜像再现。
总之,通过银幕内外“戏中戏”、舞台内外的“戏中戏”、人物自身内外的“戏中戏”等多层次的巧妙架构,影片在多个“戏中戏”的文本间形成了镜像对照的复调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合、互联互文的多重意义与复杂关联,进而延展出更深度的戏剧性、表意性与文化意义。
二、作者风格的类型重塑
影片《兰心大剧院》承袭了娄烨一贯的创作特色,即以高度作者化的影像风格来讲述类型化的故事。该片核心是一个谍战故事,但导演以极具个人风格的影像表达对类型叙事进行了解构,不仅继续惯用的长镜头、手持摄影等视听手法,使其同传统谍战片相比呈现出迥异的特色,尤其全片尝试运用黑白摄影,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灯红酒绿的上海城市景观融入黑、白、灰的光影之中,绘制出一幅低沉晦暗的上海“孤岛”地形图景。可以说,娄烨又一次完成了对传统类型叙事的颠覆解构,但同时也兼顾悬疑氛围的营造,对类型叙事进行了比较巧妙的作者化重塑。
(一)长镜头:模糊虚实边界
一直以来长镜头都被看作是电影真实性的体现。娄烨的电影创作偏爱长镜头,从《苏州河》开始,他就大量运用长镜头来展现人物行动,记录城市景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他运用长镜头创新性地将“2012年”和“1989年”两条时间线并置,完成两段时空之间的穿梭转换。新片《兰心大剧院》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有异曲同工之妙,导演通过长镜头探索性地连接“现实”与“戏剧”这两层完全不同的时空,在保有时空完整性的同时,亦有意识地模糊两者的边界,达成了特定的美学效果。
《兰心大剧院》中,长镜头被着重用于处理“戏中戏”的情节。如,在于堇回到上海后第一次参加剧团排练的那场戏中,娄烨精练地用了4个长镜头来展现排练时的情景:第1个长镜头目送着谭呐走向后台,然后环视了舞台一周,展现排练场的热闹景象;第2个长镜头切回谭呐的身后,跟随他穿过后台,重新回到舞台上;第3个长镜头拍摄舞台上的谭呐走向于堇,并在她身边坐下;随后镜头切换,两人展开了一场暧昧的对话。此处多个长镜头的堆叠,让观众对影像所展现的时空的连续性丝毫不怀疑,默认此处的时空仍停留于“戏中戏”中,两人仍在进行戏剧排练,所交谈的内容也皆是设计好的台词。然而紧接着,画面却突然切到坐在車里的莫之因和白云裳处,莫之因正拿着望远镜偷窥于谭二人。这个镜头立刻将影像时空从舞台排练场拉回到现实中,揭示出话剧排练早已结束,方才的对话是于堇谭呐二人的真实交流。再如,在于堇谭呐两人一同离开华懋饭店前往船坞酒吧时,一个长镜头拍摄了两人下车后看到船坞酒吧时感慨的神情,并跟随两人向室内移动。此处,长镜头和跟拍摄影很大限度上保留了时空的真实感和完整性,暗示之后的叙事将遵循这一套时空逻辑。然而娄烨的创作不按常理出牌,创作思维随时跳跃,接下来的故事却再次跳脱出长镜头影像建构出的连贯时空,回到了排练场上于谭二人开始以“秋兰小姐”和“参木”相称,并说起了话剧中的台词,叙事再度被引回“戏中戏”里。“戏里”“戏外”这两重相异的世界被长镜头勾连在一起,水乳交融,难以区分,成为了整部影片制造悬疑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兰心大剧院》中最扑朔迷离的,不仅是尔虞我诈的人物关系和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更是亦真亦假的戏剧舞台和现实生活。
影片结尾处,娄烨运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长镜头:该镜头先定格在船坞酒吧中,以近景拍摄于堇和谭呐的面部,然后开始缓慢向下移动,拍摄从于堇手中滑落到地板的枪支,再向左移动,并逐渐拉远。伴随着镜头的运动,音乐渐起,景别变大,画面从冷清的酒吧回转到热闹的排练场上,一切安然无恙,仿佛剧院里的杀戮和背叛都从没发生过。这个长镜头再次将现实与戏剧这两个错乱的时空粘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切重归原点的美妙幻觉,完成了残酷现实与温馨想象的完美弥合,实现了电影的造梦作用。该镜头的运用,可以说不仅是导演刻意构思的视听首发,而且还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是寄托温情想象、表达人文关怀的重要出口。
(二)手持摄影:情绪外化与假想在场
“手持摄影”是娄烨非常偏爱的拍摄手法。从《周末情人》开始,他就对手持摄影进行了尝试和探索。随后,在《苏州河》《推拿》等作品中,更是持续将“手持摄影”与“人物旁白”相结合的形式发挥到极致,塑造了一个个“旁观者”的视角,将影片故事娓娓道来。《兰心大剧院》虽然没有采用人物旁白,但贯穿全片的手持摄影镜头,仍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假想的在场感。
正如《苏州河》的主人公李学前所说,“我的摄影机从不撒謊”。手持摄影最大的特点在于它能模拟“人”的视线,让观众产生一种在场的错觉,不自觉地对影像叙事产生认同。《兰心大剧院》中,大量的手持摄影镜头让整个故事以“在场”的旁观者视角被展现出来,这种近似纪录片的视觉处理祛魅了类型化叙事,让原本脱离观众生活经验的故事变得真实且易于触摸,故事中人物的情绪心境也变得可以体会和理解。片中于堇初遇白云裳的两人交谈试探的戏中,导演没有采用传统的正反打形式来展现这场对话,而是使用了几个手持长镜头,让镜头不断地游走于两人之间,仿佛有第三人置身现场,观看两人的交流。拟人的视角清晰敏锐地捕捉到两人平静交流背后的暗潮涌动,悄然塑造出紧张感。当白云裳开始追逐于堇乘坐的汽车时,镜头跟着人物一起移动,手持摄影引起了画面的剧烈晃动,带来了一定的视觉不适感,却也直接地传达出白云裳此时的心情,将她急迫热切、想要打动于堇的心情外化出来。同样,在倪则仁被于堇接至酒店门口却遭遇伏击、准备逃跑的那场戏,倪则仁撞倒了准备离开的古谷时,摄影机开始猛烈快速地晃动,多个晃动的镜头被剪接在一起,手持摄影起到了很好的氛围烘托和情绪表达的效果。此时,手持摄影镜头模拟着置身枪战现场、手足无措的路人视角,四处晃动。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呼救的一句台词,也没有对人物的慌乱神情进行特写刻画,但晃动画面的堆叠却将片中人物慌乱不安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将案发现场的混乱可怖展现得一览无遗。片中手持摄影的运用,让隐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背后的人物情感和心理活动得到更好地展现,增强了黑白影像的表现效果。
(三)黑白摄影:极简主义风格
色彩是娄烨电影的重要审美手段,成为其影片表现人物情绪和凸显影片主题的重要载体。《苏州河》中,“红色”作为主要的意象反复出现,不论是牡丹的大红色外套还是美美假扮美人鱼时穿着的艳红色鱼尾都承载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在《紫蝴蝶》的低饱和度画面中,不断扑扇翅膀的紫色蝴蝶不仅增添了影片的朦胧美感,也成为重要的表意符号,暗示着辛夏、伊丹等人的悲剧命运;在《浮城谜事》中,画面在冷暖色调间不断转换,这两种色彩是对永照、陆洁、桑琪等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直接外化,冷暖对比交织的视觉表象背后揭示出的是他们被欲望扭曲的灵魂。
然而,在《兰心大剧院》里,娄烨导演却放弃了色彩,全部采用黑白摄影,以极简主义的视觉风格,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热闹景象和兰心大剧院的华丽精致的布景和服饰,融入黑、白、灰三种颜色之中。但色彩的简化,并不意味放弃对色彩的运用。相反,娄烨通过精准考究的光线设计,让照明与色彩充分配合,在画面中制造出强烈的明暗对比和丰富的空间层次,让黑白灰三种颜色物尽其用,发挥出奇妙的视觉效果。尤其剧院乱斗这场戏中,导演刻意将大部分画面都置于低曝光的黑暗状态,让环境中微弱闪烁的灯光和枪支发射时迸发的火光成为画面中仅有的光源。大片的黑色隐去了画面大部分内容,小面积的白色则格外显眼,强调出惊心动魄的枪火光影,黑白两色的强烈对照比彩色的色彩差异更醒目、更强烈,带出的视听效果与叙事内涵也更为扣人心弦。在这样的画面中,观众和剧中的人物一样,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现场的状况,并依靠声音和转瞬的光影来猜测黑暗中的情景。此时,观众的视点和剧中人物视点保持了一致,构成了内知觉视角,观众由此被地拉入到影片的叙事情境之中,缝合进紧张刺激的氛围里,开始与剧中人物共享命悬一线的窒息与焦灼感,同时通过黑白色的反差对比和明暗光影的配合,悬念感和紧张感被巧妙地制造出来。
整体上,全片在黑白摄影和胶片摄影的粗颗粒质感下,在寄寓情欲与暧昧、胶着智谋与暗战、浸润氛围与情绪的阴雨绵绵的意象呈现下,画面始终呈现出阴郁、晦涩的感觉,配合着贯穿全片的爵士音乐,被赋予了一种不同于好莱坞、但又呈现出“黑色电影”的质感,在银幕上精彩描绘出导演心目中的20世纪40年代初孤岛时期上海都市空间中的时代底色、特定氛围与悬疑效果。通过巧用敢用极简主义风格的黑白摄影,再加上以兰心大剧院和华懋饭店作为时代主场景无缝穿梭于现实与舞台,影片刻意模糊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线,对传统类型叙事实现了颠覆、重构与超越,形成了诸如镜像凝视般的多重叙事互文性。
实际上,《兰心大剧院》早就拍竣并在201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做过全球首映,但国内院线发行却因随后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拖延至今。
但好片不怕晚,这部影片无论就巩俐的表演艺术、还是娄烨的导演创作来说,都有着多维度、共通性的创新意义。第一,创作题材比较少见。影片将时间设定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设置四方特工暗战于多角纠葛与复杂拉锯,这种关涉抗战时期国际宏观视野、多重政治纠葛下的特工传奇故事,不仅是同时期同类中国题材电影中难得一见的,同时也具有美国二战题材隐在的东方传奇性,潜藏有丰富的戏剧张力与特定的历史想象。第二,以谍战类型为创作框架,但又进行艺术个性化挖掘。影片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逻辑起点,展开多方特工因特定的使命立场而展开隐秘的戏剧冲突,但叙事基调又不如惯常谍战片所见的那样正反二元对抗与界限分明,而尝试注入了复杂交错、暧昧模糊的多重政治情境与情感心理冲突,同时也突破常见的主流意识形态宣导模式,而更融入了身份认同、人性反思等深层内涵。第三,性别策略置入,女性电影为核。影片尽管整体上讲述的是特定宏观历史视域下攸关世界格局与中国命运的女性间谍冒险行动的故事,但创作重心却在于女性间谍的情感、心理与成长等内在动机,尝试以个体人物的内叙事来充盈人物关系搭建的强烈戏剧性的外叙事,从而为谍战片类型走向深处做出了有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