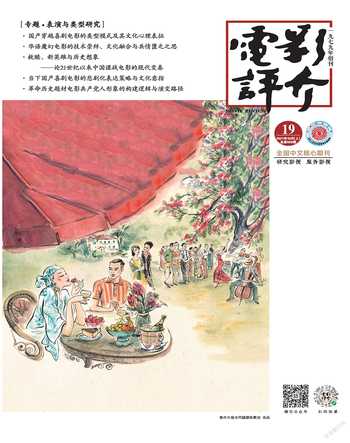由《1917》透析影像本体论中“一镜到底”叙事
2021-03-27王煜冯晓媛
王煜 冯晓媛
一、“一镜到底”与影像本体论
“‘一镜到底’,英文名为One-shot,是指用一个摄影机拍摄、在一个镜头内表现出整部影片,或者是通过后期剪辑加工让人感觉整部影片是一个镜头的拍摄手法,可分为真正的‘一镜到底’和加工的‘一镜到底’两种。”[1]其中,真正的“一镜到底”对拍摄技术、场景设置和演员表演都有较高的要求,其画面的连贯性也远超由多个镜头拼接剪辑后的效果,由此拍摄的影片的美学意义甚而可能超过本文所要表达的核心题旨;加工的“一镜到底”常被称作“伪一镜到底”,即借隐藏剪辑痕迹来使画面连接显出平顺感、一体感,它对于运动镜头的起幅和落幅有着严格的条件制约。
“一镜到底”因镜头是连续的(或要体现连续感),需在一个镜头内表达全部内容,故其在形塑人物、铺叙情节、时空转换等方面与多数由一系列镜头蒙太奇连接起来的影片有所不同,由此造成“一镜到底”文本自身的独特性,给人以流畅画面带来的沉浸式观影体验。“一镜到底”在电影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948年拍摄的惊险片《夺魂索》。其可谓最早的一部“一镜到底”影片,场景集中于一间房子,借演员背景黑幕进行转场从而给观众以连续的视觉影像。事实上,因为当时一卷胶片只能拍10分钟,所以严格地讲,《夺魂索》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镜到底”。自《俄罗斯方舟》(亚历山大·索科洛夫,2002)以真正的“一镜到底”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后,越来越多的导演尝试拍摄“一镜到底”的影片,如《鸟人》(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2014)、《维多利亚》(塞巴斯蒂安·施普尔,2015)等。
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影像本体论”认为,电影的影像是自动生成的,它与被拍摄物同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况且,作为摄影师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们的名称就叫‘objectif’。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对现象的解释中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在最终的作品中无论表露得多么明显,它与画家表现在绘画中的个性也不能相提并论。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2]基于此,安德烈·巴赞对通过大量镜头组接来渲染剧情、控制观众情绪、引导观众思考与导演创作思想趋同的蒙太奇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剪辑所创造的蒙太奇效果会破坏影片的时空统一性,而其对觀众心理的操纵实是对观众观影自由的束缚。他认为,电影是所有艺术门类中与现实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只有通过尽可能地再现“真实”,方能逼近电影艺术的真谛——“段落镜头”(俗称“长镜头”)乃是电影再现真实的一种最重要的拍摄手段,这种亦称作“镜头内部蒙太奇”的手法“能保持电影时间与电影空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表达人物动作和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符合纪实美学的特征”[3]。在本质层面上,“一镜到底”就是段落镜头的一种极致化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追求更为逼真的“真实”,即展现一个与蒙太奇所创造的“真实”大不相同的更为真实、客观的时空环境,进而给观众更多的观察角度和思考空间。
二、《1917》“一镜到底”的本事
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2020年执导的战争电影《1917》,据曾服役于英国国王皇家步枪团一营的导演的祖父阿尔弗雷德·H·门德斯的回忆录改编而成。故事的发生背景为1917年4月6日(一战期间)的法国战场。在德国与英、法两军激战时,两名年轻的英国士兵(准下士)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接到命令,需在8小时内穿过西部战线,向指挥官麦肯锡上校传达“立刻停止进攻”的命令。如命令传递不及时,前线的1600余名战士将会被敌人所设的圈套屠杀。因对前方战况一无所知,二人只能开启一场冒险。在布雷克牺牲后,斯科菲尔德继续前进,终在历尽千难万险后赶到前线,并在英军即将陷入巨大牺牲前停止了进攻。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颇有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意味——矛盾三线(撤退德军设伏、英军刚发起追击、斯科菲尔德刚赶到)并存,只是其解决方式不是用蒙太奇的切换,而是用“一镜到底”式的段落镜头予以呈现。
这部长达1小时58分钟的“一镜到底”式影片,由迪恩-查尔斯·查普曼(Dean-Charles Chapman,饰布雷克)和乔治·麦凯(George MacKay,饰斯科菲尔德)饰演主角,由罗杰·狄金斯(Roger Deakins)摄影,李·史密斯(Lee Smith)剪辑。《1917》摒弃了战争电影常用的宏观叙事与人性反思,亦没突出主人公的“主角光环”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而是聚焦军中的两个小人物,跟随他们的足迹,用“伪一镜到底”的影像实践来营造沉浸感,让观众与他们所认同的主人公一起完成一段艰难无比的“奥德赛之旅”——在看似线性简单的叙事结构下蕴含深刻的生存哲思。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Down to Gehenna or up to the Throne,He travels the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不论是下地狱还是称王,独行侠走得是最快的。)这是将军在给二人下达任务时说的话(这似乎也暗示二人最终会有一人牺牲),尽管这会对两人的情绪和心态产生影响,但这也为后文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
事实上,《1917》是首部采用“一镜到底”的手法摄制的战争题材影片,但其又是“伪一镜到底”的,即其乃由多个较长时值的运动镜头拼接而成,只是镜头间剪辑的痕迹被巧妙隐藏起来,从而营造出一种一气呵成的视觉流畅感。在某种意义上,“一镜到底”是呈现该片内核故事并产生感人效果的最佳方法,它让观众在100多分钟的观影过程中时刻与两位肩负大任的小人物同呼吸、共患难,体验独一无二的灾难性战争的现场感。也因如此,该片以数字技术与“伪一镜到底”的巧妙结合获得了巨大成功,斩获第77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并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三项奖。
三、《1917》“伪一镜到底”实施策略
实事求是地说,之于一部近两小时的影片,想“一刀不剪”“一贯到底”是非常困难的。也因如此,《1917》采用“伪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来实现美学上的追求及出乎意料的视觉效果。
(一)“一镜到底”的空间环境
1.以掠过战壕的段落镜头对比来展现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
《1917》开篇不久便再现了不少战壕的画面:全景画面中原本坐在草地上休息的两名士兵被另一士兵叫走,他们不停地穿梭在英军修建的战壕中。从草地到指挥室,从光线明亮的室外到光线暗淡的指挥室内,“一镜到底”展现了英军战壕的环境状况与士兵的精神面貌。以两个士兵为前景的画面引导观众的视觉运动方向,主人公逆摄像机的拍摄方向运动(摄像机处于后退反跟拍摄状态),在流畅的节奏中,后景或背景中依次出现正在吃饭或做饭的士兵、坐在战壕里休息的士兵、在战壕中运送物资的人员(此时摄像机与主人公同时停留在画面中,主人公不动,摄像机也静态拍摄),见到要带二人去指挥室的中士后,画面摇拍继而由倒退反跟改为正跟拍摄,即由拍摄主人公的正面转为拍摄主人公的背面。一直追随主人公连贯性拍摄的摄像机携着观众的“第三只眼”纪实性掠过的英军整体状况,为接下来不无“探险”意味的任务奠定了基础,暗示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紧张感及因士兵连日作战而弥漫的疲惫感、无助感,也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性及即将执行的任务的艰巨性和执行者作为攸关众多生命的关键信使的重要性。另外,段落镜头加景深镜头(辅以声音元素)的环境再现,也让人更客观地看到空间的全貌及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伤亡惨重的英军、被主人公踩踏过的英军尸体、写明毒气观察哨的標牌、烧焦变黑的木板、被炸倾塌的防空洞等,都为主人公和移动着的摄影机所亲历——英军战壕中的所见所闻颇为直白地展现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贪欲的危险。
同样,展现主人公穿越德军所建战壕时(此时德军已撤退),《1917》亦采用“一镜到底”。无疑,主人公置身德军战壕即置身险境,命运变得不可预知,观众的心理也随着主人公的艰难前行而剧烈波动。实际上,虽以超长段落镜头高度写实,但为缓解视觉与审美疲劳,影片还是增添了一些戏剧性色彩:在进入德军第二道战壕时,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发现了德军布下的可引爆炸弹的绊线,然就在二人庆幸发现及时之时,一只老鼠拖着一个装有食物的袋子碰到了绊线,随即引爆炸弹,二人不得不仓促逃离。显然,这一充斥幽默与戏剧性成分的段落暂时性改变了叙事节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众的紧张心理,自然也证实德军的撤离并非被迫,而是预设陷阱的以退为进。掠过英、德两军战壕的段落镜头也明示当时的时代背景:画面中的德军装备和战壕情形远好于英军,这恰与主人公所要传递的紧急命令相吻合——德军撤退到兴登堡防线之前,已在原防线与新防线间设置了地雷和狙击手,撤退只是其策略,准备追击的英军则面临惨重的牺牲。穿越战壕的画面多采用移镜头(多为纵移)、摇镜头(上下或左右摇拍)和跟镜头(正跟和反跟),保持了对战壕时空环境的完整呈现,同时交代了德军作为入侵方(德国为一战发起国)略强于英军的军事实力。
2.以“镜头内部蒙太奇”的场面调度来压缩空间
很显然,“一镜到底”难以像蒙太奇那样可自由打破影片内部的时间线和空间布局,它只能通过“镜头内部蒙太奇”即一个段落镜头内的场面调度来实现空间转换。对《1917》被隐藏的剪辑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主要实施了动作转场、遮挡转场和摇晃镜头转场,在给人“一镜到底”之感的同时,悄然压缩空间产生表意,强化中心意旨。在主人公从后方战壕走到前线战场时,即影片的10分32秒处,有个巧妙的以空间压缩来实现内部蒙太奇转场的处理:接到任务后,布雷克虑及哥哥的安全,便马不停蹄地往前走,斯科菲尔德紧跟其后;一段时间后,他们遇到一个黑色通道(穿过此通道,他们就可到达前线,然此又是一个很长的通道),于此影片实现了第一次蒙太奇转换,即以“黑色”隐藏剪辑点的手法实现难以觉察的空间压缩,将距离很远的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在25分50秒处,影片运用了同样手法将战壕和防空洞连接在一起,实现了空间的转场。
在某种意义上,电影是梦,或者说是制造幻觉的艺术。影片能借助受众的视觉幻象,来构建一种时间上的连贯感,既在显在文本层面保持时空的连贯性,又在实践层面降低拍摄难度。其实,也只有将段落镜头与场面调度有机融合,其语言意义才可能被最大限度地激活,或者说,才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更好地发挥写实表意功能。
(二)“一镜到底”的人物形象
事实上,《1917》“一镜到底”所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也使观众因认同机制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继而对人物形象塑造与接受有所助益。换句话说,因镜头语言的创新性铺叙,主人公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的形象变得更为立体,个性更为鲜明。
究其根本,接受任务且担心哥哥安危的布雷克奋不顾身地开始穿越冒险,可谓他看重亲情的表现;在防空洞里德军所埋炸弹被引爆后,他徒手扒开废墟救出斯科菲尔德,应是他重视友情的表现;在德军飞机坠落在他与斯科菲尔德的面前并燃烧时,他率先冲上并与斯科菲尔德合力将飞行员救出,继而在斯科菲尔德提议帮助重伤的德军飞行员脱离痛苦(结束其生命)时,布雷克却说“他需要水”——这是他善良的表现(尽管最后他被自己所救的人刺死)。对敌军伸出援手,昭示布雷克的反战思想。借诸多合情理的写实细节,影片塑造出立体的布雷克形象——一个善良的忠于亲情、友情但因自我“盲目的”善良而牺牲了的没有主角光环的主角。
较之布雷克,斯科菲尔德的形象更立体、丰满。从他掏出用布包着的面包分给布雷克一小块并说“我自有办法”时,展现了其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也符合他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身份);在进入德军战壕时,明知会有敌人观察哨和狙击手的他拦住了布雷克,说“Age before beauty(长者优先)”,则体现了虽是在布雷克的申请下自己被迫参加此次任务的他,依旧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尽管在他看来,承载无上荣誉的勋章有时还比不上一桶水,但在任务、危险面前,他也从不退缩)。布雷克死后,斯科菲尔德的人物形象有了升华,从厌战、被迫参加任务到对将要死去的战友强调自己一定会找到其哥哥并完成任务。之后,自我意识觉醒和肯定了自我行动价值的他,守着对牺牲战友的承诺与完成任务的决心继续前行,最终挽救了很多人(包括布雷克的哥哥)的生命。片尾,完成任务的斯科菲尔德坐在草地上,与片头他坐在地上的画面相呼应,无疑预示战争还在继续,牺牲还会存在,需要他完成的艰巨任务依然会有。
概言之,影片通过丰富的细节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鲜活而充实,给人呈现出忠诚、勇敢、善良的“平凡英雄”形象。不仅如此,在形塑人物的同时,“圣诞节”“休假”“火鸡”等令人渴望的物事言语也顺带出现在战壕中,与现实环境中的战争、死伤、苍蝇等物象形成鲜明对比,并在不无诗意色彩的视听表达中隐喻创作者的厌战与反战情绪;农场中的残垣断壁、空中飘落的樱花、横陈地上的尸体等也从多个方面展示出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令人深思、警醒。
(三)“一镜到底”的冲突呈现
毋庸置疑,《1917》属于剧情时间大于叙述时间的影片。它将一个限时八小时的任务浓缩进不足两小时的画面中,而且采用“一镜到底”的叙事手法,足见其展示剧情冲突(特别是主要矛盾冲突)之难,但亦具有不无挑战性的美学魅力。
片中最强烈的冲突在1小时37分处,垂直于发动进攻的英军前进方向的斯科菲尔德奔跑着去向指挥官传达停止进攻的命令。在长达1分钟的段落镜头中,顺利找到德文营的斯科菲尔德发现麦肯锡上校已经按原计划展开对德军的进攻(第一梯队已经攻了上去)。这意味着如斯科菲尔德没有将命令及时传递上去,将会有更多的人伤亡。影片在展示这一至关重要的矛盾冲突时,使用了俯瞰大全景,让人清晰地看到两个不同方向的奔跑:英军第一梯队从画右往画左跑(入画到出画),斯科菲尔德则从后景向前景跑(摄影机在他的前面正面俯拍)。大景别、小人物,以斯科菲尔德为画面主体,持枪冲锋的英军士兵作为前景和后景,画左连续的爆炸、纷纷倒下的士兵衬托出斯科菲尔德行动的紧急,整个段落一气呵成,有着非常紧张甚而令人窒息的节奏。
很明显,一群自东向西冲锋的战士,一个自北向南传递关乎冲锋士兵生命消息的人,不同的动作线(辅以惨烈的爆炸声响)明示了此刻的尖锐矛盾与复杂场景。一面是视死如归(为国向死,不得不为),一面是拯救生命(军务重大,战友所托),不同方向(甚至是“死”与“生”的相反方向)的交叉奔跑画面在诗意化呈现的同时颇有意味地完成了深刻的表意——暗示如命令被更快传达,第二梯队即可免遭战火,故斯科菲尔德快速的奔跑也应和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影片通过段落镜头的影像直观,既立体化了有着强烈冲突的战场,也凸显了影片的反战题旨。
四、“一镜到底”的利弊得失
一如《1917》的编剧克里斯蒂·威尔逊-凯恩斯(Krysty Wilson-Cairns)所说,影片初衷是让观众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活上110分钟[4]。因镜头始终跟随主人公的行动运动,观众便很难从他们之外(即空间距离超出画幅处)获得更多的信息,只能被主人公引导着一步步深入剧情,并获得一种沉浸感。当然,受众也会不自觉地将自我感受代入剧情,赋予主人公的命运以更多的关注。对主人公行动途中的所见所闻,影片多以布雷克和斯特菲尔德的主观视角予以展现,包括曲曲折折的战壕、战壕外面的死马及其身上的苍蝇、大大小小积了水的弹坑、弹坑中的浮尸、坑道中的老鼠、被德军毁坏的大炮、成堆的炮弹壳、烧焦的树林、摧折的樱花树、无人收养的奶牛、坠落燃烧的飞机、被焚烧的教堂、湍急的河流等,无疑都富有冲击力,并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亦象喻反战主题。可以说,“一镜到底”的战争残酷物语被普通士兵的友情和勇敢精神所包裹,残酷的现实境遇用唯美构图的画面来展现,流溢出不无“对立”意蕴的审美张力。加之流畅合理的叙事节奏,遂使段落镜头的美学功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掘空间叙事的无限可能性方面得以有效达成。
其实,《1917》“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不能简单地用纪实美学来概括,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引渡沉浸感的媒介。美国《综艺》杂志影评人彼得·迪布鲁吉(Peter Debruge)这样评价《1917》:它以电子游戏式的“一镜到底”审美实现了几近虚拟现实版本的事件呈现[5]。很明显,《1917》采用“一镜到底”完成了视听语言的游戏化处理(颇像《绝地求生》手游),给人一种在游戏世界中与队友对垒的感觉,兼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沉浸感。处于画面中心位置的人物引领着观众的视觉,其命运牵动着观众的心,残酷的环境成为主人公路过时不经意的所见所闻——這种也许是因习惯而熟视无睹所暗示出来的残酷自然,比刻意的描绘更触动人心。
“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也有局限,它无法对比性展示跨地域的更为宏阔的场景和跨度较大的历时延续,即使前后两部分的叙事转变(视点、结构、风格等),有时也难以铺垫与过渡,继而使受众在面对突然的叙事转换时产生视觉割裂感;为求得更强烈的欣赏沉浸体验,手持拍摄的镜头难免会有需要避免的晃动,遂使观影效果大打折扣。另外,若是忽视主题呈现的技术为先(如《地球最后的夜晚》),那所谓的“一镜到底”就更值得商榷。再者,就《1917》而言,观众面对仅有两个主人公的世界且整部影片都被两人引领时,他们的观影耐心能否经受住考验也是一大问题。
当然,因“一镜到底”操作起来较复杂,对场景设置、演员表演、摄影技术和场面调度有着较高的要求,具体实施时,创作者多会设计出若干剪辑点,利用剪辑特效和观众的视觉误差拼接多个段落镜头,最终达成“伪一镜到底”的视觉效果。鉴于题材和事件的独特性(《1917》据真人回忆创作,关乎生命与救赎的小兵传信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须恪守写实主义风格的《1917》采用“一镜到底”,既益于题旨彰显,亦可在镜头语言上进行颇有艺术价值的诗意探索。故而,用“一镜到底”展开叙事较之蒙太奇叙事,无疑会增加更多的客观性、真实感,主人公的亲历也会让受众自觉进行比较而深信画面呈示的战争的残酷与自我所处现实的美好,进而生出珍惜和平的期许。说到底,技术是为艺术呈现服务的,它所表现在视觉上的效果应具有意味或意义。即是说,对“一镜到底”的运用,或比之技术美学,契合影片题材、结构、风格、思想的整体叙事建构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吴婷.“一镜到底”的艺术特色[ J ].艺术科技,2016,29(10):124-125.
[2][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1-12.
[3]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5.
[4]Thelma Adam.Scripter Krysty Wilson-Cairns Broke Rules with“1917”[ J ].Variety,2020-02-03.
[5]Peter Debruge.“1917”:Film Review[ J ].Variety,201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