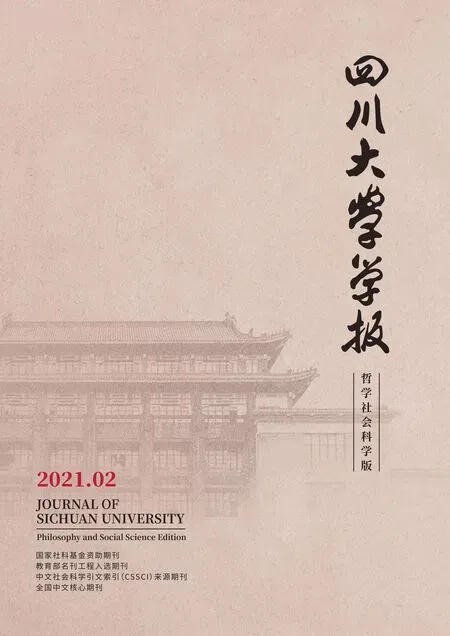日本近代神话观念与神话学:基于概念史的考察
2021-03-26高伟
高 伟
一般认为在东亚范围内,日本人最早接触西方的神话概念,并将“Myth”译为日语词“神話”(しんわ)。随后这个译词经由梁启超、蒋观云、王国维等人的使用而传入中国,因此日本是西方近代神话学传播到中国的重要媒介。(1)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6页;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9页。有研究试图通过“神話”这一词汇来追溯西方神话概念在近代日本的展开情况,并考察其被赋予了何种含义。如认为“在日语中,「神話」由两个部分构成,「神」(しん)又写作「かみ」,相当于西方的‘deity’或‘god’,「話」(わ)相当于‘tale’和‘story’,「神話」就是关于神的行事。由日文译介而来的‘神话’,其实是将「しんわ」(神話)与中国传统的话体文学(仙话、词话、话本、小说等文体)相对接”。(2)叶舒宪、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谭佳:《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45页。这种解释说明中文学术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神话学的萌芽与日本近代神话学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然而,通过日语词“神話”考究源流实际上存在一个预设,即“Myth”概念在近代日本一开始就被翻译成了“神話”。但这种预设是否符合事实?日本近代学者对“Myth”概念的翻译形态究竟如何?进而,当“神話”成为“Myth”的固定译词之后,其合理性是否受到过质疑?对于这些问题,日本学术界并不缺乏相关的历史性研究。比如天沼春树、大久保正、平藤喜久子等学者就曾从近代词汇翻译、近代《古事记》研究、近代神话学史的角度探讨过上述问题,为我们理解日本近代神话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各自的学术关注点而展开,“神话”一词的概念史意义和近代日本社会及政治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细致的梳理。因此,我们仍有必要从概念史角度对日本近代神话学进行考察。本文即尝试以明治时期(1868—1912)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重新检视以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imilian Müller)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比较神话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神话学的产生路径与展开情况,探究日本近代社会中神话在特定历史场域下得以发挥效用的原因,呈现西方神话概念与日本自身神话观念之间复杂的交互脉络。
一、麦克斯·缪勒的比较神话研究
日本神话学的诞生与展开贯穿着来自西方神话学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神话学流派众多,就日本神话学的形成期而言,19世纪比较神话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的自然神话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缪勒生于德国,后因任职东印度公司而入籍英国,且终其一生钻研印度的语言、社会、宗教和文化,并强调就这些方面的形态和起源而言,印度同英国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缪勒的理论是反种族主义的,因为他主张古代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征服给当地原住民“含米特”(Hamitic)等种族带来了文明,雅利安的武士和文化英雄的直系后裔是婆罗门,他们作为印度的上流种姓是英国推行文明教化的天然盟友。(3)Eric Csapo, Theories of Mytholog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 2005, pp.19-20.缪勒赋予欧洲文明以极高地位,因而如何解释希腊神话中的荒诞情节就成为他不可避免的课题。一方面,在他看来原本应该出现在野蛮部族的神话中的内容,比如“克洛诺斯吃自己的孩子,吞下石头,却吐出他的活生生的子孙后代”,这些“骇人听闻和令人厌恶的说法”几乎在“非洲和美洲的最低级的部落里”都找不到。另一方面,从古希腊自身的历史来看,正是在希腊神话形成后的两三个世纪中,古希腊诞生了“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伟人”。(4)以上参见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金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1、13页。希腊神话关涉西方文明源头,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种荒诞无稽的存在,无疑是缪勒的比较神话研究必须面对的。
在缪勒看来,神话中的不合理因素是语言对思想影响的结果,因而研究神名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他指出:“只要我们把传说中神和英雄名字的根本含义弄清楚,许多传说的内容就可以理解了。”(5)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通过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缪勒将希腊神话与《吠陀》神话进行神名上的对比。他认为印度人所崇拜的《吠陀》中的神“只是自然现象的不同名称”,神话不过是自然现象的反映,由此希腊神话中的荒诞情节也就可以合理解释。比如克洛诺斯吞下自己的孩子原本只是指“天空吞下又吐出了云朵”,“普洛克莉丝被克发洛斯杀死了”是指露水被太阳吸收了。至于神话语言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自然现象的隐喻,缪勒认为,这是“神话时代”(Mythological Age)或“产生神话的时代”(Mythopoeic Age)(6)缪勒将人类语言的历史分为“词的形成期”“方言期”“神话时代”和“民族语言期”。其中“神话时代”是尚未分化的雅利安人创造自己神话的时期。参见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第8-17页。的语言特性造成的,因为原始雅利安人的早期语言具有拟人化、隐喻化的特点,所以“人们在说早、晚、春、冬时,必然要使这些概念带有个体化、主动性、性别及人格这些特性”;只是随着神话时代的隐喻和语言原义被遗忘,新的意义应运而生,造成后世对神话的误解。缪勒将这一词源真义被遗忘和被误解的语言变化过程看作是“语言疾病”(disease of language),并认为这种“语言疾病”是在现代语言里依然存在的语源学本能。他的这种理论为“文明种族”的野蛮神话提供了相当巧妙的解释,因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大受欢迎。缪勒坚信神的原初概念总是太阳,(7)以上参见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第80、91、60、76、139页。并且不断将雅利安人的各种神话与太阳相联系,创造了所谓“太阳神话”(solar mythology)的解释模式。
但由于缪勒神话思想的崇拜者们将他的方法无限放大,比如乔治·威廉·考克斯(George W. Cox)认为雅利安人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所讲述的都是太阳与黑夜之间的角逐,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也是关于太阳的史诗。(8)Richard M. Dorson, “The Eclipse of Solar Mytholog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68, No.270, “Myth: A Symposium Oct.-Dec.”, 1955, p.406.因而这种解释模式很快受到人们的诟病,其中尤以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的批判最为激烈。与自然神话学派只依靠语言学分析的思路不同,兰格认为语言上的误解在神话的演变中影响很小,因为“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并非起源于语言,而是一个古老阶段的人类思想的遗留物”。那些现代人难以理解的、不协调的宗教和神话信仰及仪式,是从野蛮时代就一直存留下来的。对于当时的野蛮人而言,它们是事物理性秩序的一部分,是合理的,它们的存在也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9)安德鲁·兰格:《现代神话学·导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理论译丛》第一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32、131页。基于人类学视角,兰格反对缪勒的“太阳神话论”和“语言疾病说”,认为神话源于野蛮人认识世界的需要,是野蛮人思维逻辑的产物。在其与缪勒的反复论战下,缪勒的自然神话理论逐渐没落。正如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所指出的那样,缪勒学说的重大缺陷在于他只依靠语言学,而漠视了考古学、历史、美术对考察神话的作用。(10)Robert D. Richardson, Jr., “Friedrich Max Muller,” in Burton Feldman and Robert D. Richardson, Jr., eds., The Rise of Modern Mythology, 1680-186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82.尽管如此,缪勒的神话分析方法在日本近代神话学仍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二、日本幕末与明治前期对神话概念的理解
在西方神话概念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早已拥有自己的神话。日本神话主要记录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两书的神话又常被统称为“记纪神话”。但在近代之前,日本并不以“神話”一语来称之,而是多以“古史”“古傳説”“言い伝え”“寓言”“傳説”等词来指代,这些表达形式体现了多种神话观念。比如江户中期的儒者新井白石著有《古史通》(1716),书中提出“神即是人”的观点,(11)国書刊行会編:『新井白石全集』第3巻,東京:国書刊行会,1977年,第219頁。并将《日本书纪》的神代传说看作是真实历史的隐喻。稍后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在其《古事记传》(1764动笔)中认为:“外国因无古传说之缘故,故不知天之真实情状,只是一味空谈臆测之理。”(12)大野晋、大久保正編集校訂:『本居宣長全集』第9巻,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第123頁。江户后期町人学者山片蟠桃所作《梦之代》(1802)中也指出:“即便神学者,亦不相信但马、丹后、播磨以及其他地方的蒙昧传说。但对于神代卷,则深信不疑。”(13)山片蟠桃:『夢之代』,滝本誠一編:『日本経済叢書』巻25,東京:日本経済叢書刊行会,1917年,第198頁。
西方神话概念的跨境传播自然需要某种媒介。在幕末以前,日本虽曾流行过“南蛮学”“兰学”这些西洋学问,但主要偏于医学、天文学、地理等自然学科,与神话有关的西语词汇,如“Myth”“Mythe”“Mythos”“Mythologie”等,到幕末以后才通过编译的辞书在日本出现。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幕末与明治时期辞书中出现的与“神话”相关的词条可归纳如下表。(14)对于与“神话”相关的西语词汇在日本幕末(1854—1867)及明治时期辞书中的接受状况,日本学者天沼春树有详细的考察。参见天沼春樹:「神話概念の変遷Ⅱ:翻訳語としての『神話』をめぐって」上,『城西人文研究』第13号,1986年2月,第217-222頁。以此为线索,本文重新核查了辞书内容,并根据天沼春树此文制成本表。

辞书名及出版年词条与释义《法语明要》(1864)Mythologie:神教;Mythologique:神教的;Mythologist:神道者;Mythologyen:神道者;Mythologue:神道者《和英语林集成》第二版(1868)Mythology:神传、鬼神论《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9)Myth:小说物之类;Mythological :神学的;Mythologist:解释神的缘起的神学者;Mythologie:讲述异教之缘起的学问、神学《和译独逸辞典》(1872)Mythologie:制造无形之物的方法,解说异教之神缘起的学问、神学《独和字典》(1873)Mythe:讲释、故事之类《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Mith:小说、虚诞;Mythologic (Mythological):妄说的、神传的;Mythology:妄说、异教的神传《百科全书》(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1878)Mythology:鬼神志《法和辞林》(1887)Mythos:太古的逸事、虚妄、无事实《独和新辞林》(1896)Mythe:小说、诞言、鬼神谈;Mythologie:神祇志、神怪传、鬼神传
从上表可见,与神话相关的西语词汇在初传日本时并非一开始就被翻译成了日语词“神話”(しんわ),而是被表记为“小説”“昔話”“逸事”及“神伝”“鬼神論”“鬼神誌”等形式,其含义多与“虚诞、妄说”相关。绝大多数辞书的解释并没有结合具体的神话事例,只有187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例外,该书选译自当时英国的百科辞典《信息便览》(InformationforthePeople),其中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的神话,并分为“北欧鬼神誌”“羅甸希臘鬼神誌”(即拉丁希腊神话)和“蘇干地那威鬼神誌”(即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三部分。(15)天沼春樹:「神話概念の変遷Ⅱ:翻訳語としての『神話』をめぐって」上,第219頁。
课题日常监管由该课题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管理官员负责实施,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协助。课题监管主要通过审核报告、与受资助人保持联系、审计、检查原始实验记录、现场检查等方式实现。
辞书中出现的上述翻译形式,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理解西方神话概念应该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限于辞书的工具书特质,神话概念很难在有限的字数内得到充分展开。因此,相对而言,辞书中对神话的解说深度及其对受众的启发,不及同一时期涉及神代传说的著述。
在明治前期出版的神代传说著述中,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翻译家高桥吾良的《神道新论》(1880)。该书剖析了从开天辟地到日本神武天皇为止的传说中所隐含的意义。其中,高桥吾良在前两章首先批判了日本国学家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二书为神道之说的做法,他指出:“神典(记纪二书)之说并非神道,而是‘神传’。‘神传’之‘传’,与‘神仙传’之‘传’相同,即神之事业的传记。与英法等国所说的‘ミトロジ’(Mythology)同义。”在谈到神话解释方法时,他认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以某一假说来诠释各国神话的做法存在不足,提出应当仔细体察该国民众的性情与智力。在分析记纪中某一主题的神话时,他常征引外国神话作为参考,以此说明神话体现了对自然力量的拟人化和对历史人物的神格化。比如对于“日神”——天照大神,高桥吾良引用埃及神话中第一代国王被称为“天日”的缘由,以说明天照大神原本是上古某一部落的女主,因超群卓越而被当时的部落民誉为“天日”,后世之人又将其与真正的天日相混淆,于是便产生了天照大神的神话。特别是该书结论部分还提出了要崇拜代表自然之理的造物主。(16)以上参见高橋吾良:「諸教便覧、神道新論、仏道新論ほか」,島薗進、高橋原、星野靖二編集:『宗教学の形成過程第3巻』(シリーズ日本の宗教学4),東京:クレス出版,2006年,第3-4、43-46、71頁。由此可见,高桥吾良持有自然神论立场与比较神话的视野,他在解释日本神话时所展现的神话观念是西方神话学中的“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ism,又称“神话史实说”)。这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神话作家欧赫美尔(Euhemerus)的神话解释方法。该方法主张神话背后隐藏着历史,众神原是活跃于人类早期历史中的伟大人物。(17)Barry B. Powell,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Myth,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earson Education, 2001, pp.21-22.另可参见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
除《神道新论》外,明治前期另一值得关注的著述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该书将小说、野史渊源上溯到远古社会,认为当时的部族首领在荒蛮之境创业垂统,其非凡事迹在被后世子孙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由于传唱者记忆谬误或出于附会之心,始祖创业的情状遂渐失真,流为稀奇古怪的故事,开启了“鬼神史”“神代记”的渊源。此类离奇的神代史在各个国家都存在,促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三:其一,传唱者出于夸耀之心,对始祖之事添枝加叶;其二,人天性喜好怪奇,往往小题大做歪曲史传;其三,文明之世的子孙或耻于先祖起于卑贱,或出于尊仰先祖之情,遂将先祖视为“神”“天孙”。显然,坪内逍遥持有历史主义的文学起源论,故而他对神话性质的认识也带有“神话史实说”的倾向。他指出:“上古的‘ミソロヂー’(Mythology),即‘鬼神誌’,是‘奇異譚’(即传奇)的滥觞。……神代史虽然荒唐,但其本质与小说不一样,它记载的物语虽然本非完全的事实,但也很难说是虚构。”(18)以上参见坪内逍遥:「小説神髄」,中村完、梅沢宣夫注釈:『坪内逍遥集』(日本近代文学大系3),東京:角川書店,1974年,第52-53頁。这种认为神话包容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的观念,与高桥吾良的神话思想一样,同属于“欧赫美尔主义”。
概而言之,在明治前期,西方的神话概念与神话解释方法已经传入了日本。但从翻译形态来看,与神话相关的一系列西语词汇尚未以日语词“神話”(しんわ)作为它的表记。从解释方法上来看,高桥吾良的《神道新论》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所体现的是一种出现于西方古典时期的神话诠释思想,西方兴起的近代比较神话学理论,如缪勒的自然神话学说,此时尚未在日本登场。
三、比较神话学的传入及日本的神话解释之争
以缪勒的学说为代表,西方近代比较神话学在明治中后期至少沿着两条脉络传入了日本。其一是通过与缪勒有直接接触的日本学者,多数为赴英佛学僧。如1876年日本真宗大谷派学僧南条文雄、笠原研寿被派往英国留学,1879年二人师从缪勒学习梵语,共同研究佛典。南条文雄归国后于1885年在东京大学开讲梵语学,开启了日本近代印度学、佛教学的端绪。继南条文雄之后,1890年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也赴英国师从缪勒学习印度学和梵语,归国后亦在东大讲授梵语学。
除佛学僧之外,明治时期思想家井上哲次郎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曾赴英国拜见过缪勒。或受缪勒影响,井上哲次郎对日本神话的评价充满了比较的色彩。比如在《日本文学的过去以及将来》(1895)一文中,他认为《古事记》神话乃日本文学之丰碑,它保留了日本强劲的固有思想,在世界文学中亦难有与其相媲美者,“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仅可勉强与之相比”;并且强调《古事记》神话具有异于中国、朝鲜、印度神话的独特性格,即充满了“伟大连续之想象”“快活之气象”“纯洁之理想”,它“在世界文学中绽放一种特异的光彩”。(19)井上哲次郎:「日本文学の過去及び将来」,『巽軒論文 初集』,東京:富山房,1899年,第91-93頁。值得注意的是,井上哲次郎在该文中多次使用“神話”一词来指称《古事记》神代卷。部分研究认为日本近代作家与评论家高山樗牛所著《古事记神话研究》(1899)一书是首先使用“神話”这个术语的范例,(20)持此观点的研究著述例如有《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第93页。日本学者天沼春树也认为该词的出现不太可能早于1899年,参见天沼春樹:「神話概念の変遷Ⅱ:翻訳語としての『神話』をめぐって」上,第226頁。但就笔者目前所查证的资料来看,井上哲次郎189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应是最早使用了“神話”一词。恐非确论。
西方近代神话学传入日本的第二条路径是通过日本“一神论派”(21)一神论派(Unitarian)反对父、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观念(Trinity),主张神的单一性(Unity),认为耶稣不是神。1887年一神论经由矢野文雄介绍到日本。“普及福音教会”(22)1882年德国的自由派神学者们创立了普及福音新教传道会,该会传教士斯宾纳·威尔弗里德(Spinner Wilfrid)于1885年来到日本,接受其洗礼的二十多名信教人士于1887年在东京设立了普及福音教会,并发行杂志《真理》。等自由基督教派。比如一神论者岸本能武太在一神论派机关杂志《宗教》上发表的文章多论及缪勒的研究方法,其中《宗教的起源》(1894)一文明确指出:“著名的麦克斯·缪勒又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起源既非祖先崇拜,也不是物体崇拜,而是人想知晓无限——‘To know the Infinite’。……缪勒为了确证其学说,于是便诉诸历史上的事实。他说,人类最初的宗教是对山川植物等可感现象之崇拜,这种崇拜一变,成为对风雨雷电等时而可感、时而不可感的现象之崇拜;再变,则成为对此等现象背后存在的神力之崇拜。”而《我国神话中出现的植物与动物》(1896)一文中也提道:“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获得关于古代人民生活、社会状态以及宗教道德等的种种材料,于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无裨益。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中出现的神话时,将可以弄清高天原种族具有的种种观念,以及其社会状态。”(23)两文参引自平藤喜久子:『神話学と日本の神々』,東京:弘文堂,2004年,第9、10頁。该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缪勒,但其所主张的借记纪神话来考察高天原种族之观念与社会状态的思想,体现出受缪勒试图通过研究雅利安神话来弄清雅利安种族原始形态的方法和学说的影响。
西方神话概念和神话学方法通过辞书翻译、文学评述以及宗教研究等活动在日本知识界传播开来之后,经过酝酿,于1899年爆发了一场围绕“须佐之男神话”本质问题的论战。这场神话论战是日本神话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因为它标志着比较神话学作为一门学问在日本的开启。
“须佐之男”,又称“素戋呜尊”,是出现在日本记纪神话和《风土记》(24)713年在元明天皇的诏令下日本各地编纂的官修地方志,记载了地名的由来、传说、物产、土地状况等。现存出云、常陆、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但只有《出云国风土记》保存完整。中的神灵。《古事记》以其为天神伊邪那岐命之子、日神天照大神的弟弟,因大闹高天原而被驱逐到地下黄泉世界“根国”,并在前往根国的路上,于出云国(今日本岛根县东部)制服每年吞食少女的八岐大蛇救出了后来成为其妻的奇稻田姬。而在《出云国风土记》中,他被描写为温和的农耕之神。高山樗牛的《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及历史》(1899)一文则以须佐之男为暴风雨神,“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之间的争斗,从神话来看,乃是太阳与暴风雨在空中相竞。天照大神躲进天上的石屋,是暴风雨一时遮蔽了天日”,并明确指出《古事记》神代卷是“如同在雅利安诸民族中所见的,与天地开辟说相联系的太阳神话”。显然,高山樗牛的解说运用了缪勒的太阳神话说。正如该文标题所示,他认为《古事记》神代卷是神话与历史的混合,须佐之男途经出云国之前的内容是神话成分多于历史,此后“到神武天皇为止则变为了纯然的历史”,而这一部分神话说明的是“日本民族的起源及其迁徙的状态”:以须佐之男为祖先的“出云民族”和之后降临到日向高千穗峰(今日本宫崎县西北部)的“天孙民族”,最初的故乡都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汤加群岛附近;在迁入太平洋之前,二者“或恐栖居在东南亚细亚、或印度多岛海上”。其推论所据有四点:第一,《古事记》神话中与海有关的记述特别多,日本民族的祖先利用日本海流到达了出云或九州;第二,神代卷缺少北方的自然现象,而多海雾等南方物象;第三,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传说和《古事记》多类似之事,说明南太平洋古民族与日本民族具有某种关联;第四,印度吠陀神话与《古事记》神话存在相似点,如须佐之男作为暴风雨神与“因陀罗”(Indra)有相近之处,故须佐之男这样的暴风雨神应起源于印度。最后他征引缪勒关于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在亚洲大陆西南部的观点,推测日本民族是西南亚图兰人种(Turan)之一支。(25)以上参见高山樗牛:「古事記神代巻の神話及歴史」,松本信広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 : 民族学』,東京:平凡社,1971年,第87-88、95-98頁。
高山樗牛此文是日本第一次从近代比较神话学视角对《古事记》神话进行的学术探讨,故其刊出后很快得到关注。宗教学家、文学评论家姉崎正治于同年发表了长文《素戋呜尊的神话传说》,对高山樗牛的自然神话学观点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日本民族起源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须佐之男与吠陀神话中的“因陀罗”虽然在名称上含义相近,即都指“轰鸣”“行为粗暴”,但二者在神话与宗教上的意义不同:因陀罗是早先的天上最高主宰神“婆罗那”(Varua)的继承者,其最终成为了印度民族最高贵之神,这种关系表明印度宗教具有“一元的、统一的倾向”;而须佐之男与最高主宰神天照大神是对立关系,这说明了日本宗教的“二元对峙特色”。此外,《日本书纪》中记载须佐之男所种田地曾遭受旱灾,证明他不是暴风雨神,可知须佐之男在高天原的故事所反映的并非自然神话,而是“人文神话”。至于借助记纪神话来推测原始日本民族在人种上的起源,则是一种空想,因为形成于8世纪初的“记纪”已经受到了儒学与佛教的影响,它不是日本原始神话与宗教的直接反映,所以无法成为研究原始日本人的资料。进而,姉崎正治提出,当今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脱离语言学派神话学的影响,运用一般民俗学的方法才能避免自然神话论的这种弊端。(26)以上参见姉崎正治:「素戔鳴尊の神話伝説」,松本信広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 : 民族学』,第108-109、112、114-115、113頁。
高山樗牛与姉崎正治在神话解释上的对立反映了二者学问立场的差异。前者沿着缪勒的思路,重视由神名的语言解释来还原自然属性,并试图从神话来推断日本民族的原始形态与人种起源;后者则基于宗教人类学、民俗学观点,主张日本神话只能反映文本编纂前后日本社会的精神文化与宗教信仰,反对借此推断民族的发生史。在姉崎正治发表了对自然神话说的批判之后,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站在折衷主义立场也在同年写下《素尊岚神论》一文进行回应。他认为高山樗牛和姉崎正治二人对须佐之男神话的解读并不矛盾,二者能够同时成立。因为神话的意义往往取决于诠释者所采取的方法,某一神话既可以是自然神话也可以是人文神话。高山樗牛在主张须佐之男神话为自然神话的同时,也承认该神话中存在历史性因素。同样,姉崎正治也未否认神话中存在若干自然性分子。导致高山樗牛被批判的原因其实在于他所说的“完全的一部太阳神话”这一句,但姉崎正治似乎误解了“完全”之意。高山樗牛所说的“完全”,是指形态上构成了一部太阳神话,而不是指内容或性质上全部都是太阳神话。(27)高木敏雄:「素尊嵐神論」,松本信広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 : 民族学』,第148-150頁。
高木敏雄虽然对二者之论作出了这种调和性解释,但他也在文中征引了缪勒《德式工作坊碎片集》第四卷(ChipsfromaGermanWorkshop,1898)序言中论述比较语言神话学之根据的一段话,(28)高木敏雄抄译道:“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中,包含着可追溯到语言及思想之最古时代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经历了无数次意义的限定、醇化,但其最初具有的魔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参见「素尊嵐神論」,第143頁。来说明原本具有“自然性基础”的神格不论其后在神话中如何改变其性质与形状,其原初意义不会消失。须佐之男的自然性基础就是暴风雨神,它来源于居住在暴风带岛屿上的古代民族对暴风现象的人格化。高木敏雄通过考察日语“あめ”(ame)的含义,指出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的对立事实上是恒常稳定的“高天”与充满气象变化的“低天”(即对流层)之对立。这种自然现象的差别反映到人心上,则产生了以居于“高天”(即高天原)的天照大神为光明、清净、正义之象征,以居于“低天”的须佐之男为黑暗、污浊、邪恶之化身的神话叙事。(29)以上参见高木敏雄:「素尊嵐神論」,第142-144、157-159頁。可以看出,高木敏雄与高山樗牛一样也认可自然神话理论的立场,重视从语言角度分析神话中蕴含的自然要素。此后,关于须佐之男神话的讨论在高木敏雄和姉崎正治之间继续。(30)针对高木敏雄此论,姉崎正治发表了《评语言学派神话学兼论高木君的素尊暴风雨神论》加以回应,而高木敏雄又发表了《回应暴风雨神不可能说以明确本人立场》,两文参见《帝国文学》第6卷第1、2号,1900年。
四、神话论战的象征意义及近代日本神话研究的纠葛
1899年的日本神话论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也在于它的学术史意义。由于神代史涉及日本皇室的起源,因此神代研究在近代日本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早在1891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教授的久米邦武在《史学会杂志》第10-12月号上刊登了《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一文,对日本神道的源流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此文大意是:神道是东洋祭天古俗的遗留。它以天神之子为帝王,借助神意来裁断事物,开创了日本祭政一致的传统。神道的宗旨在于清净为先、忌避污秽,但也因此给社会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比如人死则以其屋不净而弃之。以神道古俗来决断讼狱,又相伴出现了残酷刑罚,比如“探汤”。(31)盛行于日本大化改新之前的一种占卜形式,用以决是非、辨正邪。据传当纠纷发生而是非正邪难以判断时,各方会对神发誓,然后将手放入沸水中。恶者会被烫伤,善者安然无恙。因此当人智渐开时,占卜问神式的神道祭政一致已不能安治天下。所以神道虽是日本创世立国的基础、皇统的根本,但古代天皇会根据时势进行变革。日本引入外来的儒学、佛教、阴阳道的原因亦在于此。特别是由于神道没有“诱善利生”的教典,佛教正好补足了神道在教导国民上的缺陷。可以想见,“若不以唐、韩诸国流行的佛教来开化人民,而专任缺乏教典的神道古俗,则恐怕日本今日仍停留在蒙昧野民之态,如同台湾生番”。(32)以上参见久米邦武:「神道は祭天の古俗」,松本信広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民族学』,第63-84、85頁。
久米邦武通过细致的文献考据,从宗教起源角度还原日本上古神道的风貌,旨在警醒当下神道要顺应时势、自我革新,而不是沉湎于中世以来的谬说。曾是岩仓使节团一员的久米邦武丝毫没有蔑视或否认神道与天皇制的意图。相反,他主张革新神道正是为了使神道焕发活力,由此巩固日本的国体。也正因为如此,《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一文不乏对日本优越性的赞美之词。然而,当此文1892年1月被面向大众的《史海》杂志转载后,却受到了神道家与国学者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久米邦武对天神实在性的否定,把皇祖视为朝鲜渡来人,称佛教使日本根基巩固等观点,构成了对皇室尊严的亵渎,有损国体。(33)倉持治休等:「神道は祭天の古俗と云へる文章に付問答の始末」,下田義天類編:『祭天古俗説辨明』,出版地点不详,1892年,第44頁。久米邦武在一片批判声中撤销论文,并被革除教授职务。这种状况表明,不论主观意图如何,以非传统观点对神代叙事进行学术议论,在当时是一项颇具风险的事业。
但到了1899年,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学者从神话学角度对日本神代的探讨并未招致官方的干涉。高木敏雄如此描述和解读这一年关于须佐之男神话的讨论:“明治32年乃日本神话学发生之年,神话学史上应铭记这一年。在这一年,论述日本古史神话者,有在国学院任职讲师的国学者高桥龙雄,有《太阳》杂志记者高山樗牛,有比较宗教学者姉崎嘲风(即姉崎正治)。而提供研究动机者,则是文明史家高山樗牛。其关于神话的论文,题为《古事记神代卷的神话及其历史》,刊于当年三月的《中央公论》。在五月的《日本主义》杂志上,高桥讲师将对此论文的详细批评公之于众,大力倡导神代史的自由探究。而神道家、国学者一派,对此却默不作声。即对于神代史的自由探究,至此得到学界的默许。”(34)高木敏雄:「日本神話の歴史的概観」,『日本神話伝説の研究』,東京:萩原星文館,1943年,第66頁。高木敏雄极力评价这场神话讨论的价值,将1899年视为日本神话学的诞生之年,并认为自由研究神代史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这场围绕须佐之男神话的学术论战确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在这场论战中,西方近代的神话理论——不论自然神话学派的观点还是人类学派的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这些日本学者运用了世界性的比较视角来解读日本神话,即在与印度《吠陀》神话、古希腊神话、中国创世神话的比较中来分析记纪神话,这说明西方近代神话学理论已正式与日本神话相结合,比较神话学作为一门学问在明治后期正式发轫。
不同于久米邦武的遭遇,这场神话论战并未引起神道家与官方的干涉,他们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其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从个人原因来看,高山樗牛、姉崎正治等人致力于文艺或宗教评论,其言论的影响力主要在文坛。而久米邦武当时供职于东京帝国大学编年史编纂挂——官方性质的修史机构。这一机构在久米邦武、安重野绎、星野恒等人的影响下,曾一度主张以科学实证主义来研究历史。他们推行历史辨伪与历史质疑活动,动摇了日本的传统史观。久米邦武作为这种“历史抹杀运动”的中心人物自然会受到格外的关注。(35)松本信広:「日本神話学の足どり」,松本信広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 民族学』,第4頁。其二,从内容方面来看,围绕须佐之男神话的论战并未直接触及神道的弊端,也未批判或否定国粹主义式的“神代精神”,这与久米邦武之论对神道家的刺激是不一样的。其三,从思想环境来看,自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更加注重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加速发展资本主义体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亦随之兴起。虽然在思想上明治政府对民众的国家主义控制依然在加强,但神道界的传统主张已无法适应国家的发展方向。面对上述新思潮,神道界此时已无力应对。(36)大久保正:「近代の古事記研究」,久松潜一編:『古事記大成1』,東京:平凡社,1994年,第138頁。因而,对于这次神话论战神道界与官方采取了“默许”态度,日本知识界在神代史研究上暂时获得了自由。
然而,日本的近代神话学确立之后,其发展依然曲折。西方神话概念和日本文化语境的适配问题、神话信仰与人类理性的纠葛等矛盾贯穿于日本近代神话学的展开过程。
“神話”(しんわ)是否为“Myth”“Mythology”在本土语境中的最佳翻译,当时的民俗学者对此表现出相当审慎的态度。比如南方熊楠在其《十二支考》(1914—1923)、《神社合并反对意见》(1909)等著述中极少使用“神話”一词,而是采用了“神誌”“鬼神誌”“譚原”“起因譚”“口碑”“神伝”等多样化的表记方式来称述神话概念。(37)南方熊楠对于“Myth”“Mythology”概念的多样化表述,可参见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全集』,東京:平凡社,1971年,第1巻,第93、285、296頁;第7卷,第502頁;第8巻,第512頁。在学术上与南方熊楠交往甚密的柳田国男也指出:“《古事记》《日本书纪》中记录的日本古代口头故事,在本居宣长一系的国学者那里一直被称为‘传说’,他们并没有以‘神话’一词来命名。”(38)柳田国男:「口承文芸史考」,『柳田國男全集』第16卷,東京:筑摩書房,1999年,第380頁。折口信夫从日本的信仰与文学的关系出发,指出以神学宗教为背景的“说话”才是神话,古代大和人的口传叙事应该称为“物语”。(39)折口信夫:「古典に現れた日本民族」,折口信夫全集刊行会:『折口信夫全集』5,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93-94頁。后来他以基督教神学神话为比照,断言:神话是神学的基础,没有神学的地方就不存在神话。日本没有神学,故而没有神话,只存在“众神的物语”。(40)折口信夫:「宮廷生活の幻想」,折口博士記念会編:『折口信夫全集』第20巻(神道宗教篇),東京:中央公論社,1956年,第41-42頁。
以上日本民俗学者的这些思考表明,与高山樗牛、姉崎正治、高木敏雄等人不同,他们没有简单套用西方神话概念来统摄日本的上古传说,而是注意阐明日本自身的传统。这种差异反映出日本近代的神话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重世界性,另一种是重民族性。亦即对于日本上古传说,是应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神话之比较来揭示其蕴含的人类早期普遍规律,还是应该努力挖掘日本神话中暗藏的本国固有特性。高山樗牛、姉崎正治、高木敏雄等早期神话研究者多致力于通过比照世界神话使日本神话获得普遍价值,其后的民俗学者则更强调从自身传统来诠释本国神话的内涵。诸多学者在神话概念上反复沉吟,说明这不单是一个翻译技术上的操作,而是关涉在何种体系中确定日本传统的意义这一重要命题。
近代日本神话研究中的另一张力是神话信仰与人类理性的矛盾。评论家森鸥外在一篇名为《仿佛》(かのように,1912)的小说中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神话的复杂心情。其中写道:“接受了现今的教育,我们无法再将神话和历史等量齐观,……无法把神话作为事实来看待。然而当我们清楚区分神话与历史时,祖先以及其他神灵的存在成为了疑问。这种思考再向前推进则面临巨大的危险。”(41)森鴎外:「かのように」,小林秀雄編:『現代日本文学館』第1,東京:文芸春秋,1967年,第138頁。这段话表明,经受过近代知识洗礼的人,由于开启了近代式理性而很难再将有违事实逻辑的神话本身等同于历史。但由于近代日本的立国精神植根于记纪神话,(42)近代日本的这种性格从明治政府在幕末维新期颁布的法令条文可窥一斑,如“诸事基于神武创业之始”(《王政复古大号令》)、“体认敬神爱国之旨”(《三条教宪》)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神代世界观自然不容许被公开质疑,于是便出现了《仿佛》中主人公所抱有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可以解释为一种学术良知与国家信仰间的冲突,即“言明神话非历史乃良心之所命”,然一旦某人公开表明神话不是历史,则会被视为持有危险思想,“人生之一角将走向崩坍”。(43)森鴎外:「かのように」,第143、149頁。数十年后发生的津田左右吉事件正印证了这种担忧。(44)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等著作中论证了记纪传说是人为制作的神话,指出其编纂意图在于说明天皇统治的合理性,由是在1940年被日本右翼起诉为“亵渎皇室”。
日本近代国家的神权性格决定了其神话研究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随着日本扩张主义的膨胀,当天皇权威需要急速强化时,神话研究的自由会被进一步压缩。神话研究要么因其见解不利于官方现时举措而横遭干涉,要么它主动迎合时政所需,为日本的东亚侵略摇旗呐喊。后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岛悦次于1942年所写的《大东亚神话》。该书序言清楚表明了其写作意图,即通过考察“东到夏威夷、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天地开辟传说”来论证“日本以大东亚指导者自居并非偶然”。书中提出要以日本神话为纲统合亚洲神话,使亚洲民族确信其各自信仰的对象“名虽异而实为同一神”,本体都是日本神灵,从而增强亚洲民族对神道和日本指导地位的认同。(45)以上参见中島悦次:『大東亜神話』,松村一男、平藤喜久子監修:『神話学名著選集』9,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年,第3、214-222頁。作为神话学者,中岛悦次早期著述,如发表于1927年的《神话》一书,只是从比较神话学角度对神话研究史进行了通识性的说明,主张日本神话研究要“根据时代的文化程度给出恰当的合理解释”。(46)中島悦次:『神話』,松村一男、平藤喜久子監修:『神話学名著選集』5,第503頁。而《大东亚神话》则一反其当初的学术态度,使日本神话学服务于日本的殖民侵略。
结 语
如果说近代神话学的确立宣告了理性主义在人类思维中的一种胜利,那么反观日本近代的神话观念与神话学,其轨迹则似乎在警示我们,叙事荒诞的神话在特定历史场域下依然可以影响那些自诩为已经“文明开化”的群体的行为。日本当代神话学家大林太良曾指出:只有当神话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距离,神话与人之间变得疏远,人们对神之信仰动摇时,才能够或多或少地客观审视神话。他还断言,“神话之研究与神话之没落是同时开始的”。(47)大林太良:『神話学入門』,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2-3頁。然而事实上,神话从未远离过日本社会,即便当下的日本亦是如此。(48)关于当代日本的“神话化”现象,可参见磯前順一:「祀られざる神の行方——神話化する現代日本」,『他者論的転回:宗教と公共空間』,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6年,第102-169页。甚至研究神话的神话学本身亦有可能变成神话日本的“神话”之一。
日本社会缘何产生这种神话症结?若干研究已经提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比如日本存在的借助神话表现民族意识的思想传统,皇室祭祀(天皇)与日本公共性及国民身份建构的关系等。(49)相关研究,如島薗進:『国家神道と日本人』,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磯前順一:『記紀神話と考古学:歴史的始原へのノスタルジア』,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09年;磯前順一:「祀られざる神の行方——神話化する現代日本」;以及高伟:《日本中心主义书写与中国神话研究——基于对日本近世国学神话论的考察》,《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第1-42页。这些思考并没有直接向神话文本本身询问日本神话的“魔力”,而是把目光放在不同历史空间对日本神话的容受方式上。只有通过历史性的回顾才能更好把握日本神话“生生不息”这一特性,以及它以何种形态唤起了日本人的内在情感。本文对日本近代神话观念和神话学的概念史考察也是此种思路下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