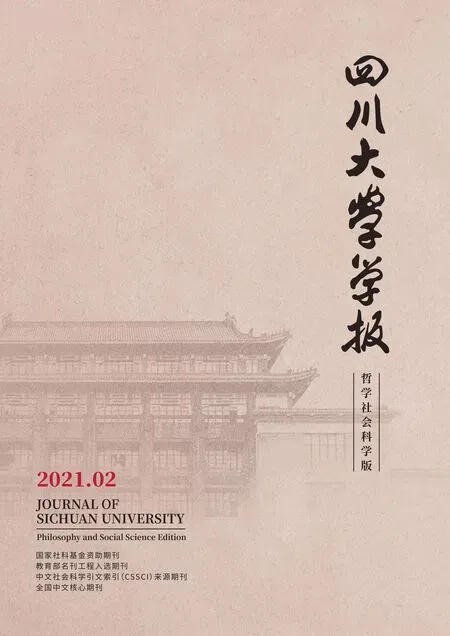清代“依法裁决”问题的再研究
2021-01-07邓建鹏
邓建鹏
一、引 言
近四十年来,随着清代司法档案进一步开放,传统司法的性质受到海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有法律史专家谓,古代主审官在处理纠纷和案件——尤其是所谓“州县自理”案件时,法律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州县官可以依据每个具体案件不同情势作出不同判决,无须顾及不同判决所确立规则之间的连续性和逻辑的一贯性。(1)贺卫方:《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展开》,何勤华主编:《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4页。这一见解后来被概括为传统中国属于“卡迪司法”模式。在2006年前后,众多法律史专家再度针对中国传统司法判决是否具有确定性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张伟仁认为,大致而言,中国传统司法者处理案件时,遇到法有明文规定的事件都依法办理;在没有法或法的规定不很明确的情形,便寻找成案,如有成案,便依照它来处理同类案件。许多地方档案及地方官的审判记录都可证实此点,极少见到弃置可以遵循的规则不用,而任意翻云覆雨的现象。(2)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第61页。高鸿钧认为,中国传统司法基本属于“卡迪司法”,尽管贺卫方关于古代法官“任意翻云覆雨”的措辞有些夸张,但他关于“卡迪司法”的判断是基本成立的。(3)高鸿钧:《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05页。围绕这个主题,近年来其他学者展开诸多争论,并成为法律史研究领域持续的热点。(4)汪雄涛:《明清诉讼中的“依法裁决”》,《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第83-100页;汪雄涛:《“情法两尽”抑或是“利益平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第29-37页;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和实质化》,《政法论坛》2007 年第2 期,第39-76页;徐忠明:《明清时期的“依法裁决”:一个伪问题?》,《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第31-39页,等等。黄宗智同已故日本著名法律史学者对此问题的激烈交锋,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重版代序”第6-9页;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民事法源的习惯》,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笔者认为,相关争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首先,“传统中国”跨时久远,在历史的长时段,司法实践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泛泛争论传统时代是否依法裁决,容易忽略法制的重要细节,使争论焦点流于空洞。其次,一些论者探讨传统中国“依法裁决”问题时,甚至直接以近现代西方概念(比如“罪刑法定”)作评判标准,这种源自不同时空的非对称评判,构成对传统司法的苛求。最后,一些争论和研究缺乏对案件裁判类型化的辨析。长期以来,针对不同案件,不同级别官员的裁判权限、裁判依据多存在差异。
为此,笔者以清代司法为具体对象,重新思索“依法裁决”问题。自王朝司法体制观之,诸如清代案件类型实质可分为两大类:“词讼”与“案件”。“词讼”大致类似今天的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及刑事自诉案件,此类案件通常由州县官自行审理结案。(5)邓建鹏:《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与实践》,《法学家》2012年第5期,第115-130页。据其与王朝政治利益的紧密程度,“案件”可细分为两类——政治性案件(直接涉及统治者利益的案件,诸如谋反或文字狱等)与命盗等重案。这些案件审理时据司法体制需要,通常应历经上级审转覆核。但是,两类案件是否严格“依法裁决”,存在很大差异。司法审判的类型化有益于深入讨论“依法裁决”问题。
二、“词讼”与“案件”依法裁决的差异
对地方官而言,严格根据《大清律例》条文规定“依法裁决”自理词讼,并非制度与实践的必要。地方官职务重点为听讼与维持治安,他们从行政事务的角度处理原本就不必向上级审转覆核的自理词讼,重点是解决纠纷、平息争执、稳定秩序,刚性地诉诸法律恰可能于事无补。对地方官员而言,通常只要在方式上有利于解决争讼,则没必要严格照规则办事。在地方官的司法实践中,受政务处理目标影响,对轻微刑事案件甚至一些命盗案件,州县官都有可能以应对自理词讼的方式解决之。
以山西省交城知县、循吏赵吉士的司法实践为例。康熙十年(1671)四月十五日,赵吉士呈本省按察司的详文称:已被革职的蠹役田福“棍违令把持,非奉宪不敢拘审,伏乞严批究拟”。按察使批复:“仰县严拿究拟,报司以凭,报院尽法。”四月二十四日再度收到详文后,按察司指示赵知县:“田福率领多人打伤张育初,本犯具有保辜,应俟限内有无伤毙,再行报夺。”对知县的第三次详文,按察司批复:对田福“拟追赔、刺配,于例是否允协?至高朝等三案,查俱赦前旧事,仍议究追捡抵,于律是否妥确?仰县再行详审”。至六月,按察司第四次批复知县详文:“事关赃私人命,仰县详请抚宪(即巡抚)批示定夺。”七月初,巡抚批示知县:田福“自应从重律拟,又奚烦多口之交攻乎?但拟以抢夺刺配,似犹未妥。夫所谓抢夺者,志在财物。今(田)福因不为说情之,故迁怒于必颺,遂乘其悻悻之忿,纠党入室,思欲得必颺父子而甘心焉,与抢夺者有异。若夫掯诈高朝、张三珍二案,情固可恨。犯在赦前,查赦款内开有:‘以赦前事讦告者,不与审理,即以其罪罪之。’今断追赃免罪,是否允协?……仰按察司覆加严讯,确拟妥招报夺”。最后,此案首犯田福在狱中自缢,其他从犯网开一面而结案。(6)赵吉士:《牧爱堂编》,郝平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7-133页。对田福案,知县、按察司和巡抚往返的公文讨论核心实为两部分,一为两名上级要求知县确查案情真相和细节;二为讨论田福罪行的法律适用和定罪问题,包括适用辜限的规定,罪犯主观意图与律例中规定的抢夺是否一致,赦前的犯罪行为是否仍要援引律例定罪。在清代前期,有官员明确指出:“拟罪全凭律例。律乃一代之典章,例为因时之断制。故有例须照例行,无例方照律行。例律俱无,则用比照法。凡有比照,须活拟上请,不得径清断决。”(7)潘杓灿:《刑名章程十则·问拟》,清康熙四十三年重刊本信编本,杨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乙编第九册,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47页。综此,命盗等重案纳入向上级汇报与监督的“射程”,则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拟判中的情罪是否允协等成了上下级讨论焦点。这在赵吉士上报的其他刑事重案的详文中,亦多有体现。(8)赵吉士:《牧爱堂编》,第120-121、123-124、134-135、170-175、190-194页。由此可见,此类案件的审理强调以法为据,律例绝非可有可无。(9)赵吉士审理的自理词讼或轻微刑事案件,一方面不必向上级请求批示,另一方面可全权量予责惩当事人,律例仅起参考作用。参见赵吉士:《牧爱堂编》,第201页。
在个案裁决中,一代名吏徐士林(雍正朝前期曾任安庆知府)的司法实践具有代表性。针对上控到知府衙门的自理词讼,比如“李廷桂违约争田案”,徐士林裁决“李廷桂背父强赎,徐孔彩抗官无状,均应惩戒,姑念二生年俱衰迈,均从宽免。”(10)陈全伦等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272页。对“张有声主婚强卖案”,徐士林裁决“张如芳代立婚书,并强抢之胡杰士,强媒之操义三,各予重责,以儆悍恶。张有声所得财礼银一两四钱,追出入官公用”。对“冯孟读私找田价案”,徐士林“故念(冯孟读)俯首认罪,从宽发学,戒饬以儆。……袒复捏议之徐翠、刘青,一衿一贡,扛帮兴讼,必非善类,仍候访夺”。(11)陈全伦等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第281、313-314页。对这些自理词讼,在程序上徐士林不必将之汇报给更高一级,只要当事人不继续上控,案件裁决至此结束。在裁决方式上,他重在辨清事实,依据时人认可的道理,定出裁决。律例并非其参考重点,就算偶尔查照律例,也可以独立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宽免李廷桂、徐孔彩等人)。
但是,如果涉及命盗等案件,审理程序及是否依法裁决方面,情况显著不同。比如“合肥县民鲍于天打死万君禄案”,徐士林明确依据“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时”律勿论,裁决鲍于天免于刑事惩罚。“桐城县民妇余阿潘控武生章正晖案”源自徐士林向安徽巡抚呈送的公文。对本案,徐士林提出:“金阿潘诬告之罪,照律移坐伊子。金燕升本应按律坐拟,姑念母瞽兄亡,情实可悯,……从宽满以儆。武生章正晖,……毁埂伐树,又复诬告挖骨谋命,亦应律拟,但念被诬搪抵,……可否从宽咨革,满杖发落,恩出宪裁。检验不实之仵作魏先,依律杖八十。……是否允协,拟合详情宪台核转。”(12)陈全伦等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第39、44-45页。以上均属刑事案件,被纳入审转覆核流程中,徐士林只是严格依据律例,在国家允许的幅度内,适当提出变通的裁决意见(比如“从宽咨革”)。但是,他并没有做出生效裁决的权力,而是等候巡抚作出指示。(13)类似案件的裁决,另参见陈全伦、毕可娟、吕晓东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第49-51页。
与上述两位奉公守法的名吏不同,如果命盗重案不进入上级监控或审转覆核的“射程”,州县官可能并不引用法律为裁判依据。偶尔摘引某些律例,为州县官强制当事人接受解决争端的方式。比如,黄岩县知县针对可能存在“人命私和”这种严重的刑事重案,都可以以刑事惩罚作威助,根本不予以彻查,迫使当事人徐罗氏撤案。(14)相关实例研究,参见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00-101页。州县官处理案件时,遇到法有明文规定的事件时,未必依法办理;在法无明文时,更未寻找惯例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州县官在司法中主要是分清事实与是非,找寻结案捷径,他们在裁判时是否引据律例、情理或参酌其他因素,以是否有益于实现此目标为考虑重点。
当案件当事人上控至府道,或案件由州县官提交,进入审转覆核体系,通常意味着进入正式受上级(府道、督抚、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以及皇帝)审核、督查的渠道。对案件的裁判,地方官较为认真谨慎,或倾向于援法为据,否则,自身可能因胡乱审判招致“官司出入人罪”,而被上级批评,甚至追究法律责任。正如有学者以台湾淡新档案为例指出,一旦地方衙门所受理的案件呈报至上级,则正堂遵从律例为堂谕的可能性即大增。(15)王泰升等:《论清朝地方衙门审案机制的运作——以〈淡新档案〉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六本第二分,2015年,第454页。比如,针对“谢鸿等互控建闸案”,知府徐士林批评原审知县断案“草率游移,难成信案”;在“王西士等互争棉地案”,徐士林指责初审知县“偏执谬断,反责西士改契占夺。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何以服民心而平争讼”;在“徐天禧捏造文册案”,“前宪董实系失于觉察,已奉部议降抵”。(16)陈全伦等主编:《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第300、307、57页。另外,上级对州县官的命盗案件的事实审理还可能提出质疑,要求其重审。比如,光绪十二年(1886)湖北省按察司针对本省竹山县申转的“柯进维殴杀大功弟柯进升”一案,认为县令的审理“互相岐异,未便率转,致干驳诘。应就近委员覆审明确,以成信谳”。(17)《清臬署珍存档案》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226页。上级的类似质疑与司法监督,加剧了州县官的压力,潜在影响官员仕途,限制其审转命盗案件的动力。
此外,若依据法制要求,应拟徒罪及以上刑罚的罪犯向上申送,将增加州县衙门大量财政负担。有学者从淡新档案的命盗案件文书与《福建省例》相关条例等的研究中发现,道光后期以来淡水厅等地方官府对覆审程序的漠视,不仅因为官员玩法或者上级官府缺乏监督机制,而且随着地方社会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犯罪活动的增加,清代原额主义的行政与财政体制未能随之有效扩张,因此地方官府并无负担覆审程序有效运作所需的行政人力与财政花费。地方官府为了节约地方治理的财政与人力成本,不得不尽量减少解审人犯,并简化一般性的审判活动。(18)林文凯:《清代到日治时代台湾统治理性的演变:以生命刑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会史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本第二分,2019年,第342页。清朝建立后,一直未对地方司法拨付相应经费,这笔费用往往由各地自行筹设。
比如,清前期文献指出:“徒罪详臬司,驿传道定驿原差批解,取该管官收管申覆,流罪详抚院达部。其路费有出本犯者,有出里递者,各处不一。解役须于原差之外,再添一名赍批同行,此系长解,不可独累一人。须令合役议出贴费,大约于各役工食中扣给为便。”(19)潘杓灿:《刑名章程十则·发落》,清康熙四十三年重刊未信编本,杨一凡、刘笃才:《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乙编第九册,第93-94页。这表明,当时差役长途解送人犯,费用要么由罪犯自行支付,要么在州县官统筹下,令差役共同承担。而差役提供的经费,往往多向民间勒索而来。论者谓,清代命案相验时的车马工食、搭建棚厂、应用器物及随后招解人犯等项开支不菲。这类经费非从财政列支,而多由民户摊派。这种费用摊派和敲诈勒索交织,民众苦不堪言。(20)黄鸿山:《善堂与恶政:清代江浙地区的命案相验问题及其应对》,《清史研究》2015第1期,第171-181页。迟至光绪年间,湖北省按察司指出:“照得命盗等案,一经获犯,例有定限,不容稍涉迟逾。乃近阅各州县详解案件,率多迁延。……查访其故,闻因解案一起,需钱百数十千,难以筹备。并闻原役筹费,或于本案或别案牵累无辜,使之帮助解费。每致良善倾家,种种弊端。”(21)《清臬署珍存档案》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3-4页。受制于有限的财政,州县官将案件纳入审转覆核体系的主动性很有限,这导致州县层级重在平息问题,依法裁决的案件比例不高。
学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半叶的台湾新竹县,严重挑战治安、理当进入疏防、审转与审限的稽查机制中的案件,却常由正堂在厅县衙门现场,自行将事处息。清代台湾地方官对于案件是否审转,有相当大的裁决空间,并非自始即被特定的规则所拘束,使案件的处理确定地分流。正堂以尽量轻判、使用非刑名处置方式、或不处理纠纷中的暴力行为等即可回避审转。(22)王泰升等:《论清朝地方衙门审案机制的运作——以〈淡新档案〉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六本第二分,2015年,第441、445页。以州县司法档案为基础,美国的法律史专家苏成捷发现地方官审理的175个涉及“买休卖休”的堂断里,几乎有一半左右的裁断违背了该律。但在刑科题本中所发现的清代司法图像与县级档案一般审判案件中的不同,刑科题本里每一个犯行都有精确的认定,并与大清律例里面的律或例一一对应,同时据此断罪。地方官府一般审判案件与刑科题本案件的比较,提醒我们大约1500个负责初审的地方官府与在帝国首都司法系统顶端的官府之间审判模式的重大鸿沟。(23)苏成捷:《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 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林文凯译,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361-367、375、390页。刑部直面皇帝监督的巨大压力,与州县官的审理思路不同。胡祥雨认为,刑部受理北京的案件时,明确区分民事与刑事(包括轻微的)案件,并且仅对刑事案件严格依法裁决,不管多么微小的刑事案件,都适用清律处刑。民事案件尽可能由当事人自行解决或寻求社区调解。(24)Hu Xiangyu,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A Study of ‘Civil’ Cases Handled by the Board of Punishment in Qing China”, in Modern China, Vol.40,No.1,2014,pp.74-104.
命盗案件审理是比较专业的司法程序,皇帝综理万机,通常认可专业人士的拟判意见。王志强认为,清代皇帝高度依赖各级司法官僚,其驳改刑部等机构拟判的数量和程度都相当有限。他初步统计《刑案汇览》近5000件案件中,有86件涉及刑事处罚的案件,上奏后经过皇帝驳改。“在清代命盗重案的处理中,普遍存在着形式上‘依法裁决’的情况,而真正具有疑难情节、需要运用典型的非规则型法机制加以个别处理的,在清代刑科题本中比例其实相当低”。(25)王志强:《“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67页。清代律例馆全士潮等纂辑的《驳案新编》收录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末年近六十年间驳案318件,均系刑部奉皇帝谕旨指驳改拟及奏准通行的定例。(26)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七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皇帝对普通命盗案件的处理,相当大程度倚赖并尊重地方督抚与刑部的拟判意见。论者谓,《驳案新编》所收总共三百余件命案中,皇帝推翻刑部判决作出改判的只有28件,占全部案件的1/10都不到。(27)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19页。美国学者认为,清代刑部审判程序具有制度化、合理化特点,忽视原则而任意断案只是极其个别的例外。参见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
俞江认为,刑科题本表明,各级官员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尚未有敢于抛开律例或背离律例去拟律者。重大命盗死刑案件如此,次一等的减流案件等也莫不如此。关于清代官员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可以恣意妄为的观点,是一种想象的产物。(28)俞江:《论清代九卿定议——以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为例》,《法学》2009年第1期,第145页。这正如亲历者、在刑部任职多年的沈家本谓,道光中期前,“刑部遇有疑似难决之案,各该司意主议驳,先详具说帖呈堂。如堂上官以司议为是,由司再拟,稿尾分别奏咨施行。若堂上官于司议犹有所疑,批交律例官详核,馆员亦详具说帖呈堂。堂定后仍交本司办稿,亦有本司照覆之稿。堂上官有疑而交馆者,其或准或驳,多经再三商榷而后定,慎之至也”。(29)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24页。这表明刑部处理疑难案件,或不同官员对案件存留争议,有一整套应对流程,非常慎重。不过,刑事案件依法裁决,前提是命盗重案被纳入审转覆核体系,置于高层官员及皇帝监控之下。
三、政治性案件裁决的特殊性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对华夷之辩、反清复明之类的话语非常敏感。清朝前期大量涉及此类问题的政治性案件中,以文字狱居多,另外还包括一些谋反和邪教类案件。政治性案件的审理方式和裁决依据与自理词讼和常规命盗重案大不相同。美国史学专家孔飞力研究乾隆时期叫魂一类妖术案时,称之为“政治罪”。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造反。政治罪危及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成为君主重点关注的问题。(30)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45-246页。政治罪被认为直接威胁到朝廷统治,因此难以用常规司法机制和标准待之。有论者谓,从统治者的层面来看,文字狱案犯触碰到了君主的“逆鳞”,事实认定主要根据作品字句判断有无“谋大逆”等罪行,皇帝的意旨决定了案犯的罪名。文字狱案在量刑上多由皇帝核准,处以极刑。此外,其家属也多受缘坐。皇帝主观态度的随意性造成在量刑上存在着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罪的现象。(31)孙光妍、宋鋆:《清代文字狱案例评析——以数据统计为中心的考察》,《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16期,第137页。皇帝本人确定文字狱是否有罪,而且定罪和减免标准也由皇帝宣示。这是讲政治的结果,而不是法律的体现。(32)胡震:《因言何以获罪?——“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64页。
文字狱案犯的“主观方面”有二类,一类根本没有犯罪动机,更谈不到故意与否;另一类却很难说一定没有贬斥、笑骂清朝的故意,但是仅此并不能构成犯罪。清统治者认为文字狱“侵犯”朝廷,是否真的侵犯,全凭统治者的臆断。文字狱援引或“比照”反逆条款定罪的文字狱案犯,恰恰说不上有什么谋反大逆的行为。(33)郑秦:《清代文字狱研究新成果》,《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48-49页。以乾隆十六年(1751)王肇基献诗案为例,在山西巡抚阿思哈亲自审讯下,王肇基供称“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据之,王肇基不存在冒犯朝廷的主观恶意,而尽管阿思哈、军机大臣及乾隆帝一致认为王肇基“语多荒诞,似属病患疯癫之人”,即类似今天所说的精神疾病,乾隆帝仍指示阿思哈“将该犯王肇基押赴省城内通衢市曹当众杖毙”。(34)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朝文字狱档》,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5-10页。乾隆帝处理此类政治性案件时,完全超越常规司法程序,对“罪犯”施以法外重刑,属于绝对的擅断。
涉案者为精神病患者(“痴呆”“癫狂”等)的文字狱在当时有若干起。众所周知,此类罪犯若犯重罪,传统法制通常允许法外施恩,或按律收赎,或减免刑罚。沈家本讨论汉代案件时曾谓:“人至病狂而改易其本性,则凡病中之所为皆非出于其本性,故虽有杀人之事,亦得恕之。”(3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第1470页。清末律学大师、刑部尚书薛允升亦谓:“疯病杀人,律无明文,康熙年间,始定有追取埋葬银十二两四钱二分之例。盖照过失杀办理,即后汉所谓狂易杀人得减重论之意也。”(36)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校》,薛允升原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过失杀在传统“六杀”中属于最轻的杀人罪行,律例通常允许罪犯给付死者家属埋葬银的方式免除其死刑。不过,有论者统计,在乾隆朝的130余起文字狱中,疯汉文字狱类型的有25起,约占总数的18%。但是,25起疯汉文字狱中13起定为逆案,一律依大逆罪凌迟处死。案件处理多不按律例规定,惩处方式不依成法。大清律徒具空文,三法司形同虚设,参与论拟的大学士等官吏不过是奉迎帝旨。(37)郭成康:《乾隆朝疯汉文字狱探析》,杨一凡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七卷,《历代法制考·清代法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31-732页。
康、雍、乾三朝的90起文字狱大案可划分为4种类型:(1)完全拥护清朝统治的,涉案人献媚求进而无意间误触禁区,这类案件约占总数1/6;(2)政治主张不明确,但无意反对清朝统治,这类约占一半;(3)对清朝统治者有些不满之处,但无抗清行动,这一类约占1/3;(4)以言行明确反抗清朝统治的,则仅有曾静案一起。(38)孙立:《论清代的文字狱》,杨一凡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七卷,《历代法制考·清代法制考》,第726-728页。由于曾静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影响,雍正把曾静的投书谋反案转化为对吕留良的文字狱处置。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发现,当时有的皇室成员与刑部官员认为曾静及其学生张熙应处凌迟之刑,雍正对案犯却未定“十恶”之罪,反而令其受到宽恕,成为代他南下宣传皇帝圣恩的工具。雍正不可思议的法外施仁,释放两个有谋反言论、有谋反行为且证据确切的案犯并无法律依据。吕留良虽死,受戮尸酷刑,其16岁以上子孙处死刑。同时,雍正将曾静悔恨言论及雍正与之的对答编成《大义觉迷录》,强令全国学生诵读。(39)Jonathan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Viking Penguin Press, 2001, pp.141,227-228.学者谓,雍正指令处死吕留良后人时,全然不顾其已故皇父康熙晚年赦免吕留良的遗训。(40)施婧娴:《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理论界》2013年第11期,第113页。乾隆继位后,立即推翻已故父皇判决,以谋反罪指令湖南地方官捕获曾静及张熙,送往北京处死,同时召回并毁坏《大义觉迷录》,禁止士人诵读。(41)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2001, pp.239-247.
所有政治性案件中,曾静案可能是最能表明皇权在司法实践中完全脱离法律、绝对擅断,是数任皇帝处理政治性案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典型。政治性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非常少,数量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学者讨论明清“依法裁决”或刑事审判问题时,均未将政治性案件一并纳入讨论范围。此类案件数量虽少,影响却极为深远。在审讯与追责过程中,皇帝往往倾注有限的国家司法资源,通常一起大案前后持续十多年时间,牵连甚广,案犯及其家属多被施以法外酷刑,一些重要官员受到皇帝严厉追究,引起全国士民震恐,绝非其他任何命盗重案可比拟。(42)在极个别情况下,命盗案件也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因素的案件或影响政坛的案件。比如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最高掌权者介入重审,一方面固然存在为“案犯”平冤的正当诉求,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打击因太平天国事件崛起的江浙官僚势力。有关这方面的深度分析,见William P. Alford, “Of Arsenic and Old Laws: Looking Anew at Criminal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72, 1984, p.1180.
除文字狱,“邪教”类犯罪也被认为威胁皇帝统治,一并处于皇帝严厉打击范围。孔飞力研究叫魂案时指出,皇帝对官员们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则刻薄训斥。此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有司法程序、法律条文和法律原则可能完全被皇帝扭曲,刑部及其他官员基本没有任何建议或评论余地,判决几乎完全听由皇帝擅自决断。在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所有叫魂案都是由民众恐慌、皇帝对地方官的苛责及审判者严刑拷打造成的,事后证明没有一个案犯施加过妖术。孔飞力甚至因此认为,没有任何可靠途径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法律让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43)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第229、305-306页。除了叫魂案,皇帝处理其他“邪教”案的风格大致类似。林志坚认为,尽管《大清律例》中有“断罪引律”令,但在打击“邪教”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有法不依现象。这通常表现为刑部或者督抚等官员处理“邪教”案件时,往往受到来自皇帝的压力,在判决过程中常选择适用量刑较重的法律,迎合皇帝意志。(44)林志坚:《清代中期“邪教”案件的惩治》,邓建鹏主编:《法制的历史维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194页。
综上所述,思索清代“依法裁决”问题,将司法影响力极大的政治性案件全然排除在讨论范围外,显然是不完整的研究。巩涛指出,美国学者罗尔斯所说的“法律的含义应当清晰地表明,……至少那些最严重的犯罪应当被严格地界定”,这些要求在中华帝国时期的法律里都得到了满足。所有犯罪都应当被法律明确地规定,法官被要求遵守法律文本的字面规定。(45)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孙家红、柴剑虹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0页。这一高见过于绝对,其已然将政治性案件的司法处理置于观察范围外。
四、“现代西方”评价标准的局限
近年部分涉及清代司法的重要评论,过度依赖如马克思·韦伯的司法理想类型等现代西方法制标准或参照模式,(46)林端:《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第26-40页;Bradly W. Reed, “Bureaucracy and Judicial Truth in Qing Dynasty Homicide Case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39, No.1, June 2018, pp.67-105.另比如寺田浩明将西欧近代“法-权利”型审判作为对清代州县司法评判的参考,参见寺田浩明:《“非规则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国为素材》,《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8、248页。极易滑向中国传统法制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忽视了支撑清代审判特质的本土政治与经济环境。这些围绕清代州县司法的研究多多少少都存在以西方法学解释标准或评判立场的嫌疑。黄宗智认为“滋贺他们研究法制的方法,主要是德国传统的法理学,要求抓住一个法律传统,甚至于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核心原理”。(47)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1期,第82页。寺田浩明则认为,黄宗智无意识地把西方近代的市民法模型作普遍的发展模式引入清代,给他贴上一个“近代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相当容易。(48)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国家学者之间的争论》,《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第616页。但是,双方均难以摆脱这种理论预设。
寺田浩明曾反省:“要说在研究过程中容易陷入近代或西洋中心的偏差,意思好像很清楚,然而这种偏差的大部分其实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已溶进了我们的认识框架。”(49)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第310页。徐忠明认为,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类型与现代西方“依法裁决”看起来处在对极位置。(50)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类型的再思与重构——以韦伯“卡迪司法”为进路》,《政法论坛》2019年第2期,第61页。类似以“现代西方”评判“清代中国”,属于不对称时间上的比较研究,无意中潜藏着以“现代西方”法制标准对“清代中国”司法实践的苛求,其合理性值得探讨。巩涛( Jérome Bourgon )质问:从过于狭隘的现代问题出发来探讨过去,并不是好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我们西方人目前还没完全把握好的法律范畴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的法律甚至中华帝国时期的法律体系,是合理的吗?(51)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孙家红、柴剑虹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第132页。对寺田浩明提出所谓清代司法存在“非规则型”的特征,有学者反思,规则型法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规则先于案件而存在,对具体个案的处理必须借助对既有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因此法有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以及法律公开等各种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不过,无论在普通法与欧陆法的历史还是现实中,这种规则先行的状态并未完美地存在。(52)王志强:《“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64页。与本主题相关的一些重要研究多使用“罪刑法定”等概念分析清代或传统中国依法裁决问题。(53)俞荣根:《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室编:《中西法律传统》第3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黄源盛:《传统中国“罪刑法定”的历史发展》,《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台北五南图出版社公司,1998版,第427页。然而,有学者指出,当我们以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照观和解构中国传统司法时,很大程度上会出现障碍和歧义,因为“罪刑法定”含义无法精准对应中国传统社会的刑事法律。(54)董长春:《罪刑法定:传统中国的立场与平衡》,《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7页。
现代法治模式下通用的“罪刑法定”概念,多包含人权、自由保障等内涵,关涉一些价值判断。罪刑法定包括一些基本下位准则,诸如禁止类推、禁止溯及既往、法律应明确,等等。以之评判清代司法实践,可能存在时空上的错讹。罪刑法定并非凭空存续,论者谓,其要借助一系列制度性架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在刑事领域的行使受到严格规制,使刑事法治成为宪政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罪刑法定的意义必须借助并依靠宪政才能界定,宪政构成它的灵魂。(55)劳东燕:《罪刑法定的宪政诉求》,《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33-134页。显然,学者今日所谓罪刑法定,已非单纯字面含意,而是存有系列内涵,尤其是国家权力被有效制衡乃其中应有之义。因此,现代西方罪行法定与清代刑部等机构大体依法裁决的司法实践,为形相近,而实相远。刑法学家另论及,所谓罪刑法定以及法的确定性,都是相对而言的。成文法体系通过立法语言本身,不可能解决法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之间的紧张与语言在核心范围内的明确和在边陲范围内的模糊之间的紧张。相对于普通法国家,大陆法国家的刑事法律在确定性与开放性之间、法的普遍性与个案正义之间往往遭遇更加严峻的冲击。(56)劳东燕:《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83页。职是之故,罪刑法定与法之确定性,某种程度如普洛透斯(Proteus)之脸,恐非一些学者用以比较和评判清代司法时那么明确无误,言之凿凿。
论者谓,西方最先宣布新刑法原则的法律文献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包括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等,至1810年法国刑法典贯彻了上述原则。(57)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7-328页。不过,法国的法律史学者甚至指出,中华帝国时代的法律家已经理解并奉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基石之一。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禁止做出如下假设,即中国古代的法律家曾经将罪刑法定原则传输给18世纪法律体系的奠基者们。(58)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等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第142-143页。进一步论之,无论是罪刑法定,或者是依法裁决,前提是可资法官参考的明确的、统一的成文法事先存在(所谓规则先行)。如论者谓,“罪刑法定”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不成文的习惯或法理等不得作为刑事审判的直接法源。(59)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巩涛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于1799年出现,当时欧洲还没有形成法典化的法律体系。在法国旧体制下,法官在很宽泛的范围内选择实施各种刑罚。在旧体制下从未存在过统一和明确划分等级的、能够根据犯罪轻重而加以调整的法定刑罚。巩涛推定作为现代法观念基础的罪刑法定原则很可能是中国在制度方面的若干发明之一。(60)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等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第133-134页。易言之,若在同一时空对比中西法制和所谓“依法裁决”问题,至少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与清代中国相比,西方法制并无明显优势。这方面,笔者综合当时欧洲法制背景以及评论家的观点,有如下充分证据以证明之。
早在1735年,欧洲出版的中国通史(TheGeneralHistoryofChina)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司法体制后就认为,中国有更好的监狱条件、更便利进入的法庭以及对命盗重案更严格的复核。(61)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16.《大清律例》于1810年被英国斯当东爵士翻译为英语后,很快就出现了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等多种版本,并在欧洲掀起了学习清律及中国治理模式的热潮。1810年,当时影响力巨大的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这样评价《大清律例》:“我们得承认,迄今该法典对我们而言最为显著的是,各条文高度合理、明晰以及前后一致,用语朴素、适中。”(62)“Penal Code of China,” Edinburgh Review,1810, Vol.XVI, p.481.很快,法国及西班牙的评论者做出了类似正面评价。当时有评论者甚至指出,中国在法律方面如此先进,以致超过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因此,为了国家荣誉和帝国利益,英国不久亦应制定法典。有确切证据表明,在1811年,英国议会辩论普通法的法典化改革时,《大清律例》起到独特示范作用。(63)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pp.134,130,143.
在英国普通法方面,论者谓,到19世纪,英国仍存在不确定性和诉讼程序的僵硬。英国法院系统极为复杂,当事人常因错误地选择了法院而浪费时间和金钱。普通法院实行的令状制诉讼程序充满了形式主义的特征,常使案件久拖不决。普通法法系国家的法典、法规通常在体系和结构上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许多条文前后重复甚至矛盾,大都不过是对以前制度法的汇编。法典和法规的适用要受到法官解释限制。法官们常把法典或法规中的规定置诸一旁,而依判例法处理案件。(64)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448、486-487页。美国汉学家比较中西法律时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华帝国的法律在有些方面更加人道、合理。中国盗窃罪一般不处死刑,而英格兰的法律却规定盗窃商店货物价值超过5先令即处死刑。这项法律规定直到1818年为国会四次否决后才被废止。(65)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第30页。
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当时中国法律与司法形象胜过同一时代的欧洲诸国。论者亦指出,18世纪无论是来华的传教士信札中的清朝司法形象, 还是西方社会内部所谓时代名流的清朝司法形象都还不错,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清朝司法的可取性。(66)柳岳武:《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天府新论》2008年第1期,第127页。这些来华人员的评价,实为潜在地以其祖国更糟糕的司法背景作为参照物。由法国开始掀起的法典化风潮,据学者考证,甚至也可能受到《大清律例》法典模式的影响。(67)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9页。在法国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典编纂前,有论者谓,在中世纪后期至18世纪,即使像法国那样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也没有真正实现法律的统一。习惯法、教会法、自治城市法,法律行会和团体的规章等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有效。(68)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第214-215、261页。18世纪时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17-18世纪初的中国曾给予较高评价,他称:“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政。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69)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1页。这种评论尽管不免溢美之词,但是,中方司法状况优于同时代的西方并无太多疑问。
在清末沈家本等人正忙于学习西法,修订新刑律之际,来华的德国法学教授郝善心却对中国法典给予崇高评价:“《大清律例》向为法学名家推为地球上法律之巨擘。昔英人司韬顿君(即Sir George Staunton,今通译为斯当东,引者注),曾将此律翻译英文,于西历1811年印刷成书,并谓其中有许多规则,他国亟应仿效者。余虽于此所得不深,然已有确证,缘近今最新之瑞士(西历1908年)、奥地利(西历1909年)、德意志(西历1909年)诸国刑律草案,其主意亦见于大清律各条也。”(70)郝善心:《中国新刑律论》,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巩涛指出,对刑罚进行数学计算的体系建立在以个人责任或社会危险程度为标准的人类行为的分类学基础之上。它们曾经在中国被运用了好几个世纪之后才成为西方法律的一部分。(71)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等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第140页。迟至19世纪初,西欧各国方推进并逐渐完成法典化,这与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即逐渐进入法律成文化与法典化相比,(72)邓建鹏:《中国法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64页。至少晚了一千多年。从这点而言,包括清朝在内的传统中国法典之成熟曾长期领先于西方,而这恰恰是“依法裁决”的重要前提。巩涛认为,法律的公开性,处罚的可预见性,对司法决定的监督等事项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内获得了比在同一时期欧洲旧体制下的法律体系内更好的保障。在那些众多杰出专家看来,直到18世纪末中国实际上是领先欧洲的。(73)巩涛:《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陆康等主编:《罪与罚:中欧法制史研究的对话》,第149页。当时沈家本曾洞若观火:“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美善。”(7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第2024页。另有论者指出,在18世纪中期,有西欧国家的君主在司法审判与执行中是独一无二的主宰,他可以任意撤销判决或加重判决。(7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7年,第58页。据之,当时西方君主司法上的擅断与清朝皇帝在处理政治性案件时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中期之前,清代中国成文法的法典化、法律的明确性以及依法裁决的程度,并不逊色于同一时代西欧诸国。因此,在此时间节点之前,从同一时段中西比较视野观之,西方司法审判谈不上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与所谓“罪刑法定”亦有较大距离。以现代西方法治评判模型,论述比较清代依法裁决问题,无异于以现代西方科技评判中国清代科技发展水平,实为苛求古人。若法律史专家深陷于此种不对称比较,则失却应有清醒。从固有司法实践出发,就中国论中国,或是一条正路。
五、结 语
综前所述,在清代州县一级,只要州县官能将案件在本层级结案,那么他们往往倾向于脱离律例的硬性规定,甚至可能从自由裁量滑向擅断。对大部分涉讼的“愚夫愚妇”而言,州县官通常有能力压制大部分自理词讼甚至部分命盗重案,使得这些案件免于进入上级监控的视野,对这些案件,只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州县官倾向于纠纷解决而非规则之治。如孔飞力研究叫魂案时连带指出,清代甚至连知县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而几乎没有被绳之以法的危险。(76)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05-306页。因此,在这个层级,依法裁决的空间有限。若限于制度要求或当事人的抗争,案件可能进入上级官员视野,诸如徒刑以上案件一旦进入审转覆核制,则州县官倾向于自动限缩擅断空间,至少形式上尽可能依法拟判。
应审转覆核的案件途经督抚到刑部时,大部分官员在经手命盗案件时尽可能依法裁决,以免申送卷宗时被刑部或皇帝驳回,进而危及个人仕途。对于皇帝而言,为了维持正常的国家治理,皇帝基本尊重刑部官员的专业意见,当自己的建议遭到刑部反对后,赞同刑部的拟判,也是皇帝明智之选。但是,审理政治性案件时,无论是事实的最终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则完全听由皇帝个人旨意。在正统理念中,皇帝是所谓“天之子”,天为人世间统治者虚构的最高权威。皇帝向虚构的天负责,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不必负担政治责任。不用承担实际义务与责任的最高权力,在裁决涉及自身统治利益的案件时,易趋于擅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