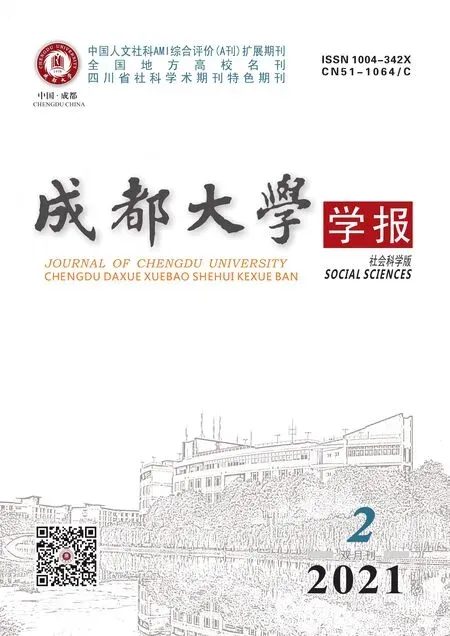“镜像”映照下女性的“自我”构建*
——电影《嘉年华》的女性主义阐释
2021-03-25胡晋博田义贵
1.胡晋博 2.田义贵
(1.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2.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电影《嘉年华》以极具力量感的叙事将性别议题,以及女童遭遇性侵等社会问题引入观众视野。该电影自公映以来即引发热议,曾代表中国电影入围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54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电影主要叙述未成年少女小文与新新遭遇性侵,掌握重要证据的旅馆服务员小米是一位流浪的未成年少女,小米在艰难的生存境况下对于手中重要证据的处理犹豫不决,而受害者小文与新新在追寻公正的道路上不断遭遇男权社会的一次又一次伤害。最后在郝律师的周旋下,小米交出证据帮助受害者小文、新新。作恶者受到法律制裁,小米却失去工作而前途未卜地流浪着。电影描绘的虽是未成年少女,但却展现了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是拉康镜像理论女性“自我”建构的寓言。当女性遭遇伤害后,她们最初认为这只是简单的偶发事件,并以利己的态度漠视这一切。可当这些伤害具有一定广泛性时,女性开始自我反省,并在相互扶持的过程中,镜像映照着彼此,女性“自我”意识慢慢觉醒,开始女性“自我”尊严的建构,“自我”命运的救赎。在该电影叙事中,导演很好地运用了拉康的“镜像阶段”与“凝视”理论。
一、“镜子”与“凝视”:“梦露”意象
“镜像阶段”理论是拉康精神分析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6到18个月的婴孩在尚未掌握使用语言之前,对于自我身体与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支离破碎的,婴孩感知世界与自我的途径是通过视觉观看。当婴孩在镜子面前识别自我影像时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婴孩将镜中的影像误认为其他婴孩;第二阶段,婴孩识别出镜中的影像是“自我”。在婴孩与镜中影像认同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婴孩的双重误认:一是婴孩将自我形象认同为“他者”,二是婴孩将镜中的虚幻影像认同为真实的“自我”。因此,尚未掌握语言的婴孩混淆了真实与虚幻。拉康“镜像阶段”理论进一步引申出“眼睛”与“凝视”的辩证法,拉康认为眼睛既是欲望化的器官,又是被充分象征秩序化的器官,人们通常只愿意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事物。“凝视”(gaze)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观看(look,see),当“凝视”发生时,“凝视”者投射着他们的欲望,并将他们由象征秩序再度拉回“镜像阶段”。[1]日本学者对拉康镜像理论亦有叙述:“镜像阶段是‘自我’的结构化,是自己第一次将自身称为‘我’的阶段。”具体而言,“镜像阶段是指还不会说话、无力控制其运动的、完全是由本原的欲望的无序状态所支配的婴儿面对着镜子,高高兴兴地将映在镜中的自己成熟的整体形象理解为自己本身的阶段”[2]。
导演在《嘉年华》叙事中很好地运用了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并将“眼睛”与“凝视”的辩证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序幕以简洁的电影语言使用了一组组“眼睛”与“凝视”的镜头。主人公小米观看着海边嘉年华中巨大的玛丽莲·梦露雕塑,镜头跟随小米对梦露塑像的观看带领着观众窥视梦露雪白的小腿。小米抚摸着梦露雪白的脚踝和鲜红的脚指甲,紧接着,小米的观看被一群与梦露塑像合照留影的少女打断。她倒退几步,观看着这群欢笑打闹的女孩,然后像她们一样拿出手机拍摄着梦露,镜头跟随小米拍照的动作向梦露大腿游移,特写着梦露的白色内裤,周围传来与梦露塑像合影的少女们的欢声笑语,镜头最后停留在凝视着巨大梦露雕塑的小米的脸上。作为影片的开端,没有台词,没有花哨的镜头转场,只有主人公小米对于梦露这面“镜子”默默无声地“凝视”。而这组镜头所表现的内容,正如萨特所叙述的出于嫉妒、好奇心、怪癖而无意中把耳朵贴在门上,通过锁孔向内窥视。窥视者没有自我意识,因为他完全被所窥视的事物吸引,就像墨水被吸墨纸吸掉一样。窥视者什么都不是,只是虚无。当窥视者突然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他的窥视被打断,“有人注视我”,一切突然发生了转变,“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在我的存在中突然被触及了,一些本质的变化在我的结构中显现”[3]。电影序幕中,当小米凝视梦露雕塑时,她的意识完全被梦露雕塑所吸引,小米呈现出“无自我”意识的“凝视”状态。当一群欢声笑语的女孩出现时,正如萨特描述的窥视者一样,小米“无自我”意识被打破,而进入“自我”状态,小米后退观察这些欢声笑语的少女们靠近梦露雕塑,她注视着梦露雕塑飘扬的白色裙摆和内裤,以及与之合影的少女们。这看似简单的序幕,导演却独具匠心,它隐含深刻的主题,在梦露这面“镜子”的影像中出现了“凝视”关系中“非自我”与“自我”的转移关系。电影序幕有统领整个电影主题的作用,象征女性由“非自我”走向“自我”的结构关系。
电影中的“梦露”是一重要意象,她是深具象征意义的重要符号。在该电影中,她多次以巨型雕塑、金色发套、白裙服饰、白色高跟鞋等出现在电影叙事中。玛丽莲·梦露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最耀眼的巨星,一生所饰演的角色多为天真愚钝、性感无脑的形象。玛丽莲·梦露性感的肉体,极具光泽的金色头发,站在通风口吹起的白色裙摆与极具诱惑力的性感造型姿势,成为男权社会被“凝视”的象征符号,以及男权社会被规训的“他者”。当“梦露”这一象征符号出现在电影《嘉年华》中时,她体现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镜像”的功能,规训着电影中这群女性们。在电影中,“梦露”一方面是女主人公们想象界的“自我理想”的投射,携带着女主人公们的“自恋性”认同;另一方面,“梦露”也是男权社会所指认的象征符号,“梦露”作为象征界的“自我理想”出现在电影中,“梦露”形象被转化为巨型雕塑、金色发套、白色裙子等出现在女主人公面前,并时刻影响、规训着电影中的少女们。因此,作为未成年少女小文初次登场时戴着与“梦露”同样的金色发套。施暴者刘会长带着小文与新新来到旅馆大厅,不知危险临近的两个小女孩兴奋地在大厅自拍。新新羡慕地对小文说:“你好看,我不好看,因为你有发套!”小文、新新视女孩“好看”的标准是如梦露的外表,有着强烈的女性特征——带金色光泽的头发,飞扬的白色裙摆等。金色发套在此后的电影叙事中多次出现在电影台词与电影场景里,金色发套既是男权社会“凝视”关系存在的证据,也是女性被“梦露”这一镜像规训的重要痕迹。小文、新新正如电影序幕中那群与梦露雕塑合影的女孩们一样,被象征界男权社会所指认的“自我理想”规训着,在遭遇性侵前,她们都无意识地被男权社会的“镜像”规训塑造着女性特征、女性行为。她们观看“梦露”时,被男权社会指认给她们的“自我理想”无意识地塑造着她们的女性形象,投射女性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此刻她们的“自我”认知与被指认的“自我理想”是相符合的,但这样的平衡在遭遇性侵后被打破,并最终发现真正的“自我”是什么。
由于电影的魅力,“梦露”还作为一个极具广泛象征意义的社会符号,打破时空,穿越出银幕,让观众也进入“无自我”意识的“凝视”状态。由于观众的接受视野,电影序幕既是小米对“梦露”的凝视,也是观众对“梦露”的凝视,观众跟随小米由最开始的无自我意识的观看到被与“梦露”合影的少女们打破,小米观看那群观看“梦露”的少女们。这些既是小米的凝视,也是观众对“梦露”以及这群少女们的“凝视”。对电影观众的“凝视”,有学者叙述道:“当影院灯光渐去,深陷幽暗的观众将目光投向银幕,此刻银幕内外一场看与被看的戏剧便悄悄拉开了无形的帐幕。观众屏息凝视,银幕人物目光流转,摄影机推拉格移,三种视线的互动成为这场戏剧的主角。”[4]《嘉年华》借由“梦露”这面“镜子”,非常巧妙地表现了现实社会中女性们被全方位“凝视”的生存状态。在全方位“凝视”状态下,女性被规训着:她们的思维,她们的外貌特征,她们的一切言行。在拉康看来:“甚至看似主动的观看其实一直都受制于他者的凝视,我们总是根据他者的凝视来调节自己对世界、对自己的观看,来表征和刻画自己。”[5]因此,“梦露”意象频繁出现在电影叙事中,她成为男权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镜像”。
二、男权指控中女性的“自我理想”
正如前面所述,电影序幕有引领主题的作用,但其主题却是在“性侵”这一事件发生后才逐渐显露。小文在遭遇性侵后随时受到男权社会“凝视”的“指控”,她的叙事线由第二天去学校上课迟到正式开始。而另一位“性侵”受害者新新与小文的差异也开始显现。从老师对小文和新新上学迟到批评的态度中,观众了解到,小文是一位离异家庭的孩子,母亲常常不在家中。而新新是一名成绩优异的重点中学的预备生,新新的家庭条件明显优越于小文。小文和新新由于家庭背景、身世的不同,在面对“性侵”事件的后续处理所遭受的二次伤害也存在差异。
在随后的电影叙事中,重点表现了小文的“自我”认知与被指认的“自我理想”被打破。成年人对于小文被“性侵”的后续处理,直白地指控小文遭遇“性侵”后不再符合男权社会所指认给女性的“自我理想”。小文的妈妈得知小文被“性侵”伤害后,她不但没有安抚小文,而是在众多医护人员面前给了小文一记耳光,她责备小文:“让你再穿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还有你这头发,一天天披头散发的干什么?”刑警队的王队长对“性侵”事件的调查则采取恐吓盘问,还指责小文“主动”喝酒,还连续盘问:“喝了一点是多少?一罐还是两罐?旅馆的服务员第二天可是在房间里发现了四个空罐,我们可以给你做个尿检,看看你到底喝了多少?”这一切指责都将小文遭受“性侵”的责任归结在小女孩自己身上。“性侵”的后续处理都在有声无声地指控着小文。这样的“指控”被电影叙事强化到了顶点,这就是小文母亲残暴地割裂了小文遭遇性侵前想象界的“自我理想”形象:像梦露一样极具女性特征的形象。她认为是小文的女性特征——她的长发、漂亮的裙子——等导致她受到了侵害。电影叙事中,小文母亲愤怒地撕毁了小文漂亮的裙子,暴力地剪掉了小文的长发,小文的女性特征被切割。小文对此的反应也是电影叙事强化的重点,小文凝视着镜中被剪掉长发的自己,将母亲的化妆品全部毁坏,显示了小文对于母亲破坏她镜中的“自我理想”的报复。当然,她只能背着母亲毁掉这带女性特征的化妆品。被母亲剪掉长发的小文带着金鱼负气离家出走,而“梦露”再一次作为象征意象出现在电影叙事中,无处可去的小文来到梦露雕塑前,巨型雕塑下成了小文露宿的栖身地,梦露飘扬的裙摆成为她遮风挡雨的港湾。梦露雕塑的巨大与小文蜷缩的小小身躯形成强烈反差,小文仰视着“梦露”,在“梦露”脚下卷曲着微弱的身躯疲惫地睡着了。“梦露”作为意象与“镜像”频繁出现在电影叙事中。
根据拉康理论:“邪恶的眼睛是凝视的力量得以直接实施的维度之一。”[5]电影叙事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邪恶“凝视”所带来的伤害伴随着第二次法检达到了最大化。刘会长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施暴的罪魁,而调查处理性侵案件的王队长与接受贿赂的三名法医专家则是男权社会“邪恶眼睛”给受害者带来伤害最大化而助纣为虐的帮凶。在第二次法检中,男权社会对小文、新新遭遇“性侵”后所指认的“自我理想”明朗清晰起来,她们身体的隐私被全方位观看,“凝视”关系昭然若揭。滨海市公安局特意请来省人民医院三位“法医专家”对小文、新新进行新的法检,在确认小文、新新无性侵痕迹后,政府专门召开权威发布会通告性侵者无罪。在法检过程中,受害者被三位“法医专家”(包括一位女性专家)轮番检查女性性征的完整性,他们不顾幼小受害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男权社会的邪恶“凝视”编织成一张密实之网,让柔弱的受害者无处遁形,她们被再一次指认为象征界新的“自我理想”:一个被物化了的处女膜毫无损伤的少女。小文在遭遇性侵前,被男权社会指认的“自我理想”极具女性特征,美丽的“梦露”成为她们的“理想镜像”。当她遭遇性侵后,男权社会所指认的“自我理想”又成为“被物化了的处女膜毫无损伤的少女”。男权社会对“性侵”案件的处理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尊严与心理承受力,他们还上演了一场“皇帝新衣”式的谎言来掩盖“性侵”者的作恶,其借口就是受害者还仍然是处女。第二次法医检查是男权社会借政府的权力话语遮掩作恶犯罪的事实真相,这对受害者的伤害远远大于施暴者“为恶”所带来的伤害。
三、男权社会女性的“自我”麻木状态
在电影《嘉年华》的叙事中,新新这一受害者较少呈现她的负面情绪,更多表现了她懵懂麻木的精神状态。新新的人物形象在电影叙事中所留空间较少,但却更切近现实,新新遭遇性侵后的“自我”麻木精神状态是当下女性受害者的缩影。在第一次法医检查中,小文和新新两位受害者家庭的差异就显现出来。陪伴小文的监护人只有小文母亲,但陪伴新新的监护人却是父母双方,新新的家庭是完整的,家庭条件明显优越于小文,但新新的父亲却是施暴者刘会长的下属,这为新新家迫于上下级利害关系对于被“性侵”的自我欺骗埋下了伏笔。新新对于“性侵”始终表现出一种懵懂而麻木的精神状态,这很大部分来自新新父母对于新新被“性侵”的自欺欺人的态度,在他们眼中,维护女儿的“清白”要远重于追寻正义,而这也正是男权社会许多女性受害者不得已的现实选择。
面对“性侵”的后续调查处理时,新新的父母主动找到小文的父亲企图以利益为诱饵协商“解决”这件事:“他(指施暴者刘会长)说只要我们不追究,他来负责俩孩子今后的学费!”新新的父母甚至为施暴者刘会长辩解:“他那天确实喝多了,一时糊涂,他现在呢也是特别后悔,希望能够尽力地去补偿!”而新新父母这样的行为有他们最自私也最现实的看法:“判了又怎么样,他进监狱几年出来照样呼风唤雨,可咱们孩子呢?这辈子都得让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咱们得为孩子着想啊!”新新父母认为孩子的“清白”要远高于公正和对施暴者的法律制裁,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应是一个符合男权社会“被物化了的处女膜毫无损伤的少女”。显然,新新父母认可的“清白”名声只是男权社会给予的“虚假”遁词,他们维护的实际上是男权社会所指认的“自我理想”,但这明显是自欺欺人。新新父母的伪善与男权社会对“性侵”事件的态度不谋而合,这也导致了类似于新新的女性被“性侵”后不是去寻求正义,而是自欺欺人,以无知或麻木的精神状态承受这一切。因此,两位受伤害少女在面对第二次法检的权威结论时,小文的态度与新新截然相反,小文悲伤而愤怒,但新新却长舒了一口气,她不自觉地成为编织这“皇帝新衣”式的谎言的一员。她安慰小文:“我妈说,医生们说咱俩没事儿,学校见!”就实际情况看,新新所遭受的创伤在她“自我”麻痹下就消失了吗?显然不会,新新遭遇性侵伤害后会偷偷向隔壁班的同学要“吃了就不疼”的药片,并将这药片给小文。新新看见父母为此事争吵时会害怕地拉住小文的手,而这些创伤肯定会在新新的“自我”意识觉醒时愈发严重。
电影对“性侵”所造成的肉体与心理伤害主要表现在小文身上。在电影重要叙事中,小文在一次沐浴后,茫然地看着残破镜子中被剪掉长发的自己,这无疑让观众产生了震撼。小文决然地离开母亲而愿意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她认为,父亲虽然不能提供给她好的物质生活,但会给她安全保护。在电影的重要场景里,小文爸爸深夜尾随在游乐场嘉年华中徘徊的小文,发现小文在和新新视频通话,小文给新新拍摄嘉年华中游乐管道设施:巨大的管道在黑暗之中曲折冗长,管道尽头的大喇叭面向大海,小文爸爸并没有打扰小文与新新的快乐交流。两位女孩来到嘉年华,穿越嘉年华曲折冗长的管道,来到管道尽头的大喇叭里。在这里,两位女孩显得渺小但却充满了生命活力,她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对方的名字,跳跃着,欢笑着!这漫长而曲折的管道与面对大海的圆形大喇叭是极具女性性征的象征符号,也象征她们所要走的曲折而漫长的路!这是电影刻意为她们留下的一方安全之地。在这里,没有伤害,两位受伤害少女只有彼此!在这里,没有男权社会复杂的关系,她们逃逸了被全方位“凝视”的生存状态,只有在这里,两位少女才真正感到幸福快乐。
四、“镜像”关系中女性的“自我”觉醒
《嘉年华》中的小文与小米,正如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面人生》中两位女主人公一样,虽然身世不同、从未谋面,但因为某种联系而在生命的平行线上产生了交集,而互为“镜像”,在相互映照中重新构建“自我”,完成“自我”的最终确认。电影中,小文、新新是当下女性受害者的缩影,由于全方位被男权社会“凝视”,新新的“自我”多呈现为混沌朦胧状态,而小文则有朦胧的“自我”意识,有出自她本能的抗争。在学校里,同班小男生将她与新新的照片发到群里,她会找这位小男生理论,并以打架违反纪律来抗争。“性侵”事件后,她母亲愤怒地剪掉她的长发与裙子,她也毁掉她母亲的化妆品,并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她回到她父亲的身边,在她父亲看护下,她开始努力重塑“自我”,并尽快从受伤害的阴影中走出。相对于小文、新新,小米是电影极力塑造的“觉醒者”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镜像”映照中,独立的女性意识慢慢觉醒,最终重构独立的“自我”,并对未来的命运自我救赎。电影在塑造小米时并非像小文、新新一样清晰,只是粗略地呈现了她是一位未成年流浪打工者,残酷的现实处境为小米留下的空白极大,这给观众更多思考与投射“自我”的可能性;同时,小米作为底层女性与小文、新新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也使小米视小文、新新为“自我理想”成为可能。
小米与小文、新新的初次见面是在刘会长施暴的夜晚。小米熟练地为宾馆厅院的绿植花草浇水,一辆载着女孩欢声笑语的轿车驶入宾馆。接下来的镜头中,小米的聪明干练与不知危险将近的小文、新新的幼稚单纯形成对比;小米穿着不符合她年龄与身高的粉色旅店服务员服装,这与小文、新新身上的校服形成鲜明对比;小米繁杂而辛苦的服务员工作与进入宾馆无忧无虑的小文、新新形成对比。在电影叙事中有一组小米在打扫宾馆房间卫生的间隙,她躺下感受着宾馆舒适大床的镜头,把本应在校园读书的花季嘉年华少女却沦为宾馆服务员,并干着与她年龄不相匹配的辛苦工作表现了出来。小米作为一名未成年黑户少女,三年流浪了十五个城市,现留在这个城市是因为它暖和得连个要饭的夜里也能睡个好觉!这与新新、小文的优裕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使得小米不自觉地在新新、小文身上投射“自我理想”,她们生活的强烈反差也成为小米拒绝帮助小文、新新的理由。在电影叙事中有一重要细节,小米对戴着玛丽莲·梦露样式的金色发套欢声笑语的小文、新新投去欣羡而复杂的眼光。正如前文叙及,戴着金色发套的小文受到过“梦露”这象征男权社会所指认的“自我理想”的影响,这也是小米视小文为“自我理想”的重要依据。刘会长性侵小文、新新后,小米将遗弃在旅馆的金色发套收藏在自己枕头底下,这成为小米与小文之间一种隐秘关系,也表现小米对于“梦露”这一男权社会规训的“自我理想”形象的向往。在随后的叙事中,金色发套落入健哥手中,小米与健哥激烈地争夺发套。金色发套对于小米而言并不是一般宾馆客人遗留下的普通物品,也不仅仅是刘会长性侵的证据。金色发套是小米与小文初次见面时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小米透过“梦露”这面镜子在小文身上看到了隐秘的“自我理想”。在她们旅店初次见面的情景里,影片特意交代了小米和小文、新新生活极大反差的对比镜头,身为黑户流浪打工者的小米,她是希望自己与小文、新新一样,也是一位在校读书,穿着校服,充满欢声笑语,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
郝律师是小米在“镜像”中映照小文、新新为“自我理想”,以及女性“自我”重构的关键人物。小米起初对于是否帮助小文和新新极为矛盾,一方面,她受制于宾馆老板以及她黑户少女客观而残酷的生存现实,她不得不藏匿好证据以保护自己;同时,要将证据轻易地给郝律师帮助小文、新新又不甘心。这样的矛盾心理体现在小米面对警察的质询和面对郝律师的交流时完全不同的态度上。对警察的质询,小米是躲闪而害怕。但当郝律师出现时,即便另一位服务员莉莉姐特意嘱咐:“你自己找个地方躲着啊,千万别让她看见你!”但小米仍悄悄地带引郝律师进入被警察封锁的犯罪现场。在与郝律师交流中,郝律师指出小米对于是否帮助小文、新新的矛盾心理:“你一定在想能住上这样房间的女孩一定不需要你的帮助!”因为小米作为服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不超过六百,可这个房间一晚上的住宿费用就是七百多,这比小米一个月的工资都要高。即使郝律师给小米看小文露宿梦露雕塑下的照片,试图打动她,但这些对小米触动都不是太大,甚至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来显示自己至少在这方面优越于小文、新新。因此,相对于提供视频证据帮助小文、新新而言,她会选择要挟罪魁刘会长一万块钱,再用这一万块钱给健哥去疏通关系办理她急需的身份证,来取得她合法的身份。小米的选择很符合她的生存处境,以及她对是否帮助受害者新新、小文的矛盾心态。
但小米随后的遭遇使她难以应付,要挟刘会长的一万元钱已经不够支付健哥帮她办理合法的身份证,且这一万块最终被海滨那群“弱肉强食”的匪徒抢走。被劫匪暴打后的小米,带着伤痛与绝望到了医院,直到此刻她才明白,小文、新新作为性侵受害者并非个案,受害者可能是任何柔弱女性,特别是与她类似的女性。她将刘会长进入房间的视频交给了郝律师,让法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失去工作的小米无法生活,残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小米穿着像梦露一样的白色裙子和白色高跟鞋,一边化妆一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此刻镜中的她,已成为男权社会塑造给女性的“自我理想”形象,但这不是小米期望的“自我理想”,这有她不得已的现实选择。正在此时,小米听到正播报“性侵”案的最终消息,作恶者刘会长与玩忽职守的王队长、受贿的三名法医专家最终被绳之以法。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这给小米重塑“自我”以极大信心与勇气。小米逃离她卖身的房间,砸开锁住摩托车的锁链,骑着摩托车向未知的路途漂泊着。虽然,小米未来的命运不可预知,但经历这一切逐渐成熟的小米一定能战胜生活中的坎坷而把握“自我”的命运。
有学者指出:“镜像阶段理论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秘密诞生地,是进入拉康迷宫般的思想世界的最佳入口。实际上,其镜像阶段理论本身也有一个隐秘的入口,可以说入口的入口,那就是个体在镜前的凝视:自个体走向镜子向里探视的那一刻起,自我朝向异化的戏剧就一幕接一幕悄然上演。”[6]我们再反观电影《嘉年华》,拉康镜像理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凝视”所带来的女性“自我”异化贯穿电影始终。电影中女性“自我”异化主要指男权世界对女性的塑造与规训,这在小米、小文、新新等女性身上得到了重要体现。自序幕开始,小米透过梦露这面“镜子”探视“自我”,她“凝视”着梦露,仰视着这个男权社会为女性指认的“自我理想”形象,并携带着自恋性认同的“自我理想”,她无意识地被男权社会塑造、规训,其“自我”被异化。她撕掉梦露塑像所贴的小广告,尽力维护着男权社会塑造的女性“自我理想”。作为一个黑户少女,她要想方设法办理身份证,这是她自觉地想成为被男权社会所塑造、规训的一员,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像一个正常女性一样具有“合法”性。她后来为了生存而卖身,她穿着与梦露一般的白色裙子和白色高跟鞋,只有这样的装束与外表,才能获得男性的认可与接受。在男权社会,小文一步步走向“自我”异化。作品中的另一位女性莉莉姐,她似乎只有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依附于健哥这样的男人身上才能生存,她是男权社会“自我”异化的牺牲品。假如小文最终未完成“自我”救赎,莉莉姐的命运就是小文的未来。电影中的小文、新新,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及由此相联系的“凝视”辩证法在她们身上演绎着,她们被男权社会塑造、规训,她们的“自我”被异化。拉康镜像理论复杂、难懂,导演为更好运用这一理论,还有电影中在意识地运用现实中的镜子,让小米、小文等女性出现在镜子面前,这对拉康镜像理论有暗示作用。电影《嘉年华》用拉康镜像理论,以小文、新新及小米等女性的遭遇为切入口,将几位女性的生存境况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总之,电影《嘉年华》是一部女性主义意识浓厚的电影,对女性尊严与权利、对女性命运及生存处境的关注,对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肯定等是该电影表现的重要内容。拉康镜像理论是该电影的理论基石,它贯穿电影始终,这与拉康镜像理论的强大影响相联系,有学者指出:“镜像不只在婴儿时期发挥作用,作为‘他者’,它对自我的塑造功能贯穿于人生的始终。”[7]由此可见,拉康镜像不仅仅只对婴幼儿影响,它照样对成人世界给予规范与影响,这也是在该电影中,我们看到男权社会为女性指认的无所不在的“自我理想”镜像的重要原因。就这样,电影《嘉年华》以拉康镜像理论为基石,将未成年少女“性侵”事件升华为当下女性生存境况的思考,显示了导演的匠心。电影的发展应该有潜在的理论做基石,这是电影叙事、电影主题表达以及电影人物塑造等的重要手段,而这正是当下不少电影所欠缺的。可以说,电影《嘉年华》为女性主义电影与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