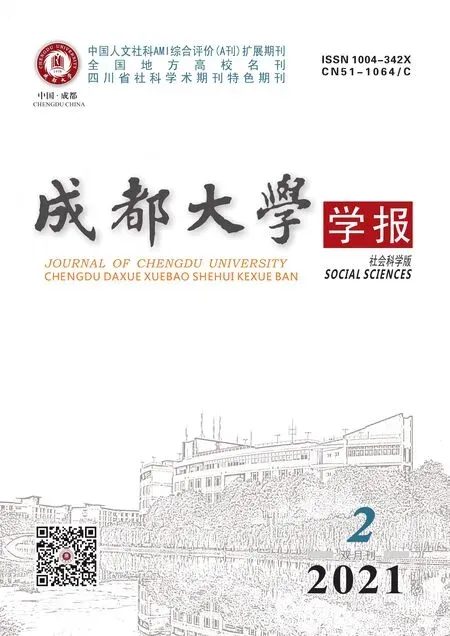改写与颠覆
——《中国佬》中的神话元素解读
2021-03-25黄颖思
黄颖思
(厦门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国佬》的叙事结构由历史和神话两个层面组成,这两个层面相互补充:历史层面叙述了作者汤亭亭的家庭中男性祖先的经历,而神话层面则神话化了这些经历。该小说共18章,6个主要章节的标题页上都盖有“金山勇士”的印章,记载了汤家男性祖先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的经历。在这些传记故事之间穿插着12个篇幅短小的章节,有的是作者从报纸上剪辑的,有的是她改编中国古典文学、英国文学、中国古代神话以及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故事而成。
这些长度不一、主体各异的小章节经作者的精心安排,穿插在传记故事之间。它们的作用经常被批评家们所忽视。约瑟夫认为:“《中国佬》中各松散的章节缺乏明显的连贯的主题来衔接。这些神话因素仿佛是作者事后产生的想法。”[1]在一个《中国佬》的汉语译文版中,译者干脆就以小说文风松散为借口删掉了6个小章节——“鬼伴”“论死亡”“再论死亡”“沼泽地里的野人”“鲁滨逊历险记”“《离骚》:挽歌”。
一、“关于发现”:英雄的神话
小说的第一章“关于发现”是作者根据明朝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的故事改编的。唐敖为了寻找金山,来到了女儿国,结果被那里的女子们逮捕了。他的武器被卸掉,他的双手被铐住,双脚被链子锁在一起。两个女子骑在他身上给他扎了耳朵眼,而且还威胁说让他闭嘴,否则将缝上他的嘴巴。她们给他裹脚,在他的脸上施粉,让他吃女人的食物。不仅如此,她们还让唐敖洗自己的裹脚布,让他服侍女王用餐。在这则神话的末尾,作者补充说明发现女儿国的时间可能在武后执政期间(公元694—705),也可能在公元441年,而发现女儿国的地点是在北美。
唐敖变成了女人印证了关于华裔男性女性化的刻板形象。就像唐敖被迫洗自己的裹脚布和服侍女王用餐一样,华裔男性在修完铁路、金矿关闭以后,被迫去白人家当仆人、去餐馆当侍者或去洗衣店工作。这三种工作是当时他们最可能找到的职业,而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些工作是女人干的,是低级、下贱的工作。美国主流社会认为华裔男性被动软弱、唯唯诺诺,只能胜任这几项工作。唐敖难堪和痛苦的经历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以及20世纪前半叶华裔男性的困境与无奈。
汤亭亭改写唐敖的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复关于华裔男性女性化的神话,她真正的用意在于颠覆这则神话,并且重建一个华裔男性不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英雄的神话。在小说后来的插曲中,她颠覆了传统的金山神话、失音的神话,重构了华人创造自己的金山的神话、开拓者中国佬的神话,以及漂泊离散的华人的神话。这些故事与小说历史层面作者家族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主题上都齐驱并进,彻底摧毁了主流社会中一度流行的关于华裔男性女性化的刻板形象。
唐敖找寻金山的行为表明像其他民族一样,华人也富于冒险精神。为金山神话所吸引,许多华人漂洋过海苦苦寻找,希望可以找到遍地黄金的金山。在故事中,唐敖一去就被抓获,但他一点也没有感到将被变成女人的危险,因为他“对女人不设防”。相反,他被这块美丽的土地所吸引。如果当时有其他男伴的话,他一定会调皮地回过头来眨眼睛的。为什么唐敖在异国他乡还觉得如此安全甚至完全不设防呢?作者在后来的神话故事里回答了这个问题。
二、“鬼伴”:传统的金山神话
第二则神话“鬼伴”揭示了金山神话(换句话说是华人的美国梦)的诱惑性,这是唐敖故事的延续。在前一则神话里,唐敖是一位学者,而在“鬼伴”中,被迷惑的年轻人可能是学者、农夫、鞋匠或工匠。
学者高燕指出女人国与“鬼伴”中的寡妇都是美国梦的化身。以女人作为美国的象征在该国文献中屡见不鲜。让我们来看看克洛德尼是怎么说的:“根据美国人的经验,美国这块土地不是类似于或相当于女人,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快意的女人。它拥有传统上男人心目中母亲、情妇以及处女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也许从一开始,人们应该更确切地把它称之为‘这块土地是女人’。”[3]62
在“关于发现”中颐指气使的女人以及“鬼伴”中媚人的寡妇在很多方面都象征着美国梦(在华人方面则是金山神话)。这位美丽的女人穿着的古代服装表明了美国梦有着悠久的传统。首先,她财富充栋的大宅子暗示着华工们把美国看成一个富裕国家的幻想;其次,寡妇给年轻人吃他从来没尝过的东西,看他只在故事里听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寡妇就代表新生活。尽管他没有完全忘掉他过去的生活,他与寡妇在一起的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生活。最重要的是寡妇不停地向他许诺:“我能满足你的愿望。我能让你有时间学习,有钱买金线和昂贵的光亮剂。”[3]75她说:“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可以告诉你如何把它做得更好,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3]76对从中国以及从旧世界(欧洲)来的移民来说,美国是乐土,是自由之乡,就像“鬼伴”中的寡妇一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很多愿望。最后,年轻人告诉她,他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给了她了。他终于挣脱她的怀抱回到自己的妻子身旁,也回到了尘世的喧嚣。这暗示着幻想不长久,在美国梦(金山梦)幻灭之后,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现实。年轻人的经历也使人想起受到剥削的华工们把自己的青春——他们一生的鼎盛时期留给了美国。
汤亭亭还在历史的层面显示了金山神话对华工们的无限诱惑力以及她的家族一代又一代的男性祖先们是如何为了实现淘金的梦想而前赴后继的。首先,家里流传着各种故事说美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度:“‘在金山,一个男人一顿吃下的肉足够这里一家人吃上一个月’……家里的人饿得越慌,这种故事就吹得越大,也就越相信这些吃大块肉、到处可捡拾黄金的故事是真的。”[3]37其次,对移民来说,美国还代表着自由和新生活。作者的父亲埃德刚到纽约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在美国传统里象征着自由的自由女神——这并不是偶然。他庆幸地说:“金山真是个自由的地方:没有礼仪、没有传统、没有女人。”[3]57最后,美国是机会的同义词,就像埃德跟他的妻子所说:“在金山什么可能都会发生。”[3]69总之,美国被誉为和平之国、自由之国、金山和美丽的国度。埃德急于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式中:f1 、 f2、 f3分别为系统有功网损、静态电压稳定指标、无功补偿设备投资成本;pk为各场景概率。
就这样,一个虚构的神话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唐敖们”来到美国,就像日本裔历史学家高木所说:
去的时候人们称他们为华工、旅居者。他们希望能在外国工作,三五年以后发一笔财荣归故里。他们为各个目的地起上名字——夏威夷群岛叫檀香山,加利福尼亚叫金山。自19世纪40及50年代始,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在19世纪后半叶大约有46,000人去了夏威夷;在1849到1930年间,大约有380,000人去了美国大陆。[4]
除了以上这些类似之处,小说中代表金山神话的女性形象与传统中代表美国梦的女性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欧洲人眼里,美国是纯朴的处女、慈爱的母亲和风情万种的情妇,柔情款款地邀请他们来这里定居;那么在《中国佬》里,美国则是一个有权有势骄傲自负的女皇:女人国的女人很明显地作威作福颐指气使,而“鬼伴”中美丽的寡妇则以她的财富和柔弱的外表来凌驾于年轻人之上,她不断地要求年轻人对她忠诚付出,使得年轻人欲罢不能。如果欧洲人是怀着征服和殖民的目的来到这块土地的话,那么华裔男性在这块土地上的经验则是以被奴役、被殖民、被女性化开始的。很多华工和华人移民终于意识到金山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福地。通过改写神话,汤亭亭挑战了传统的美国梦,解构了迷人的金山神话。E.珊·胡安说金山神话不过是谎言:“‘金山’是华人给美国所起的神话般的名字,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财富、自由和幸福等的渴望。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华人旅居者和定居者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各种压力使他们不堪忍受。这使得‘金山’这个醒目而有趣的地名失去了它神话般的光环。”[5]
三、“论死亡”“再论死亡”:打破沉默的神话
在“关于发现”中,女人国的妇女们威胁唐敖如果不保持沉默的话,就要缝住他的嘴巴。沉默的规则以及打破沉默的主题在接下来的两则神话“论死亡”“再论死亡”中得以延续。在“论死亡”中,杜子春被道士邀请,去帮助他炼长生不老药。在炼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无论杜子春看到什么,都必须保持沉默。杜在幻象中忍受了各种折磨,但最后一次试验中他被变成一个哑巴女人,当他/她看到丈夫要把自己的孩子往墙上撞时,他/她惊叫起来。杜子春能够忍受欢乐、痛苦、愤怒、恐惧和邪恶,但他/她战胜不了爱。这使得人类不能长生不老。后一则是波利尼西亚神话。爱开玩笑的莫伊想从夜神希娜那里偷得让人类长生不老的东西。他首先教人、禽、兽和众万物保持寂静,然后他趁希娜睡着的时候进入了她的身体,抓到了她的心。希娜醒来了,关上了自己的身体之门,把莫伊嵌死了。
这两则故事中的主人公个性不一:杜子春逆来顺受,而莫伊调皮并且有反抗精神。但他们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两者都力求寻找使人类长生不老的东西,两者都自愿遵守沉默的规则(杜子春自愿遵守道士的规定,而莫伊则主动要求万物恪守沉默);两者都忍受了痛苦和折磨,都为此做出了牺牲;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些神话的寓意很明显。正如学者高燕所说:“沉默是一个有关死亡的传统比喻。”[2]72如果沉默的规则过于严厉,那么遵守它就等于精神上的死亡。在沉默中生存是很不自然的,是生不如死的生存之道。两则神话作为能指有着共同的所指:为了生之意义有必要打破沉默。这两则神话与小说历史层面伯公和阿公的经历相呼应。伯公为了自己更为了其他华工们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他不仅在实际意义上,而且在比喻意义上打破了沉默的规则。总之,这紧紧相连的两则神话呼应了小说里家族的历史故事,强调了打破沉默的必要性,驳斥了华工们只不过是逆来顺受不知抱怨的刻板形象。
四、“鲁滨逊历险记”:开拓者的神话
鲁滨逊的神话揭示了华工是西部的开拓者这个主题。汤亭亭改写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使其归化为鲁滨逊的神话。在“论死亡”和“再论死亡”中,作者暗示了打破沉默的重要性,以及反对关于华人逆来顺受沉寂无声的刻板形象;在“鲁滨逊历险记”中,她暗示了华人在异国他乡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忍受痛苦并且有创造的勇气。[6]既然金山没有随处可以捡拾的金子,华人们就必须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金山”。他们意识到所谓的金山神话不过是一则具有欺骗性的美丽谎言。然而,他们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神话变成现实,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鲁滨逊是殖民者、征服精神、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象征。汤亭亭把这个文学形象归化为一个神话式的华裔先驱——鲁滨逊。像作者的曾祖父和祖父一样,鲁滨逊沿海而居,深深地理解大海的广阔与无垠。他每天都听到大海永不停息的倾诉,就像海在召唤他。沿海而居的人们天生具有冒险精神,鲁滨逊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经营家族的生意,而决意要出外闯天地。他命中注定要辛劳一辈子。
鲁滨逊是汤亭亭创造的一个典型的华人形象。他是一个“苦力”,他辛苦劳作,而美国却不把他当人看。那时美国法律禁止华裔女性进入美国,也禁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华工们没有家庭,不能生儿育女,住在由华人男性组成的单身社会里,所以他们被美国社会看成没有性别的骡子。把华工们描述成没有性别的骡子并不是汤亭亭的首创。早期的华人移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金山挨骡仔。”
然而作者的真正意图不是把鲁滨逊描写成一个负面形象。她接着指出鲁滨逊名字的另一层含义:“‘Lo’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罗汉’里的‘罗’;像‘阿罗汉’,像‘菩提达摩’”[3]233。众所周知,在中国佛教的寺庙里供着罗汉或菩提达摩,中国人把他们尊为圣人。这种文字游戏揭示了鲁滨逊作为圣人的一面,他是令人尊敬的。作者接着改写鲁滨逊的故事,把他放到华裔美国人的语境中。船触礁以后,鲁滨逊被海水冲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孤岛上。他没有一味地等着救援,而是从坏船上弄回了大米、大麦、小麦、笔、墨、纸、枪支、弹药、斧头、锯子等有用的东西。储藏纵然丰富,他也不准备仅靠它们生活。他开始在这个陌生的海岛上辛勤工作。他用捞回来的文房四宝(中国的笔墨纸砚)记笔记。他种豆子做豆腐,像中国南方的农民一样种水稻。他做陶罐、做面包、驯服一只鹦鹉,并寻找可以代替文房四宝的东西。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人的脚印,他赶忙巩固了自己的藏身地。后来他看到一群野人在吃他们抓获的俘虏,鲁滨逊搭救了一个俘虏。由于这天是星期五,他就给俘虏取名“星期五”,并教星期五广东话。鲁滨逊在这个岛上待了28年,他开荒种树养山羊。天长日久,他对这个小岛不再陌生。他用紫色和红色的墨水记载他在岛上所做的一切,他成了“他自己小岛的君主”。[3]236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罗汉。
《中国佬》四代家族男子故事中的曾祖父、祖父几代人大抵从事体力劳动,以淘金、铁路建筑等为职业赚取微薄的工资寄回国内以养家糊口,甚至致富。但这些人从未想过要在海外定居,一则因为在他们的时代,排华风潮此起彼伏,他们很难在国外立足,比如铁路修好之后,中国工人即遭到残酷驱逐和杀害。二则在他们意识里,安土重迁的习性,落叶归根的观点占很大的比重。比如与祖父一起在内华达山脉中开山修路的华人在开凿隧道时死伤无数,当冰雪融化后,“遗失的工具,开始解冻的尸体,有的手上还握着工具站着,铮亮的铁轨,一切都一目了然”[3]237。临死前还能喘口气留下遗言的人说:“‘别留下我在雪下挨冻。把我的尸体运回家。烧掉它,把骨灰装在一个锡罐里。你们下山的时候,把我的骨灰也带下山。’‘你们坐火车到中国后,告诉我的后代到这里来看看我。’……‘哎呀!葬在这里等于死无葬身之地。’‘可这儿是个了不起的地方,’祖父保证道,‘这里是金山,我们正在这块土地上做标记呢。每条轨道都编了号码,你的家人会知道我们把你留在什么对方的。’但祖父是个疯子,他的话没有人会听。”[3]265华人临死前的嘱托道出了中国人对死亡、对家乡的观念,认为人死后只有躺在家乡的土壤里,有子孙祭祀,才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几十年的异国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在美国生根,他们所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而到了父亲一辈,则费尽心思进入美国。一则因为中国当时的战争状态,局势很危急;二则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进入美国的不同版本实际记述了好几种进入美国的方式,很有代表性。但是他们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着中国文化传统。
通过改写鲁滨逊的故事,汤亭亭颠覆了一则广为人知的神话,重构了华裔美国祖先的神话。首先,她挑战了美国“开拓边疆”的神话。在“关于发现”中,作者把女儿国的地点移到了北美,并暗示发现女儿国的年代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甚至有可能更早,即公元441年。她通过改写神话而质疑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哥伦布和亚美利哥发现了美洲,并提出中国人早在此之前就发现了这块大陆。用同样的方式,她质疑了美国一贯的神话,即白人开拓了美国西部。这个白人们乐于相信的神话无情地抹杀了华工们在美国西部所做的巨大贡献。在历史层面,作者叙述了华人祖先们在西部的艰辛劳动和不懈努力;在神话层面,她声称华裔移民也是美国开拓边疆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鲁滨逊开垦荒岛使自己成为“小岛之王”的经历反映了早期华工们开发美国荒野的经历。伯公和其他华工一到夏威夷就发现那儿没有现成的农场供他们劳作,他们终于开垦出一个农场。作者把他比作唤醒睡美人的骑士:“一日,像骑士营救公主一样,伯公将浓密的灌木丛全部清除。”[3]101阿公与其他华工一道砍树开矿建铁路。他们帮助美国打开了西部。伯公在夏威夷耕耘土地,就像把睡美人从沉睡中唤醒一样;阿公则在比喻意义上征服了美国的土地。在这两个故事里,华工与美国的关系不再是仆人与女皇的关系了。他们不再是被有权有势的女皇(美国)奴役的唐敖,而被描述成“美国边疆的开拓者”。无论是在历史层面还是在神话层面,作者都似乎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哥伦布、亚美利哥以及其他欧洲殖民者一样,华工也是新世界的征服者。因此,他们也应该是美国开拓边疆神话的一部分。通过改写,作为殖民者原形的鲁滨逊变成了华裔美国人鲁滨逊的神话。不可否认,他是新世界的祖先。
五、“《离骚》:挽歌”:悲剧的神话
由中国古典文学中屈原的故事改编而来的“《离骚》:挽歌”还暗示出华裔移民的情感困境,他们寻求家园的痛苦,以及他们文化身份的复杂性。“《离骚》:挽歌”一反将中国人视作没有灵魂的群氓形象,把他们刻画成了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个体。屈原是一位诗人,是战国时代忠于楚王的一位政治家。屈原力谏楚怀王不要和秦国开战,结果反而在国内招来不少诽谤。接着,他失君宠、遭流放,在心灰意冷中,流浪天涯,最后投汨罗江而死。[7]中国人为了纪念屈原,从此开始了赛龙舟、吃粽子的活动。据说,赛龙舟是为了把鱼吓跑;投进河里的粽子也是喂鱼的,这样可保证屈原的身体不受打扰。汤亭亭认为这就是“龙舟节”的起源。
汤亭亭重述屈原故事的目的在于反映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她非常强调诗人感情的痛苦和去国怀乡之情。屈原的困窘在于他既不能回到祖国,又不愿羁绊于浪迹所至之处。一方面,“他对祖国的爱得不到回报”;[3]265另一方面,他所到之处人们并不欢迎他、理解他,因而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弃儿。在一首诗歌里,屈原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却从卜测者那里得不到任何的答案。他陷于两难之地找不到可以调和的办法,于是毅然选择了投河自尽。这个神话反映出许多华裔美国人的窘迫处境。在这种意义上,“《离骚》:挽歌”从神话的层面上揭示了中国移民的复杂身份,它是一首华裔美国人的漂泊离散之曲。
六、结语
综上所述,汤亭亭的《中国佬》不再仅仅是一部四代华人移居美国的家族史,而是升华为一部华裔美国人的移民文化史。通过分析《中国佬》对6个故事的改写,可知这6幅画面不仅是对传记故事从神话层面上做出的回应,而且彼此互相关联,构筑了一个华裔美国人的神话。通过改编中国古典文学、英国文学、中国古代神话以及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故事,汤亭亭借历史和神话故事颠覆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美国神话,如美国梦(金山神话)、开拓者神话等等,同时还就征服荒凉艰险的美国大地、修建华人自己的金山等壮举建构出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