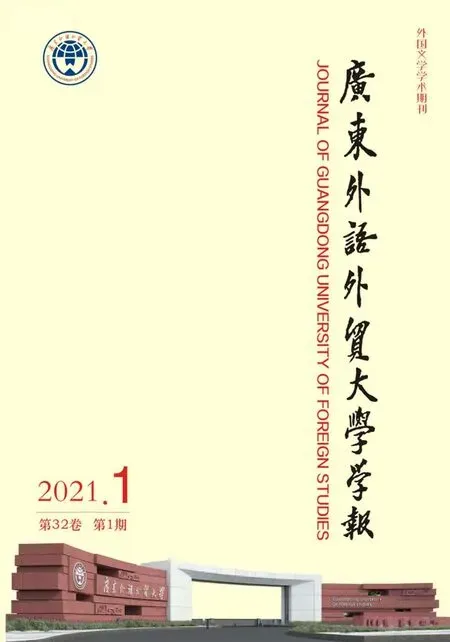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后种族”时代背景下的黑人女性身体叙事
——托妮·莫里森《孩子的愤怒》解读
2021-03-25王丽丽
王丽丽
引 言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关于美国进入“后种族”(post-racial)时代的论调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甚至人文研究学术会议上也频繁引用这个词语来争辩奥巴马当选总统是否意味着美国不存在种族差异了(Babb,2010:35)。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当代一些黑人艺术家和领导者的成功证明:在美国不论肤色,只要努力都有可能摆脱种族的桎梏,获得事业的成功和美满的生活,因此美国社会已经摆脱种族主义的牵绊。波利卡普·艾库诺布(2013:447)提到,“后种族”时代,人们潜意识理解为“种族差异不存在了,超越了将人根据种族特点分为不同的群体并区别对待的种族划分的时代”。
事实是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后,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并没有消失,因此众多学者对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的论断持反对意见。“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二倍”,黑人在租房和寻找工作时经常遭到歧视,“一旦他们的种族身份明确了,他们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Goldberg,2015:41)。黑人更容易成为偷窃、贩毒、杀人的怀疑对象。2014年美国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圣路易斯市弗格森镇遭白人警察枪杀、埃里克·加纳在纽约遭枪杀、塔米尔·埃里克在克利夫兰市遭白人警察枪杀,引发了“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大规模种族抗议活动。特别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非裔美国人仍是美国所有族裔群体中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陈后亮,2020:71),而在此期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跪压颈部窒息而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关注。这说明,“后种族”主义 “不是种族主义的终结,是种族主义扩展而来的新的种族观念”(Goldberg,2015:24)。 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以一些细微巧妙的形式存在并流行”(Ikuenobe,2013:447)。以隐性微妙形式存在的种族主义被谢罗·皮德尔(2015:2)称为“美国当下一种不同类型的种族主义——‘看不见’种族的种族主义”。“看不见”是因为美国社会重组的权利关系,有目的地不让人们看见,用“后种族”的概念试图消除过去的种族历史,实际上,种族主义以人们不容易识别的方式依然存在着。
“后种族”的“后”不是代表时间先后关系,而是“对先前种族观念的修正和重新赋义”(翟乃海,2019:71)。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以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为代表的美国非裔作家再现了美国当代的种族问题。莫里森反对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的观点,她在《每日电讯报》访谈时也指出,与其相信种族主义消失了,不如看看它以哪种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种族问题不是静止不变的”(Wood,2015)。莫里森反对“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和非裔美国人已经从阻碍他们自我实现的社会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论断(Bennett,2014:152)。她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孩子的愤怒》体现了她的“后种族”观念,即当代的种族主义以隐性的、多变的、复杂的多种形式存在于美国社会。莫里森着力于黑人女性的身体叙事解构了“后种族”时代话语,与奴隶制和民权运动时期女性身体被虐待、被殴打、被强暴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不同,当代黑人女性身体遭受的是隐性的冷暴力,女性身体成为光鲜亮丽外表伪装下供人消费的商品,男性凝视下的客体。
“后种族”时代的女性身体冷暴力
莫里森在《孩子的愤怒》(GodHelptheChild)中以现实的手法否定了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的观点。她刻画了生活在当代社会的美国黑人女性,她们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后种族”时代。但是社会现实却与她们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她们的身体不断受到不同形式的侮辱和暴力。莫里森对女性身体的描写使读者认识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对黑人群体,尤其是黑人女性造成的身心伤害仍然广泛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
《孩子的愤怒》的女主人公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将名字从卢拉·安改成布莱德(Bride),将自己由一个受母亲嫌弃、漠视的黑人女孩变成一位经济独立、年轻、漂亮的黑人女性。她是一个成功的广告经理,跻身于白人社会,这似乎暗示黑人同样能够获得美好生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这一切光鲜亮丽却掩盖了她遭受种族歧视,承受种族暴力的事实。与《宠儿》中塞丝受到毒打,身体留下伤疤显性的身体暴力不同,布莱德身体遭受到隐性的、看不到伤疤的冷暴力,即“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对对方恶意诋毁、讽刺挖苦、冷淡漠视、歧视疏远、侮辱恐吓等”(张翼杰,2014:110)。“后种族”时代的种族矛盾不再是白人对黑人直接的身体暴力,而是内化了种族主义的黑人群体内部的彼此伤害。布莱德的父母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了深黑肤色人种遭受的暴力和歧视,他们坚信肤色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拥有浅肤色或者白皮肤就等于拥有了尊严、拥有了地位、拥有了摆脱种族歧视的特权。正因如此,布莱德遭受到来自亲生父母的身体冷暴力和身体规训。
在莫里森的其他作品中,作为母亲的黑人女性“用身体作为抗拒策略,用被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家庭”(史敏,2013:76),如《宠儿》中亲手弑女的塞丝和《恩惠》中卖女为奴的悯哈妹。但是深受种族歧视伤害的母亲甜蜜(Sweetness)深信肤色决定命运,面对深黑肤色的布莱德,她刻意疏远和女儿的关系,故意漠视女儿的存在,拒绝碰触女儿的身体,甚至拒绝给她喂奶,“给她喂奶就像让一个小黑崽子吮我的奶头,一回到家,我就改用奶瓶喂她了”(莫里森,2017:5)。即使给女儿洗澡时,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用打满肥皂的浴巾擦一擦我的身体,然后冲掉而已”(莫里森,2017:31)。即使她犯了错误,甜蜜也“总有不碰撞她憎恨的皮肤也能惩罚我的法子”(莫里森,2017:31)。
甜蜜对布莱德深黑色身体的控制和规训也证明她将种族主义渗透到对女儿的养育过程中。米歇尔·福柯(1999:155)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蓄奴制时期,黑人的身体属于白人,受到白人的控制。在美国当下社会中,黑人女性获得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但是种族歧视思想依然以某种形式对她们身体实施严厉的控制。首先,肤色政治导致了黑人群体内部歧视:肤色越浅,受到歧视越少,越有优越感;反之,肤色越深,就越遭歧视。对于浅肤色的布莱德父母来说,她的身体“黑得发蓝”(莫里森,2017:5),好像是罪恶的标记。对于甜蜜和她的丈夫路易斯(Louis)来说,浅肤色使他们在肤色政治的世界中拥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尊严”(莫里森,2017:4)。显然,作为黑人在社会中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浅色肤色,这是他们享受接近白人一样待遇的特权。而布莱德的出生破坏了他们迄今为止一直享受的浅肤色的特权。对布莱德的父亲路易斯来说,刚出生的女儿是“敌人”,连甜蜜也认为女儿的出生“毁了我们的婚姻”(莫里森,2017:6)。布莱德深黑色的身体让父母无法接受,互相指责。在肤色不同、命运不同的社会中,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尊严”。路易斯抛妻弃女,离家出走,虽然甜蜜最后和女儿待在一起,但她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故意疏远布莱德。
肤色政治决定了黑人女性身体在社会中的等级,进而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深黑肤色的布莱德没有任何优势条件,甜蜜无法改变女儿的肤色,就通过限制她的身体和行为实行以“保护”为名的身体规训。她声称,“我必须严厉起来,非常严厉。卢拉·安需要学会乖乖听话,低眉顺目,不惹麻烦”(莫里森,2017:8)。她没有注意到这样严苛的教育使女儿内心充满自卑、胆小,失去作为黑人的自信和自豪。相反,她把严酷的身体行为规范教育看作是生存的工具。在甜蜜看来,规训布莱德的身体是为了防止她受伤害。她反复强调教育女儿的必要性,否则女儿“可能会因为在学校里顶嘴或是打架就被送进少管所;招工时人们最后一个考虑你,裁员时你却是第一个倒霉的”(莫里森,2017:45)。甜蜜对女儿的教育似乎是为了让女儿能够在社会上被认可和接受,实质上她是对女儿身体和心理的压抑,反映了她内心根深蒂固对深黑色肤色的厌恶。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于身体的认知越来越趋于理性化,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谦, 2019: 110)。与蓄奴制时期赤裸裸的身体冲突暴力和身体规训不同,当代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以微妙的形式仍然对黑人女性的身体实施冷暴力及以保护和教育为名的身体规训。作为母亲,甜蜜刻意避免接触布莱德的身体,这导致女儿幼小心灵上爱的缺失,产生了病态的心理渴求,甚至希望通过犯错得到母亲的毒打实现与母亲身体接触的目的。母亲对女儿身体的厌恶和刻意疏离同样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生难以愈合的创伤。甜蜜对布莱德的身体规训造成她内心的不自信,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导致她为了博母亲一笑,在法庭作伪证,愧疚感一直萦绕内心难以摆脱。
白色消费文化中女性身体的商品化
在宣扬自由平等的幌子下,当代美国社会似乎模糊了黑白肤色的差异,但事实恰恰相反。白人文化意识形态中固有的破坏力量规训黑人女性的身体,使黑人女性迷失自我,进而强迫黑人接受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揭示了黑人,尤其是深肤色的黑人,无论男女,他们的身体在美国白人霸权文化中成为取悦白人、供白人消费的商品。布莱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主要原因在于她听从白人设计师的建议,用白色包装自己,凸显黑人女性身体独特的美,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商品。
戴维·斯沃兹(1997:1)在《文化与权力: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中论述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文化为人类互动和交流提供了基础;它也是控制的源泉,不论以分配、客体、系统、组织哪种形式存在,文化都包含权力关系”。因此,文化成为统治者驯化社会成员的权力工具。美国社会中,白人文化通过传播“自然化”,即“种族现象是自然发生”(Bonilla,2017:56)的价值观念让美国黑人承认其文化劣势,从而实现对黑人精神上的奴役。这一驯服过程体现在营造白人文化优越的文化空间,使黑人对白人文化无限崇拜与向往,产生对黑人文化的厌恶和困惑,如《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柏油娃》中的雅丹及《孩子的愤怒》中的布莱德。
米歇尔·福柯(1999:187)指出身体是“权力的客体和目标”,对黑人身体的控制和规训体现了白人文化利用权力实现对黑人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乡下长大的卢拉·安若想在商业化浓重的加利福尼亚生存下去,她必须从内而外地改变来迎合白人文化的消费取向。首先,她为了谋取销售职位改变了带有乡村气息的名字卢拉·安并“缩短成了‘布莱德’”(莫里森,2017:12)。布莱德这个名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的简短发音更时尚,似乎更符合商业化的城市中成功女性的命名方式;另一方面Bride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新娘,结婚时新娘必须穿白色婚纱,暗示布莱德必须包裹在白色的外壳中,才能被白人的审美价值观念认可,才能获得进入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广告世界的特权。接着布莱德将自己的身体改造成时尚商品,成为白人热衷的消费品,从而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这说明黑人女性的身体需要迎合白人文化的价值理念包装改变之后才能获得与白人一样享有所谓的平等与自由。
布莱德在工作第一次面试时因其外貌遭到拒绝,但是在“整体形象”设计师杰瑞(Jeri)(莫里森,2017:36)的建议下,她全身只穿白色,在第二次面试时不但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公司中迅速晋升。杰瑞认为布莱德 “太黑”的肤色“不同以往……更像‘好时’巧克力酱”“巧克力蛋奶酥”“奥利奥”“手工糖果”(莫里森,2017:37)等受欢迎的食品。黑人女性身体被比喻成畅销的商品,成为满足欲望的食品。“构成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提供了思想的模型和类型,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完成的”(Bob,et al.,2018:81)。从这个意义上看,杰瑞对布莱德的话语已经蕴含了将她的身体变成商品的含义。他努力将布莱德打造成一种引人注目富有吸引力的商品,尤其是“奥利奥”的比喻,暗示黑色肤色下面被洗白的内心。在杰瑞的话语中,黑色与甜品广告联系起来,这些甜品能够增加食品的风味,暗示女性身体的价值在于成为增添美感、增加乐趣、愉悦白人的商品。
作为形象设计师的杰瑞,依据白人的规范和白人的想象规训布莱德的身体。他让布莱德只穿白色的衣服,杰瑞的设计使布莱德成为白色的奴隶,色彩主义的奴隶。斯托克顿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衣服尤其是白色衣服就是“人造的,第二层皮肤”(莫里森,2017:44)。他的建议迫使布莱德为了获得成就感而拥抱白人文化,“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犹如穿上一件衣服。穿上这件外衣代表一种时尚,也是一种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Bonilla,2017:77)。因此,布莱德穿的白色衣服实际上是白色权力编制的文化外衣,只有包裹在白色外衣中,布莱德才能超越种族的界限。白色与她的深黑肤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加强了她的“商品视觉感”(Delphine,2016:8),她的“黑皮肤是种卖点,是这个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莫里森,2017:40)。身着白色的布莱德与她深黑肤色形成强烈对比,杰瑞通过白色衣服不但凸显了布莱德的与众不同,还制造了肤色主义的等级。布莱德的身体受到赞誉,黑色的身体被商品化,因为她黑白对照的美可以愉悦白人,这也是她身体的商业价值所在。因此,黑人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文化空间中,黑人与众不同的美成为愉悦貌似文明的白人的商品。
杰瑞对布莱德的身体包装和身体比喻揭示了“后种族”主义的谬误,因为他继续通过动物形象凸显黑人女性身体的吸引力。杰瑞看布莱德不带任何配饰的身体更“像冰里的黑貂,雪里的黑豹”(莫里森,2017:37)。杰瑞将布莱德的身体比作糖果(Bonbon),是bonobos 一词的变体,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最常与黑人及其性行为相关的灵长类动物,突出黑人女性强壮野蛮的刻板形象,是对黑人女性身体的贬损和歧视。布莱德黑色的身体成为带有食物和动物性质的商品,成为满足白人欲望和需求的消费品。她的身体陷入白色文化包装的困境,只有这样她的黑色才能被接受,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奴隶制时期,黑人的身体被盖上章确定他的归属,在美国的当代社会,黑人的身体仍然被白人文化刻上消费品的名签。同布莱德一样的黑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不经过包装,保持本色的黑色身体,这样就受到歧视,难以融入美国社会;要么经过白色包装,披上白人文化的外衣,这样就失去本色沦为白人的消费品。
从文化的视角看,种族主义在美国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仍然以各种不同形式控制驯化黑人女性的身体,导致黑人女性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布莱德试图逃脱肤色政治的阴影却陷入对白色的痴迷,白色文化的价值观念将她束缚在身体商品化的牢笼中。为了在主流文化中生存,迎合白人文化中理想的审美,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布莱德夹裹在白色外衣包装的虚假空间中,将自己身体变成愉悦白人的消费品。这充分说明“后种族”时代的种族主义通过文化社会空间将黑人女性身体客体化、商业化。
男性凝视下女性身体的客体化
白人文化将黑人女性身体变成炙手可热的商品,而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又将她们身体变成男性凝视下的客体。长大的布莱德经济上独立,拥有豪宅豪车,似乎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但实际上女性的身体“受到男性权力运作的诱导,沦为男权社会的他者和客体”(金美兰,2018:360)。布莱德依靠杰瑞的白色包装改变自我外在形象,靠销售化妆品获得事业成功,她将这些视为女性独立解放的手段,但是她忽略了外在包装实质上是控制女性身体的手段,也就是罗伯特·戈德曼(1992:121)所说的“商品化女性主义(commodity feminism)”,即“男性凝视的评判力内化为女性自我监管自恋式的凝视”(Goldman,1992:130)。长期在男性价值影响下,女性已经内化了男性的审美观念,自觉地改变身体以获得男性的认可,满足男性的欲望。
作为形象设计师的杰瑞将布莱德包装成迷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有黑人文化特点的黑人女性形象。杰瑞作为男性设计师,他深知男性的需求,因此他对布莱德身体进行改造,凸显布莱德的性感和黑人民族特征,使她成为男性文化的消费品。布莱德受制于白色为美的着装规范和取悦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念,彻底地沦为男性的客体。经过杰瑞的改造,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迈着大步,走得缓慢而坚定。男人们如饿虎扑食般袭来”(莫里森,2017:40)。布莱德的身体给男性带来愉悦,成为男性的玩物。与她交往的男性要么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简单粗暴,让人在虚拟环境中享受人畜无害的兴奋感”(莫里森,2017:40),要么享受征服她的身体带来的成就感,他们把她“当成奖牌,是对他们英勇战功闪亮而沉默的证明”(莫里森,2017:40)。布莱德只是男性消遣逗趣的对象,他们只对她“怎么打扮感兴趣”(莫里森,2017:40),从没有哪个男人将她视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布莱德的身体满足了男性的审美欲望和性欲望,成为男性施暴的客体。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她也获得了虚伪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内化的男权价值观念使她放弃自己女性的主体性,沦为男性的附庸品和消费品。
即使后来她认识了男朋友布克(Booker),他们的相处也停留在肉体和物质关系上,布克对布莱德来说是一个“谋生手段未知、谜一样的男人”(莫里森,2017:13)。布克从不称呼她的名字,而是喊“我的女孩”,“重音落在‘我’上”(莫里森,2017:13)。布克不以名字相称,说明他没把布莱德放置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在称呼时重点强调“我”字,体现了他对布莱德的占有关系。布克与布莱德分手时没有解释,只留下一句话:“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莫里森,2017:9)。布克的语言不仅是对布莱德感情的伤害,女性主体身份的否定,更等同于对她身体实施的暴力。离开了男性的欣赏和依附,布莱德质疑自己“不够热情?不够漂亮?”(莫里森,2017:9-10),甚至自责经济独立“威胁到了他的自尊”(莫里森,2017:14)。内化了男权价值观念的布莱德认为,作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取悦于男性,而自己让布克感到作为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才决定与她分手。布莱德说出了黑人女性容易受伤的共同原因,黑人女性的成功威胁到男性的威严和地位,使男性丧失了两性关系中的主体核心地位,这就会打破固有的两性关系平衡。
事实上,布克的离开否定了布莱德的女性身份,使布莱德不仅不再是他的女人,而且不再是女人。布莱德身体的退化阐明了男性凝视在建构黑人女性身份中的作用。布克的离开将布莱德从一个富有魅力、成功的黑人女性变成了一个胆小的、“要融化了”的小女孩(莫里森,2017:9)。布莱德的美貌需要在男性欣赏的目光中得到认可,即“男性驱动的女性美”(Ashe,1995:36),失去了男性,成熟女性的身体特征也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布克离开的第二天,布莱德突然发现“阴毛一根也不剩”(莫里森,2017:14), “自己的胸平了”(莫里森,2017:103),“月经诡异地推迟了”(莫里森,2017:105)。所有这些作为成熟女性的身体特征随着布克的离开都消失了,布莱德也意识到“不是在他离开后发生的,而是他的离去导致的”(莫里森,2017:104)。失去男性的欣赏目光和依附,成熟女性的身体特征也不复存在了。当布莱德见到布克,两人的关系和解,布莱德的身体又恢复了成年女性特征,首先是她“可爱、饱满的胸脯”(莫里森,2017:183),然后就是她“怀孕了”(莫里森,2017:192)。布莱德的身体随着与布克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说明男性对女性身体和女性主体地位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莫里森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布莱德身体变化,强调性别观念是导致当代美国黑人女性身体客体化的主要原因。
结 语
莫里森在《孩子的愤怒》中通过主人公布莱德的身体叙事,揭示了“后种族”的谬误,旨在展示种族主义在当代美国社会对黑人女性身体、感情、精神方面产生的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否定了当代美国的“后种族”时代已经到来,种族歧视已经消失的观点。肤色政治依然致使黑人女性遭受种族观念造成的冷暴力;白人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使女性身体沦为白人的消费品;男权观念让女性身体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成为男性的附庸。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性别视角看,宣布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后黑人”“后女性”的时代还为时过早。莫里森对布莱德身体变化的描写暗示广泛存在于黑人社区的种族主义的深远影响,文化暴力和父权政治仍然是黑人女性种族意识和身份建构的最大障碍。通过这部作品,莫里森表明:“后种族”不是种族无关紧要,不是种族歧视已经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