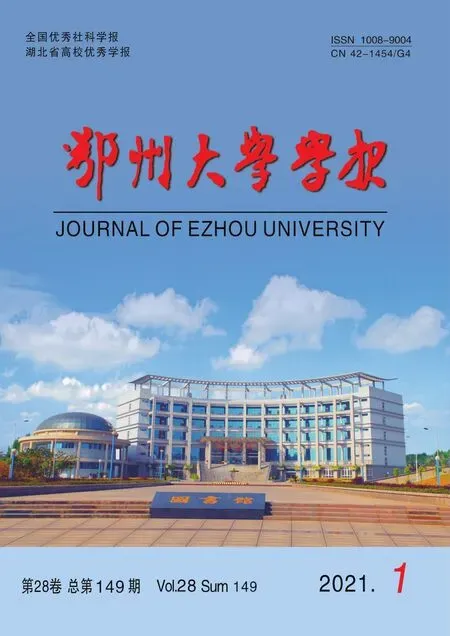《史记》的文学语言研究
2021-03-25孙溪
孙 溪
(西安石油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5)
《史记》是我国不朽的历史巨著,是倾注司马迁心血的文学著作,也是对我国史学、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瑰宝。在文学创作层面,《史记》采用纪传体的方式,将情、理、事充分地融为一体,形象生动地借事达理、写人叙事,借理抒情,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司马迁杰出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的艺术加工、文学语言的细致刻画及思想理念的深入融合,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及严谨的创作方法,为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通常来讲语言是文学创作的核心机理,是表现文学张力、渲染文学氛围、承载文学思想、坦露文学机理的关键载体,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语言艺术上拥有较高的造诣,具备独特的风格和审美张力。其中审美张力主要指两种不同的语言元素相互统一、相互对立,并形成对立的整体,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中,能够看到两者相互映衬、相互比较、相互冲击、相互抗衡的关系。譬如长短句、雅言俗语等,虽然在语言内涵上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但在相互映衬与制约下,却能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效果。
一、长短句的参差之美
司马迁的《史记》语言富丽多彩,变幻莫测,诸多线索错综交错、巧言妙语纷至沓来,独居匠心之处,可见一斑。而在条理清晰、井然有序之中,短句与长句的参差相间,构筑了《史记》语言的张力之美、行为之美、节奏之美及韵律之美。在轻缓如流水、急促如暴雷的行文风格中,司马迁能够将人物形象、情感抒发及思想理念呈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深折服其中,感受到《史记》深厚的思想价值与文学魅力。通常来讲长句主要指“结构复杂、词汇多的句子”,拥有表意细致、精确、严谨、周密的特征和特点,可以将所有的语言元素、信息元素及旁门杂类的信息全面融合到句子表述中,使阅读者更全面、更有效地获取信息。譬如《高祖本纪》中“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便将人物的经历、事件发生时间,人物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语言精湛短小,但内容复杂深邃。[1]又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一句“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於汉”,不仅交代了时间,更交代了王朝的地理位置,所属关系,在节奏上轻缓自在,从容有序地明确了战国时期的主要势力及各自的实力关系。而《伍子胥列传》中“楚平王以其边邑锺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於两国举兵相伐”则将复杂的历史事件浓缩为简短的长句,使读者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发生背景。[2]而在短句应用上,司马迁可谓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通常来讲,短句主要指“结构简单、词汇少”的句子,拥有灵活、明快、简洁的特征及特点,《史记》中的小句、短句普遍出现在场面紧张、主题抒发及情绪表达等场合中。譬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3]便展示了蔺相如与秦王对峙的情景,将蔺相如慷慨赴义,舍身救国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韩信卢绾列传》“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中,作者则用四字短句,将事情的经过进行表述,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巧妙地融入到事件表述中。[4]其中“遂陷无道”有“点睛”之妙处。然而在《史记》中较为常见的句式风格是长短句错杂并用,这种错杂的句式结构,富于变化,能够构建出疏朗之美,使文句更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譬如在《韩信卢绾列传》中“汉十年,故胡骑复与韩王信入居参合,距汉。十一年春,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便表现出清晰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二、体态与对话的灵动之美
《史记》的语言精湛、鲜明、流畅、自然,富有韵律之美、节奏之美、参差之美及对照之美,对后世戏曲创作、小说撰写有鲜明的影响和贡献,能够创作出性格化、个性化、特色化的语言体系。而根据语言学理论研究能够发现,语言层次与人的层次,能够反映出人的学识、职业、修养、性格等特征,比外表形象更真实、更内在,所以语言是人类的第二形象。《史记》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对人物语言进行反复斟酌及深入思考,明确了历史人物在思想情感交流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体位变化、姿态变换及表情动态,使得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更具有节奏美与艺术美。其中对话语主要指人物在历史事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特征、形态及内容。体态语则指历史人物姿态、表情等描述话语。在罗伯特·麦基的《对白的解刨》中,对白包括两个层次,即表层和潜层,表层即说出来的话,潜层即隐藏在语言、动作、表情中的内心动态、心理情感、主观诉求及人物思想所呈现的载体。这些潜层要素是通过身体姿态、表情特征进行表达的,通常与表层所呈现的语言内容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司马迁的《史记》便鲜明地表现了体态语与对话的对立关系,如《酷吏列传》中,酷吏面对高后的苛责时,内心惶恐不安,却假作镇定,说道:“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然而在对话描写及之后的事件描写中,能够发现酷士所言与所想相差甚远,完全是在应付高后。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话语言却直接地将人物的内心情感,思想状况及个性特征直接呈现出来,譬如在《西南夷列传》中,汉使和夷王会面时,夷王是这样问的:“汉孰与我大?”此句虽短小,但简洁精湛,将夷王目空自大,嚣张跋扈的气焰表现得入木三分。然而更多的时候,对话语与体态语是相互映衬、相互依托出现的,如《高祖本纪》中,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如是尔”。将不同历史人物的情感和身份呈现得鲜明而透彻。此外,在语言的应用过程中,语言的模糊性被不断地凸显出来,譬如相同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及情感内容。如果不加规制,将导致文章缺乏严谨性,极大降低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而体态语能够有效弥补此类问题,通过添加人物的动作、神情及姿态动作,使对话表述更加鲜明,同时也能结合上下文,深化人物的情感思想。在这里,体态语和对话语则表现为统一的整体,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提炼文句的精髓。譬如《淮阴侯》中一句“少年有侮者曰:‘中情怯耳,好带剑……’”体态语“有侮”能够鲜明地提示出对话内容中的讽刺意味,暗示读者少年所言之物,并未流连于表面。总体来讲对话语能够有效反应历史人物的气质、性格,体态语则能更深入地表现人物的个性、思想,两者存在相互补充、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
三、雅言俗语的语言之美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运用了大量的雅言,更引入了诸多的俗语、俚语、典故,能够在严谨的历史诉说中,增添文章的层次感、结构感及艺术感。并将自身对人物的憎恶、喜爱及是非态度融入到文章叙述中,提升了《史记》的思想内涵。《史记》篇篇精美、字字珠玑,是司马迁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的苦心力作,同时也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散文佳品。在文学语言上,司马迁充分发挥了文学语言借景抒情、借物咏志、借古讽今、刺贪刺恶的功能,将讽刺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为有效地呈现自身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之情,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及思想情感,司马迁通常将民间俗语与古代典籍融合在一起,以正式与俏皮相融合的方式,讽刺并挖苦历史人物。譬如《李将军平原列传》中“下自成蹊,桃李不言”便是借助民间俗语,讽刺李将军为人。而在文学效果、艺术表达及思想呈现等角度,官方雅言与民间口语、俗语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托的关系,雅言者高之而寡,俗语者俗之而广,通过运用雅言,能够有效地提升文章的正视性、规范性、严谨性及说理性。而引入俗语,则使文章浅显明晰,简单易懂,适宜推广。正所谓“雅俗共赏,秋水一色”,《史记》能够有效地将雅言与俗语融合成系统统一的语言体系,使文章富于动感,使民间语言独有的魅力得以呈现,使官方雅言在多变的风格下,更显得“高风亮节”。而雅言与俗语的矛盾性、冲突性又使《史记》充满了张力美、动态美及人文美。
《史记》行文语言拥有长短句参差错落、对话语和体态语相互映衬、雅言与俗语相映成趣的张力之美,能够通过不同语言艺术、层次及思想内涵,提升叙述语言的结构美、节奏美、韵律美与形式美,使《史记》流传千古,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