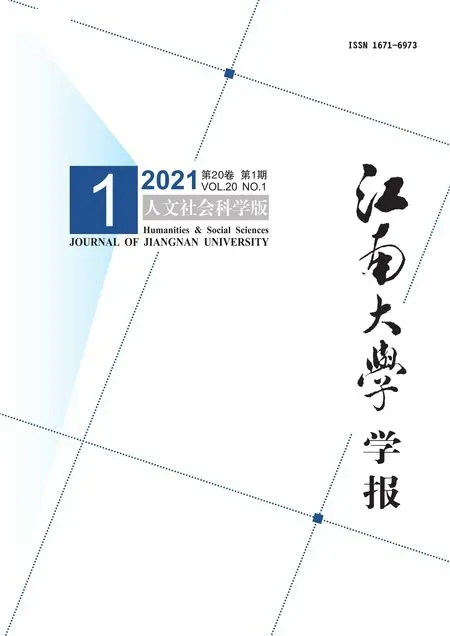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派文学”的批判
2021-03-25方汉文
马 宾, 方汉文
(1.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1;2.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明研究中心,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条顿狂”的民族主义与“世界精神”之间的关系
威尔斯所说的“机械革命”所促成的世界管理与安全的新需要,其实就是工业文明的世界秩序。按照当代学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的“工业革命”时代划分,第一次工业革命处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早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延续到1840年”[2]。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8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指出,工业化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打破了民族工业的闭关自守,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变化。马克思特别提出了“世界的文学”概念,这里的“文学”包括了文史哲与意识形态,即精神生产。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一如既往来自于实践,其中就包括了他们批判十九世德国民粹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这种批判的对象正是威尔斯所称的“民族主义”与“帝国”观念,其核心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文学。马恩在批判民粹主义与黑格尔世界主义思想改造中,建立起了工业文明中的“世界的文学”学说。
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推动了欧洲新秩序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宣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德国陷入长期分裂之中。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在《最后总决议案》中明确决定成立由奥地利主持的“德意志联盟”,由奥、普等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从那时起到1848年于法兰克福举行的国民议会,一直在商讨德国统一事宜。这三十余年是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尤其是19世纪初到30年代,被恩格斯称为“条顿狂”的作家歌颂历史上的条顿人(Teutones)所坚持的日尔曼民族精神、神圣罗马帝国甚至中世纪十字军的战争,以基督教神秘主义为主要思想,以德国封建贵族的复辟作为德国统一的理想;他们打着“统一”的名号,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一股歌颂“德意志精神”的逆流。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次“民粹派文学”风潮,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派”互相呼应。无论是德意志派还是斯拉夫派,都是欧洲民粹主义文学的主要推动力。
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德国分裂为纷乱的大小城邦,经历了长期分裂,在工业革命中远落后于西欧的英法等国。19世纪前20年间,部分文学青年特别是莱茵省与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新作者们,已经不满足于浪漫派作家所表现的颓废与低沉,而是以作为德意志国家光荣镜像的祖先——条顿人为豪,他们在创作中对内赞美旧日的封建贵族统治时期,对外则要求法国归还亚尔萨斯等占领地区。这是一种打着“德国统一”旗号的民族主义文学,其精神主旨是仇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一方面肯定海涅等具有历史进步精神的反分裂的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则严厉批评在德国统一名义下的民粹派文学,特别是被称为“条顿狂”的民粹派作家。这一时期,马恩的“世界的文学”思想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之中,从最初对黑格尔“世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扬弃,直至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业文明时代“世界的文学”思想。此时也恰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之际。而到1859年4月著名的“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发表时,则是马恩用“世界的文学”理论分析了拉萨尔悲剧《弗朗茨·封·西金根》,指明其根本缺陷是主题思想追求“宗教自由”与“国民统一”,是一种“国民戏剧”,这种追求其实是一种“席勒主义”表现,即把自己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从文学思想上延续了民粹文学的余脉。剧本反映的骑士精神与封建贵族冲突在工业革命时代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拉萨尔剧本主题是具有民粹思想余绪的“国民戏剧”。
恩格斯的“条顿狂”批判集中针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代表性作者:阿伦特、斯特芬斯与明采尔。首先是以艾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的《回忆录》为对象,称其为“条顿狂”的德国民粹主义文学。他认为“条顿狂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抽象”[3]148,“条顿狂”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德意志精神的恢复与解放,但是却并没有发扬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进步方面,而只不过是宣扬黑格尔的民族自我中心论的“日尔曼主义”。所以从文艺思想主题角度来看,这种文学是地道的德国民粹派文学。而形成这种“条顿狂”思想的历史观念则是复古的,其主旨精神是要返回中世纪德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种反对工业文明的封建复辟思想。当时德国正处于迈向工业化与退回封建社会的十字路口。而“条顿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托伊托堡林山的初期条顿精神的纯正中去”[3]148。其实日尔曼民族的祖先从罗马时代起就受到排斥。古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没有能征服日耳曼民族,而对于罗马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文明人,日尔曼人被认为是野蛮人。直到公元9世纪的查理大帝时代,日尔曼民族才成为欧洲封建文明社会的成员。公元962年,鄂图受教皇加冕称帝,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从此德国人将“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精神象征,也成了“条顿狂”的偶像。19世纪30年代前后,德国经济开始转入工业革命初级阶段,德国人所憧憬的帝国形象在受到民粹派膜拜的同时也成为民主派攻击的目标。另一方面,“条顿狂”是反对工业文明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的,他们反对的具体对象就是当时具有进步性的法国思想界。“应当更加坚决地反对条顿狂的另一个倾向,因为目前它在我们这里又有占上风的危险——这就是仇视法国。”[3]157
当时存在德法之间的领土纠纷,围绕亚尔萨斯与洛林的归属之争,德国与法国之间关系紧张。而民粹文学则渲染对法国人的仇恨,攻击法国与法国大革命。民粹文学将德国的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归之于法国大革命。这当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所以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恩格斯指出,亚尔萨斯问题的最终解决要取决于亚尔萨斯人民的意愿。因为亚尔萨斯人现在仍然享有在欧洲列强之间的“自由社会生活”,如果德国要求其归于德国,“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那以前,我们可以安静地让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问题”[3]159。这里所说的“世界精神的发展”的概念虽然出自于黑格尔理论,但此处所指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化,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实行封建制度的德国处于分裂且落后的状态,而且它不能促进亚尔萨斯实现工业化,那么它是没有权力来要求亚尔萨斯归属于德国的,更没有理由指责经历了大革命的法国人。恩格斯指出,德国当时的任务是统一德国,“只要我们的祖国仍然是分裂的,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不能彻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3]159。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立宪制度、出版自由与“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要求,而这些都是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政治目标才是德国所要去追求的,而不是去“消灭法国人”。
英法两国通过产业革命在欧洲已经率先进入工业文明,而亚尔萨斯地区的未来应当是工业文明,而不是中世纪或是罗马神圣帝国式的的统治,恩格斯对此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所以,德国的文学应当是具有“世界精神”的文学,应当以歌颂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应当破除民族主义思想壁垒,推动世界贸易和工业化的发展,构建起世界的文学,而不是民粹派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文学。
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邹市明卫冕奥运拳击金牌,贵州省领导留他再打一届全运会。“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他写了一份退役报告,一份辞职报告。“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他形容,“我人生梦没有去完成的话,我觉得有遗憾。”4个月后,邹市明和妻子前往美国。
二、伊麦尔曼、容克与马恩的“世界历史”
1830年以后,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条顿狂”的势力和影响迅速衰落,民粹文学从形式上也销声匿迹。但实际上民粹主义思想却在继续发酵,形成更有隐蔽色彩的文学形式。1840年,在文学创作活动活跃的莱茵省,伊麦尔曼的《回忆录》出版了。伊麦尔曼是莱茵省诗人群体中的中坚分子,虽然他本人对相对保守的莱茵地区并没有很深的好感,但是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较大,极具莱茵人所喜爱的创作风格,所以被推举为莱茵地区的代表性作家。伊麦尔曼也是浪漫主义作家,但他的创作风格多变。他的《模仿者》受到歌德的较大影响,风格宁静,具有德国人喜爱的田园诗风。而他的另一部作品《缪希豪森》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现代诗风。而《回忆录》则又是一种变体,以历史叙事风格写就,而且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一方面采用现代诗句形式,另一方面则呈现了作者自己当年的田园诗风与复古主义思想。作者认为,他的诗之所以这样写作,是采取了一种“现代德国人”的立场;而当时德国社会思想分为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德国民族主义,另一方则是世界主义;而他本人则是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德国人的。他的作品讴歌德国民族主义,批评德国人“缺乏自信、曲意逢迎和卑躬屈膝”的生活态度。这种德国式的民族精神批判与民族主义既是互相对立的,同时也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赞扬过歌德创作的进步意义,同时也批评过歌德身上有德国人“庸俗的辫子”;而哥德的这种两面性在伊麦尔曼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回忆录》从作者的童年写起,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并且反映出1806年普鲁士复兴前后的历史变化。作者所要表达的是,旧的家庭中青年为家人所宠爱,而学校教育使青年变得孤立,离开了家庭的温暖;文学教育则使青年进入一个广阔的天地,但是社会中同时又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
因此恩格斯指出,在伊麦尔曼的作品中“社会变了样,社会生活作为崭新的因素出现了,文学、政治、科学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深入到了家庭中去,家庭却很难安置所有这些陌生的客人。全部问题就在于此!家庭里旧习惯还太深,它不能同外来客人取得谅解,友好相处”[3]171。恩格斯赞赏其对旧制度与旧家庭生活的批评,他说莱茵省是德国思想最活跃并且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地方。伊麦尔曼比较了新旧生活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变化,揭示了封建德国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艰难处境,他认为虽然这一进程是痛苦的,但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是无可阻挡的。
同时恩格斯还认为作者不完全是“条顿狂”式的民粹主义者,“他毅然拒绝似乎是他最接近的那个倾向——条顿狂”[3]173。恩格斯虽然从他身上看到了以前“条顿狂”的某些特征,但仍然公正地评价了他只是“最接近”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条顿狂”。肯定他介于“浪漫主义”与“普鲁士精神”之间,前者在他的散文中代表一种死板的样式,而后者则形成一种漫无节制的敏感。而最终这两者都会对国民的心理越来越漠视,以致完全脱离人民。同时代的德国作家都会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关于哲学的观点,如同其他人一样,伊麦尔曼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涉及了哲学家费希特的思想观点。他描写了费希特的演讲场面,其实质是肯定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德国19世纪哲学,虽然这种描写只是细微末节的刻画,与作品主题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恩格斯遗憾地指出伊麦尔曼虽然受到当时进步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是其思想离黑格尔相距较远,甚至达不到“老黑格尔”的思想体系的高度。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相信,现代青年已经从黑格尔的学校毕了业,他们并不害怕斗争,而且坚信会迎来新时代精神。所以他们将这种仍然具有“普鲁士精神”的文学,看成是民粹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这是切合德国当时的历史语境的。
除了对诗和散文等民粹派文学创作实践进行批判之外,恩格斯还对民粹主义的文学史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大·容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这部文学史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现代事物”,什么是现代事物呢?容克主张为黑格尔哲学与青年文学。但是他本人并不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深义,而只是将黑格尔哲学说成是一个大杂烩:无神论、自我意识万能、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等等。青年文学则是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消失的“青年德意志派”文学,容克将“青年德意志派”说成是“现代事物”的主体。其实这个“青年德意志派”文学确实曾经发挥过一段时期的进步作用,但并非如容克所说每个人都是杰出的作家。恩格斯多年来一直注意观察“青年德意志派”,并且写过评论来分析其中的谷兹科夫等代表性作家。恩格斯认为,关键是容克其实以一种媚俗的态度来对待现代德国文学,一方面是吹捧过了气的“青年德意志派”来表明自己发现了新事物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则是暗中有意遗漏了一些真正勇于揭露现实的作家,对真正有新思想的作家如贝尔涅等,则加以攻击与贬抑;最重要的是,对黑格尔的解读完全是哲学门外汉的议论,其中就涉及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点。对黑格尔而言,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其对内和对外政策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实现。
这里恩格斯提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尤其是早期著作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中,流行最广的是见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文字:“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有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68
黑格尔1822年开始系统讲授《历史哲学》课程,直到1837年,黑格尔逝世之后7年,《历史哲学讲演录》由他的学生甘斯整理出版。其中有关“世界历史”概念的阐述立即引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其进步意义以及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性:“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5]这里所说的唯心论历史观,主要就是指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黑格尔运用其一贯的总体系统论,把世界历史说成是东西方各个民族的精神自我实现;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东方向西方的时空递进,亚洲是起点,而欧洲是终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过是其唯心论的“世界精神”的实现过程,而不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且他的世界历史与世界精神,都是最终以日耳曼民族精神作为终结的。所以这种理论不仅是唯心论的而且是民族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也都对《历史哲学》的辩证发展观念与独特的历史哲学观念予以极高评价,恩格斯在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说:“他(黑格尔的)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3]540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世界历史”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将客观唯心论的观念结合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历史唯物论的创新。马克思较多地使用“世界历史”概念来谈及19世纪中期。这个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指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在大工业生产的推动下,产生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联系,客观上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世界的文学与文化。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这是我们的科学上根本重要的一点,而且必须从本质上把它牢牢把握在思想中。这种区别既在基督教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由’)的原则上吸引了注意;它又在‘自由’的一般原则上,同样表现为一种主要的区别。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6]
而马克思在阐释自己的关于世界历史的观念时,坚持了唯物论观点,明确提出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4]51-52
可见就历史认识论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背道而驰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的“自由”,是纯粹理念的发展史。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的、个人生存活动的历史。那么,精神的作用是不是完全取消了呢?马克思强调,在社会中人人都在进行思维,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时,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但是,无论是何种精神占统治地位,世界历史不会成为精神发展史。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论述过世界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当然,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并不是完全以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为依据划分世界历史阶段,而是从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规律来考虑。主要是依据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世界历史。从马克思起才真正把东方社会即亚细亚作为重要因素纳入“世界历史”概念的。而且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有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特殊的,只为亚细亚民族所具有。但是这一历史阶段同时也具有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说,这种形态也可以在其他民族中存在。这观念看起来费解,其实是相当精确的,即一种特殊的历史规律却可能成为共同的发展规律。它并非机械地重复发挥作用,而是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来实践这种历史规律。
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观念是世界历史观上的一个决定性变化。马克思实际上已经从全球文明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规律。而把东方文明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来考虑,也就是意味着,西方所经历的世界历史阶段,在东方国家同样会出现。马克思的预言在他身后一个多世纪终于成为现实。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率先进入工业革命。亚洲的现代化模式引领了东方现代化文明的到来。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文明道路上大步前进,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都承认:世界历史是多元的,东方文明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并不是部分美国学者如福山等人不承认东方现代化,而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习惯于从西方中心或是民族自我中心来研究世界历史,同样没有把东方国家如中国、新加坡、韩国等的现代化看成是东方文明现代化,而只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东方化”,实际上这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认识是从社会生产体系来看世界历史,他认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从大工业时代开始的。但是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体化的历史,而是存在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最根本的意义并不是海外探险,也不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由于交通所引起的接触,而是大工业化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曾经使用过一个词——“交往”,这个词原义包括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这个词以后被哈贝马斯等人所使用,马克思以后并不经常使用它。马克思使用较多的仍是生产,真正形成世界历史的标志是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
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明确否定了黑格尔的“精神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成为世界历史的关键是世界性的生产关系的建立,而不是精神观念。只有以大工业与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化,才把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各民族的壁垒无不会被打破,不是被内部的力量所打破,就是被外来的侵略所打破,世界历史时代不会允许闭关锁国的古老帝国存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是宝贵的精神武器,可以用来批判民粹派所依据的黑格尔“世界精神”“世界历史”。实际上,也正是在马恩世界历史观烛照下,在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中,19世纪德国民粹派才最终土崩瓦解。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世界的文学”,这是处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文学,而工业文明时代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工业革命中,德国19世纪民粹派文学已经成为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封建贵族迷梦,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一切封建势力都因其“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而受到社会的嘲笑。
三、以马恩“世界的文学”重论拉萨尔《弗朗茨·封·西金根》之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名言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7]275-276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增加了一则编者注:“‘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7]276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有所不同的,此处文学的概念范围更为广泛,超出了狭义文学的范畴。
《共产党宣言》发表十年之后,拉萨尔将自己的悲剧作品《弗朗茨·封·西金根》寄给马克思与恩格斯请他们阅读和点评,马恩分别给他回信并且对作品提出了批评。这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研究话题,从苏联到中国的马列文论专家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1个世纪,尽管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因为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拉萨尔悲剧中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理论关注。现在我们可以从马恩“世界的文学”概念出发来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关于“民粹派文学”的历史与余脉的新观察。我们可以从“拉萨尔悲剧”的研究历史中找到一个新的途径,以“世界的文学”作为一种独有尺度来分析民粹派或民族主义思想文学的历史延续,并提供一种新阐释。
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剧本最重要的是冲突,而拉萨尔所选择的主题并不适合于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冲突。因为当时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德国的工业文明与封建贵族社会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世界历史当中的新冲突,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冲突。而拉萨尔的主题却远远落后于时代,他所选择的是旧式戏剧冲突形式——骑士对封建贵族的起义,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冲突,而不是新时代的现实主题。于是马克思说:“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8]572马克思认为“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8]572由于主题错误,所以全剧的内容完全不对,马克思指出:“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8]573-574
马克思所说的“宗教的自由”与“国民的统一”其实并不只是拉萨尔悲剧的思想主题,而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它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初期与中期的“条顿狂”以及其他各种民粹派作家、民族主义作家们的作品。马克思绝对不能容忍这种陈腐的、歌颂封建贵族时代精神的主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借尸还魂,更不能让其在1848年革命之后延续。《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世界的文学”,指出工业文明将冲破一切传统民族国家的壁垒,克服民族的片面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在这一伟大进程中,拉萨尔的充满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的戏剧简直是与时代背道而驰。在马克思看来,这不过是民粹文学在新时代的思想延续。恩格斯同样认为,拉萨尔的戏剧不过是一出“国民戏剧”,由于忽视了农民的因素,所以也将贵族的国民运动表现得不正确。恩格斯批评拉萨尔戏剧忽略了悲剧最根本的要点——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而拉萨尔恰恰根本就没有抓住这个要点。拉萨尔所写的骑士反叛贵族,与德国现实当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历史斗争完全无关。德国在统一后即将步入工业化时代,这时候再讨论所谓的封建贵族精神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理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但拉萨尔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写给他关于剧本的信后,竟然又分别写信给两人,反驳两人的批评,为自己辩护。马克思在1859年6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到拉萨尔写给自己的反驳信:“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功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8]432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德国民粹文学一直持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拉萨尔在欧洲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竟然写出这样的民粹文学或者说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戏剧,虽然他们之间书信来往和观点交流颇为频繁,但是这也令他们极为反感,尤其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世界的文学”概念之后。
而且有一个细节也必须提醒大家注意,马克思这里再次使用了“世界历史”的概念,此处的“世界历史意义”如果理解为《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最为适宜的。他们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无视工业文明的历史时代巨变,仍然囿于德国“骑士起义”与“贵族镇压”的“国民戏剧”,使其创作重拾民粹派文学的陈旧主题,沉迷于对德意志封建时代的怀念。
与拉萨尔的“国民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十分喜爱德国作家海涅。他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在诗中表达了对封建德国的强烈反感。作者在诗中借用纺织工人织进对“老德意志”的“三重诅咒”来表达对德国封建专制的憎恨和决绝态度,这首诗曾受到恩格斯的肯定与赞扬。
综上所述,如果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19世纪民粹文学的批评联系起来看,可以展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个崭新视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以前研究的重要理论点,包括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世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改造、马恩提出的“世界的文学”的重大文学理论价值、以及中西理论界讨论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拉萨尔悲剧的批评”,都会有关于历史语境与理论观念方面的突破性发现。这些新发现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当下的世界历史走向尤其是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在改革大潮中找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