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阈下《边城》
2021-03-15李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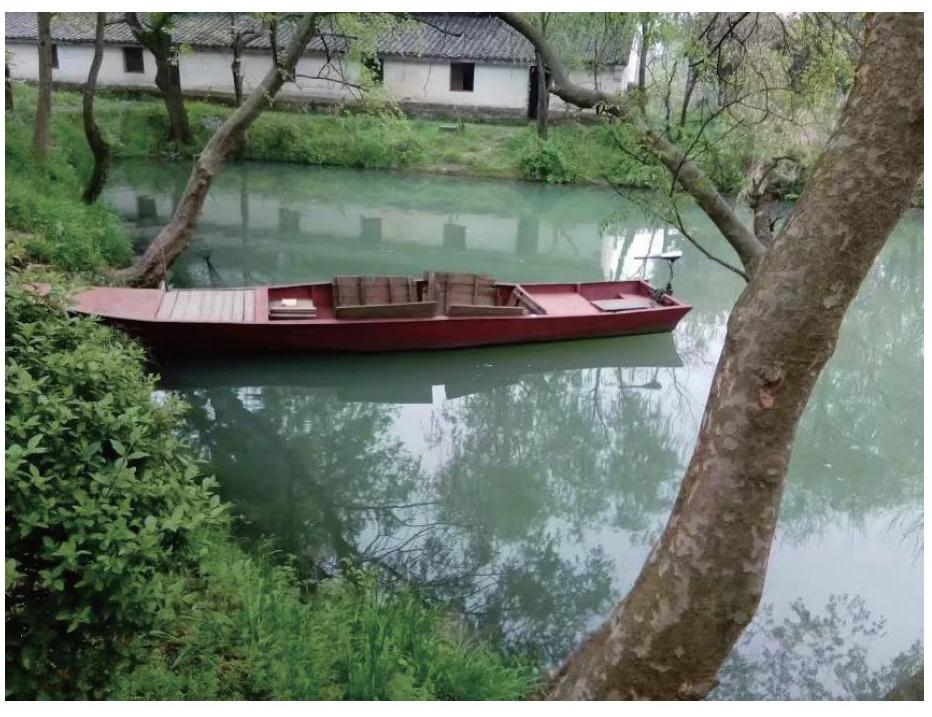


摘 要:“空白”与“未定点”增添着作品的含蓄美,激发着读者的想象力,给予读者更多的参与权与参与感。读者通过阅读时的文本重建,不断产生着并改变着自己的阅读期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边城》是一部存在多处“空白”与“未定点”的叙事作品。这些“空白”与“未定点”的存在,让读者对《边城》的人物与故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知,也让作品的意义得到了充分增殖。
关键词:接受美学;《边城》;空白;未定点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湘西小镇茶峒上翠翠与祖父的亲情故事以及她与天保、傩送两兄弟的爱情故事。自从《边城》问世以来,学者们对其多有讨论,探讨了翠翠与老船夫的人物形象、作品中蕴含的生命主题、作品表现出来的湘西地方特色风情等。但对其创作手法尤其是作者在作品中运用減笔、删削、语言的含混等手法所产生的“空白”与“未定点”,研究相对较少。金圣叹曾言:“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1]即作者未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无”的部分往往更精妙奇特,更能体现作品的意义。而接受美学也认为:“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致文学作品的实现。”[2]本文主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边城》的文本“空白”与“未定点”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沈从文《边城》隐藏的审美意蕴。
一、“空白”与“未定点”的基本内涵
继承并发展了英伽登空白理论的伊瑟尔认为,空白“是从文学本文的不确定性中产生出来的。……它表示存在于本文自始至终的系统之中的一种空位,读者填补这种空位就可以引起本文模式的相互作用”[3]。这里的“空位”,也可以理解为“框架”。朱立元在他的《接受美学》一书中指出:“文学本文只提供给读者一个‘图式化方面的框架,这个框架无论在哪一个方向和层次上都有许多‘空白。”[4]22空白在古今中外的文本结构中随处可见,它是文本因叙述的中断而造成的、没有明确写出来或表现出来的部分。如中国古代的《陌上桑》一诗,诗人对秦罗敷的外貌就进行了空白处理——未明确写出她的美貌,而用“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其他人的表现来反衬罗敷的美,激起读者的好奇。可见,这种艺术的空白“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虚而不空”[5]。
所以,空白是作者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架起的无形的桥梁。而据伊瑟尔的观点,空白的形成又与作品中留下的许多“不确定的点”密切相关。这种“不确定的点”即伊格尔顿所谓的“未定点”,它是“指作品言语意义含混模糊与传达信息的不确定”[6]69。伊格尔顿认为:“任何一部作品,不论它多么严密,对接受理论来说实际上都是由一些‘空隙构成……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一些看来靠读者解释的成分,一些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或许矛盾的方法来解释的成分。”[7]也就是说,“未定点”能够“一”中生“多”,即通过单纯的确定的语言表达出多重的不确定的意味与信息,产生含混的言说效果。如《孔乙己》中,鲁迅写到“孔乙己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大约”与“的确”是两个程度不同的词语,用在一起让文章显示出矛盾与张力,传达出不确定意味的同时体现出鲁迅自身的矛盾心情。在《阿Q正传》中,鲁迅并没有指出阿Q真正的姓名,而是用字母代替,进行模糊处理,让读者对阿Q及其行为所映射的对象产生了无穷的想象。
事实上,接受美学的“空白”与“未定点”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早已广为存在。晚唐司空图誉之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一种“不写之写”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不直接呈现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是让读者自己想象,进行体会与感悟。如《红楼梦》中秦可卿、贾蓉与王熙凤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充分体现着“不写之写”的含蓄美。其它如古代文论家提到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虚实结合”等,也都表述着接受美学“空白”和“未定点”的艺术功能。总而言之,“空白”的存在让读者发现无字句处的美妙,而作品中“未定点”的存在则丰富了叙事内容,让故事人物承载起更多的意蕴。
二“空白”与“未定点”
与《边城》文本的意义增殖
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空白”与“未定点”,首先表现于时间交代上的空白。沈从文在小说中提到祖父“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8]3。作者没有明确交代祖父从二十岁开始的这五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而是通过时间的变迁暗示祖父任劳任怨,坚守渡船的美好品格。作者对翠翠的长大,仅仅是用“一转眼便十三岁了”[8]4来表述。在看到新嫁娘时,祖父说:“翠翠,朱家堡子里的新嫁娘年纪还只十五岁。”[8]42一方面,这是祖父对翠翠的暗示,表明翠翠也到了嫁人的年纪。另一方面,作者也暗示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的婚恋嫁娶观念。此外,翠翠母亲这一人物形象也能够体现出“空白”与“未定点”的表现手法。翠翠母亲在小说里共出现六次,但沈从文在小说中却没有明确完整地写出翠翠母亲的悲剧爱情故事。“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也懂在一些小处,使家中长辈快乐。也仿佛永远不会同家中这一个分开。但一点不幸来了,她认识了那个兵。”[8]28短短几句,即给故事的情节结构留下了“空白”:翠翠的母亲和军人是如何相识、相爱以及死亡的,作者都没有具体的、明确的交代,只是通过祖父之口含混模糊地讲述出翠翠父母的情事。他们两人在白日里对歌,就是这种对歌,唱出了他们的爱情,唱出了他们的女儿翠翠,但两人唱歌的具体场景、歌唱内容都处于空白状态——不写之写。《边城》的“空白”与“未定点”还表现于更多有关翠翠的叙事。比如,沈从文在《边城》中就空缺了翠翠与祖父在船总顺顺家过端午的情节,也省略了大老和二老为翠翠唱歌的具体场面,仅仅通过翠翠做梦摘虎耳草来表现她内心的爱情萌芽。作者对翠翠如此含蓄的心理描写,受到了学者刘艳琼的欣赏,她在《无言之美——论沈从文小说中的艺术空白》一文中赞叹:“这种心理的虚化处理,更是于它的空白结构中召唤读者回忆或憧憬最美好情感,读者在这里获得极其丰富的审美情感体验”[9]13。
作者在对杨马兵这一人物的描写中,也运用了“不写之写”的“留白”手法。在小说中,杨马兵这一人物形象很容易被忽视,实际上他是不可缺少的。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作者模糊地交代了杨马兵的事情,这无疑会改变读者对杨马兵这一人物的传统认知,让读者对这一人物以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的认识与了解。“到了下午,翠翠同老马兵商量,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再回碧溪来陪她。”[8]81从这里不仅可以推断出杨马兵为军队养马一生,更能够看出五十多岁的他在祖父去世后成了翠翠的依靠,他身上有着湘西人淳朴的美德。小说没有介绍杨马兵的家庭状况,对他的妻儿丝毫没有提及,只提到在他年轻时为翠翠母亲唱过歌。由此可知,杨马兵喜欢过翠翠的母亲,甚至可能为了翠翠母亲而终生未娶。看似是一个与翠翠没有太多关联的人,实际上却与翠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读者有足够丰富的联想。
沈从文《边城》中的一些叙事意象,也深具“空白”之美。沈从文没有直接讲述现代文明对湘西世界的影响,未曾直接表明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意象来进行含蓄的表达。例如《边城》中反复出现的白塔。韦勒克曾言:“一个意象反复出现就构成了象征。”[10]白塔在《边城》中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翠翠在白塔下玩耍,在白塔的阴凉中熟睡,她是在白塔下成长起来的,而白塔又是老船夫形象的体现,是老船夫精神人格的象征,这表现出翠翠是在祖父的悉心呵护中成长的,她的身上也具有祖父质朴的品格。白塔的倒下在与祖父的死亡相照应的同时,也象征着淳朴自然的湘西世界之坍塌、质朴人性之异化。再如《边城》中的渡船。傩送宁愿要渡船也不要王团总女儿陪嫁的碾坊,体现了湘西人重义轻利的美好品格。渡船在《边城》中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交通工具而存在的,而是变成了一种含蓄的表达,天保与傩送兄弟二人都有意接手渡船,含蓄地表现出兄弟二人都钟意于翠翠。此外,渡船也象征着高尚的民族美德。老船夫朴实慷慨,真诚待人,恪尽职守,用渡船接送来往行人五十多年,这是一种传统而美好的民族品德,年轻一代愿意继承渡船也“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理想和重建民族精神品格的祈愿”[11]。最后,渡船的消失,也暗示出质朴自然、美好的湘西世界的消失,“突出了作者寄寓的意蕴:美不会恒久,终会消失,总会有缺陷,使人愁郁的”[12]。虎耳草这一意象在现实与梦境之间交替出现,表现翠翠爱情意识的变化,也是作者“不写之写”的一个意象。作者省略了对翠翠内心的直接描写,将翠翠的内心情感外化为虎耳草这一符号,通过摘虎耳草这一行动来表现翠翠的感情波动。沈从文在作品中“不直接指明所表达内容,邀请读者参与其中,将‘含蓄艺术表达推向更高点,将‘含蓄意蕴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达到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9]27。读者通过对含混的意象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进行解读,无疑可以品味到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感受到更为深厚的意义,而这也正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增殖。
三、读者通过“空白”
与“未定点”对《边城》的想象与再造
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讀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13]文本的潜在意义须通过读者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文学文本是一种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结构,读者可以借助既有的文本和语言进行个人的自由想象和建构。读者们凭借想象补充文本中的空白,重新对文本的结构进行组建,这就是“召唤性”。朱立元认为:“召唤性是文学本文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成为读者再创造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4]25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讲述:军人想要翠翠母亲跟他一起逃到下游,但是翠翠母亲却未选择与军人一起离开。性格强硬的女子为何没有抛弃自己的父亲,与爱人远走高飞?为何在军人死后没有立即喝冷水,而是选择生下翠翠后才喝冷水死掉?这些“空白”与“未定点”导致的不确定性,激发读者进行自由的解读。小说中多次提到翠翠的一个可怕的、古怪的念头——假若爷爷死了。这种念头的产生表现出翠翠对于人生命运的隐忧。作者并没有明确写出翠翠精神世界的成长,而是通过她对一系列事情的思考来表现翠翠的成长。同时,翠翠经常想到的这个念头也与后文祖父真正去世时翠翠的镇静淡定相照应,“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抹澡”[8]139,她没有表现出慌乱、不知所措,在看似不经意间,翠翠不断地成熟。之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乃是因为:不同读者在这种开放式结构中产生着不同的感受与想象。
沈从文在《边城》中浓墨重彩地叙述了祖父与翠翠老少两代,而对中年一代却进行了轻描淡写的模糊处理。他之所以要这般选择用空白的方式进行叙事的搁置,他是想表现在湘西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一代代人的悲剧,一代代人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的状态。同时,“从思想意义上来说,‘留白祖孙之间本应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还暗示着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的生成伴随的是何等巨大的产前巨痛,象征着一种昂扬舒展的生命状态与现实世界的深刻矛盾”[14]。在《边城》的最后,沈从文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83他通过语言意义上的含混与模糊给读者传达出如此不确定的信息:傩送也许会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正是作者这样的“不确定性”叙事让小说的结尾呈现一种开放式的结构,使作品韵味无穷,让读者产生无穷的想象。学者樊尊贤说:“由空白与未确定的言语符号所构筑的文本,能带给读者更广泛深远的审美意味,并使这些空白与未定点的意味辐射延伸到阅读活动结束之后,让稳定的文本结构所蕴含的有生命力的审美对象继续在读者的意识中增殖或者衰谢。”[6]69沈从文的《边城》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上述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于“不确定性”的描述,无疑源自于他对生命“不确定性”的宿命般的隐忧。如祖父对翠翠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8]76祖父这样说,并不仅仅安慰翠翠:不必担心雷雨的到来,更是含蓄地表现出对翠翠未来生活的担忧。何平在《〈边城〉中空白的艺术效果》一文中就呼吁读者对翠翠的悲剧进行逆向思考,想象并思索翠翠即将面对的困难。而任何一个人读《边城》至篇尾,也无不从翠翠的故事中,体味着人世的不幸与悲凉。
四、结语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化的乐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质朴自然、完满自足,但是沈从文却在平淡的讲述中透露出一种悲悯情调。在文本中留下的“空白”及“未定点”,促使读者进行想象与思考:翠翠是否会安于现状,延续父母命运的悲剧;生活在湘西世界中的人们是否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是否已经让人们体会到了生存的困惑;在充满变动的时代大潮之中,固守宁静至上的湘西世界是否会出现现代性的断裂。沈从文作为文体作家,用抒情的笔调表现人们生命之美的同时,也擅长展现湘西人的生命之忧。生活在湘西世界中的人们表面上看来和平宁静,实际上却处于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处于生命的跌宕和不可捉摸的命运之中。正如王路所言:“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15]所以,读沈从文的《边城》,至少须有两个透视:一,从他笔下的田园牧歌中透视到人世悲辛;二,从他笔下的那些“不写之写”处体味人生难以言说的忧患。
参考文献:
[1]金圣叹.金圣叹全集(三)[M].曹方人,周锡山,标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93.
[2]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出版者前言4-5.
[3]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31.
[4]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狄昱吟.无声的召唤——文学中的艺术空白[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6]樊遵贤.论“文本空白与未定点”对读者鉴赏的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0(5):67-70.
[7]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16-117.
[8]沈从文.边城[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9]刘艳琼.无言之美——論沈从文小说中的艺术空白[D].温州:温州大学,2017.
[1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4.
[11]罗才平.《边城》“渡船”意象初探[J].荆州师专学报,1997(1):93-94.
[12]施军.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1.
[13]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5-277.
[14]邓琼.小议《边城》的“留白”笔法[J].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27-30.
[15]王路.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201.
作者简介:李雪,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