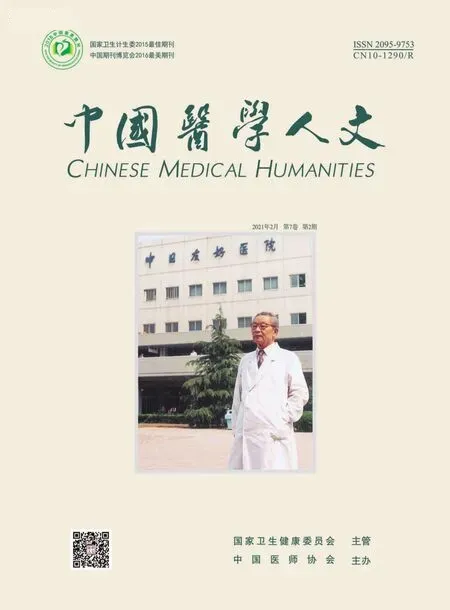医生的听诊器和作家的笔
2021-03-11周晓枫
文/周晓枫

1
假如妈妈不是医生,我就不会那么早见到生命的脆弱;假如不是被语文老师当众表扬作文,我就不会那么早体会到虚荣心带来的快乐;假如我不是小学就躺在手术室里等待开腹手术、十五岁就面部烫伤……假如不是这些必然或偶然的因素,我未必成为今天的写作者。
我爸爸是军人,我妈妈是医生。我小时候住在部队大院,每天见到小战士。他们处于最健康、体能最饱满旺盛的年纪,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强悍。妈妈所在的医院全国有名,所以我频繁见到从各地前来求助的病人。他们焦虑,哀告的脸上备受折磨,我看到太多衰弱到绝望的生命。我的童年,经常面对这两种反差极端的对比形象。
爸爸的军人职业和妈妈的医生职业看似冲突,但他们共同看管我,并且我也落到两者的融合体……军医手里。我多病,住过各种编号的军队医院,也不是那种生理上多重、文学上多抒情的病,其实就是各种零零碎碎的毛病。比如九岁竟然住了妇科,全麻手术摘取从母体带来的畸胎瘤。这个没有发育成的胚胎,一直寄存在我体内。它是天生的毛病,不是我个人的罪过。妈妈叮嘱我:“不要跟别人乱说,说你肚子里有个小孩。”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但那个被我视为警告的瞬间,让我的耻辱感过早发育,伴随像畸胎瘤那样因受伤而不正常发育的自尊。
小时候妈妈特别忙,很多医生都顾不上自己的孩子。现在回忆,简直像是虐待儿童了。很小的孩子,腰系绳子拴在床头,这样就能不摔到地上。我三岁多就在妈妈宿舍独自呆着,妈妈看病到中午迟归是常事。再大一些,小孩子们在食堂里自己打饭自己吃饭,都习惯了。独自度过的时光,让我觉得医院像座孤儿院,只是没有孤儿的孤儿院。我比较早地习惯了孤独以及孤独中的阅读。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作家?理由和道路各不相同。但许多人有着共性:特别的童年,对孤独和无常的体会,尊严和耻辱的过早苏醒,以及对阅读的热爱。
所以我说,没有妈妈的医生身份,没有被医生的救冶过程,我未必在童年就开始思考疾病与生死的意义,未必在成年后走上作家的道路。
2
大家知道,医生中有许多作家,身份几乎是交互渗透的。像心理医生和科普作家的著作,他们从来置身科学与文学的交界地带。且不说那些重要而有趣的医学科普作品是出自医生之手,因为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根本难以完成,且不说契诃夫和鲁迅最早都是学医出身,后来成为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就说今天中国最畅销的作家吧,数位都是学医出身,小说家里的余华,散文家里的毕淑敏,他们的作品都是最畅销的;连畅销书里的畅销书作家冯唐,都是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
医生与作家之间有许多相似,也有一些不同。
医生的手修补肉体,作家的手解剖灵魂。
医生面对一个个体,挽救一个家庭,帮助一个群体;作家塑造一群形象,建立一个世界,进入一个内心。
医生始终关切他人,由每个人的表征走向自己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以寻求解决之道,千万人走向一人内心;作家由内心出发,走向人和更广大的世界,一人走向万千人。奇妙的是,当我们互换,说医生从一己经验走向千万人,或说作家是千万人的经验进入一人的内心,说法同样成立。
我们说,医生针对人的生物属性,作家针对人的社会属性,但人的生物属性会受到社会属性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会受到生物属性的影响。无论医生药力的渗透,还是作家文字的渗透,都需要有效有益,都需要尽量减少负作用,完成对人体和内心直达毛细血管的影响和改变。
3
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文学编辑。有些作者觉得自己写得荡气回肠,遗憾于编辑看起来却无动于衷,我总是用俄罗斯的谚语来回敬:“在葬礼上流泪的人不适合做外科医生。”是啊,在我们的印象里外科医生仿佛有鹰的眼睛、狮子的心,似乎有种职业赋予的冷漠。但我们忽略了,不是所有的难过都是用流泪来体现的。外科医生必须从血肉模糊中判断创口和病灶,必须保持冷静,不能轻易心潮澎湃,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手术水准。这些不流泪的外科医生拥有必要甚至是必须的冷静与勇敢,绝非无情——他们也许不在葬礼上流泪,但他们所有的努力在于不想出席更多的葬礼,不想让更多的人在自己亲人的葬礼上流泪。医生的感性,可能是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就像作家的理性有时要以非常感性的方式呈现。因为作家不是卖保健药品的,他只能把菜肴做得色香味俱全,让读者主动地摄取营养。所以,医生和作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行业要求和行为模式。
对我来说,医生不仅帮助人们修补肉体,也解决精神上的困惑。我想拿疼痛这件事举例,来说明医生如何改变了我对痛感的理解。
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半夜腹痛。送到急诊室,各个科室或各个门类的医生轮流来看,询问患者和家属:哪儿疼?怎么疼?什么时候发现,现在状况是加重、减轻还是间歇性的持续?然后他们平静地开单子,检查吧。我眼看朋友疼得满脸汗水和泪水,再也说不出个完整句子,然后发不出声儿,只剩标点符号般的喘息和呻吟——医生重复性地询问却不提供治疗手段,我的失望逐渐转化为愤怒。医生竟然集体忽略患者的灾难,就让她那么活活疼着,哪怕给片止痛药呢,也算医院采取了治疗办法。我表面有抱怨的微词,心里简直想投诉。我能想象假设父母带着孩子看病,遇到类似情况导致的急躁、失智甚至疯狂。
其实医生疲惫,要应对急诊室层出不穷的情况,不可能像科普机构一样重在讲解基础知识,无法做到对每位病患都从ABC讲起,以平息他们由于紧张和无知带来的压力。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停下来两分钟,他解释性的回答让我立即闭了嘴。他说,如果盲目地给出止痛片剂,表面上是安抚,是见效,但会使病人出现欺骗性的身体舒适,导致无从准确判断发病的真正原因和具体情况,那才叫真正的贻误;有时,甚至必须让病人就那么疼着,使问题尖锐化,才能让容易混淆的病情逐渐被区分,从而达到对症下药的准确疗效。
我这才恍然大悟。后来,我妈妈因高烧急诊入院,她的反应特殊,本应剧疼的炎症她却毫无感觉。症状不典型,造成专家会诊时迷惑,判断不明险些拖延,好在后来把妈妈从败血症的危险边缘挽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最为畏惧的疼痛,也是一种对身体的守卫,对健康的提示——疼痛,就像为了群体安全放哨鸟发出并不好听但却保命的刺耳尖叫。
世界著名外科医生、美国麻风病专家保罗·班德,曾在印度投身麻风病的治疗和康复工作长达十八年之久。他在作品里写到一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麻风患者来说麻木带来危险,比如脚部筋腱撕裂却不自知的患者继续奔行,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截肢。所以,医生会反复修改去制作一双保护患者不受伤害的鞋子。有位住院很久的麻风病患者准备回家过节,要住两晚。没有疼痛的警告机制,什么尖的烫的都可能伤害他,所以做了充分预估的病人一路非常小心,终于得以团聚。第二天清早,病人例行检查自己,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食指被咬得血肉模糊,被一只老鼠咬破了。这件事后来影响了医院的规定,所有回家病人必须带一只猫同行。当时病人还要在家停留一夜,且店铺由于节日纷纷关门,买不到捕鼠器,病人决定一夜不睡,免得再次受伤。当晚他点着油灯读书,到凌晨四点越来越困,熬不住了——书掉到膝头,手滑到一侧,碰到了油灯的玻璃燃罩上。第二天早晨,病人绝望地盯着自己的双手:一只被游荡的老鼠咬坏,另一只被夜读的烛火灼伤。其实他更大的绝望在于,觉得自己对不起医生的辛苦付出。双手裹满纱布的病人对陪着自己一起流泪的医生哭诉:“我感觉完全失去了自由……我如果不能知道疼痛,我怎么能有自由呢?”
我从医生那里受到了教育,对疼痛有了新的理解。当然,不疼痛,可能是一生中的好运,尤其对处于中老年或疾病中的人来说,是非常隆重的礼物。但,我学习到了,疼痛也存在特殊的意义。
对于写作亦是如此。不疼痛、不焦虑、不愤怒、不恐惧的,未必是好文字,其中也许还潜藏巨大的隐患。有的作家下笔凶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她三十九岁就因红斑狼疮而过早离世,她有时显得恶毒而残忍。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作家?事实上她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生活显得比常人还要单调和墨守成规。有些作家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他们是在与人性的伤口打交道,背后同样是有时不被理解的善意和柔情。不错,弗兰纳里·奥康纳写了一些深洲与黑暗的故事,但她说:“能使我们看到黑暗的只有光,并且,我们所看到的光可能完全在作品之外。”
优秀作家写下的文字是疗救。不是说只有鸡汤才是疗救,为什么会有毒鸡汤之说?就是因为有些文字使读者的神经麻木。就像没有痛感并非健康,有时痛感才能保护肌体;作家的疗救,包括使读者不再麻木,不再浑浑噩噩,而是恢复丰富的感受能力,哪怕甚至是包括痛感。
4
我觉得医生的听诊器和作家的笔,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我的童年,简易听诊器是孩子普遍热衷的玩具,每个孩子都愿意去玩扮演医生的游戏。被听诊器金属诊头和胶皮导管传递和放大的声音里,一个陌生人的心跳会在医生耳畔,坦露他的秘密,他的节奏,他的心音里夹杂的力量以及流露的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笔也相当于医生的听诊器,他需要去探测人性隐藏的幽微之处,从中倾听灵魂里的力量与隐忧。
医生接触病人,作家靠近素材,无论有什么样的仪器和资料,你还是要尽量近对面对,而不是仅仅靠数据会诊、资料写作。我想起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在冬天看病的医生,总是习惯先用双手握一下听诊器,用掌心的暖意驱散金属的寒凉,然后再去触及病人的胸口。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医生就是不懂体察的记录仪器,难以真正疗愈生命;作家就是积累字数的书写工具,无法真正警示人生。无论多么强悍的作家,“妇人之仁”在写作里是重要的,它并不等于文学的软弱,而是一种对他人深切的疼惜与护佑。
5
我们总是让医生提供关爱,谁又来关爱医生呢?
医生也是血肉之躯,牙医自己也会牙疼,医生自己也会生病。医生不是万能的,把他们当作神是一种苛刻的为难。我们要承认人类医学的局限,有时药到病除是个事实,有时药到病除是神话,有时解除痛苦的过程伴随着超过疾病本身的痛苦,有时根本就没有药,有时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到病不仅不除反而加重的情况。医生每天要面对种种的复杂状况,有时难免受挫。
我们说,患者和家属在缺乏力量的无助时刻,容易缺乏理智和耐心……那么这些医生呢?除了治病救人的喜悦,平常又要面对多少超负荷的劳动,进行多少艰难的探索,冒着多大的风险,承受怎样的误解?当他们青春年少,是因为深怀爱意才选择这个职业,路途中却遍布现实的磨损。有时医护人员是在用自己个体的小小肉身,去背负庞大的医疗制度和医疗体系的不足,并且在承重中砥砺向前、不悔其志。他们是非凡而有着能力限制的天使,因为他们不断在做出逾越自己极限的努力,才能成为令人尊重的天使。
前一段,我准备看看凯博文的书《照护》。凯博文是精神病学、人类学、全球卫生以及医学人文领域最著名的学者,这本书讲述他的医学历程,并回忆他照护阿尔兹海默症的妻子十年。由于深厚的情感基础以及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亲力亲为地照护自己的亲人。虽然凯博文是非常有名的专家,具有强大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但照护妻子期间,他和任何一个病患家属一样的手足无措、身心俱疲,一边绝望一边盼望,有糟糕的沮丧也有暖心的慰藉。通过这些经历,凯博文更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护医者珍贵的初心。
我当时看的是这本书的电子版,出版社正准备印刷。“照护”,这个词不怎么用,看着有点怪。编辑曾让我帮着想想,能不能换个词。可想来想去,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性的常用词来概括它丰富的含义。照顾,缺了精神性;保护,缺了日常性。最后反复斟酌,编辑只能选择并确定这个词。它是由两个词语里各抽出一个字组成的,是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词。它描述出日常的关照与呵护,综合出那种既肉体又灵魂,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的感受。
医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包含着道德、伦理和哲学等等。凯博文照护妻子的过程经历过痛苦,最终照护的过程也是他梳理自己、理解他人并获成长的过程。写作《照护》,凯博文是三合一的身份,既是医生,又是病患家属,同时也是作家。他的所言所行,正如医生和作家一样——当他以内在的光源努力照亮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眼前的路也不再陷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