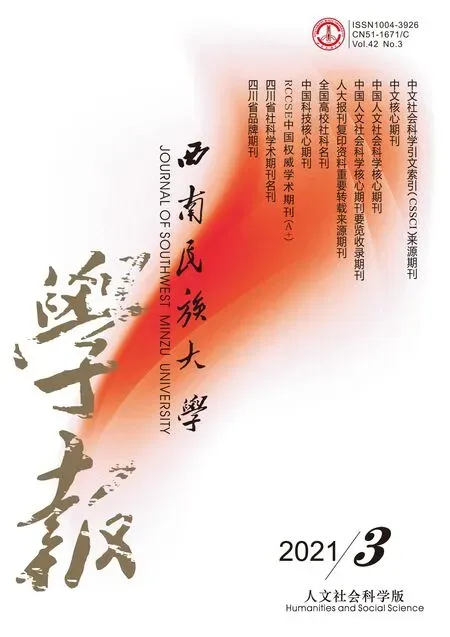言语行为革命视角下舆情治理类型研究
2021-03-10程中兴
程中兴
[提要]当前舆情治理研究大多聚焦于自媒体且有着较强的技术主义取向。然而,仅仅停留在自媒体去中心化、碎片化、超大规模等技术特征来理解当代舆情治理挑战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的革命性,只有达到思想与实在交汇的言语行为,才能真正成为舆情治理的挑战,所谓“言语行为革命”的真正意蕴也在于此。因此,当代舆情治理应回到舆情的言语行为本质上来,并从言与事的时间张力中梳理舆情演化类型与治理逻辑:如果“言”在“事”后,只是一种社会评价,则应保持足够的宽容与反思;如果“言”在“事”中,与主流话语“抢话筒”,则应及时提供有竞争力的话语以稀释其烈度;如果“言”在“事”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则应依据言论自由的四条边界判断是否需要实施媒介规制。当然,以上归纳只是韦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现实中的舆情治理往往处于杂糅状态。
一、当代舆情治理的三大挑战
如果说当代舆情治理与既往舆情治理存在着诸多差异,那么交往媒介变革无疑是最重要的区隔变量之一。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应“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时就曾指出:与2003年的“非典”时期相比,今天的媒体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那时,“尚不存在自媒体的概念”,“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媒体环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这种复杂局面,也是当今国家治理进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①。
从时间上看,“自媒体”(we media)与“非典”疫情似乎注定有“一面之缘”。2003年1月,“非典”开始传播时,美国学者丹·吉摩尔(Dan Gillmor)即提出“We Media”概念[1],2003年7月,“非典”结束时,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S. Bowman&C. Willis)撰写的 “We Media”研究报告[2](P.7),对“自媒体”进行了明确定义。可见,中国的自媒体时代是从“非典”疫情结束时开始的,而按照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说法,2009年新浪上线微博,2012年腾讯推出微信是中国自媒体发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3](P.7)。
从2003年至今,已有很多文献探讨了自媒体所带来舆情治理挑战。据CNKI主题词检索(截至2020年12月),共计71篇CSSCI检索论文触及了这一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家宜、郭继荣的《“中美贸易战”涉华舆情、层级成因及对策研究: 基于Youtube平台的考察》[4],相德宝的《国际自媒体涉藏舆情及舆论斗争的规律、特征及引导策略》[5];还有一些聚焦于特定事件的舆情挑战研究,如《网络突发事件的舆情影响与引导对策——以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为例》[6]《社交媒体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传播与演变——以2018年疫苗事件为例》[7]《舆情“类反转”现象分析与反思——以“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8],等等。综观上述文献,就自媒体为什么会导致舆情危机的机制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去中心化机制
“去中心化”导致“把关人”机制的弱化。由于“人人皆媒体、时时可爆料、点点能爆发、环环易交流”, 政府网络舆情信息识别与研判能力不足,难以完全掌控舆情指向和提前做出预警,造成政府回应被动的局面[9]。
(二)碎片化机制
“碎片化”导致社会舆论呈现多元而又复杂的状态[10],传播中的联想叠加又使议题序列化、集中化,不断衍生出新的热点,从而延长事件的兴奋周期[11]。与此同时,政府层级节制、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降低了网络舆情政府回应速度,导致舆情进一步扩散与蔓延。
总之,“个人崛起”是自媒体时代最重要特征,由此造成的“舆情燃点低,舆情爆点多,舆情管控难”是当前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12]。
(三)超大规模机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规模对于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言:“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②然而在讨论当代的舆情治理挑战时,超大规模至今是被忽略的。我们认为,这种“超大规模”至少包含着三个维度的叠加:首先是常住人口空间集聚的超大规模,或者说城市的超大规模。一般来说,城市越大,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也会越大,所带来的舆情治理挑战也会越大;其次是流动人口的超大规模,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当前中国流动人口高达2.44亿,也就是说,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③。事实上,流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碰撞是当代舆情最大的引爆点之一。最后是网民的超大规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40亿,相当于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④。
我们认为,无论是去中心化、碎片化,还是超大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复杂性的提升,而复杂性正是舆情治理挑战的根本所在。泮伟江曾借用卢曼的“复杂性”概念,将复杂性理解为系统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连接)可能性,指出了传统中国与当下中国的根本性差异所在:传统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但低度复杂的社会,而当下中国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13]。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一转变呢?答案是: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言语行为革命。
二、言语行为革命视角下的舆情类型
综上可见,当代舆情治理挑战,关键不在于自媒体的“去中心化”“碎片化”“超大规模”,而在于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言语行为革命。这种革命性,按照哈贝马斯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社会进化(从而达成上述传统“低度复杂社会”向当下“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转变)。简言之,技术的革命只有达到思想与实在交汇的言语行为,才可能真正成为舆情治理的挑战。因此,要回应舆情治理挑战,必须回到言语行为本身,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纷纭芜杂的舆情场域里找到治理的头绪。
当然,言语行为何以成为交往媒介所带来的社会进化分析单位,哈氏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里做了详细的理论论证。在哈氏看来,社会行为可分为工具行为、符号行为、交往行为、战略行为,其中交往行为最为根本。而在交往行为中,哈氏认为,只有言语行为(verbal)最适合作分析单位。这是因为,任何交往首先须以达到理解为目标,而要达到理解目标,又须满足四个条件:“①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②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③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④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14](P.2-3)。如此一来,正如马克思分析资本的逻辑从商品开始一样,分析舆情的逻辑应从言语行为开始。确实,舆情的本质是一种言语行为。那么,言语行为革命视角下的舆情又有哪些类型呢?
(一)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的先驱奥斯汀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可以抽象出三种类型,即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说话行为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发声行为、发言行为和表意行为;施事行为又可分为裁判类、职权类、承诺类、表态类、阐述类。对于取效行为,奥斯汀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分类[15](P.95-108)。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划分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首先,对于舆情来说,仅仅理解为“发声”“发言”是不够的,舆情中的说话行为显然重在“表意”。事实上,舆情话语的复杂性,相当程度上源于它的表意技巧,总能让传播者心领神会。根据P.F.斯特劳森的分析,“表意”在话语交流的过程中,需要被“有效识别”。而为了能够“有效识别”,斯特劳森认为两个原则是必备的,即无知推定原则与知识推定的原则。斯特劳森认为,“告知某人他已经知道的某事这是毫无意义或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无知推定原则”;而“当说者想要提供信息做出经验性断定的陈述时”,至少要有一个基于听者的“知识推定”。可见,舆情中的“表意”具有斯特劳森所说的“识别性指称”功能。[16]。
其次,舆情中的施事行为。就其表意特征来说,“裁判类”、“表态类”与“阐述类”可能是最主要的;大部分舆情既不会做出承诺,也不会通过话语行使相应的职权,因而“承诺类”与“职权类”话语就比较少见了。
最后,舆情中的取效行为。按照奥斯汀的逻辑,取效行为有四个要素:说话者、说的内容、听众、说话效果。显然,舆情也离不开这四要素。但是奥斯汀把话语效果解释为因果关系却备受质疑。显然,效果有时候并不等于因果。舆情中的话语,与媒介是否具有交互性紧密相关,如果是单向的,则因果关联容易看出,如果是自媒体,则很难区分谁是因谁是果了。
(二)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最大弱点是没有一套清晰或一致的原则作为分类的基础,实际上等于没有分类的标准。例如,他对施事行为的分类实质是对施事动词的分类,其背后的假定是施事动词与施事行为能够一一对应。显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而非一个事实。对此,他的学生塞尔在继承和批判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四条标准——话语目的(基本条件)、心理状态表现(真诚条件)、话语与世界关系(先决条件)及命题内容(命题条件)。塞尔认为,这四条标准就是所有言语行为应该满足的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在这个标准之下,施事行为被重新划分为:断言行为、指令行为、承诺行为、表情行为、宣告行为[17](P.10-34)。
就舆情的类型划分来说,塞尔所提出的四条标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以施事行为中“表情行为”为例:舆情无疑有其话语目的(基本条件),反映出话语者的态度(真诚条件),寻求的是心灵对世界秩序的投射(先决条件),表现为对一事件的描写(命题条件)。
塞尔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的概念,以解决奥斯汀在解释取效行为时所面临的因果困境。显然,以言行事的最简单情况是,话语的字面意义与话语者的意思相吻合,句子的结构和功能是直接对应的,这就是直接言语行为。但在舆情中,相当多时候是通过字面用意实现言外意图,进而呈现为间接言语行为。换言之,舆情中次要的施事行为是字面的,而主要的施事行为不是字面的。间接言语行为是舆情话语的主要力源。
(三)以言说事、以言成事与以言谋事
无论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还是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都聚焦于言内与言外、效果与因果之别,忽略了“言”与“事”的时间张力。换言之,在奥斯汀、塞尔那里,“言”与“事”,两者是一体两面,相统一的,套用他们本人的话来说,“说话就是做事情”,“言”与“事”之间不存在张力。然而,对舆情来说,“言”与“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时间维度显得如此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舆情演化。假使舆情中时间可以停止,则舆情治理面临的挑战要小得多。事实上,这也是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言语行为革命”的关键所在。
舆情中的“言”与“事”的时间张力很早就为研究者所知晓。不过,这些研究中的“时间”是暗含的,尚没有上升到“存在与时间”的哲学高度,因而也无法为当代舆情治理提供一个理论高度。为此,必须强调:任何舆情,对它的“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18]。那么,从“存在与时间”的张力中,如何梳理舆情的类型呢?在这里,我们区分出了三种理想类型:
第一种舆情类型可称之为“以言说事”型。这种舆情,“言”在“事”后,即事件已经发生了,舆情所做的只是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解读。一些暧昧不明的谣言、流言、闲话也属于此类。
第二种舆情类型可称之为“以言成事”型。这类舆情,“言”在“事”中,即舆情作为事件的重要推手,贯穿整个事件的演化历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5年出版的《网络舆情分析教程》中所说的“次生舆情”亦属此类。
第三种舆情类型可称之为“以言谋事”型。这种舆情,“言”在“事”前,即某一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舆情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促成。按照默顿的定义,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指“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有效性,使错误的观念永久性地成为一种现实。预言者从一开始就认定事件的真实性并以之作为一种证据……这是一种社会的反常逻辑。”[19](P.477)
当然上述归纳只具有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意义,现实生活中舆情演化,更多的是一种杂糅状态,不同言语行为类型常常勾连在一起。
三、当代舆情治理的三个面向
舆情演化的“理想类型”划分,实际上为当代舆情治理提供了一个话语坐标。
换言之,言语行为革命视角下的舆情治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言”与“事”的时间张力,这种张力在交往媒介变革,特别是在自媒体的“即时性”“共在”技术支撑下,愈加难以应对——所谓“言语行为革命”的真正意蕴也在这里。因此,立足“存在与时间”的演化张力,梳理当代舆情治理类型,才能直面舆情治理的真正挑战。

图1立足“存在与时间”演化张力的舆情治理类型
(一)“以言说事”型舆情治理
当舆情作为一种“言”在“事”后的“以言说事”时,它实际上是一种边缘性的话语,“在本质上是众多个体的评价活动通过传播所形成的意见”,是一种“社会评价”[20](P.77),是“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形式之一。
例如,在新型肺炎重大疫情中,疫情披露初期,武汉警方对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信息的“造谣者”进行了谈话并开具训诫书,显然是反应过度。“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谣言”离真相是如此之近,“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这对今天我们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因此,“有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⑤。古人尚有“采风”之说,以“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国语·晋语六》)。 今天的人们更应明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换言之,“在政治自治的方式中,最高利益并不在于言者之言,而在于言者之心”[21](P.25)。总之,对于“以言说事”型舆情,宽容加反思也许是最好的话语治理策略。
(二)“以言成事”型舆情治理
当舆情作为一种“言”在“事”中的话语,试图“抢话筒”时,主流话语要充分意识到,它是与自己做时间赛跑,最好的应对之道是及时提供有公信力的竞争性话语,以稀释舆情的话语烈度。所谓话语稀释,套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用“先进的意见”对“落后的意见”进行稀释。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22]
话语稀释策略的关键在于:所提供的话语要有竞争力,是有针对性的“先进的意见”。说它是“先进的意见”,是源于它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基于事件本身的调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3]。说它是“有针对性的”,是它必须回应公众的质疑,如此才能“稀释”谣言的话语烈度,因此,回到舆情的话语本质上来至关重要。不过,遗憾的是,当前重大疫情的防控中,这种话语供给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疫情发展的早期,武汉地方政府对舆情的话语治理仍嫌刚性,其出发点仍为消除政府所认为的“负面影响”,以维护“政府形象”。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舆情生态中, 制度化地回应各种舆情关切,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以言谋事”型舆情治理
当舆情呈现为一种“以言谋事”的话语类型时,它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此时区分它的话语指向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舆情的话语指向具有显著的“危害国家安全”特征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降低舆情的“话语烈度”,采取媒介规制手段就显得非常必要了。问题是:媒介规制常给人以限制言论自由之嫌,为此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我国立法机构并没有对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的内涵做出详细的解释。不过,根据我国政府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⑥可以一窥端倪。根据《公约》,言论自由须“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同时“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可见,四条言论自由的四条边界,一条在私人领域,另外三条都在公共领域。对舆情来说,需要实施媒介规制的一般都在公共领域。
四、结论
当前舆情治理有着鲜明的技术主义取向。然而,如果执于交往媒介的技术变革及其所带来的复杂性,伴随而来的舆情治理只会越来越复杂,进而在能力跟不上技术变革的步伐时,表现出简单粗暴的倾向且给人以限制言论自由之嫌。事实上,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技术总是有所“解蔽”,有所“遮蔽”:交往媒介在展现技术复杂性的同时,也让人们深陷其中,忘记了舆情的本质乃是一种言语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的本质不是任何技术性东西”[24](P.4),因为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技术复杂性,只有达到思想与实在交汇的言语行为,才可能真正成为舆情治理的挑战。换言之,舆情治理需要回到言语行为本身,才会找到技术变革的发力点——这也是“言语行为革命”的真正意蕴所在。
从言语行为自身出发,本研究从“言内与言外”“效果与因果”“存在与时间”等三个维度逐一剖析了舆情演化内涵。进而指出,在上述三个维度中,“存在与时间”才是真正突显“言语行为革命”内涵的关键维度——因为交往媒介变革所带来的“即时性”“共在”技术,已极大地改变了“言”与“事”的演化历程——舆情治理的真正挑战也在于此(例如,治理者往往没有宽裕的时间去达成共识、采取应对举措)。
科学的舆情治理不是越复杂越好,因为越复杂操作性就越差。为此,本研究立足于“言”与“事”的时间张力,梳理出了舆情演化的三大类型:“以言说事”型、“以言成事”型、“以言谋事”型。不同类型的舆情,其治理策略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对于“言”在“事”中的“以言成事”型舆情,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话语进行稀释,也许是最佳治理策略;对于“言”在“事”前的“以言谋事”型舆情,应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四条边界决定是否采用媒介规制手段;对于“言”在“事”后的“以言说事”型舆情,本质上是一种边缘话语,一种社会评价,因此,“最高利益并不在于言者之言,而在于言者之心”,宽容加反思也许是最好的治理之道了。
注释:
①参见:唐兴华《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最高法这篇文章说清楚了!》,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28/c_1125508460.htm, 2020年1月28日。
②参见:孙杨生《温总理的“乘除法”》,载于《共产党人》2004年第11期。
③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b0e96 88.shtml,2018年12月22日。
④参见: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9/5548176/files/1c6b4a2ae06c4ffc8bccb49da353495e.pdf,2020年9月29日。
⑤唐兴华在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发表这篇文章,对“什么样的谣言必须严厉打击”做了归纳。参见:唐兴华《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最高法这篇文章说清楚了!》,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28/c_1125508460.htm, 2020年1月28日。
⑥参见:《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200-XXI-2-new.shtml,2020年11月10日。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该《公约》第二十条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