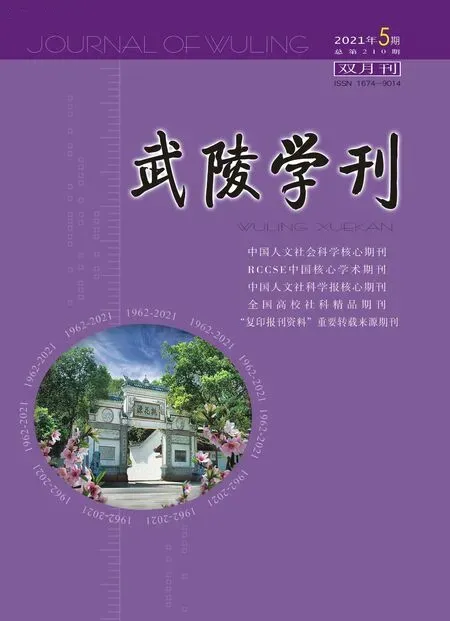后经典叙事学与“后认知”叙事思考
2021-03-08李丹云
李丹云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国内已有学者论述了当代西方叙事学史论纲的重要性,指出当今西方叙事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前叙事学时期、经典叙事学时期、后经典叙事学时期[1]。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叙事学研究迎来了后经典叙事时代。在此阶段国内学者,比如申丹、王振军等对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修辞叙事的后经典理论争鸣[2-3]。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经典叙事学呈现活力。国内叙事研究学者关于后经典叙事的观点也在不断更新拓展,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后经典叙事理论范式基本包括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诗歌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4]。熊沐清教授更是连续撰写系列论文提出“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已经实现,并衍生出多种认知文学研究范式或方法[5-6]。截止本文成稿,在中国知网以“后经典叙事”为主题关键词搜索得出的论文有218篇,最早一篇发表于2009年。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后经典叙事研究刚进入起始阶段,潜力无限。本文就后经典叙事研究的历时发展本源、主要流派和理论主张做简要整理论述,希冀能为其在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启发。
一、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叙事最早可以追溯至亚氏《诗学》关于情节修辞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叙事的本源立足于修辞,而修辞的本质是“劝说”,即天生具备交流的本质。所以,修辞叙事学的核心就是交流。修辞叙事学起始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克莱恩(R.S.Crane)对情节的修辞效果的研究,历经第二代代表人物韦恩·布斯(Wayne C.Booth)、第三代芝加哥学派詹姆斯·费伦、彼得·拉宾诺维兹(Peter Rabinowitz)的发展,重点关注叙事交流模式研究。费伦认为西摩·查特曼提出的“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模型忽视了人物角色,因而他提出叙事应该包括三种调节渠道的多向度叙事交流模式(mult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l),即“作者—人物—人物—读者”“作者—叙述者—读者”,以及“作者—结构安排—读者”这三个渠道相互作用[7]。他强调:“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交流中的两个常量(作者或者隐含作者、真实读者)以及多种潜在的资源——叙述技巧(如自由间接引语、叙述者、受述者)、对话、叙事场景、副文本、叙事文本结构安排、文类、互文信息、文本模糊性、叙事进程、叙事可信性等多种修辞手段的综合配置。”[8]82
关于叙事的“自然”与“非自然”区分,已有很多学者展开探讨。“非自然”(unnatural)是相对传统“模仿”而言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反模仿”(anti-mimetic) 之意。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的《非自然声音》堪称是非自然叙事的一部开创性理论著作,其最核心部分是对叙事文本的摹仿和反摹仿的区分[9]。丽萨·尊希恩(Lisa Zunshine)认为非自然叙事就是违背了我们现实世界的知识,并且“暗示性地违反了某种重要的概念”边界[10]19。简·阿尔伯(Jan Alber)则认为“非自然”指的是在物理、逻辑和生理上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事件[11]3。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推论出unnatural和impossible意义相近。非自然叙事学家们认为,模仿的偏见限制了叙事的解释能力。当一个人透过非自然叙事的视角来阅读模仿小说时,他对非模仿元素的感知会变得更加敏锐。虽然非自然叙事主要代表人物理查森不仅提出了“叙事消解”、第二人称叙事和“we”叙事等概念,但是,费伦认为非自然叙事只不过是关注到传统叙事理论中被忽视的领域,并对其进行补充而已,而非真正从新的视角,比如从修辞行为、身份交叉性角度另辟蹊径[8]74,所以,非自然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正的新的叙事理论范式还有待探讨。
我们对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似乎不以为然,且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小说即虚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对叙事虚构性的探讨突出了普遍存在的虚构的意义和价值。沃尔什在《虚构的修辞》中提出,我们不应把虚构简单地等同于“小说”,而应该理解为“虚构性”(fictionality),它不是叙事类型,而是一种创作策略[12]。他认为“非虚构”是指说话人的话语是受到真实状态限制的一种被动模式,而“虚构”是指说话人主动创造出非真实状态的模式,强调主动“创造”(invention)。虚构不仅遍布我们整个日常话语,也是思维实验、模拟、假设等多种科学研究的关键工具。它使我们认识到,从非虚构语篇转向虚构语篇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叙事虚构性研究既突出了区分虚构/非虚构的实用性,又为跨界交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让我们注意到全球写实叙事中的虚构性和虚构叙事中的写实性。
近年来,“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已然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沃霍尔和兰瑟(Warhol&Lanser)所主编的《叙事理论的解放:酷儿和女权主义的干预》一书汇编了22篇不同职业的学者在不同阶段对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移情、宗教、生命书写等话题,该书核心概念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兰瑟认为交叉性意味着身份的多面性,比如种族、民族、阶级、国籍、全球地位、年龄、性别、能力、宗教、语言、历史情境,通过在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世界里的聚集和交互活动,去创建现实的或感知的社会地位、含义、经历以及各种表征。她提醒学者们在研究身份交叉问题时,不应“把复杂的人物进行简单粗糙的分类,或对叙述事件进行简单的解释”[13]。由此足以见得叙事研究中的身份交叉融合问题极为复杂,如果从身份交叉研究的视角着手,则需要建立在多样性原则之上,对该作品人物身份会有更丰富、多样的阐释。费伦也承认读者自身多重身份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他们对身份交叉性的理解和评价,这意味着评价一致与否本身会因个人的或政治的原因存在进一步开放性的解读[8]80。
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当代西方叙事研究持续保持密切关注。申丹是国内较早全面引介西方叙事理论的学者之一。她主要关注修辞叙事研究,比如分别对查特曼、费伦、迈克尔·卡恩斯(Michael Kearns)的修辞叙事学进行了系统述评[2][14-15]。她后期则侧重于对西方叙事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探讨[16-17]。尚必武著述成果甚为丰富,一直持续关注修辞叙事和非自然叙事研究新进展[4][18-19]。另外,唐伟胜和胡全生对女性主义叙事学和酷儿理论范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0-22]。还有部分学者注重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比如王瑛提出空间叙事是中国叙事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基点,她反观民族经验和中国叙事学建构问题与方法,提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的宏伟愿景[23-26]。同样,王振军也探讨了中国叙事学的学科建构和对比问题[27-28]。毫无疑问,还有很多叙事研究者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范式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但研究倾向呈散发状,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不作赘述。下文重点论述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成果。
二、认知叙事学研究
在广义的认知诗学或者文学认知研究领域,认知叙事学已成为21世纪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且呈现跨媒介、跨学科、多理论融合的研究势头。其中,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是广义认知诗学研究中的比较经典的理论范式之一。丽莎·尊希恩《我们为什么读小说》一书对认知叙事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解释了心智理论、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或称信息源追踪(source-tracking)等概念,并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概念与日常生活和小说阅读的关系。尊希恩认为“ToM”是指人类“解释他人行为的思想、感情、信仰和欲望的能力”[29];“是一组认知适应的综合能力,它能够指引我们的社交,并构建这个世界”[10]162。元表征是一种认知能力,用来追踪信息源,并根据个人对信息源的了解来判断信息源的质量。尊希恩以四层内嵌意向性(embedded intentionality)的复杂句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小说是如何挑战读者的读心能力。她大力倡导文学虚构作品阅读,强调将文学作品阅读纳入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实施有效的教育干预政策,在一篇中文译稿《虚构作品的秘密生活》中对类似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30]。尊希恩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有效的文学作品阅读能挑战人们的读心能力,让我们得以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复杂的社会认知互动。
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的领军人物非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莫属,前文已提及了国内多位学者都对赫尔曼的叙事理论进行了引介和评述。赫尔曼也被公认为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思想最为活跃的西方认知叙事学领军者。目前,国内学者陈礼珍对认知叙事学的最新发展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31]。除了对赫尔曼的世界建构方式、故事话语模式提示认知过程以及后期的多物种故事世界理论进行了概述之外,他还系统介绍了当前认知叙事学领域的其他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关于普适认知模式与认知地图理论,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的认知地图和叙事空间建构理论,玛丽莎·博托卢西(Marisa Bortolussi)和彼得·狄克逊(Peter Dixon)的实证心理学认知叙事研究等。近年来,受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神经美学研究成果的影响,认知叙事学越来越紧密地与神经认知科学交叉融合在一起,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吸收计算机人工智能运作原理,提出修辞—认知叙事学研究,主张以窗口聚焦机制和框架嵌入叙事为基础来解释叙事意义产生的认知原理。
本世纪以来,认知叙事研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主题就是情感(affect)问题。苏珊·金(Suzanne Keen)在《移情与小说》中认为作者和叙事学家把移情用在人物创造、可能世界创造以及不同读者的反应方面,并提出了限定性(bounded)、代表性(ambassadorial)、普遍性(broadcast)的策略叙事移情分类,引领镜像神经元理论与叙事共情机制研究[32]。埃德·谭(Ed S.Tan)、弗兰克·哈克穆尔德(Frank Hakemulder)研究电影、小说和其他媒体引发的情感方面的问题,探讨各种媒介的文学作品如何利用人类普遍情感诱发感情[33];弗卢德尼克《“自然”叙事学》涉及了体验[34]。帕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的《情感叙事学》等学术著作为认知叙事研究从情感和审美角度拓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更多关注叙事移情唤起(empathy-evoking)文学文本的研究,比如伤感小说、创伤叙事、灾难叙事或特定族群身份主题叙事的文学作品研究[35]。
国内对认知叙事学的引介、论述和应用也产出了很多学术成果。张万敏引介了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事”,玛丽-劳勒·瑞安、弗鲁德尼克和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思想[36-39]。唐伟胜探讨了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之间的分歧与联系,在认知叙事学视域下,对小说的三类人物认知理论展开辨析[40],并对叙事理解中的图式层级结构和类别进行论述[41]。马菊玲对认知叙事学视域下的文学叙事交际进行了分析和阐述[42]。
三、认知叙事学的“后认知”思考
近年来,计算机叙事生成研究涵盖人工智能(AI)和认知科学领域多种极具挑战的主题,亦有“自动叙事生成”的提法。可以说在21世纪刚刚过去的第二个十年里,文学叙事研究似乎也更注重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神经网络、认知科学、实证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范式相结合。
比较突出的是日本几位研究情报学的学者借助计算机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计算认知叙事领域成果显著。2016年日本岩手县立大学小方孝(Takashi Ogata)和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秋元泰介(Taisuke Akimoto)所著的《叙事学的计算和认知方法》一书,重点围绕叙事学的计算和认知方法研究,尤其关注叙事生成(narrative generation)过程以及叙事学在广告、管理、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43]。他们认为文学叙事的概念和方法与未来的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发展紧密相关。2019年,两人又合作编著《后叙事学——计算认知方法》,提出“后叙事学”(Post-Narratology)概念。他们认为后叙事学是指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每一种特定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的叙事学和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叙事学[44]。该书不仅考察了小说、诗歌、电影、漫画、广告、商业通讯、日记或个人叙事,以及歌舞伎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生成叙事研究,还关注了计算建模和叙事实施加工、概念思维、设计、叙事现象批评,以及对叙事文本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小方孝紧锣密鼓又与青森大学的小野淳平(Jumpei Ono)于2020年编著出版了《以叙事生成弥合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叙事学之间的差距》。整本书拓展了许多叙事学研究全新视角,包括:视觉叙事结构模型分类和建构以及认知效应研究、电子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s,NPCs)虚拟主体情感模型、对300-500间数字的语境记忆阈值研究[45]。三位日本学者所汇编的计算认知叙事生成研究论文绝大部分出自日本研究者之笔(只有四位来自韩国、意大利、土耳其和美国),足见这股生力军的强劲发展势头。
国内学界也兴起了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研究热潮,仅以“人工智能文学创作”为主题关键词模糊搜索中国知网,就可以获得103篇论文,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AI文学叙事生成的文章发表于2011年。杨守森在《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一文中基本阐述了AI文艺创作的优势,即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拓展了艺术想象空间,变革了文艺观念。他也坦言AI文艺创作存在局限性,比如电脑和人脑毕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AI文艺创作系统仍然只是模仿、复制与重组而已[46]。从此,国内学界展开了对人工智能文学叙事的诸多讨论和争鸣,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物质层面而言,涉及著作权问题;第二,是从创作生成机制、传播方式、艺术表达等三个角度来探讨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问题;第三,核心问题是关于作者主体性的哲学思考。
有部分学者从艺术审美角度探讨AI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一方面,由于必须凭借庞大的写作语言资源库、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神经网络计算、情感算法等技术手段,易造成逻辑语法、文体风格混乱的问题,作品真实性就因技术缺陷而遭受质疑。另一方面,有多位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文学叙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黄鸣奋系统论述了人工智能和文学创作成功对接的可能性,包括符号人工智能、行为人工智能以及社会人工智能,都为实现AI叙事提供技术基础,逐步使人工智能和文学创作在社会、产品、运营层面实现逐步渗透。这也将促使由此生成的文学作品具有人工性和文化性、类智性与创造性、似能性与作用性[47]。王志钢比较详细地论述了AI文学创作语言输出的问题,以及抒情类文体(主要是诗歌)、叙事类文体(包括历史、爱情题材、志怪类叙事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等)在AI创作中应遵循的艺术规律和发展可能[48]。张斯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的功能和传播演变,提出AI时代文学叙事面临的双重语境中,创作主体呈现多元化,出现了“人智”和“类智”的新文学场域,这种现状和趋势导致文学叙事中人类主体性的消弭,叙事模式得到扩展,还将导致叙事艺术和审美的形变。作者展望在AI媒介生态的传播大语境里,我们或许可能实现“多元裂变”和众“智”成城的殊途同归[49]。由此可见,国内学界比较倾向于认可人工智能文学叙事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和功能。
有关“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一直是文学创作与文艺争鸣的核心话题之一,所谓“人学”自然涉及作者的主体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类进行文学叙事生产所构成的“后人类”景观,虽然威胁到人类主体性地位和文学作为“人学”的审美基调,但并非预示必然的替代,而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促使人类反思自身,不断调试自身存在的合理价值[50]。卢文超从形式和过程两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作品和人类作品之间的区别不是“拙”与“劣”的形式区别,而是涉及关联和际遇,体现为事件。因此他提出要进入到“事”的层面,即艺术事件的区别。事件关涉主体性、经验性、过程性。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事件性”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51]。周建琼认为人机共存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话题,赞同陈楸帆等所提倡的平等对话方式,认可构建具有“人—机间”性的作者主体不失为AI背景下作者主体重构的有效途径[52]。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主体性逐渐消弭的可能性问题,抑或说是一个程度的问题。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理念,当时的人们或许还只是认为那是计算机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游戏,而今,AI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对文学精神世界的浸染。被大数据操控和裹挟的我们深感无奈,在量化、精准、可控的人工智能面前,艺术的“光晕”和文学的“偶然性”价值是否需要被重估?黄悦提出“在道德、伦理、审美都被数据解构甚至操纵的时代,那些原本构成人文学科基础的基本命题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53]?这些问题对人类如何建立和维系情感和道德的新规则提出了挑战。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尾声,人类经历了一场遍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许多熟知的交流和叙事方式遇到了冲击,我们认识、理解、接受新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颠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手段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愈加密不可分。那么在广义的叙事范畴里,有人交流的地方就有叙事存在,在人类与机器逐渐融合甚至密不可分的总体趋势下,出现人工智能叙事生成、创作和阐释研究,亦或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新生现象。在这样一个过度充斥着屏幕、画面和声音,却无法勾起我们所谓传统文学阅读欲望的世界里,人们的审美感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文学叙事和阅读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或者已不再是纯粹的人类叙事,或许能引发我们对认知叙事研究的“后认知”思考。机器叙事,或人机叙事的共生体似乎也能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弗鲁德尼克曾评论说,认知叙事学“引发了创新认知方法及其实践的爆炸式增长。当我们尝试所有这些方法的时候,或许会加速这个学科的危机,但是也可能会在未来15—20年内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