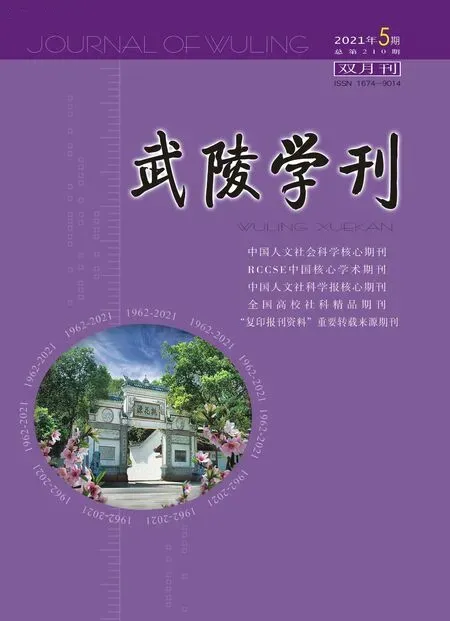女性写作的两种趋向及其胜境
——基于《母亲》与《易经》的比较研究
2021-03-08陈娇华
陈娇华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丁玲和张爱玲(下文简称“二玲”)有太多相似性,她们都在没落世家出身、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并且都有追求独立自由的母亲等,因此她们的创作不时被学界拿来比较研究,且这种比较大多集中于创作风格、女性主义及作品个案等方面①。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性,有的甚至相当深入,但总感觉意犹未尽,觉得“二玲”创作之于中国女性写作发展的意义仍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这种感觉在比较阅读《母亲》和《易经》后尤为强烈。《母亲》是丁玲1932年创作的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的传记体小说,《易经》(包括《雷峰塔》)是张爱玲于1957年至1964年间创作的追忆童年琐事的自传体小说。两者都基于真人真事,都属于创作转型期作品,都塑造了一位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母亲形象。但因创作动机的不同,特别是两位母亲形象塑造的不同,两部作品其实揭示了“二玲”创作发展的不同趋向,也是中国女性写作发展的两种趋向:宏大社会化叙事和个人情感化叙事。《母亲》是对宏大社会化叙事的开创与展望,《易经》则是对个人情感化叙事的回望与承续。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它“是现代性的标志: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的价值的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1]167-169。即如俞吾金概括的,“宏大叙事”包括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解放的叙事,如基督教叙事、启蒙运动叙事、马克思主义叙事等;另一种是思辨的叙事,如黑格尔哲学,事实上黑格尔哲学蕴含着解放的叙事[2]。这里的“宏大社会化叙事”指关注社会历史事件,以女性的生活、情感和命运折射时代社会变迁。“个人化情感叙事”则指以个人化立场叙述女性个体的情感、心理和体验等,即便涉及社会历史事件,也仅是作为背景。
一、创作动机:再现社会历史与回溯个人往事
《母亲》创作计划宏大,预备要写30万字左右,分为三部曲,但因作者被捕,仅完成了第一部。作品力图通过母亲的成长历程再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面貌,反映现实社会中大众对于革命的向往与追求。谈到《母亲》创作动机,丁玲说,在家乡听闻了许多动人故事,“完全是一些农村经济的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穷途的一些骇人的奇闻”,其间杂有“贫农抗租的斗争,也还有其他的斗争消息”,“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些关于小城市中有了机器纺纱机、机器织布机、机器碾米厂和小火轮、长途公共汽车的,更有一些洋商新贵的轶事新闻……和内地军阀官僚的横暴欺诈”[3]7-8。这些同小时候在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完全两样,使她产生“在一个家里,甚或一个人身上,都有曾几何时,而有如许剧变的感想”。于是,决心创作一部反映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作品,“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几个小村镇”。同时,以母亲作为贯穿人物,“包含了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3]8。可见,作者试图通过叙述“母亲”由一位封建家庭的少奶奶蜕变为一个向往革命的新女性故事,折射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面影。作品创作于1932年,正值作者创作与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时期。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编《北斗》杂志,思想急剧左倾。1932年初总结1930年代前后创作不振原因与出路时,丁玲指出:要改变生活,到大众中去,“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要“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4]。为了配合和反映当时“左联”大众文艺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作品以母亲向往革命的精神来体现和引导当时“大众的向往”[3]8,可谓立意高远,视域开阔,社会历史内涵丰富。
如果说《母亲》写作有宏大社会化叙事倾向,那么《易经》写作则属于个人情感化叙事。它主要追忆童年琐事,没有“罗曼斯”式传奇。张爱玲曾担心“没有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5]3。作者虽没有明确道出创作动机,但从其信件、创作心境及作品情感内容来看,《易经》隐含作者对个人往事的依恋与回望。张爱玲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6]187《易经》创作于作者刚到美国不久,中西文化和语言的不同,生活的不安定及安全感的缺失,使得她试图通过回溯往事来治愈童年创伤。或许在原应回避的创伤记忆里,作者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7]。同时,由于时空距离,往昔那些并不美好甚至是创伤性的记忆也会得到情感润泽成为漂泊灵魂的抚慰剂。正如《易经》中所言:“过去是安全的,即使它对过去的人很残忍。”[8]8另外,也有作者寻找闯入欧美文坛创作路数的努力与尝试。《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早期作品以叙写男女情爱故事享誉文坛,后来受到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批评,张爱玲虽不服气,但内心其实也在寻求突破。1953年至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创作了突破早期男女情爱题材拘囿的政治题材作品《秧歌》《赤地之恋》,但她并不满意,多次述说这是命题作文,表示以后不再写作这种“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9]28。她以英文写作《粉泪》试图立足西方文坛,但数次修改都未成功。正是想寻求创作突破,尤其想闯荡欧美文坛的焦虑下,张爱玲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9]51。此外,韩素英《瑰宝》和凌叔华《古韵》等自传性小说在西方的畅销和成功也刺激其创作的转向。于是,张爱玲创作了《易经》这部关于自我的“成长小说”或者“心理小说”[5]3。情感基调倾向温情怀旧,既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又呼应早期对女性情感命运的执著探索。
总之,《易经》主要书写个人家庭生活琐事,疏离宏大社会历史,缺乏开阔、宏远的生活视境和丰富驳杂的社会内容。尽管作品中出现香港战争,但如同《倾城之恋》一样,战争只是为了衬托和印证个体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因此,如果说《母亲》属于社会历史宏大叙事,那么《易经》则属于个人情感化叙事。只不过,《母亲》是对宏大社会化叙事趋向的开拓与展望,《易经》则是对个人情感化叙事趋向的回望与承续。
二、母亲形象:社会解放与个人自由
《母亲》和《易经》分别给我们塑造了两位具有不同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的母亲形象:于曼贞与杨露。她们都是反叛传统观念,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曼贞30岁时,丈夫去世,留下累累债务和嗷嗷待哺的幼儿,她于悲痛中勇挑家庭重担。后又顶着家族压力卖地还债,进城读书,与同学义结金兰,决心团结互助,期待为国效力,为革命做点事情,终于从一个封建旧式家庭的少奶奶蜕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杨露也是如此。她不满吃大烟、养外室的封建遗少丈夫,反叛传统夫权统治和女性规范,冲破家庭亲情阻力,出国学习新知识,追求自由平等,开创属于女性自我的真正人生。然而,由于出生背景、成长经历、性情气质及社会交往的不同,她们的价值追求和女性意识内涵截然不同。
首先,曼贞期待为国效力,追求和向往革命;杨露则始终关注个人情感,追求自由独立。曼贞生活于辛亥革命前后,正值中国思想界反对传统“贤妻良母”、力倡“女国民”时期。吕碧城在《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中指出:“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10]478-479而培养“女国民”关键在于女子教育。“因为女子教育不但可奠定女子自立的基础,而且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女子的爱国主义、独立意识和女权观念。”[11]曼贞进入女学堂就是获益于这种兴女学、培养女国民思潮,深受“女国民”思想影响。而杨露生活于“五四”前后,其时思想解放、个性解放风起云涌,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成为时代号角,而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又是个性解放的重要内容。杨露的婚姻破裂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上述相异的时代背景形成了她们不同的精神面向和价值追求。
如果说曼贞走进社会,融入集体生活,追求社会解放;那么杨露追求个人自由,疏离社会集体,走的是个人主义道路。在家里,曼贞与仆人平等互助,相互关爱,她信任他们,把家事托管给他们。她的思想深受其弟影响,而他在学堂“教学生们怎样把国家弄好,说什么民权,什么共和,全是些新奇的东西”[12]155。曼贞在学堂很快融入集体生活,与同学们志同道合,谈论的不是学问及“读书求自立”,就是革命及“挽救中国”或报纸上的国事。她们以秋瑾和罗兰夫人为榜样,希望为国尽力,为革命做事。可见,曼贞真正由闺阁少奶奶转变成倾向革命、投身社会解放的新女性。她追求整个社会解放,向往一个能让孩子们快乐生活,不做亡国奴的“光明的世界”[12]204。其反对封建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理想昭然若揭。相反,《易经》中杨露始终停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解放阶段。她生活于五四运动前后,受时代思潮,特别是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追求自由独立。她生性冷傲,与下人保持距离,甚至呵斥、打骂下人。她教育琵琶,“老妈子们都是没受教育的人。……不要太依赖别人”[13],要“为自己着想,当个新女性”[9]5。可见,她追求自由、平等,却没有把这些现代观念普及到民众身上。作者虽没具体叙述杨露的国外生活,但从其回国后的人际交往及与珊瑚、雪渔太太及琵琶等人的谈话,不难发现她始终关注的是爱情婚姻话题,追求独立自由。除了与有限的几个朋友见面、吃饭、跳舞或打麻将,杨露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她虽然为了独立自由离婚,但其实并未真正独立起来。她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经济独立。她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叛离家庭,勇敢走出国门,但其实仍依靠嫁妆过活。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指出,女性倘若不能经济独立,不能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则所有好名目都是空话[14]。而要经济独立,女性只有融入社会,参加社会工作,将个性解放汇入社会解放大潮,女性的自由、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这是《母亲》和《易经》揭示的共同主题,也是两位母亲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追求给予当代女性解放的启示。
其次,她们的女性意识内涵也不同。女性意识指女性“为女”和“为人”的双重觉醒,“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15]。然而,传统女性只有“为女”意识:在家做父亲女儿,出嫁做丈夫妻子,有了孩子做母亲,却没有独立人格,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尊严。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和妇女解放大潮唤醒了许多女性,她们追求独立自由,但大多停留于对个体自由、平等的追求阶段。文学作品中也涌现出许多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娜拉形象,但她们极少跳出个人主义拘囿,关注社会解放,特别是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这类形象到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之间,才在庐隐、茅盾、丁玲、巴金等人作品中出现。《母亲》中的曼贞即是其中之一,这是丁玲探索女性解放道路的结晶。如果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从女性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探索女性解放出路,梦珂、莎菲代表了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但她们不是以沉沦就是以消极抗拒宣告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最终走投无路;那么同一时期出现的《韦护》《母亲》《一九三○年春上海》等作品,开始跳出个性解放拘囿,尝试从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方面探索女性解放出路。曼贞已脱去少奶奶袍褂,融于新的集体生活。过去“她一个人在孤单里向前奋斗,她不敢希望有朋友,然而现在她却有了这么多的朋友”,她们“愿意在社会上,在事业上永久团结成一体”,愿意为国家尽一份力,甚至希望加入革命党,为了孩子们将来能生活在一个光明美好的世界。曼贞显然已突破狭隘的个人情感上升到整个社会解放,即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如果说曼贞是将女性解放融入社会解放,走集体主义革命道路;那么杨露的女性解放追求则更多停留于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阶段;且女性意识显得模糊暧昧,既追求自由独立,又保守落后、不无依附性,特别是在贞洁观念和自由恋爱方面存在矛盾心理。正如张爱玲指出的:“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6]《易经》中杨露始终牵挂的事情是恋爱、婚姻,所谈论的是国外发生的杀妻悲剧、大爷偷养外室及娘家侄女们的婚事等,最切己的事情是与丈夫离异及离异后的交友、恋爱等。可以说,整部《易经》(包括《雷峰塔》)所叙写的与杨露有关的情节,除了与女儿关系外,基本不出爱情、婚姻话题。而在五四启蒙话语中,恋爱婚姻自由正是体现个性解放的重要方面。“爱情成为新道德观的总体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传统社会精神特质的礼教,并且把礼教等同于外在的限制……恋爱也被视为挑战和真诚的行为,通过宣布脱离伪善社会所有的人为限制,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向爱人展示自我。”[17]杨露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社会活动,除了约会、访友,就是看电影和打麻将。她反封建包办婚姻,却又依靠旧式家庭给予她的嫁妆生活,并未真正从经济上独立起来。她追求独立、平等,向往自由恋爱,却对女儿琵琶灌输所谓“处女‘冰清玉洁’”等贞洁观念;担心女儿出国留学没毕业就恋爱;特别是怀疑女儿奖金来路不明,不惜窥浴验身。一个追求独立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母亲却肆意践踏女儿的纯洁心灵和尊严。这是杨露这位半新半旧母亲的可悲之处,她追求独立自由,也努力培养女儿的独立自由,却恰恰又是她在利用传统思想摧残女儿内心刚刚萌生的独立、尊严和自由之花。其女性意识的模糊暧昧可见一斑。两位母亲形象的差异塑造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两位母亲的不同性格命运、人生遭遇及价值追求,折射了她们留给各自女儿的不同印象;另一方面也是两位作者创作时的不同现实需要(一个是社会革命需要,一个是个人情感抚慰需要)所致。两位母亲的不同影响昭示两位女儿日后创作发展的不同趋向。
三、创作趋向:宏大社会化叙事与个人情感化叙事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作者内在情感和意欲的一种创造冲动。丁玲初登文坛是由于内心寂寞、苦闷,发抒为文。处女作《梦珂》叙述一位现代女性为了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及追求真挚爱情屡遭挫折,最后不得不沉沦的故事,开启了作者对于女性情感精神和人生命运执著关注的创作道路。依循这一创作路数,丁玲又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等作品。但即便这些在创作精神上与张爱玲较为接近的早期作品,其独特性依然显著:它们始终没有丧失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没有忘却对困厄中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姐妹情谊的书写,以及对叛逆、反抗的女性倔强、孤傲精神个性的凸显。《梦珂》描写了梦珂对女模特的援助、对表嫂婚内痛苦情感的理解与同情;《莎菲女士的日记》记述了蕴姊对莎菲的关心和照顾,特别是莎菲追求失败后一个人“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孤绝坚守;它们都揭露、批判了导致女性追求失败的黑暗社会现实和堕落时代风气。这些不难看出作者书写和探索女性生活、情感和命运出路时,对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的揭示与批判,这既是作者童年生活经验和母亲教育影响所致,也是其1930年代初思想和创作发生转变的重要基础。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丁玲思想和创作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1931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思想急剧左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联”领导,倡导文艺大众化,并创作《水》《多事之秋》《法网》等表现工农革命运动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如前期作品细腻、深刻,艺术上显得粗糙。丁玲自己也不满意,却又不愿回到《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前期恋爱题材作品的旧路。通过对此前创作的总结与反省,她决定创作《母亲》。一方面,借此梳理自己的家庭身世及精神来源,另一方面继续探索新的创作路子。《母亲》出版后,深受评论界好评,鼓舞和坚定了丁玲创作前行的信心。沿着这一宏大社会化叙事方向,丁玲又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关注视域已超出女性婚恋题材,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生活领域。毋庸置疑,时代社会影响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生活范围的扩大及童年时代母亲追求和向往革命的影响所致。丁玲追忆向警予给她的影响时谈到:向警予把她在长沙经历的各种新闻、新事和新道理讲给她母亲听,她母亲又把这些拿来教育她和她的学生[18]。在答记者问时,丁玲也说:“我的小说中以女性为主人公,日益减少,并非有意为之,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领域日益宽广,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关心的事物大大增多了的缘故。”[19]可以说,正是这些影响和经历导致丁玲思考女性解放时,倾向把女性问题放置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宏阔视域中,既注意对女性内在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开掘,又努力再现广阔的社会历史面影,使作品既有人性的真实和深度,又不失反映生活的广度和厚度,视野开阔,气势宏博。但应当看到,丁玲1940年代后特别是解放后,由于担任社会职务较多,工作范围扩大,也由于受时代社会和极“左”思潮影响,后期某些创作如《在严寒的日子里》《杜晚香》等存在过于强调外在社会事件反映,忽视人物内在心理刻画,流于社会现象描述或者过度演绎时代的政治倾向。这可以说是宏大社会化叙事可能存在的拘囿。
相反,张爱玲从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以来,便沉浸在对男女情爱的书写上,不论是1940年代的《红玫瑰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还是1950—1970年代的《易经》《小团圆》《色戒》《少帅》等。诚然,40年代的男女情爱题材小说为张爱玲赢得巨大声誉,但批评之声依然存在。傅雷指出:“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20]张爱玲后来一度试图有所改变,1950年《小艾》涉及到当时正在发生的土改,但未正面展开。1953—1954年的《秧歌》《赤地之恋》则直接取材于大陆土改,但张爱玲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向朋友抱怨以后再也不写这种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随后,又回到以前熟悉的男女情爱书写旧路,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金锁记》为《怨女》等,创作《五四遗事》《易经》《小团圆》《少帅》《色戒》等作品。这些作品不是叙说童年往事,就是描述男女情爱。稍微与国族历史有些关联的《色戒》《少帅》,也被作者写成彻头彻尾的情爱故事。《少帅》“小心翼翼地止步于个人情欲,于国族利益两败俱伤的书写上不作深究。以男女主人公的私情沉迷搁置多事之秋的家国焦虑,将‘历史’压进‘个人’背景中”[21],而《色戒》也因以情爱模糊国族的正义/非正义界线被视为“汉奸文学”[22]。可见,从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到《色戒》,张爱玲创作始终没有摆脱男女情爱题材范围,印证了她所说的: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因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6]188。在张爱玲看来,恋爱中的男女能更自然、更纯真地展现人性。不可否认,对人性、生命的浅吟低唱,能使创作深入到人性的幽微境域。但人性、生命的美好离不开社会、历史和人群,甚至离不开政治。因此,张爱玲这种个人情感化叙事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局限:其一,单一的人性化视角可能会导致对大是大非界线的消解,甚至造成对深厚历史文化意蕴的疏忽。《色戒》发表后遭到的质疑就是显例。其二,过于悲郁幽暗的基调不利于情感抚慰或给人以信心。作者刻写人性幽微时,总是“远远地看着那些生死之间的人生,同情与悲悯是淡淡的,多的是大的暗影。……人在黑夜里,只能以黑色包围他人,也包围自己”[23]。特别是面对笔下悲剧,作者“更带几分自己记忆的投影。这也限制了她的作品的格局”[23]。最后,张爱玲作品描写了许多与女性关联的人生悲剧和爱情悲剧,但大多归因于人性的幽微阴郁,缺乏宽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剖析,因而无力导向对现实女性、社会解放出路的探索。
四、女性写作胜境:两种趋向的有机融合
丁玲的宏大社会化叙事与张爱玲的个人情感化叙事分别代表中国女性写作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如果参照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划分,那么丁玲的宏大社会化叙事较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的情感化叙事则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事实上,绝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后来都转向激进女性主义[24]40。这两种流派又分别对应于西方两次女权运动各自的侧重点。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掀起的第一次女权运动强调争取女性社会权利,追求“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而掀起于“二战”后,盛行于197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强调“思想革新”,要求“剔除在风俗、习惯、语言一直到学问和艺术等各领域内深深渗入的性别歧视,要打破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男性的优越思考方式”[25]。因此,被日本女性学者称作是关于个人内部和家庭内部的运动[26]。当然,这里的流派划分和对应只是一种权宜之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被废止构成了女性在世界历史上的失败。由于经济权力转变,男人掌握了家庭支配权,妇女降到奴隶位置,沦为性的奴隶和生儿育女工具。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因此,解决妇女压迫的方案是妇女应投身到社会劳动大军之中[24]105。奥古斯特·倍倍尔也说:“解决妇女的问题就等于解决社会的问题。”[24]107这些妇女解放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国内,引起广泛反响,涌现许多倡导妇女解放的女界先驱,如秋瑾、向警予等。这些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丁玲母女,《母亲》中曼贞就是在这种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下,勇敢走出家门,进入新式学堂,蜕变成具有新思想和知识文化的新女性。丁玲的社会化叙事显然渗透着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但是,这种妇女解放思想在1970年代遭到质疑,因为“妇女并没有像恩格斯预见的那样因为加入社会劳动力大军而获得解放,妇女发现她们肩负着双重责任:在社会上为谋生而工作,回到家中还要继续无偿的家务劳动”[24]115。因此,女性主义者提出:“要重建劳动,就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思考和行动、计划和日常工作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24]124这些观点其实已接近激进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具有天赋人权,她们与男人在智力和精神上是平等的,认为家庭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场所[24]38,解放妇女是正义的,因为这将保证每个人体验到最大幸福,而幸福来自最大限度地开发每个人的才能[24]37。激进女性主义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它包含许多重要思想,如个人即政治,父权制或男性统治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应同其他妇女联合起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压迫她们的男人的斗争中去等。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性、爱情和家庭的独特看法。她们认为妇女解放不等于性解放,所谓性解放其实是迫使妇女屈从的另一种方法,认为所有压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政治上令人压抑的男女角色制度,婚姻是迫害妇女的主要形式。她们攻击爱情,认为它是一种“体制”,带来脆弱、依赖性、占有欲和对伤痛过度的敏感,妨碍了女性人类潜力的发展。她们主张消灭婚姻和家庭及“异性恋体制”,发展“子宫外的方式来繁衍人类”,强调女性心理、情感和精神的独立等[24]198-200。以这些女性主义观点考察张爱玲创作,不难发现,它们更贴近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在张爱玲笔下,不论是在大家庭里生命之花抑郁而至凋谢的旧式女性,还是以谋爱为谋生的现代都市女性,她们都是一些内囿女性,需要“凭借性的吸引力来获取经济利益”[24]65。其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不仅在于婚姻制度本身的性别压迫,更在于这些女性自身心理、情感和精神上的依附性及人性的懦弱与卑怯。婚姻制度既是她们生存的保障,也是使她们沦为性奴隶而不自知的枷锁。虽然经济缺乏独立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作者强调的。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一个女性经济上无法自立时,其他所有好名目必定是空的。这也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为什么那么虚弱、卑怯,最终不得不沦为结婚员的真正原因。固然,经济解放不能完全保证女性的解放;但没有经济上的解放,女性想获取解放绝对不可能。张爱玲个人情感化叙事对女性解放问题思考和书写的偏颇于此可见。张爱玲审视和探索女性问题的这一偏锋路径与其母亲的影响脱不开干系。张母婚姻破裂,数次恋爱无果,不时向张爱玲灌输“男人好归好,不能发生关系”“现在才明白女人靠自己太难了。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人对你真心实意”[8]98等思想,使得年轻的张爱玲对于男女情爱关系及这种关系中的女性处境洞察透彻,而这种洞彻反过来又影响到其日后的人生与创作,形成执著于男女情爱书写及在这种情爱关系中思考和探究女性解放的创作趋向。
综上所述,丁玲的宏大社会化叙事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比较切合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发展的实际情形,对于中国的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并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得到承传和发展,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主流。但是,这个创作趋向在某些特定时期因过于关注外在社会历史事件,疏忽了对女性自身解放问题的探索及对女性内在心理、情感世界的开掘,这是应引起注意的。张爱玲的个人情感化叙事则从男女情爱关系及女性内囿的情感心理,思考与探索女性解放,显示出对于女性解放及人性、人心等话题挖掘与探索的深度。这个趋向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在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及铁凝的“二垛”、《玫瑰门》中重新兴起,并在1990年代女性“私语化写作”及新世纪初“美女写作”中得以承续发展。应当看到,这种创作倾向发展到后来,只专注于对女性内在心灵境域的开掘,随之出现了忽视底层女性生存境况、脱离社会现实及创作视域窄化等现象,这显然偏离了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解放运动初衷。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指出:“我们的责任还不只在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且还要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27]可见,丁玲和张爱玲以各自创作的利弊印证和昭示:女性写作的胜境应是宏大社会化叙事与个人情感化叙事的有机融合,这样一来,女性写作既不失观照外在世界的广度,又有开掘人性、人心的深度,同时对女性解放的思考也能结合女性自身的内外两面进行。同时,这个理想胜境也暗合1970年代后,女性写作研究的社会性别理论趋向。因为理想的女性文化建构和女性解放,并不是单一性别的问题,而是关乎全社会的共同话题,需要结合阶级/阶层、性别、民族和种族等多方面因素来考察。故而,“二玲”创作显示的女性写作路向值得深究。
注 释:
①参见钱荫愉著《丁玲与张爱玲: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坠落》,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吴晖湘著《激越的与苍凉的——丁玲、张爱玲创作文本的歧异》,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3期;陈理慧著《革命中的女性角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色·戒〉比较》,载《理论月刊》2007年第1期;郜元宝著《都是辩解——〈我在霞村的时候〉和〈色·戒〉》,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