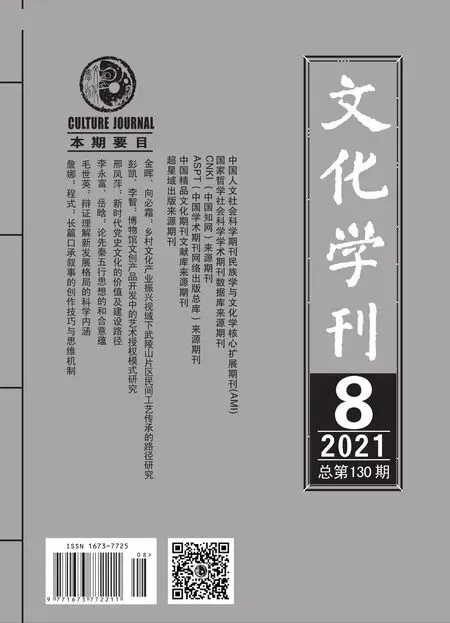程式:长篇口承叙事的创作技巧与思维机制
2021-03-08詹娜
詹 娜
长篇口承叙事是民间叙事中篇幅较长、叙事套路明显、创作技巧灵活、史料价值丰富的一类民间口承叙事。从叙事内容来看,长篇口承叙事多是族群先民对早期历史、社会环境和群体意识形态的记忆反映。其人物塑造也多以族群祖先和族群英雄为重点,将族群祖先的个体成长经历与族群早期的历史建构相结合,多层面地反映族群社会发展的具体细节,以及族群普通民众的历史活动。从叙事价值来看,长篇口承叙事更多地承载着记录民族历史和生活经验的史料价值。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长篇口承叙事的出现是底层民众用自己的方式和声音记录族群的历史和发展,是对所谓的族群正史进行讲述、补充和阐释的独特方式和策略智慧,是特定族群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珍贵遗产和宝贵资料。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曾经对口述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指出口述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受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限制,一些族群内部传承已久的生产技术、生活习惯、信仰观念等民俗事象和文化记忆不断弱化、减退直到消失。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各民族广泛流传的民间口承叙事进行挖掘和研究的价值就更显突出。于是,在口头传统研究中,大量的史诗不断被挖掘出来,如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马纳斯》、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梅葛》,以及同样具有史诗价值的长篇口承叙事,如满族说部、锡伯族何钧佑长篇叙事等。
然而,对这类叙事规模宏大、演述篇幅冗长、民族精神与情绪高度凝练的长篇口承叙事而言,演唱者是如何进行逐字逐词地记忆,如何完成篇幅冗长地讲述,如何在每一次的表演中轻而易举地随性发挥与创新,这些有关人类口头讲述创作技巧与思维机制的手段与方法问题一直调动着学者的研究热情与探讨激情。我们说,无论是从口语文化的记忆技巧和讲述方式,抑或是从口承叙事的创作逻辑与讲述过程来看,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节、对仗、套语,即“程式”都集中体现出长篇口承叙事的创作本质及思维技巧。
一、记忆术和套语:口语文化的本质特征
口承叙事,又称“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含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涵盖较广,泛指一切采用口头形式进行交流的表现方式;狭义的口头传统特指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口头类艺术形式,它们都是传统社会的沟通和记忆模式,也是民间文艺学关注和研究的范畴[2]。口耳相传是口头传统叙事的重要传承方式与本质特性,正是通过师傅与徒弟之间的口传心授,演唱者与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等口语文化的使用与传播,口头传统叙事才得以在一次次具体的说唱表演中展现出形态迥异的体裁类型。
无论是在无文字社会抑或是在有文字社会,口语总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交流和记录工具。尤其是在无文字社会,口语的存在价值和应用意义更为重大。然而,与文字的可保存性、可倒逆性及书写权威性相比,口语的主要特点就是即时的、随意的、不易保存的且缺乏讲述权威的,这样口语就不便像文字记录那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正是因为口语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以口语交流为本质特征的口承叙事而言,师傅与徒弟之间要通过多次的口传心授才能使叙事文本得已保留,而讲述者和听众之间也要通过一遍遍地口语讲述才能使叙事的文本得以传承。那么,在口语交流中,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又具有什么样的呈现和特点呢?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Ong)在其论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专门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得出结论:在口语文化里,语词受语音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过程是不同于书面文化的。“在口语文化里,记忆术和套语使人们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构建知识”[3]25。与文字和印刷术的思维和表达不同,在原生口语文化里,思维和表达具有以下特征:(1)口语的实用性;(2)相似或对仗的词语、短语或从句;(3)不断地重复;(4)口语交流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反复吟诵世代流传的经验、知识和传统等,通过反复吟诵加强记忆和传承;(5) 贴近人生世界的;(6)口语将知识纳入世界和竞争当中,谚语、谜语不仅是知识存储的宝库也是斗智的工具;(7)移情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即口语文化是贴近认识对象、达到与其共鸣和产生认同的境界;(8)衡稳状态的,即口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当下之中,人们借以保持社会的平衡或衡稳状态;(9)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即口语文化是处于一定情景之中的。[3]25-27
在对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沃尔特·翁详细总结了口语思维的形成及其特征。提出,口语思维的运用决定了语言必须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平衡的模式;有重复和对仗的形式;有头韵和准押韵的特征;有许多别称或套语;有标准的主题环境;有大量的箴言。这些平衡模式、对仗形式、押韵语汇、别称套语、箴言惯用语等多次重复使用,一是引起听众注意,二是唤起讲述人的回忆,也可以用其他辅助记忆的形式。……”[3]25-26从上可见,口语文化的输出有惯用的记忆术和搭配套语,这种记忆术和套语的运用不仅是口语文化表述者的主观心理需要,更是表述者在进行口语思维和交流的外在技巧性表达。于是,对应到以口语文化为本质特征的口承叙事中,在一次次的讲述表演中,大量重复使用类同的主题、相似的情节、相同的空间以及对仗、套语、箴言等现象比比皆是。
二、“在表演中进行创作”:长篇口头叙事的创作逻辑
同样,在口头传统研究领域内,也有学者注意到口头传承叙事中常会出现一些重复使用的主题、情节、对仗、套语等口传文化特征明显的文本形式问题,并将这些重复现象统称为“程式”,这一学术流派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及学术渊源要追溯到20世纪初史诗学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口头程式理论。
由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创立的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初口头传统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又称“帕里-洛德理论”。两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了一套严谨的口头诗学分析和研究方法,开创了口头传承研究的新领域,现已成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范式。《故事的歌手》是该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从20世纪30年代起,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在南斯拉夫对当地活态史诗的表演时间、地点、听众、表演的具体语境以及表演对史诗艺人的创作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详实的田野调查,两人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弄清歌手们创作、学习、传递史诗的方式,最终得出颇具创见性与影响性的结论:第一,史诗演唱是一种口头传统,它不依靠文字媒介。第二,史诗艺人对史诗的传承不靠逐字逐句地死记硬背,而自有一套创作技巧与方法,口头歌手的表演过程同时也是口头诗歌的创作过程,口头歌手是以表演的形式来进行创作的。每个歌手在成长中都要经历聆听阶段、学歌阶段和提高演技和增加演唱篇目阶段。其中,熟练掌握和使用大量的程式是学歌和提高演技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位歌手逐渐成熟的主要标志。第三,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是口头程式理论的重要概念和研究框架。口头诗人在学艺中一方面坚持类型、主题、语言、表演等技巧,同时也会根据即时的情境进行创作。[4]“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的出现,不仅对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提出传统性与时代性兼具的深刻解释,同时也对口头史诗创作技巧与规律进行了创新性的总结。所谓“在表演中进行创作”,其实质即是对大量程式的熟练掌握和反复运用。
此后,在口头程式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史诗创作的形式技巧与思维机制问题,在对程式所具有的“在表演中进行创作”的逻辑本质一致认可的基础上,纷纷将研究视角放到程式在口头传统中的多种体现与运用上,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口头传统程式研究成果应运而生。如高荷红的《满族萨满神歌的程式化》[5]《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萨满神歌程式化之比较研究》[6]、秋喜的《论〈格斯尔〉史诗的口头叙事传统——以〈圣主格斯尔可汗〉的时间程式为例》[7]《论〈琶杰格斯尔传〉之马匹的程式》[8]《论〈圣主格斯尔可汗〉的人物程式》[9]、扎西东珠的《藏族口传文化传统与〈格萨尔〉的口头程式》[10]、戚晓萍的《“阿欧怜儿”的程式与主题》[11],李建宗、韩杰、阿尔斯兰的《口头诗学:西关裕固语口头诗歌程式分析》(上、下)[12][13]等。学者们多从口头传统的文本形式入手,探讨程式在形态各异的口头传统中的具体应用,强化对程式作为口头传统的本质特征及创作技巧的认知与理解。
三、“反复的呈现”:长篇口承叙事的讲述技巧
按照米尔曼·帕里最初的解释,“程式是一种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13]这组词语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含义往往非常相似,能够组成一组可以替换的模式,且具有一定的修辞作用。在后续的口头传统研究中,程式的涵盖外延不断扩大,既包括最初的主题、故事形式、动作和场景、诗法和句法等,也包括时间、地点、典型人物、动物等惯用词。程式既然是可以替换的,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反复出现的,正是这些大量反复出现的模式化事象才使程式具备了建构文本与不断被替换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可以把程式理解为文本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文化事象,如反复出现的主题、故事情节、时间、空间、人物称呼、动作、场景、修辞方法等。
在口承叙事中,这种不断反复出现的模式和序列的现象非常常见,尤其是在长篇口承叙事中,模式化的呈现不仅是口语文化的必然表现,更是讲述艺人高超讲述才能的塑造工具。与一般的叙事讲述者不同,长篇口承叙事艺人往往具有较高的讲述才能,他们从小就对民间叙事有着强烈的喜爱,记忆超群,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极其善于把零散、片断的故事组织起来,经过生动描述再传播出去。特别是对叙事文本的表述和处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发挥其个体性和能动性,根据不同的讲述对象和表演空间,在文本主题的选择、题材内容的确定、叙事情节的加工、语言表述的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讲述风格与创造能力。此时,反复出现的数字、时间、地点、名称、空间乃至模式化的人物设置、情节发展、结构设计等套路均成为他们讲述的技巧与特征。以口承叙事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发展为例,口承叙事中的人物设置常常是两兄弟、三姐妹、哥仨、姐俩、两个伙伴等。情节结构常有“单纯式”(一般的寓言、笑话和生活小故事的结构)和“复合式”之分,“复合式”又分三段式和连缀式。 其中,“三段式”是民间叙事的常见结构,情节推进往往经历三个层次,三次考验、三次较量、三次历险等。这种不断反复出现的情节不仅有助于讲述者和听众的记忆,同时,以对仗的形式、套语、箴言、复语等形式出现既能引人注意,又便于回忆,更能增加听众对叙事内容的兴奋度及融入度。
如在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头叙事中,由同一角色行动引起的同一事件连续在叙事中重复出现的状况非常多见。仅以《勃合大神传奇》(1)《勃合大神传奇》,载自《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为例,整部叙事中分别出现勃合大神三次被砍掉脑袋、乌洛厚国三次和铜枪国换铜棍、勃合三次遇到伯西里、勃合和亚勤哈杰四次偷听别国国跋的谈话等情节。因何钧佑叙事篇幅较长,这些重复情节多分布于段落之外,数量上一再出现,结构上并列铺排,但内容上或是平行或是递进。例如:勃合和亚勤哈杰用神帽子先后偷听美女国、铁枪国、铜枪国和黄金国的消息,四次偷听邻国消息在结构上构成平行关系,在内容上也平行并列;而勃合三次被砍掉脑袋的重复叙事略有不同。当勃合被砍掉第一个脑袋,即爱财的脑袋后,天堂国将敌人赶出了大木石部落。当勃合被砍掉第二个脑袋,即爱黄金的脑袋后,天堂国战胜了黄金国。当勃合被砍掉第三次脑袋,即爱美女的脑袋后,天堂国战胜了美女国。三次砍脑袋的叙事序列尽管在结构上构成平行关系,但在内容上却层层递进,事件发生顺序不能互换。从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和叙事主题的展现层面看,勃合就是在一次次被砍掉脑袋的量的多次积累过程中,完成从普通人向族群大神的质的突变。勃合创建天堂国的理想也一步步接近,最终得以实现。
瑞士民间文艺研究者麦克斯·吕蒂曾经对民间童话在叙事内容、讲述场景、讲述方式及与听众互动等方面进行过专门研究,对“三段式”的重复运用作出经典阐释。例如,兄弟俩一起去完成同一项任务,要救出三位公主,征服三条恶龙,连续三次从遥远的王国弄来珠宝。此外,童话开头与结尾常有固定的叙述方式等。(2)参见[瑞] 麦克斯·吕蒂著,张田英译:《童话的魅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112 - 119 页。黄天骥、刘晓春:《试论口头传统的传承特点》,《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这些固定叙述方式的出现,使儿童不断地体验早已熟悉的故事场域和生活环境,在体验中经历心理上的紧张、刺激、悲伤及愉悦,并对故事的发展、结尾充满渴望和期待。随着故事情节向前推进,儿童的紧张心理得到缓和,心理期待得以实现,这恰恰是孩子们在听故事时的心理体验,也正是孩子们喜欢听故事的深层原因。(3)同上。
综上所述,在口头程式理论的理解与应用中,仅将程式作为一种口头传统的本质特征而用一个个详实的个案去印证它、充实它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研究思路还远没有触及到程式作为一种技巧在文本建构与讲述情境中的深层次文化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讲,“程式是传统诗歌的惯用语言,是多少代民间歌手流传下来的遗产,对口头创作的诗人来说具有完美的实用价值,还包含了巨大的美学力量。”[14]从口承叙事的传承特征及讲述过程来看,程式作为一种“口头叙事的魅力”体现,它的运用不仅是口语文化的必然表现,也是讲述者组织叙事、设计人物、谋化情节、吸引听众、突出主题的一种技巧手段,更是长篇口承叙事的创作逻辑与思维特征,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