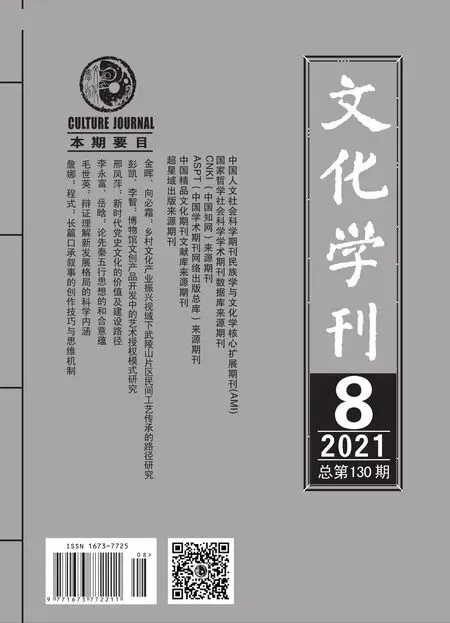从哲学系统的价值契合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021-03-08董琳利
田 柳 董琳利
引 言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中国化?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典型的西方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背景、阶级基础与理论渊源。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言,它“确确实实是一种异体文化”。[1]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谈到,自古哲学有两大系统:一是形式上的系统,即哲学的逻辑与体系;二是实质上的系统,即哲学的要义与精神[2]。如果单就哲学的形式系统看来,各个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哲学无一相通,更遑论契合传承。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中国化,必然要从哲学的实质系统出发,寻找两大哲学系统在精神价值上的共通之处。任何哲学的核心要义和精神总是指向一定的时代主题,并且以一定的理想价值为导向。例如,西方传统哲学探讨世界从何而来,而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人的实现。因此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性,从价值取向出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途。
一、注重人事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
从哲学关心的对象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都非常注重现实人事。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早期的四大学派到古典三杰,哲学家们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在人以外的自然世界,追寻的是超验的“神”或者本体。中世纪哲学之后的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虽然将人纳入到了哲学的考察范围之内,但其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并未能解决人与世界的二分。“在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存在’规定为‘第一哲学’的理论主题后,到了黑格尔这里完成了一次形而上学的大循环。”[3]而人与世界的现实价值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得到了完整统一。
马克思对现实价值的专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首先,马克思关怀的世界是现实的属人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与问题不是人以外的世界与超经验的问题,而是专注于属人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尤其是其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其次,马克思关怀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本体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种先验的“神”或者“上帝”;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作为本体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实践的、现实的存在。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视为人的存在方式,从实践出发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始终重点关注人以及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命运。“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由的论述都是以人事的现实主义价值为导向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的人的幸福必须是人的现实幸福。马克思批判宗教带给人的是“虚幻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人民的现实幸福”。[4]在此,马克思将宗教驱逐出人的幸福。幸福“不是仅指人的直观感觉或心理感受”,因此幸福并不等于伊壁鸠鲁学派所说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状况”。[5]所以,幸福并不是超历史与超社会的体验,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与社会关系中对人的根本价值的实现。
中国传统哲学在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相似性,都对经验人事与社会人生投注了极大的关注。孔子讲:“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由孔子始,中国传统价值观就具有了注重社会人事而不谈超验对象的倾向。此后的历代哲学家都不太讲神性逻辑和神本价值:孟子强调“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其民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关注社会民生的价值取向;“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易传·系辞下》),也强调圣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百姓,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墨子“兼爱”,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墨子·兼爱下》),胡适将他的理论称为实利主义,正是看到了墨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对现实人事利益的追求。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哲学关注人的尊严、注重人的价值是以承认阶级秩序为前提的。[1]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都对现实主义的价值投注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对象上关注现实的世界、注重现实的人、追求人的现实幸福,才使其能够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上落地生根。
二、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
从哲学体现的价值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都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将社会整体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中诞生的个人主义具有显著差异。个人主义过分强调的个体价值本位,却[2]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二分。个人主义所讨论的个人的尊严、价值和自由权利都是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抽象价值,离开社会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作为价值主体并非一个个体概念,而是指社会整体的人,他将个人价值放回到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自由。”[6]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自由价值自然只能在社会中体现并实现,所以社会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因此马克思将社会集体视为最重要的价值主体。高扬集体主义体现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要理解马克思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须先厘清“集体”这一概念。简单来讲,人本身的社会属性决定人的最高价值,即自由的实现也必须要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都共同追求着自由,所以他们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除了这一目的之外,其他一切的制度设计都是保障自由实现的手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实的集体”。从集体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价值主体的规定: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并非独立的个人,它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一个群体;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又并非一个简单的群体,而是具有共同的自由目标的全体人类。因此,有人说马克思对价值的判定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重视个人的价值到无产阶级的价值,再到人民和人类价值”。[7]虽然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但是他的终极的追求是全人类的解放,关注的价值主体也是人类整体。
中国传统哲学在价值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致,其“尚公”[8]的伦理精神恰恰体现了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先哲也认识到了人的社会性:荀子说,人的力气比不上牛马,但牛马却能为人所用,这是因为“人能群”(《荀子·王制》)。人的社会性决定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因此,中国哲学家们普遍认同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之“私”应该服从整体之“公”。“公”也称“公义”,“私”即为“私利”。中国哲学对整体主义价值的强调也在历代思想家的“义利之辨”中得到集中凸显。虽然其中也有思想家强调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是他们都认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人民之大义。诚然,中国传统的“尚公”精神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所指向的价值主体是不完全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是指人的“自由联合体”,是关怀全人类的整体主义;而中国古代的“公”则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整体主义。就内涵而言,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似乎要比中国传统的尚公精神更加进步、更加高级。但是对于今人所处的这个时代而言,二者的彼此扬弃则是必须的:一方面,马克思理想的集体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而对于目前来讲,理想的集体固然是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现实的集体才更具有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所具有阶级性是必须抛弃的,但是它所具有的民族性与国家性则具有时代适用性。
三、自由世界的理想主义价值取向
从哲学承担的价值使命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包含着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现实世界的矛盾,还承担着指明通向理想世界道路的使命。上面,我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互补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取向上更具理想性,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更多地体现了保守性。但这一区别仅是就现实价值而言的,从理想价值来看,两大哲学系统所包含的人类终极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
马克思的理想世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不再停留在对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追求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与道德觉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世界”的含义是指人的社会性与个性协调发展的世界,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公正充分得到尊重与实现。但现实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雇佣劳动造成了人的异化,使人不能获得自由。因此,马克思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哲学必须承担的价值使命。共产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终极理想的描画,是人类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人类尊严的终极表达。“自由是正确认识必然性基础上的意志自觉自愿与行为自主自立。”[9]因此,马克思对自由世界的描述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世界的自足,二是意识领域的自觉,三是实践活动的自主。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自由世界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极其突出人类对自由世界的使命感。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自由世界的存在。老子的自由世界是一种“小国寡民”的朴素生活状态:人们对自身的衣食感到满足,安居乐俗,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保持互不侵扰,百姓回归到自然自足、质朴善良的本真状态。孔子的自由世界是“大同”社会:社会组织“选贤与能”,人际相处“讲信修睦”,人情关怀“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天下为公”是一种秩序井然而又温情脉脉的状态。孟子的自由世界是通过“仁政”实现的“王道乐土”:“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总结的是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伦理和谐有序的图景。张载则从道德境界的层面阐发了他“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凸显了天下一家、平等互爱的人情关怀。虽然历代先贤所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不同的概念,但他们所勾画的人类自由世界都具有以下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气致祥的相互成全,二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得的温情关怀。
就自由世界的表现形式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具有很大区别: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阐发的,是物质性的理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是从社会伦理意义上阐发的,是道德上的理想。但是,两大哲学系统所指向的终极价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一,以人为价值尺度。马克思的“自由世界”要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世界衡量标准是人的自我实现;而中国传统理想社会的实现总是集中表现为人的幸福生活,自给自足、人际和睦、平等互爱。第二,强调人的作为与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解放是人自己解放自己,人对自身异化的扬弃是人自由选择的必然使命。靠自己的努力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中国传统哲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强调人的作为在建立理想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强调人的自觉作为的同时,将人的历史使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上,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体现了一定的阶级局限,并且具有很大程度的空想性,但是其理想世界所体现的某些价值取向仍然具有普遍意义[3]。也正是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理想才能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哲学“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正是如此不同的民族、地区之间的哲学才能够进行‘对话’”。[10]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有了可能。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成为必然,这是与两大哲学系统的精神价值的契合分不开的:从价值对象来看,两大哲学系统的关注的对象都是现实的人事;从价值主体来看,两大哲学系统讨论的价值主体具有互补性;从价值使命来看,两大哲学系统追求的理想与使命具有同向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又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后又与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相联系。历史表明,在马哲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了无数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挑战。而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融合生长还在继续,我们面对的挑战还将继续并长期存在。我们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如何处理好马哲与中哲之间的关系,都关系着我们能不能继承好中国传统哲学,能不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