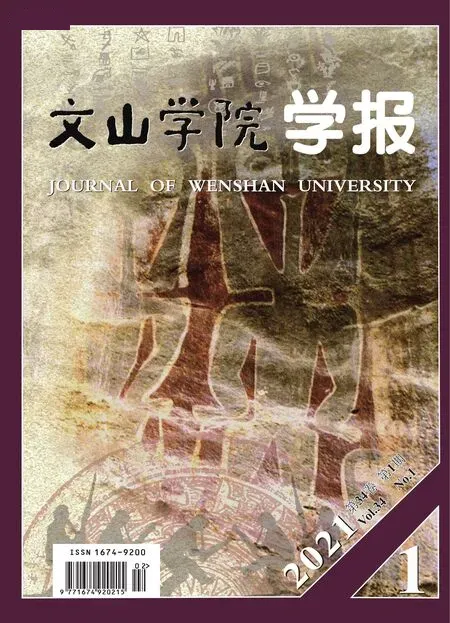内蒙古乌梁素海渔民生计转型与生态适应
2021-03-07陈蕾
陈 蕾
(1.内蒙古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2.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00)
一、为什么要研究“乌梁素海”的生态与生计
生计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生计转型在社会转型中最为根本,内蒙古乌梁素海传统的渔民生计在自然环境变化、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推行的新理念、新技术以及渔民自身发展诉求等三方作用合力下发生转变,形成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的多元生计共存局面。
关于生计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关系早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生态人类学开创者——朱利安·斯图尔德认为,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而非是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在环境的型塑下而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征,文化生态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并认为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变迁都由技术或生计变化而引起的,其中生计方式是其文化核心。[1]贵州当地人为适应独特的喀斯特山区,发明创造具有山地特色的多种渔业手段,这种延续千年的传统渔业生计对当下生态维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还有针对其麻山地区喀斯特石漠化的现实困境,当地苗族通过多种作物之间系统配置形成复合种养生计,巧妙规避当地高温辐射、表土稀缺、水资源匮乏及土石不稳定等脆弱的自然环境,使复合生计模式与生态环境耦合运行。[3]德昂族生计选择变迁受到历史上民族战争、迁徙等社会因素影响,从坝区种植水稻向山地农业转变,为了适应生境变迁而做出生计方式转型的调整。[4]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的族群,通过家庭、团体等社会组织形式,族群的生计方式、婚姻状况、人际关系、社会规范等都与该社会组织息息相关,有学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选择能有效地抵御自然环境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期实现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适应。[5]还有的学者从环境人类学视角分析水环境恶化对渔业的影响,将其与所在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以及当下全球化和现代化相关联进行分析,从政治、经济、历史等多重视角来理解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化之间的关系。[6]此类相关研究都反映出生计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是一个动态过程,既要考虑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又要考虑社会环境在全球化、现代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社会组织及规范等层面的变迁,从而实现生态、生计和文化相互调适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注重南方少数民族生计文化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研究较多,对北疆民族地区生计与自然环境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对北疆乌梁素海区域的渔民生计研究甚少。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的北部边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同时也是具有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多元生态环境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形塑着不同的生计,而“水”又是其他一切资源的基础和根本,因此,水生态的治理与保护尤为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乌梁素海渔民生计转型与生态适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地方经验和个案研究。
二、乌梁素海区域与传统渔民生计
自古以来,乌梁素海区域确有系天下安危的区位重要性。古代地理概念里的乌梁素海区域属陕西的一部分。顾祖禹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7]该区域一直是历朝历代的边疆战略要塞。近代以来,随着大规模“走西口”移民浪潮涌入以及利用黄河开发的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再结合当地的“山水林田湖草”复合生态环境,不同民族以各自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及生存策略等衍生出农、牧、渔等传统生计。简言之,边疆要塞、复合生态环境、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和走西口人口迁移四大特点构成了传统渔民生计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一)边疆要塞
就地理位置而言,乌梁素海位于北纬41°,东经108°,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境内。地处乌梁素海区域平原最东端,是承接该地区灌溉排水的唯一区域,也是全国八大淡水湖之一及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素称“塞上明珠”。乌梁素海区域平原北有阴山,南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乌兰布和沙漠。《汉书》记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而唐代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阴山的屏障作用,自商周至清朝2000余年一直是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双方冲突的战略要塞,历史上,乌梁素海区域一直处于边疆军事战略要地,而近代以来,乌梁素海区域的角色发生转变,由战略要塞变为了农田垦区,“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是近200年以来的真实写照。
(二)复合生态环境
就多种自然环境而言,乌梁素海区域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构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囊括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样化自然环境,其中,以水为中心,形成农业、畜牧业及渔业等多种生计模式并存,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依据各自独有的生计文化对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加以利用,“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在特定民族生计方式的作用下具有社会性和文化归属性。任何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的客观外部自然环境并非百分之百地加以利用,总是按照该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去有选择地利用其中的一部分。”[8]而生态环境也并非是纯客观自然环境,而是经过文化加工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与生计文化之间互为影响,耦合运行,而不同生计模式背后是不同族群文化的互融及社会组织的运转。
(三)引黄灌溉水利工程
乌梁素海区域水利开发是随农业生产而兴起。据史料记载,该地区水利开发最早始于西汉,相继北魏以至唐代,均有不同规模的开发。后因黄河故道变迁,古代引水渠道废弃,清乾隆年间,近代农业逐渐开发,水利事业又随之而兴,到清末民初,已开挖塔布、长济等9条较大河渠,并开挖数十条支渠和大量下级引水渠道,农田水利初具规模,民国年间,由于战乱,渠道管理不善,年久失修,加之黄河大水频繁泛滥,许多渠道引发水灾,造成严重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筑坝防洪,治理黄河,保障沿河人民的生产与生活。[9]而乌梁素海是引黄灌溉水利系统中唯一的退水渠,是引黄灌溉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灌溉退水和季节补水的重要功能。
(四)走西口与传统生计
“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移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清朝以及民国年间陕西、山西等地的大批民众经长城西段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等关口出关,徙居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从事农耕与商业经营等活动的移民运动。它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到民国后期达到高峰,持续了近三个世纪。在“走西口”这一漫长的移民过程中,大批来自内地的汉族的进入,使内地汉文化广泛地传播到内蒙古西部地区, 引发了当地人口结构和生计的剧烈变迁。乌梁素海区域早在战国时期,游牧是其最主要的单一生计模式,自秦、汉至隋唐时期,乌梁素海区域一直是中原和少数民族争夺的边疆要塞,虽实行移民屯垦,但由于政权更迭、战争频繁,农耕时断时续。直到明清之后,黄河改道,土壤肥沃、水资源充足,为农业、渔业等生计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使得中原地区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大规模迁至乌梁素海区域。
正是由于该地区处于军事战略要塞,兵家必争之地,促使各民族在此交汇,从而形成农牧交错地带,同时又基于多种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走西口的移民中多以汉、回、满等民族为主,与乌梁素海区域蒙古族相互交流、交往,逐渐形成今天汉、蒙、回、满等多民族共同体(杂居格局),“人是生物圈中最高消费者,人口因素通常被认为是产生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根源,人口问题成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0]从而也构建了该地区独有的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生态文化共同体。
三、传统渔民生计向新型渔民生计转型
近年来,国家对内蒙古的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视。2019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时强调:“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的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2019年7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2020年5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可见,北疆生态治理与保护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不仅关乎北方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更关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经济的新发展理念的推行与实践。新时代的乌梁素海区域正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下,传统渔民生计向生态渔业转变。
(一)渔民生计发展与繁荣
发展起步期。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乌梁素海区域交通闭塞,人口较少,1954年开始陆续从河北的安新县、霸县、文安县,山西的保德、临西,内蒙土默川等地为谋生迁入该区域,利用乌梁素海特有的自然环境,形成以捕鱼、打苇等为主要生计,过着秋去春来的迁徙生活,当地人称之为“雁行渔民”。随渔获量增加和经济收入提高,不断吸引周边人口迁入,使得这一时期渔场居民达到320户,总人口1789人。在党和国家政策引领下,个体渔民因生产需要组成9个渔业合作社和1个船运合作社,并于1960年6月成立了国营乌梁素海渔场,改变过去零散的个体捕鱼行为方式,形成产供销一体的渔业组织。该时期乌梁素海水域达800平方千米,水质好且明水面大,每年渔获量均在200万公斤以上,其中大鲤鱼约占90%以上,人水关系和谐。乌梁素海区域渔民生计的起步发展,一是得益于该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良好,新中国成立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劲头十足,且水生态环境良好,水域面积大且水质好,不同的自然环境型塑不同的生计,优质的水生态环境与渔业相适应;二是得益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入(走西口),自然环境与生计文化之间互为影响,耦合运行,因此,大量移民进入乌梁素海区域依据自身的文化特性、价值观念、生存技能等充分利用当地的水生态环境,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生计模式。
发展缓慢期。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由于受“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渔业发展遭受重创,不切实际的围湖造田、拦河筑坝,造成水域面积的一再缩小,严重影响渔获量,1966年最高渔获量300万公斤①,而1974年最低捕鱼量只有30.5万公斤,形成强烈反差。另外,由于人口的不断迁入,使得渔场劳动力大幅增加,加大鱼的捕获次数和频率,一定程度上造成鱼产量减少,使传统捕鱼业发展缓慢。
发展腾飞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末,渔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呈现出生产发展快,经营效益高局面。80年代末,芦苇年产量高达73300吨,创自建场以来的历史新高,并成立芦苇公司,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销往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营口、呼和浩特、包头、西山咀、前期、集宁等以及北京、宣化、丹东等地造纸厂,极大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鱼、苇、蒲等产量剧增且经济价值颇高,当地渔业村民家庭收入相比其他生计村民高出很多,从而导致其他生计转向渔业生计;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加强渔政管理和水生态修复,使得该水域面积得到扩大,渔获量较快回升,年均渔获量达80万公斤左右。
总而言之,20世纪50至90年代末乌梁素海区域的传统渔业整体呈快速发展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渔场)因地制宜,传统渔业生产“以养为主,养捕并举,多种经营”为方针,极大调动当地渔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该时期乌梁素海水生态良好,受到农业化肥、工业废水等排污较少,水质好,渔获量多、芦苇产量适中,渔民经济收入较高;除此之外,传统渔业生产中如休渔期禁止打鱼、冬季打苇等行为都是渔民保护生态的地方性知识的具体体现,渔民积累了许多保护海子生态的经验和知识,并融入其日常生活和价值文化中。
(二)渔民生计衰落和水生态恶化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乌梁素海区域的渔民生计遭遇发展困境。2004年特大水污染案到2008年黄藻大面积爆发,导致“靠湖吃湖”的传统渔业失去赖以生存的资源,渔民生活水平一度降低甚至陷入贫困,不得不外出打工或兼营其他生计。一位当地渔民回忆起2004年的情景,当时海子里面是发黄的,水里面是发黑的,一闻就是臭的,就有股刺鼻的那个味道,水面上漂浮着那白色的东西,鱼塘的鱼死了,整个死的多。看到死了大量的鱼很可惜,以前海子水直接舀上就能煮鱼吃,现在这酱油色的水别说吃了都不能靠近,太刺鼻了。自从这以后,年轻的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由于渔民没有耕地,所以只能养一些猪、羊、鸡、鹅等维持生活②。
这一时期渔民生计的衰落与水生态恶化有直接关系,探究水生态恶化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导致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为了极力摆脱贫穷状态,一切向“钱”看,地方开始招商引资,投资建厂,自1958年兴建造纸工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展为2个中型造纸厂、1个小型造纸厂以及其他相关企业,成为当时该区域的主要产业③。由于企业数量增加,废水排污量大,远远超出了作为排水渠的乌梁素海承载量,一度造成乌梁素海水污染事件,形成“公有地悲剧”[11],人们一味地利用乌梁素海的水、渔业、苇业等资源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极少对其进行生态保护和维护,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利益的失去,捕鱼量减少、芦苇滞销迫使传统渔民不得不转向其他生计。
(三)渔民生计转型与水生态恢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以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为对立面扭转为统一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已然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梁素海区域正是这一新发展理念的践行个例,传统“靠湖吃湖”的渔民生计向生态渔业、生态苇业及生态旅游等多元生计转变。
“捕鱼人”成为“护海人”,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再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转变思路,许多捕鱼人通过专业培训和技能学习,逐渐转变为保护乌梁素海生态的专业人,为了统一实施捕鱼作业,渔场集中收购捕鱼人的渔具,达到了既不闲置渔具也有一定经济补偿的双赢局面。渔民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思维和价值观的转变和渔民文化内部自身发展诉求。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推行下的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并举的新发展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人是发展的主体,渔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传统渔业生计转型的主观内驱力,正是这一主体性发挥,从以前单纯追求经济的捕鱼人转变为既保护生态又发展经济的护海人。
“土特产”成为“艺术品”,以前乌梁素海芦苇在人们固有思维里仅是用于牲畜饲草、编织苇席、苇帘等手工制品,由于市场需求量少,导致人们冬季打苇一直处于不打不行但打了也没用的矛盾。在生态经济引领下,转变思路,引进新技术,从以前简单粗放型的芦苇加工蜕变为创新型的艺术创作,渔民们开始意识到科技知识、创新能力及思维观念的重要性,逐渐从传统渔民向文化渔民、生态渔民转变。在乌梁素海坝头特色旅游纪念品基地就业扶贫车间,56岁的刘月琴拿起一片用水浸泡过又沥干的芦苇,用滚轴将其碾平,然后开始编织。一个多小时后,一个精致小巧的收纳篮就编好了。“芦苇秆用处特别多,可以编织席、筐、帘子、鱼篓子等,还能做芦苇画。这些老师都教过,我也都学会了。”说着,她指了指身后展架上摆放的各种手工艺品及摆件,个个精巧别致。2018年,地方转变观念,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芦苇、蒲叶、芨等资源,渔场与乌拉特前旗一家工艺文化公司对接,推出了旅游特色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公司提供原材料,进行免费学习,学员做的合格作品公司全部回收。
生计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外界力量的介入,更重要的是人们思维的转变,从而影响其行为模式。从传统的捕鱼、打苇等生计到渔民身份的转变、新技术的引入以及生态旅游业的兴起,改变了当地人的传统生计,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真正地参与到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经济的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四、结语
北疆乌梁素海区域的传统渔民生计方式是在自然环境、国家力量、市场经济以及渔民自身发展诉求中发生转变的,该区域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边疆地理位置、复合多样的生态环境、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以及历史上走西口的人口迁移等特点,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方式发展渔业,从而完成传统渔业向新型渔业转变。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以及渔业市场的经济利益诉求都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但乌梁素海区域的渔民文化内部的自身发展诉求和发展实践是最为重要的动因。
在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行与实践中,乌梁素海区域的人们根据自然环境、自身历史经验和发展诉求改变原有的传统渔业,不断调适人与生态环境的适应度,以期实现人水关系和谐,这才是最为实际而有效的发展路径,同时,这也生动地体现乌梁素海渔民作为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区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中突破原有的发展困境,并且不断探索人与生态相适应的生计模式,这种生计转型实践,不仅能够让乌梁素海渔民在渔业市场体系中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路径,也能够驱使他们继续寻求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地区文化以及促进人性发展的路径。
注释:
① 《乌梁素海渔场志》编纂办公室编,乌梁素海渔场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16-20.
② 此访谈资料均来自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乌梁素海实地调研所得。
③ 《乌拉特前旗志》编纂委员会编,乌拉特前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15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