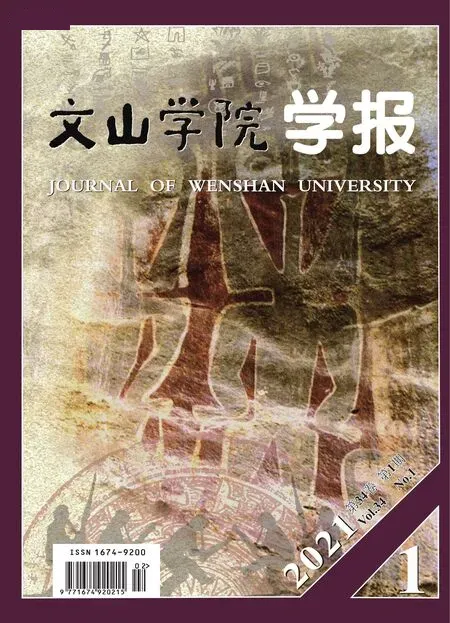民国《大理县志稿》的编纂及其时代内涵
2021-03-29魏舜召
魏舜召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地方志因突出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成为研究区域社会生活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激烈变化的一个时期。云南则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自治州县最多的边疆省份”[1]。民族与边疆构成了云南突出的“地域性”,加之清末民初激烈的变革赋予的“时代性”,使得此时期的云南地方志极具研究价值。民国《大理县志稿》创修于民国元年(1912年),初稿完成于民国四年(1915年),并于民国六年(1917年)重新删订,是此一时期云南地区纂修为数不多的体例较为完备、内容较为充实且经付梓的地方志书。其对于了解清末民初大变革后,大理乃至整个云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人民思想状况,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然笔者检阅知网、读秀等学术平台,均未见有关专门论著。《云南地方志考》[2]与《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3]虽对其都有著录,亦做了提要式的介绍,然未免简略。笔者窃不自揣,以下仅从编纂情况、志书所体现的时代内涵两方面,对民国《大理县志稿》略抒浅见,求教于前辈方家,兼为抛砖引玉之作。
一、志书的编纂情况
民国时大理县,在明清时称太和县,为大理府治所。民国二年(1913年),政府通令废府厅州制,改太和县为大理县,辖区与今大理市略同。按有关文献记载,大理县修志始于明万历年间,其后于康熙、道光年间又有纂修,可惜均未见传世。[2]68民国《大理县志稿》属于官修方志。虽然官修方志自明清以降,已形成了地方官主修、社会各界参修一套相对固定的地方志编纂模式。然因地方志有其地域差异性,尤其对于云南边疆多民族省份而言,更是如此。民初的云南,有“衣冠人物,颉颃中州”[4]61的大理,又有“交通闭塞,文化榛秠”[5]的镇越,可谓经济、文化发展极其不均,如此势必影响到修志活动的进行。兹就编纂过程、人员组织分工、志书文本情况四个方面对民国《大理县志稿》的编纂情况论述如下。
(一)修志过程
按卷首序言,是志之修,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大理士绅因感于“宇宙重光而邑志阙如,无以信今而传古”,遂集体商议重修县志。周宗麟、杨楷、范宗莹等人主其事,并“假毛公祠设局采访”。初定体例为“十二部分目三十六”,由众人分门编纂。民国二年(1913年)冬,书稿将毕,虞舜知来任县知事,定李文琴、杨楷、周宗麟共为总纂,又推李德徵,周宗莹为校正。民国“甲寅(1914)秋七月”,全书脱稿。[4]13-21志书成后,旋由县知事“送省长交辑刻丛书处审核”。“丙辰(1916)十月”,省公署发还志稿,“命将指驳各节重加校正”。众人又公推周宗洛为总校。周氏“几经审慎”,删订志书,定“纲十二,目六十有四”,“阅九月而蒇事”,并于省城续捐印费,印书两百部,“分布全邑学校”。[4]73-76
民国《大理县志稿》的修志过程大致如此。从中我们可一窥官方修志的一般过程,大致要经过倡议、设局、定体例、采访、纂修、校对、送审、删订、刊行等步骤。可以说,民国《大理县志稿》是一部流程相对“规范”的官方志书。然是志的修纂,并非一帆风顺。正如是志总校周宗洛所言,是志修于“兵戎初靖,震恐未安知”之际,“中间更番经历梗阻,而赖有定力支持,迄未蹉跎”。[4]76是志主纂杨楷亦谓:“虽城乡之冲突、士绅之龃龉,杨逆之叛乱,屡次经破坏,而卒底于成。”[4]65可知民初纷乱的时局,对修志的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大理为滇西名城,人文荟萃,素称“文献名邦”,尚且如此艰难,修志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
(二)组织分工
按民国《大理县志稿》卷首“修志姓氏”,是志分工有监修、纂修、分修、采访、干事、缮写、绘图。
监修也称主修,纂修也称主纂,是一部志书的主要负责人。如目录书记述志书的责任人时,通常仅记“某某修”“某某纂”。主修通常都是地方官长,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如修志机构的建立、人员的组织、经费的筹集等。主纂则通常是地方上有学问的名士硕儒,主要负责整体上把握志书的编纂,如体例的制定,材料的取舍,以及对分纂的成果“集其成”。按是志之修,从始至终,皆由大理本地乡绅邑人发起与纂修,期间大理共有四任县知事走马上任,虽都列“监修”之名,实则仅是挂名而已。何以见得?试看卷首唐继尧、由云龙等人的序言,通篇只提“邦人君子”[4]1、“邑中贤智”[4]7,却只字未提地方官长。时任县知事虞钺亦只说:“邑绅设局修志。”[4]61再结合是志主纂李文琴在序中言:“一切凡例则出于杨正修君楷,财政则始于张荫远君肇荣,成于周瑞章君宗麟。”[4]69则是志的经费亦全由士绅负责。由此可见,民国《大理县志稿》可以说是一部完全由地方士绅主导修纂的地方志书,外来官长于其中影响甚微。
是志虽分主纂、分纂,实则并无主次,或者说主次意味不甚明显。通常而言,主纂之职,应定于志局建立之初,并由主纂订立体例,制定纂修计划,所谓“笔削宗纲,唯总纂是赖”。然按卷首范宗滢序言,是志设局之初,众人对主纂之位“皆谦让未遑”,故体例章程只能“折中一是,集议商榷”。[4]20体例定后,由众人分门编辑。至编稿渐脱之际,主纂之职仍然虚位,后才由县知事定周宗麟、杨楷、李文琴为主纂。现根据周宗麟序,将各部门分纂人员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民国《大理县志稿》各部分工表
由表1可知,是志名义上的主纂,除李文琴外,周宗麟、杨楷亦任分纂之职,且所任之部门,亦无较他人为多。综上,似乎可说明,民国《大理县志稿》的纂修,实为大理士绅群策群力之结果,其中难有主次之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劳动成果。其他如采访、干事、缮写、绘图诸职,顾名思义,职司分明,本文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志书的文本情况
是志共三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附正误表一册。卷首分别列唐继尧、由云龙等十一人序言,其后依次为纂修姓名、凡例、目录、捐款姓名、书后。正文共分地理、地志、建设、食货、社交、学校、武备、祠祀、秩官、人物、艺文、杂志十二部,共计子目六十有四。每部首都撰有小序,述其意旨。文中于记叙之外,又常有按语、附论,于此尤可见时人的思想状况。是志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其一,天文、地理、地质各部,多运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叙述,卷首各图亦采用新法测量。其二,经济、教育、军事的内容在志书中的比例较旧志大幅增加,体现了志书的时代特色。其三,是志于人物、艺文两部尤详,占全书近四分之三的体量,大量收录大理人物资料与地方文献,详实地反映了大理的风土人情。是志存民国六年(1917年)铅印本,云南省图书馆藏,另《中国方志丛书》《大理丛书·方志篇》《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均收录其影印本。
二、志书的时代内涵
“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6]6地方志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自然也不例外。又因方志的书写必是在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下,由具有相当思想能动性的编纂主体,精心设计,然后完成的。其修纂的初衷、体例的选择、材料的取舍、叙述的重点、情感的表达等方面,无疑又会反过来映射其身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现有的方志研究,多集中于志书本身,或考订其作者、版本、编纂事迹;或探讨其编纂思想、体例的变化;或发掘其内容的史料价值,将地方志当做获取史料的宝库。凡此种种,都无疑割裂了志书与其书写者,及其所处的时空情境的联系。
(一)改朝换代背景下的情感表达
辛亥鼎革,国体骤变,由专制而为共和。这对于在传统儒家封建纲常理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群体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在清末民初的那场巨变中,云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武昌首义,云南积极响应,为“第四个独立的省级政权”[7],其后又有援川、援黔、援藏,护国之役。彼时的云南显现出革命积极践行者和维护者的姿态。但以上这些历史叙述的中心点都是所谓的大人物与精英阶层,都是被“置于一个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8],从而忽略或者说较少地关注地方上小人物的历史叙述与情感表达。民国《大理县志稿》,从倡修到完竣,皆由大理本地士绅主导,可以说,是地方意识的集中体现,正可为我们研究地方士绅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的情感表达提供“标本”。
民国《大理县志稿》的编纂者们在各自序言里,无不着重强调了改朝换代与是志纂修的联系。周宗麟认为:“以往者既废兴迁移之莫稽,现在者则改革建设之宜纪。”[4]13金在镕则更明确指出:“时代变更,志其尤亟。”[4]59范宗莹也说:“宇宙重光,而邑志阙如,无以信今而传古。”[4]20概言之,他们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都认为眼下的改朝换代应该马上被记录下来。更有甚者,将地方志的纂修同“共和”与“民主”相联系,认为方志是“共和”必然的产物,称“专制时代可以无志,共和时代则不能无志”,因专制时代之“国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在民主的共和时代已不合时宜,而方志正是“民史之滥觞”。[4]63-65由此言之,是志的纂修,非但是应该为之,更为必要之举。
是志的编纂者在改朝换代这件事上的态度或者说所持的立场是鲜明且激烈的,即反对专制,拥护共和。如周宗麟所谓:“中华民国共和告成之岁,邑之人士额手称庆,以为自今以后始脱奴隶籍作主人翁,永享莫大幸福矣。”[4]13又如范宗滢所谓“宇宙重光”。“重光”“奴隶”“主人”“幸福”等词,已是寓意明显,褒贬自明,即是对专制制度及清朝政府的厌恶,以及对实行地方民主自治的期许。二者实为一体两面,专制制度与清朝政府是地方民主自治的阻碍,地方民主自治是消除专制及推翻满清政府的目的。大理士绅对专制制度以及满清政府,可谓深恶痛绝。于专制制度,书中言道:
古昔圣君贤相,抚有国家,莫不顺人情之自然,听人民之自由,集合自由,交际自由,……夫何间然自后世暴君污吏,执天下一切权利皆为私有物。猜忌横生,厉行愚民政策,于人民乡约社会之交际弗辨是非,悉著厉禁。致使人民不知爱群,不知爱乡,极其弊而流于不知自爱,人不自爱,何有于国,我国之弱,由是而已。[4]343-344
而于满清政府,大理士绅更是加之以无情地控诉:
自建虏猾夏,神州陆沉,吾邑抗违受殃独烈,明令之诛残既酷,无形之摧挫尤深,以故二百余年之间,士气郁湮,人才消歇,上溯有明,判若霄壤。……此苍洱文献名邦受虐于虏者之信而有徵也。[4]661-662
综上,大理士绅于专制制度,于清朝政府,最大的痛点在于其对地方的层层压制,以至地方“士气郁湮、人才消歇”,更不得“集合自由,交际自由”,不能自由发展。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大理士绅已认为“公仆役于民事”为“古今同揆,中外合符”的世界公理。自然越发对“督藩道府,高拥位禄,层层钳制,势如赘瘤”的清朝政府嗤之以鼻,[4]133进而对于新生共和国满怀期待。他们认为,只要给予大理人足够的自治权力,“无有压力,无有掣肘”,凭借大理人民的聪明才智,通过社会改良,假以时日,便并可比肩西方,“方之瑞西,讵遑多让”。[4]17
(二)内忧外患下的危机意识与奋发图强
自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列强纷至。英、法觊觎我西南已久,不断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我西南边疆攫取利益。1894年英国强迫清廷签订《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将江心坡、片马以北之中国领土,定为“未定界”,至1911年,英军更是强占江心坡,“逼近大理丽江,有横截川藏,直据长江上游之势”[4]477。灭种之祸,势如累卵。辛亥革命虽推翻了专制王朝,却并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北洋政府不仅对外完全承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权利,对内也无法掌控全国的局势。民初的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正如周宗洛感叹的那样:“嗟夫!异族据国,毒痈残贼,殄灭今已六年,武人专制,祸国殃民,消除不知何日。”[4]76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大理士绅们的忧患意识被唤醒。
1889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其糅合了斯宾塞和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创造性地宣传了一种适应中国现实改革需要的进化论思想”。[9]5如果说现实的环境激发了大理士绅的忧患意识,那么进化论思想则给予了他们思想的指导和理论的依据,进而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便是“力图进步,并驾齐驱于富美强欧”[6]54。此种信念首先体现在修志目的上。传统的修志目的,不外乎“存史、资治、教育”[10]三条。而民国《大理县志稿》却于传统修志目的外,鲜明地增加了警示与激励世人的目的。如是志凡例所言:“综覆全志精神,不外注重乡土,警励乡人。”[4]36再如以下两段文字:
方今世界潮流,浩浩滔天,国势之危,日形颠覆,非人人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而仍麻木不仁,宰割听之,吾恐为主人者复降为奴隶且旋等于牛马,究何冀幸福之克享也,何不惧哉!可不警哉![4]17
虽然尤有虑天演公例,优胜劣败,自今以往,日陷于竞争旋涡之中,负山面海,地仅百里,加之土地瘠薄,物产无多。苟不于学校、农业、工艺、商务诸大端兢兢焉,日思所以胜人,其何以立足于生存之世乎?[4]65
都出自是志编者序言,几乎是异口同声,且言辞恳切,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其忧国忧民之思,催人奋进之意,读之令人动容。方志编纂者们爱国爱乡、拳拳赤子之心,在此间表露无疑。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列强的步步紧逼,大理士绅们清醒地认识到“侵略即分割之初步”。在进化论得影响下,他们明白了“国际竞争,弱者必受支配于强者之势力范围下”的道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非人人知兵,乌足以图存”,要想自强,必以“铁血主义为立国无上之政策”“扩充武力,去罄文弱”。[4]477-478对于如何实施铁血主义,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即实行“军国民教育”。[4]457-458“军国民教育”思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极其风行,其内涵简而言之,即“寓兵于民,全民皆兵,批评传统的文弱教育,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素养”[11]。志书的编者们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使现有之领土,共图保存”,进而更提出了“即已前失之东隅者,亦不可不收之桑榆”[4]478收复失地的愿望。
除了军事上的改良,大理士绅的这种危机意识与改良图存的迫切愿望还体现在对工商业的重视上。在古代中国,历来重本轻末,视商务为末流,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地方志虽都有“食货”一部以记地方经济状况,然大多仅记赋税、户口,于工商业却鲜有涉及。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输入,对中国的自然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云南地处西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历来为中外交通要道,又因蒙自、思茅(今普洱)、腾冲先后被迫开关,对于西方的经济侵略,云南便更是首当其冲。是志对此有着生动的记述:
吾邑自咸同以前,初无所谓洋货。光绪初,洋货始渐输入,洎越亡于法,缅沦于英,于是洋货充斥,近则商所售售洋货,人所市市洋货,数千年来变迁,未有甚于今日![4]349
面对如此局面,大理士绅们已认识到,单单是“力崇简朴”“节衣缩食”,已“不足以图存”,而只有“驱重事业,食足货通”,才能“不至入于淘汰之域。”[4]224
(三)“华夷之辨”历史记忆与“五族共和”新思想的矛盾交织
云南作为多民族地区,地方志书中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载较中原地区为多。对于少数民族记载的考察,除了可以一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外,从记述者的笔法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其鲜明的民族观念。虽然在“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亦将“夷狄”看成“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又因“华夷之辨”的存在,始终不能平等待之。此种思想已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观。及至清末,清政府立宪派为缓和国内矛盾,提出“五族大同”的口号。1912年1月1日,孙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首提“五族共和”论,即“合汉、满、回、藏、蒙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回、藏、蒙诸族为一人”,继而成为了民国的官方思想。[12]
民国《大理县志稿》虽言之凿凿,明确喊出了“合汉、回、藏、蒙、满,数族建立一完全无缺之共和国体”[4]504的口号,体现了对官方政策的尊奉。却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华夷之辩”的传统思想。前文已述及志书编纂者在改朝换代大背景下对清政府专制体制的抨击。然除了直抒胸臆的口诛笔伐外,似乎用了另一种相对“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其对“旧朝”的不满,那便是突出了其异族政权的属性。如用“建虏”“满虏”等明显带有异族标识及矮化意味的称呼,又如更明确指出清朝为“异族据国”。笔者进一步发现,不只是对清朝政府,是志的编纂者对于同属于异族政权的元王朝亦给了相同的待遇,与此同时,给予了同为汉族政权的宋、明王朝以尊奉与同情。此从志书对以上王朝兴替的历史书写中便可见端倪。试看是志记载宋元之事,称元朝为“蒙古南侵”,称窝阔台为“蒙酋”,称其亡宋为“入主中国”。[4]491-494再对比康熙《大理府志》与是志,前者于忽必烈即皇帝位后(1260年)即改用元朝年号叙事,[13]而后者至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灭亡前,仍用宋朝年号。其中含义,不言自明。志书对于明朝的尊奉与同情则更为明显。如记明太祖平定大理事时,称梁王为“蒙古遗孽”,又称其“遁去滇池,死岛中”,而土司们“相率归附”,俨然是王师讨逆的叙事方式,后又称郑成功“割据一隅”为“起义”,其尊奉明朝,矮化元、清的立场已十分明显。再看其记永历帝由云南逃往缅甸事时,称“云南百姓愿从未及者,号哭震天”,“过大理,士民携扶欢泣往迎”,[4]497-503对永历帝暨明王朝的同情与惋惜溢于言表。
综上,在“五族共和”为官方政策的背景下,是志编纂者虽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官方政策的奉行,但在对“旧朝”的书写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充满了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意味,这看似矛盾的一面,笔者以为,恰好体现了其复杂的时代内涵。这种不自意的习惯正反映了数千年来“华夏之辨”“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影响。虽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新思想,但潜意识里仍不能摆脱“华夷之辨”的旧传统。这是新知识体系与旧历史记忆矛盾交织的体现,也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且具有浓厚历史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