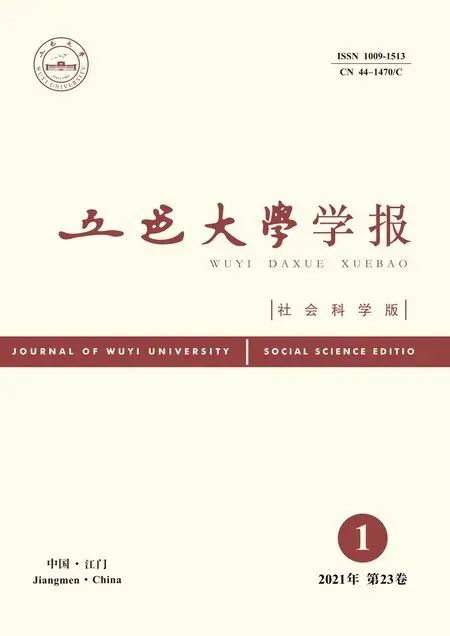《郭沫若全集》编选的历史考察与文化阐释
2021-03-06刘竺岩
刘竺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对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全集编选是其一生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和表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作家全集的编选与出版,均被纳入政府出版体系。什么样的作家能够出版“全集”、什么样的作家能够出版“作品选”、什么样的作家的作品仅能作为“史料”、什么样的作家无法出版作品,是对某一作家身份合法性的承认,据此能够确立某位作家的话语权等级。换言之,能出版“全集”,是一位作家在文学、政治领域的重要身份象征。
在众多现代作家全集中,《郭沫若全集》最具典型性,其“全集不全”问题已被诸多论者注意。税海模的《<郭沫若全集>的学理审视》首先指出《郭沫若全集》的“不全”现象,对其成因进行初步阐释,同时对修订提出建议。[1]魏建的《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更全面地分析《全集》的“不全”问题,以具体史料为依据,对“不全”的原因进行发掘,尤其指出经济因素和读者需求对郭沫若佚文的收集整理工作造成了困难。[2]此后,蔡震的《关于<郭沫若全集>的考察》提出了造成“全集不全”的“拆分与新编”“‘集外’文与‘集内’文”等具体问题。[3]廖久明的《全集就要全——<郭沫若全集>重新出版之我见》对《全集》的重新出版提出了三个建议。[4]将《郭沫若全集》的编选放置在现代作家全集编选的大背景下审视,它既具备郭沫若文学活动的特殊性,也关乎现代作家全集编选的一般性问题。因此,从历史事实考察《全集》成因,对其原因进行文化层面的阐释,以之管窥现代作家淑世意识与晚年作品编选的矛盾,具有典范意义。
一、《郭沫若全集》:作品修改与版本变迁后的“定本”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是从官方到学界的重要任务。这部全集的一个意义,是通过三家权威出版社以“全集”形式,进一步赋予郭沫若“鲁迅接班人”的历史评价。对于新时期初期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郭沫若全集》编辑原则的制定、具体文本的剔除等项工作,是在郭沫若逝世后,由郭沫若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完成的,迥异于《巴金全集》等由在世的作者亲自编选、校阅。但郭沫若生前曾多次修订他本人的作品,这让其本人选本颇为重要,由此产生的版本变迁对《全集》编选产生的影响亦可厘清。
(一)《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的蓝本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很大程度延续了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指导思想与管理体系,将出版事业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出版界的绝对领导地位。因此,新中国成立前那种以市场为导向、由作家和出版机构即可完成的出版流程大幅改变,“现代文学中那种各种出版社林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出版性质也由原来的出版、文化传播等行为,演变成为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行为和文化导向行为”[5]。
在全新的出版制度下,现代作家的作品选本被赋予了等级色彩,即作家不再较为随意地命名自己作品选本的名称。现代作家的作品选本被命名为“选集”或“文集”,体现作家身份的某种“等级”。在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寥寥几部现代作家文集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份书目:《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等。从作家身份看,除郑振铎因1958年牺牲于空难,其文集带有某种纪念意义外,其他作家均被视为新文学作家中的典范。换言之,这些作家之所以能够出版“文集”,代表了一种身份和资格,即他们在当时的文学权力场域中,占有极高的话语权。
由此,不难看出《沫若文集》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肯定的版本。正因为其典范意义,尽管该书出版说明规定“收辑郭沫若到最近为止四十年创作生活中的文学著作”[6],但它绝无可能收录郭沫若这四十年来的全部作品,必须以当时的政治方向和历史状况为准绳,剔除其中的某些篇目、修改其中的某些措辞,再形成一部“定本”。例如,《沫若文集》第五卷剔除了富于争议的历史小说《马克斯进文庙》,第十一卷中的《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删去所引蒋介石《告全国民书》等。经过作者本人这样的剔除与修改,《沫若文集》基本上规避了他在“《女神》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错误认识、在“左联”时期与党内主流意见不合的表述、在抗战时期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对蒋介石及重庆国民政府的正面评价等。《沫若文集》的这一次修订,也成为郭沫若一生中对其作品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修订。
因此,在编辑《郭沫若全集》时,《沫若文集》成为最重要的蓝本。在“出版说明”中,编者明确规定:“收入《全集》的著作在这次出版时,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修订。”[7]亦即《郭沫若全集》的收录,主要参照《沫若文集》。未依照《沫若文集》进行收录的有几类特殊情况,但只占较少比重:其一是被《沫若文集》剔除,又被《郭沫若全集》重新收录的作品(如《马克斯进文庙》等);其二是郭沫若晚于《沫若文集》的作品(如《沫若诗词选》等);其三是不属于《沫若文集》主要收录对象的考古著作和古籍校注(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管子集校》等);其四是郭沫若在《沫若文集》之后又校订过的作品(如《甲申三百年祭》等)。这样的优势在于充分尊重作者对本人作品的修订,使作品以作者认同的样态呈现在《全集》中。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最主要的就是忽略了初版本的价值。
概言之,从初版本到《沫若文集》,郭沫若对其作品进行思想内涵上有颠覆意义的修改。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较之初版本,《沫若文集》中趋向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分增加了。由此可见以《沫若文集》为《郭沫若全集》主要蓝本的巨大缺陷——即通过阅读修订过的《沫若文集》,读者易将新中国成立前的郭沫若与1950年代的郭沫若相混淆,从而对郭沫若早期文学思想产生误读。
(二)“杂集”:《郭沫若全集》收录的尴尬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说明”规定:“有的著作,曾先后收录于作者若干不同的集中,现只将其收在最初编成的集内。”“主要根据作者修订过的最后版本,其与最初版本有较大改动处,有的加注,有的作为附录。”[7]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作者最初编成某集,此后又将该集编入其他集子,产生了一个修订后的最后版本,应该怎样处理呢?这种情况的代表就是没有作为独立诗集收入《全集》的《邕漓行》。此外,《全集》主要收录郭沫若本人编订成集的著作,遗漏其在世时未及成集的作品,郭沫若晚年具有深远意义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即属此类。对于这些有充分理由被收入《全集》而未果的集子,不妨将其统一命名为“杂集”,逐一加以分析,以探究《全集》在编选过程中怎样处理这些版本,又是怎样将其规范为一个“定本”的。
首先是《邕漓行》。《邕漓行》所收录的若干旧体诗词,是郭沫若1963年游览广西时所作。这些诗词,原非一个单独的集子,而是被统一名为《广西纪游二十六首》,收在1963年作家出版社版《东风集》中。196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经郭沫若本人审定,将这些诗词从《东风集》中抽出,另编一集,名为《邕漓行》,由郭沫若写一《书后》,叙述其出版缘由。依《文学编》的“说明”规定,这些诗词应按照“最初编成的集子”收录,即录《东风集》,不取《邕漓行》。但“说明”又紧接着规定,使用作者修订后的最后版本。显然,晚于《东风集》的《邕漓行》才是“最后版本”。《郭沫若全集》的编选者最终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按照《东风集》收录,将《邕漓行》以注释形式标明。
但这样的处理明显不足,因为作为“最后版本”,《邕漓行》对这些诗词进行了较大改动。收录于《东风集》时,其统一标题为《广西纪游二十六首》,但到了《邕漓行》,它们又从原来的26首变成21首。这并非只是作品的增删,而是由于郭沫若常将相似题材的诗词冠以总名,而后又加以拆分所致。在编选《郭沫若全集》时,编者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在页下标注:“《邕漓行》中这组诗的标题、顺序、文字、标点以及注释,均有所改动。”[8]即《全集》收录时,未按照《邕漓行》,仅就其改动进行简单说明。对于《书后》,《全集》也未把它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收录,仅以注释形式收录全文。在《文学编》其他各卷中,类似的序跋(如《百花齐放·后记》《骆驼集·前记》等)都被作为“附录”,单独成文。但对《邕漓行·后记》的收录方式,使作为独立文章的《书后》消失了。不得不说这是《全集》编辑过程中前后体例不一所导致的失误。
接着是《东风第一枝》。这部郭沫若逝世后由家属及工作人员编选的集子,集中反映郭沫若从“文革”结束直至逝世的创作情况。其收录内容也颇为复杂,包括诗词、讲话、楹联甚至寓言。全书除少量篇章如《怀念周总理》《毛主席永在》因被收入《沫若诗词选》而进入《郭沫若全集》外,其他篇章皆为《全集》所未收。从《郭沫若全集》的编辑体例看,不收《东风第一枝》有所依据。因为《全集》主要收录郭沫若生前已编集的著作,同时采用作者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但作者生前未编集或未经出版的著作也有大量进入《郭沫若全集》的情况。概言之,不收《东风第一枝》的弊端显而易见,涉及到郭沫若的遗稿问题。就《全集》收录诗文的创作时间看,截至1977年3月的《沫若诗词选》。也就是说,从此时直到郭沫若逝世的1978年6月,郭沫若的一切创作均未被收录到《郭沫若全集》中,这也是《全集》编选中的遗珠之憾。
整体看,这些特殊的“杂集”与《郭沫若全集》之间的复杂关系,使《郭沫若全集》的编选原则产生巨大的尴尬。首先,编辑体例的限制,让《东风第一枝》这样的重要选本不被收录;其次,如《邕漓行》这类被非“定本”所涵盖的最终修订本,对其处理亦属《全集》体例问题。由于作者与编选者之间的不能衔接所导致的散佚诗文、不合理收录的产生,让人不得不思考《郭沫若全集》作为“定本”的合理性。
二、多种文化力量参与下的郭沫若集外文本
郭沫若集外文本的产生,既和作品修改、版本变迁相关,也和郭沫若文学思想的转变密切相连。由于文学思想的大幅度转变,郭沫若曾将大量诗文剔除在自编选本之外,因而在《郭沫若全集》的编选中产生集外文问题。但仍存在若干特殊文本,它们未进入《郭沫若全集》,原因在于多种文化力量的参与。这类文本,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最为典型。
此文中,署名“杜荃”的作者批评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9]此文究竟是否为郭沫若所作,在当下也许仅具有史料意义,而在1970年代末,鲁迅的崇高地位尚未消退,因而格外敏感。尽管众多当事人都直面与鲁迅论争这一事实,但他们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多选择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与反思,而非完整叙述。如冯乃超的《鲁迅与创造社》,更侧重澄清、反思创造社和鲁迅间的论争,强调鲁迅与创造社的亲密关系。又如郑伯奇的《左联回忆散记》,在回忆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时,只称:“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和鲁迅先生的论战,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分歧,都是在党的领导和指示下宣告结束的。”[10]这使此文的作者问题在长期以来未有定论。
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鲁迅全集》即将再版时,这个问题浮出水面。对于《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作者是郭沫若与否,出现了两派迥然相异的意见。首先是反对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成仿吾重新发表的旧文《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成仿吾在其中明确表示:“杜荃,这是一个假名,是谁的假名,我始终不知道。我只知道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都没有用过这个假名。我自己呢?也只用过‘石厚生’这样一个假名。”[11]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对“杜荃”身份的否认,是反对者的依据之一。另一见证者冯乃超也进行过调查。“杜荃是不是郭沫若?我过去认为不是的,郑伯奇也认为不是的。”因此冯乃超向郭沫若本人求证,“他有点茫然的样子在回忆后说:他用过杜衎、易坎人……的笔名,杜荃却记不起来了。”当冯乃超举出“杜荃”的另一篇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时,郭沫若也只表示“该文的观点和他相似”[12]。冯乃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杜荃”这个人还没有找出来。这一说法持保留态度,但由于作者对郭沫若本人进行访问,得出的结果更倾向于郭沫若并非“杜荃”。在此时,学界亦有类似声音,如甘竞存的《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与郭沫若》,其中断然否定郭沫若即“杜荃”:“但这些人没有接受郭沫若的意见……恶意谩骂鲁迅是什么‘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双重的反革命’等等。这完全违背郭沫若的愿望。”作者最后得出结论:“郭沫若当时不可能化名杜荃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13]相异的声音主要来自学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早春的考订。这是由新版《鲁迅全集》关于“杜荃”的注释所引发的,其考订受林默涵认可,继而转至胡乔木、周扬处审定,最终由胡乔木批示同意该注释,“并说,今后《郭沫若全集》中应收杜荃的文章”[14]。此外,亦有以鲁歌、单演义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赞成这一结论,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的《郭沫若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还将此文作为郭沫若佚文,收录其中。
尽管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家全集,《鲁迅全集》以注释方式认定“杜荃”即郭沫若,但为何《郭沫若全集》最终未予收录?首先可以从郭沫若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窥见端倪。名单里既有赞成将“杜荃”注释为“郭沫若”的周扬,也有成仿吾、冯乃超、郑伯奇。尽管有史料显示,该注释“批送周扬、夏衍、成仿吾、冯乃超等审阅,均表同意”[15],但从他们所发表的文章看,始终对于此事存在疑虑。其次,从编辑思想角度看,编者在编选《郭沫若全集》时,将其视为一部扩大了编选范围的“文集”,而非求“全”的“全集”。早在1978年,“杜荃”问题还未掀起波澜时,郭著编委会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中,“多数人不赞成出全集。少数赞成出全集的人也说:‘就是编全集,也是允许有选择的’‘全集不一定全收,有些是可以不收的’。”[2]这足以说明,或许郭著编委会在1978年未必注意到“杜荃”问题,但对此类文章的收录问题早已有所考虑,甚至作出将这类文章排除在《郭沫若全集》外的充分准备。这种考量对《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不入《全集》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从一方面看,《郭沫若全集》的编选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而《郭沫若全集》“盖棺论定”的重要任务又决定,郭沫若的形象应是正面的,因此历史遗留问题既要直面又不能不有所保留;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遗留问题又涉及各种文化力量的不断碰撞。恢复文学场域的秩序尚未完成,又何谈重审1930年代的文学论争?在这个意义上管窥《全集》编选,可见它只能以这样“不全”的形态面世。
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与其作品编选
陈占彪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中指出:“鲁迅、胡适、郭沫若他们既看重知识分子研习学术,又强调知识分子干预社会。”“入世,而不是出世,是他们的共同主张。”[16]这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特征。无论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还是转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郭沫若,还是投向延安的众多革命知识分子,甚至是一度被排除在现代作家群体之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相反意见的通俗文学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干预社会视为其任务之一。甚至在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干预社会是其第一任务,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则成为其干预社会的一种途径。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明清史研究和革命文学创作、侯外庐等人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等等,都是其政治思想的表征。因此在对其作品进行美学价值、学术价值探讨之外,探究其入世思想仍然大有可为。
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的作品集编选,不可能忽略其带有某种淑世意识的作品,而仅收“纯文学”的创作,这也是《郭沫若全集》产生大量集外诗文的症结之一。在这一方面,郭沫若是最具典型特征的作家,但并非个案。事实上,大量的中国现代作家都面临这一问题。例如早年曾鼓吹安那其主义的巴金,在后续活动中不得不承受他早年之强烈淑世所带来的尴尬甚至猛烈的批评。即便在新时期,这一问题也困扰着巴金。正因如此,当他本人主持《巴金全集》的编选时,遭遇了“集外文”问题。在巴金面对自己早年的“佚文”时,他显示了某种迟疑:一方面是“无法不拾起它们”的现实困境和坚定不移的“讲真话”的决心;一方面又是“害怕翻看旧账”“把住‘关口’”的犹豫。矛盾双方的碰撞使得“害怕翻看旧账”的犹豫占据上风,因此对于过去的佚文,“没有给放进来的大约也有一卷左右”[17]。如果说杂乱无章甚至相互矛盾的佚文无足轻重的话,巴金的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因为鲜明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而更显突出了。这部批评马克思主义、推崇安那其主义的专著最终没有被纳入《巴金全集》,在序跋中亦未作出具体说明,可见巴金早年干预社会的行为与著作影响之深远。
与此相似的则有1980年代,众多作家出版其各种形式的“文集”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竟只是一本薄如杂志的小册子。这与其作家身份产生极大的差异。其中以《天蓝诗选》《适夷诗存》等最为典型。翻开这些选本,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是作者所理解的“纯文学”,其中与时事密切相关的诗作少之又少。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作家对早年之淑世的一种内蕴复杂的“反思”?
总体看,《郭沫若全集》的编选是文学场域内权力博弈的结果。作为一部有重新确定现代作家话语权力等级意义的“全集”,《郭沫若全集》不可避免地置身这一场域内。作为其前身的《沫若文集》,它的话语权意义在意识形态被重视的时期更加重要。当这种影响传递到《全集》的编辑思想上时,塑造了《郭沫若全集》的体例,产生了部分集外诗文,以及某些集内诗文的大幅度版本变迁。而体例的不健全,随之又产生了“杂集”的一系列问题。郭沫若某些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成为集外诗文,往往与历史语境转换以及不同文化力量的碰撞密切相关。《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就是一个典型文本,它关乎郭沫若乃至创造社的历史评价问题,终至被《全集》排除在外。由此可见,郭沫若作为深处中国现当代文学权力场域中心的作家,其《全集》编选不可能只简单地求“全”,这不仅是个例,更是“五四”以来大量具有强烈淑世意识的作家们所共同面对的“晚年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