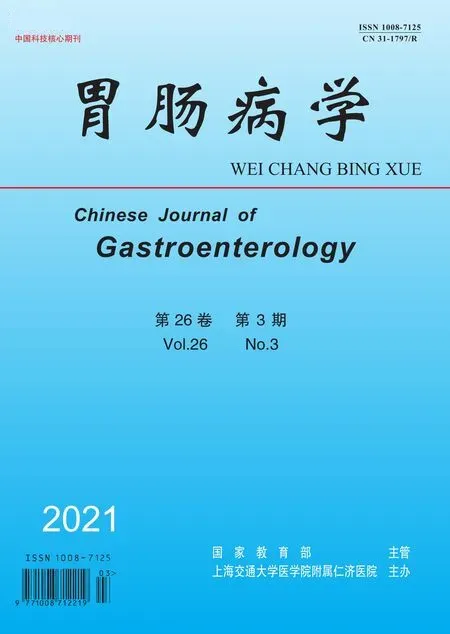幽门螺杆菌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2021-03-06张梦洁崔振宇陆伦根陆颖影
张梦洁 崔振宇 陆伦根 陆颖影*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嘉定分院/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医院消化内科1(201803)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2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Hp)是一种微需氧型的螺旋状革兰阴性菌,感染后依靠其毒力因子,定植于胃型上皮,是导致慢性胃炎活动、消化性溃疡形成和复发的重要原因,Hp是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的致病因素。有效根除Hp可预防胃癌的发生,降低死亡率。最新meta分析显示,任何年龄段根除Hp均是有益处的[1]。我国Hp的感染率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感染率为59%。《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推荐含铋剂的四联方案[质子泵抑制剂(PPI)+铋剂+2种抗菌药物]根除Hp,疗程10~14 d[2]。近年随着Hp耐药率不断升高,加上治疗方案不当、宿主CYP2C19基因多态性、Hp球形变等因素,Hp根除率逐渐下降。Hp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逐渐受到重视,本文就Hp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Hp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定义
个体化精准治疗本质上是指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技术,在人群中进行特定疾病生物学标志物的分析与鉴定,以基因组成和表达变化的差异为基础,精确寻找到疾病原因和治疗靶点,最终实现个体化精确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预防与诊治的效益[3]。Hp感染个体化精准治疗多是针对按共识治疗失败的患者,根据Hp耐药情况、患者个体状况、病史、生活环境、家族史、宿主CYP2C19基因多态性等综合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涵盖诊疗前、诊疗中和诊疗后的各项个体化诊疗措施[4]。
二、Hp耐药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药敏评价
1.Hp耐药现状:Hp根除治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Hp对抗菌药物耐药。全球Hp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治疗Hp感染的抗菌药物包括硝基咪唑类、大环内酯类、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以及四环素类,其中甲硝唑、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而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和四环素耐药率较低[5-6]。我国一项前瞻性研究[7]结果显示,Hp对甲硝唑、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阿莫西林、四环素的耐药率分别为78.2%、22.1%、19.2%、17.2%、3.4%和1.9%。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Hp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存在差异。在西太平洋地区2007—2014年的克拉霉素耐药率由32%升至35%,甲硝唑耐药率由52%升至57%,左氧氟沙星耐药率由12%升至31%。在欧洲地区,Hp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最高达47%;对甲硝唑耐药率最高达57%;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最高达30%;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阿莫西林或四环素的耐药性可忽略不计(<5%)[6]。我国湖州地区Hp对左氧氟沙星和克拉霉素的耐药率分别达23.09%和17.8%,对甲硝唑的耐药率几乎接近100%,而阿莫西林、四环素和呋喃唑酮尚未发现耐药[8];2010—2014年间,北京地区Hp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上升最快,其次为克拉霉素,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9]。因此临床医师在根除Hp感染前,须了解患者所在地的抗菌药物耐药情况,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2.Hp培养与药敏试验:美国胃肠病学会临床指南推荐对于反复治疗失败的Hp感染患者进行Hp培养和抗菌药物药敏试验[10]。我国《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提出,不论初次治疗或补救治疗,如选择含克拉霉素、甲硝唑或左氧氟沙星的三联方案,应进行药敏试验[2]。内镜下组织活检目前已在临床广泛开展,这为Hp的培养提供了基础。日本学者曾主张在病变部位(如炎症或糜烂灶)或病变部位与正常黏膜交界处(如溃疡或胃癌边缘)多点位正规取材[11]。我国专家共识建议在胃窦小弯侧距幽门5 cm(邻近胃角处)或胃窦大弯侧正对胃角处取活检1~2块[12]。三气培养箱提供了良好的微需氧环境,极大地提高了Hp培养成功率;药敏试验采用经典的纸片法或Etest法,通过抑菌圈大小评价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经验性铋剂四联方案的疗效与基于药敏试验的三联方案相当,但前者服用药物数量多,不良反应率稍高,后者则存在药敏试验的可获得性和费用可能增加的问题,需行成本-效益评估。有研究[13]表明对于通过13C-呼气试验诊断Hp感染而无胃镜检查指征的患者,建议首选经验性四联方案;对于行胃镜检查明确Hp感染的患者,建议在进行Hp药敏试验后根据结果制定个体化根除方案。
三、基于Hp基因检测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
1.Hp耐药基因突变检测:Hp耐药基因突变检测相对于细菌培养物药敏试验有更高的检出率,可应用于因培养不成功而无法进行药敏试验的患者,同时可提供分子生物学层面的耐药信息[13]。Hp耐药基因突变检测的方法包括定量PCR法、DNA酶免疫测定法、寡核苷酸连接或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CR-反向点杂交法等。新近的研究发现,基于碱基互补配对原理的DNA芯片技术也是一种检测Hp耐药性方便快捷的方法,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高通量的能力,可直接从胃活检标本中进行检测。临床中,该基因芯片技术可用于儿童Hp感染的快速诊断和耐药性检测[14]。
Hp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基于细菌染色体上的点突变。与甲硝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和左氧氟沙星相关的Hp耐药基因分别为rdxA、23S rRNA、pbp1A和gyrA[15]。Hp甲硝唑耐药株的硝基还原酶rdxA基因突变导致rdxA基因功能失活[16]。Hp对克拉霉素耐药的主要原因是肽酰转移酶区编码23S rRNA V区的A2142G和A2143G出现点突变,导致抗菌药物无法与细菌23S核糖体亚基结合,而这些核糖体亚基专用于特定抗菌药物相关蛋白的合成[17]。一种新的基于肽核酸探针的实时PCR法可用于检测Hp中与克拉霉素耐药性相关的23S rRNA基因的A2142G/A2143G突变,可评估Hp对克拉霉素的耐药性[18]。此外,一项横断面研究[19]利用PCR法发现北京地区Hp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严重,双重耐药率高达19.6%。故有必要根据Hp耐药信息来选择合适的根除方案。Pbp1A多重突变可能导致阿莫西林耐药性的逐渐增加。虽然Hp对阿莫西林耐药率较低,但有研究[20]发现阿莫西林根除Hp每失败一次,其MIC90增加2倍,因此Hp对阿莫西林的耐药性是在根除失败后逐渐诱导的。Hp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主要由gyrA蛋白突变引起,gyrA蛋白是氟喹诺酮类药物的靶目标,可导致DNA复制受抑[21]。第四代喹诺酮类药物(双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根除Hp的疗效优于左氧氟沙星,原因可能是双氧氟沙星和莫西沙星可克服gyrA突变[22]。
此外,有研究[23]发现新的Hp耐药基因rfaF与药物敏感性直接相关,可降低细胞膜对药物的通透性,促进菌株发生耐药。临床菌株中的rfaF氨基酸保守序列具有高突变率(K331R突变最频繁,占所有突变的44.44%),导致菌株对阿莫西林、四环素、克拉霉素和氯霉素发生交叉耐药。综上所述,对Hp进行耐药基因突变检测可指导临床医师选择对Hp更为敏感的抗菌药物,这对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至关重要。
2.Hp全基因组测序和毒力抗体检测:Hp表现出广泛的种内多样性,全基因组测序不仅可将不同菌株之间的差异比较精确至单个碱基,还可揭示菌株的遗传背景,了解菌株的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
Hp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各不相同,东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胃癌发病率相当高。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调节感染免疫反应的宿主遗传学,以及细菌遗传学和环境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最新的研究[24]发现,胃灌洗液的全基因组分析和单分子实时检测技术可确定Hp菌株的癌症相关遗传变异。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典型的非洲Hp分离株具有巨大潜在毒力,可通过功能性CagA癌基因蛋白的移位促进胃上皮细胞发生癌变。此外,有研究[25]发现全基因组测序可预测临床中Hp的耐药性。有趣的是,研究[26]发现了一种网络工具CRHP,可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数据检测Hp对克拉霉素的耐药性。
Hp是具有最高突变率和重组率的病原菌之一,且重组率远高于点突变率。Kumar等[27]分析比较了27个马来西亚Hp分离株的基因组,发现CagA和VacA等位基因可因菌株的寄主遗传背景出现变异。Thorell等[28]对尼加拉瓜的52株Hp分离株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比较,发现77%的分离株携带与癌症相关的毒力基因CagA、S1/I1/M1空泡细胞毒素以及VacA等位基因,且与疾病严重程度有关。此外,Hp可产生多种毒力因子,主要为CagA和VacA,根据是否表达CagA和VacA将Hp分为Ⅰ型和Ⅱ型,Ⅰ型菌株表达CagA和VacA,Ⅱ型菌株不表达上述基因,Ⅰ型菌株致病力高,与胃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发生、发展有较为明确的关联[29]。
总之,随着耐药性的增加,临床上需要准确的药敏试验来指导Hp感染的治疗,而全基因组测序可准确预测人群中Hp整个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潜在耐药性突变,并在序列突变时识别癌症相关的遗传变异,从而为临床医师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
四、基于Hp球形变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
Hp在人体内主要保持螺旋状,但在不利的环境中,如氧分压升高、pH值变化、体外培养时间延长和接触抗菌药物等条件下可转变为球状[30]。与螺旋形式相比,球形Hp毒力较低,不太可能定植和引发炎症[31]。根据Hp相关性腺癌的活检结果,93%的样本中可识别出球状形态,表明球形Hp可直接黏附和侵入人胃黏膜上皮细胞[32]。Hp从典型的螺旋杆状到球形体的变化可能是对不利环境的一种短暂适应,当环境重新恢复至对Hp生长有利时,Hp可能会恢复成可增殖的螺杆状而重新具有致病性[33]。
通过免疫组化染色可直接观察胃黏膜组织中Hp的形态、数量。不同浓度的甲硝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红霉素在不同的暴露时间均能诱导Hp球状形成。已有研究表明克拉霉素等蛋白质合成抑制剂抗菌药物和甲硝唑等DNA抑制剂抗菌药物对活体球形Hp有较好的杀菌效果,阿莫西林对Hp的体外杀菌作用最强,但阿莫西林在2倍MIC时对活体球形Hp没有杀菌作用[30]。存活的球形Hp对阿莫西林具有抗药性。因此,对于Hp感染成功的治疗,不仅应根除螺旋状和球状Hp,而且还应防止球状的诱导。仅靠药敏试验可能不足以确定抗菌药物根除Hp的临床效果。
深入了解Hp球形变,对临床医师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非常关键。预防Hp球形变、Hp球形变检测以及根除胃黏膜中的球形Hp等课题内容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五、基于宿主CYP2C19基因多态性指导个体化精准治疗
CYP2C19主要存在于肝细胞微粒体中,属肝微粒体细胞色素P450酶(CYP450)的亚型之一,其基因多态性可影响药物药代动力学。PPI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和雷贝拉唑依赖CYP450进行肝脏代谢。CYP2C19基因突变可影响胃pH值,从而影响克拉霉素、阿莫西林等pH值依赖性抗菌药物的稳定性[34]。因此PPI的抑酸强度和速度及其作用的稳定性对整个抗Hp方案的疗效起有重要作用。
CYP2C19基因代谢型主要分为强代谢型、中间代谢型和弱代谢型。CYP2C19中间代谢型和弱代谢型的Hp根除率明显高于强代谢型[35]。奥美拉唑等第一代PPI主要经CYP2C19和CYP3A4代谢,相同剂量的奥美拉唑对弱代谢型的Hp根除率高于强代谢型[36]。Sezgin等[37]给予134例Hp感染患者大剂量奥美拉唑的改良序贯疗法,CYP2C19强代谢型患者的Hp根除率无明显升高。第二代PPI则不完全依赖CYP2C19[38]。强代谢型患者使用第二代PPI(如艾司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后,总体Hp根除率高于第一代PPI(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39]。新一代PPI艾普拉唑是唯一不经CYP2C19代谢的PPI,不受基因多态性的影响,在不同代谢型患者之间疗效无明显差异,效果更稳定可靠[40]。富马酸伏诺拉生是一种新型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断剂,可持久抑酸,主要由CYP3A4/5代谢,部分由CYP2C19代谢,受CYP2C19基因型的影响小于PPI[41]。因此,在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精准治疗过程中,可检测患者CYP2C19基因代谢型,从而选择相应的抑酸剂,充分的抑酸治疗对Hp的根除至关重要。
六、其他因素在Hp个体化精准治疗中的作用
1.患者随访教育:患者依从性差不仅会导致根除失败,而且由于药物剂量不足,还会导致感染Hp菌株的继发耐药。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42]表明,每天两次的短信提醒可提高年轻患者的Hp根除率,提高所有人群的总体治疗依从性,并减轻不良反应。提示在临床实践中,详细指导和服药前及时提醒是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关键,可有效提高根除率。
2.中药:目前已有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根除Hp的疗效更好,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明确指出某些中药或中成药可能有抑制Hp的作用,可用于抗Hp的临床治疗[2]。黄芩、金银花、乌梅等单味中药对Hp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用。用于临床的复方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包括半夏泻心汤、荆花胃康胶丸、摩罗丹等药物。
3.益生菌:近年益生菌联合抗菌药物根除Hp感染逐渐受到关注。益生菌提高Hp感染的机制包括产生抑制Hp的物质如有机酸、抑制Hp定植、抑制Hp感染后的炎症以及减少不良反应提高患者依从性[43]。但益生菌不能完全替代抗Hp药物,与标准的抗Hp治疗方案相比,联合益生菌可增加根除率和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目前益生菌抗Hp还缺少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验,益生菌的选择、剂量,以及如何与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需行进一步临床试验探索。
七、小结与展望
Hp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Ⅰ类致癌原,早期根除Hp可显著降低胃癌风险。Hp根除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是Hp根除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此外,Hp分子生物学差异、宿主CYP2C19基因多态性、Hp球形变等均可影响Hp根除率。个体化精准治疗可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技术,精确寻找到疾病原因和治疗靶点,提高根除率。治疗前对患者进行Hp培养和药敏试验或耐药基因检测,可更有针对性地选择抗菌药物。Hp的全基因组测序和毒力抗体检测可揭露菌株的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Hp球形变可导致感染更易复发和流行。宿主CYP2C19基因检测可指导临床医师选择抑酸剂。此外,中药和益生菌等可作为辅助根除Hp的药物,增加患者的获益。加强患者的随访教育是提高患者依从性的关键,可有效提高Hp根除率,减轻不良反应。抗Hp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但有效率不高,未来预防性或治疗性疫苗接种来控制Hp感染仍是临床研究的热点。同时还需加强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以及耐药基因靶向治疗策略的研究,更好地指导临床个体化根除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