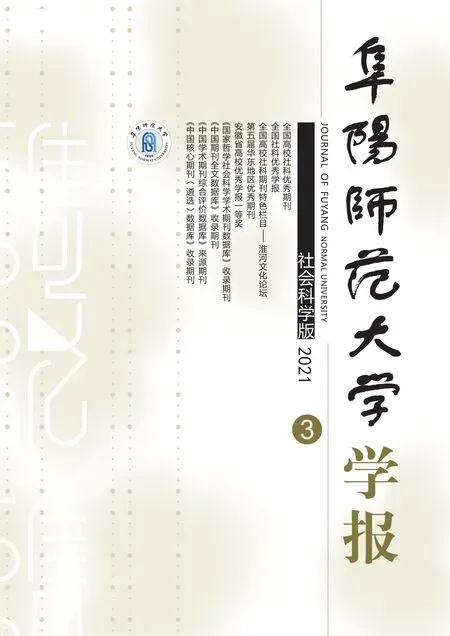医学与政治的对话:基于“上医医国”的考察与研究
2021-02-27崔兰海
崔兰海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9)
《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1]1780首先,这里医学被赋予“生生之具”的价值定位。《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大德在于创造并维系生命之活力,医学既被赋予“生生之具”,也就被赋予了天地大德同样的价值地位,这从学术源流上肯定了中华医学具备重“生”的特质,或者说中华医学起源于对生命的敬畏和维系生命活力的责任担当,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2]13医学之贵在于能救济生命。张介宾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3]2医者能佐天地大德以活人命。其次,这里明确提出医学本来就是“王官之一守”,意即中华医学从来都不仅仅是民间社会行为,治疗疾病从来都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主要职能之一。汉成帝时校雠图书诏“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医药之书也。”[1]1702方技书籍被视为医药图书。医药书籍位列天下六大学术类别之一,也折射出时人心目中医学的学术位置、学术价值之高。再次,这里提到中华医学名家善于论医及国,原诊知政,行医与从政是相通的,医者应该具备宏大胸襟,关心民瘼,博济苍生。中华医学从一开始就没满足于被定义为“术”的层次,而是赋予了医学鲜明的伦理价值。作为“生生之具”,它被视同于“天地大德”,维系生命活力。“医乃仁术”与治国仁政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点,医学与政治有了互通的桥梁。这一理念自先秦被明确提出后,为后世医家继承、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演绎出医学与政治互动的华丽画卷。这一理念让行医与治国之间有了互通、对话,凸显了医者对治国的道德责任。
一、“上医医国”源流
医涉政治,由来已久。《国语·晋语八》载:“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4]473至唐代孙思邈复言:“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2]17“上医医国”自先秦被明确提出以来,被历代医家视为崇高人格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演绎、诠释着医家“悬壶济世”的大仁大爱。而上医与治国者的对话,又客观上促进了治国者道德责任、从政理念的提升。
(一)上医医国:先秦医家对中华医学的杰出贡献
“上医医国”彰显了中华医人对医者身份的高度自信,也是早期医家医理与先秦诸子学理互动的结果。
《道德经·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可能是诸子中最早把身治与国治关联起来的论述,林语堂语译:“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把天下托付给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把天下交给他。”[5]43《墨子·兼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此墨家论医理与治理之相通,疗疾与治国均要察乱之所起,找到病灶根源,有的放矢,采取针对性对策。既然承认“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那么医家借病理阐述治国之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上医医国”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此事互见于《国语》《左传》。
《国语·晋语》:“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出曰:‘不可为也。是谓远男而近女,惑以生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宠其政,八年之谓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4]473
医和从医理入手,纵论晋国政治。晋国国君昏乱,溺于女色,而大臣不能谏阻,苟且偷安。医和大胆预测:“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医和不但看出晋国国政衰微的苗头,而且也预测晋国大臣命不长久。这里面闪烁着医和善于见微知著、辨证推理的智慧。文子厉声责问医者何故论及国政?医和自信回应,说出了“上医医国”这一经典古训。这一古训犹如一道震铄长空的闪电,点亮传统医家的信仰之门。医家不满足于被视为“术”层面的“小道”,而是能够“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1]1780,医者与将相有了同等的人格气象,医不是“小技”而是融通治国的“大道”。后代医家每以“上医医国”自况,下以疗疾济民,上为帝王之师。
(二)无怍于帝师:道医对“上医医国”的践行
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学遂为“干禄”之学,儒生渐成官僚士大夫之主体,作为“王官之守”的医学因与仕途分离,渐被视为“小道”,而医者的身份常被“君子不齿”(1)。儒学和儒生游离医学,并没有阻断中华医学的持续发展。以尊道、养生为特色的道学中人渐成医家主体,医学进入“道医”时代。
与儒家等百家书籍惨遭秦火不同,医学书籍在秦火中并没有受到冲击,“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6]255。中华医学呈现稳定的持续发展态势。汉唐间“道医”延续了先秦医家“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宏达情怀,不仅名家辈出,而且涌现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等经典医学典籍。
“生生之具”之医学首先关注生命的健康与质量。《黄帝内经·素问》借助黄帝与歧伯对话写道:“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2)376生命至重,医学宗旨就是针除疾病,呵护健康,让民众无“全形”之忧。有意思的是《黄帝内经》以黄帝与大臣对话来阐释医理,仍留医乃“王官之守”的先秦色彩。
传统社会里,官方医疗系统往往只能满足贵族官吏阶层的需求,对于平民而言,能够得到官方疗疾的机会甚少。道医以悲悯之心,深忧生灵之苦,陶弘景目睹穷乡民众疾苦,感慨道:“夫生人所为大患,莫急于疾,疾而不治,犹救火而不以水也。”[7]4医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促使医学持续沿着其“生生之具”之初衷发展,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2]17由于“道医”自身践行“全形”的成功,往往也成为帝王期许和羡慕之对象。帝王谦卑请益,既然治身与治国为一体之理,那么借助帝王请益之时,“道医”们便以“上医医国”之心态借助医理纵论治国大道。
《旧唐书》中保留一段唐代道医司马承祯与唐睿宗之间的对话:“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8]5127-5128道医立足道家“无为”之理,阐释治国应“无为”,无为而成,不失为廉洁高效。无独有偶,宋代道医皇甫坦面对帝王咨询,复以治身犹治国之道答之。《宋史·皇甫坦传》:“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祷青城山,还,复召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静’二字以名其蓭,且绘其像禁中。”[9]1353皇甫坦首论当以“无为”修身,进而由修身论及治国,言人主应以无为而让天下安宁,与民休息。
道医接续了先秦医家“上医医国”理念,并在帝王询问治身与治国之理时,纵论治国“无为”之旨,在新的时空,把中医医理与治国之道贯通,不仅成就了道医自身的伟岸医者形象,也延续了中华高尚医德,让“上医医国”理念得以在唐宋后由“儒医”接续。
(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儒医对“上医医国”的发展
唐宋是中国历史转型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在学界影响很大,如果我们从中华医学发展角度去审视,唐宋期间中华医学发展与前代变化最巨者即为儒医群体的兴起。唐政府对医学系统的重视,加上出于儒家“孝”道等诸多原因,文士通医在唐代中后期蔚然成风,这一现象随着宋代理学兴起后得以延续并加强,理学对儒学“仁”思想的阐释和发挥,使得医学人道主义更多与理学“仁德”思想交融。援儒入医,成为唐宋以后医德发展的主流趋势。
范仲淹曾祷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3)。后人阐释道:“良医之权与宰相等。而宰相所以治天下者,即良医之术所以治一人之身者也。盖病者之死生安危系乎医,而天下之戚休治乱系乎相。医之良,则能回死以为生,易危以为安,而利及乎一身。相之良,则能化戚以为休,革乱以为治,而利及乎天下。虽所处有高下,所施有广狭,而权之所寄,实无以大相异也。昔人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岂不以此欤?”(4)良相与良医,虽然地位身份有高下、施及对象有广狭之分,但其本质为利他,皆能转危为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可视为先秦“上医医国”理论的发展。
先是东汉儒者王符《潜夫论·思贤》曾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医与贤能并举,此固医者之荣。王符这段论述蕴含着良医与良相互通意蕴,这股潜流至宋,终被响亮地提了出来。医家社会地位在儒医推动下得以显著提升,而“以儒从医”也从良相与良医互通中找到更高境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医者以其高度人道主义、博施济众的情怀日益受到世人的尊重,明人谓:“范仲淹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则医岂小道小艺哉?”(5)。
儒医对医德的重视也高于前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开篇即言:“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明理以尽术;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若不能正己,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10]1正己的医德,摆在了医术之前,且是日后成为良医的必备条件,医德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明陈实功《外科正宗》强调医者“一要先能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而陈实功提出的医德“五戒十要”与希波克拉底誓词齐名,是世界公认的古代医德文献,被编入美国《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11]171。
(四)医乃大道:近现代医家对“上医医国”的弘扬
近代中国政治上因循守旧,文化、经济、科技等与世界发展脱轨,国运不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随着“西学东渐”在中国盛行,中国医学也同样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医在近代时空下激烈碰撞。近代医家,传承“上医医国”之理念,胸怀医学救国之志向,投入谋民族振兴之宏业,在推动中国向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推动中医向近代医学转型
伍连德针对近代中国医学弊端和困境,指出:“学者徒守旧法,昧于发明,惰于研究。精粹尽失,新理无闻。悬壶业医者,凡遇病症, 多不知其病源。如时症瘟疫传染等病,究由何病发生,如何预防,莫不愕然,无以应对。”[12]穷则思变,近代医家力主援“西法”入“中医”。施今墨说:“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相互佐证,实无别途。”又说:“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吾国医学陈陈相因之玄学奥理,而走向科学化一途。”[11]217施今墨肯定了中西医各有所长,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民国政府取消中医的做法,力主中西医融合。
2.以医强国
近代国运衰落,近代医家站在“医学和健康”的角度,力求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怀“以医强国”之志,演绎着“上医医国”的近代画卷。丁福保说:“人皆病夫,则国亦病国矣。医一国之人民,俾皆跻康强而登仁寿,则国亦寿之千万祀而不朽,壮哉医乎!”[13]以医学支撑国家强大而永续,发“上医医国”近代之余响。
3.造福人群
近代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杨崇瑞,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美国普林斯顿医学院学习,学成后归国投入于近代中国妇幼保健事业,1927年创办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附设产院,其校训为“牺牲精神、造福人群”。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海外归国把一生积蓄捐献出来兴办新中国的妇幼事业。近代伦理学奠基人宋国宾论医家预防责任曰:“公众卫生之意义,在于保护一地人民避免当地之地方病或外来之传染病。”又论医家补救责任曰:“治疗疾病为医家之本分,有以国家之津贴实施贫病之免费诊治者,此医家所以为公众慈善事业之最重要助手也。”[14]132-133显然无论是预防还是补救,医家承担者,皆为造福社会的责任。
二、“上医医国”逻辑内涵
医人与医国的内在关联性在哪儿?古人是如何实现把个人病与天下瘼关联起来思考的?这些都要从“上医医国”内在逻辑上进行分析。下文我们将从治病与治国之间的价值、方法、目标、明德等四点互通之处加以论述,借以分析治病与治国之间互动的内在机理。
(一)仁术与仁政:治病与治国内在的价值统一
“医乃仁术”,是传统医家对医学价值的高度凝练,这既是作为“生生之具”医学本质属性的概括,也蕴含“医者仁心”的医德伦理诉求。而爱民、利民、惠民、富民等民本理论是传统“仁政”理论的核心,“仁政”也是传统士大夫政治孜孜追求的理想善治。“仁”成为医学与政治互动、互通的价值原点。明人贝琼《清江文集》:“古人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夫良相位尊,势之所及者广,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医位卑,势之所及者近,苟施仁术,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与医,虽非等伦,其心则一耳。”(6)良相与良医在“仁心”上找到互通的价值基点。
在医界,医者仁心被视为“王道之心”,新安医家程文炳,被明人赞曰:“先生之医,王道之医也。先生之心,长厚仁爱,不问富贫,病有所急,虽万金良药不以贫者而靳。病有所缓,虽牛溲马勃不以富者而遗。而先生之心,王道之心也。”(7)程文炳医者“仁心”被视为士大夫追求的“王道之心”加以赞许,医学之“仁”,需要借助王道之“仁”寻找价值认同,提升价值定位。同样的,当政府关心民瘼,实施仁政时,也往往借助医学之“仁”,医学之“仁”成为王道“仁政之急务”。《宋大诏令集》曰:“人肖形于天地,气盭則形病。昔圣人救以医药,跻之寿域,仁政之急务也。比者医不穷理,流于世好,人以夭折,朕甚悯焉。”[15]283宋代帝王把医道之“仁”喻为“王道之急务”。医界与政治在“仁”上找到相互亲和融通的理由。
(二)防微杜渐:治病与治国方法论上的共同取向
“治未病”是医学伦理一贯诉求,医者视其为治病的最佳方案。《黄帝内经·素问》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渇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晩乎?”(2)299-300能够治未病,治未乱,《内经》赞之为圣人,是大智慧。《史记·扁鹊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司马迁从疗效上高度肯定了见微知著的临床意义。
同样的,治国中防微杜渐、弥乱于未萌也尤为传统政治所强调,《资治通鉴》论唐代宦官之祸曰:“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徳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16]879司马光借助《周易》履霜坚冰说,批评唐代对宦官之祸未能防微杜渐,致使宦官之祸愈演愈烈,卒使唐政败坏无法收拾。能够从源头上弥乱、防患于未萌,是治病、治国共同的方法论追求。防微杜渐能极大降低祸乱带来的冲击,以小的代价换来最优的结局。
(三)重在治本:治病与治国互通的目标取向
古人论政,常引医理,《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管子》借助身体机理来论证国家治理中“君位”犹如人体之“心”位。君循道,百官皆依理行事,朝堂自然秩序井然。医家论病理,也往往旁通政理。《抱朴子》言:“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17]145《抱朴子》提出治身与治国触类旁通,治身之要在于“气”,治国之要在于“爱民”,提出“气犹民也”。治身重在“养其正气”,治国重在“君心爱民”,两者皆为“治本”之策。
元人王旭《兰轩集》曰:“昔人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岂不以此与?然而其术之相似则未有知之者。今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行其血脉而导其壅滞,养其正气而防其风邪,然后随其证而药之,则疾去身安可以享和平之福。彼良相之治天下,亦何以异于此哉,内有以格君心之非,而外有以达四方之情,然后随事顺理而区处,则弊去政行而可以致隆平之盛。”(4)“养正气”“格君心”分为治身与治国之根本,凡事抓住根本,自可身安、国治。
(四)精勤敬诚:治身与治国明德上的契合
《论语·子路》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自古为医者就有品德上的规范。孙思邈著《千金方》把《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置于首卷序例,借以阐释从医之德。而医德之要,则为精勤、诚敬。
“精勤”指医学者于医技当精益求精,不可丝毫马虎懈怠。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2]15对生命的重视,要求从医者对医术、医道务必“寻思妙理,留意钻研”[2]16,宋人沈括《苏沈良方·序》论为医当谨慎精细,文曰:“其精过于承蜩,其察甚于刻棘,目不舍色,耳不舍声,手不释脉,犹惧其差也。”(8)为医之难,可见一斑。要立志为大医,自当勤奋苦读,熟稔经方:“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2]15
“敬诚”指医家要心存真诚敬畏,不可嗜利鹜名,心存邪念。《灵枢经》论针刺之道曰:“凡刺之道……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9)心存敬畏方能慎之又慎;心存敬畏,方能传医道而行仁术,恪守医道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的宗旨。由敬入诚,医者当表里如一,真诚待人,决不可欺世盗名,甚至骗取钱财。《小儿卫生总微论·医工论》曰:“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难。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苟能如此,于道几希,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10]2这里提出医家当志存谦和,动合礼节,决不可矫饰欺殆,诓人钱财。应实事求是地告知患者病情,做到真诚无欺,表里如一,这样才能彰显医道,不愧苍生大医;反之,则为生灵巨贼。
三、“上医医国”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上医医国”自提出以来,极大提升了医者人格。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医疗卫生同样具有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伦理价值。站在新时代审视“上医医国”的伦理价值,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有助于提升从医者人格
上医医国让传统医者志存高远,有力地抵消了视医为“小道”的职业歧视。它如一缕阳光,让学医、从医成为士大夫日益高涨的志趣所向。“上医医国”不仅从内心成为良医、大医的心理慰藉,而且也促使士大夫可以毫无愧色地张扬医学情趣,辛弃疾“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言谈中彰显学医、为医之自豪。宋代宰相崔与之的父亲崔世明“试有司连黜,每曰‘不为宰相则为良医’,遂究心岐、黄之书,贫者疗之不受直”[9]12257,作为读书人的崔世明在医学中找到了价值归宿。上医医国,让医者自视医德如政德,医者在人格上获得与官僚士大夫比肩之感。杨泉《物理论》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里提到的仁爱、聪达、廉洁实为官僚士大夫为政之“德”,医者引以自居,极大提高了医者人格气象。
当代医务工作者同样存在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许多医务人员不再把医学视为神圣的职业,而是将其视为谋生的手段;不再把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视为自己的担当,转而以患者不闹事、不发生医患冲突、明哲保身视为处事原则;不再把追求人类健康、社会进步作为职业理想,而是把自我私利满足作为做事的最终考量。这种身份定位在矮化医者人格的同时,也造成社会对医生评价的整体下滑。回顾“上医医国”,重新正视医者在“以德治国”中的引领价值,必将极大地提升医者人格和医者身份认同,也必将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认同度。
(二)有助于构筑和谐医患关系
“上医医国”理念在提升医者身份认同同时,提高了医者对医学工作的挚爱,规范着医者疗疾的行为规范,从而在伦理层面上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内在基石。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2]16强调要平等善待患者,医者疗疾不得过问患者贵贱、贫富、长幼,丑俊,亲和与否,甚至不得过问患者种族、智商等因素,而应一视同仁,提出医生视患者当如至亲。南宋张杲《医说》曰:“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无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10)专以救人为心,就等于在临床实践上坚持了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自当尊重患者,所谓“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9)是也。
医患关系紧张仍是当代社会一大顽疾,医者、患者、社会都饱受煎熬。传统大医以“患者为中心”的行医行为取向,可以从医者层面上率先给予价值引领,医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必将极大地拉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构建医者与患者之间原本应有的“相依”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冷漠的“相处”关系。
(三)有助于营造“尊医重卫”社会风气
上医医国,在提升医家人格气象、提升医学职业认同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对医学、医者的极大尊重。唐太宗贞观初,召见孙思邈,赞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8]5095又:“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18]1409太宗对医家、医学的尊重,既彰显了太宗贞观仁政,也是中国历史上医学与政治良性互动的范例。尊重医学、尊重医者成为传统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内涵和保障。宋承唐风,对医学、医者的重视尤为空前,宋人说:“我宋勃兴,神圣相授,咸以至仁厚徳,涵养生类。且谓札瘥荐臻,四时代有,救恤之术,莫先方书……其好生之徳,不特见于方论而已。又设太医局、熟药所于京师,其恤民瘼,可谓勤矣。”(11)宋人对本朝重视医学、关心民瘼是给与高度肯定的。
出于恤贫救疾而建构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周礼·天官冢宰》下设有医师、疾医等职能部门负责全国医疗卫生,其中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此等文字代表着时代诉求,也彰显中国古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管子·五辅》篇曾有“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的制度设计。此后历代政府在灾疫面前,也常常有发布医药卫生政令的举措。当然受到政府阶级性和技术发展等时代条件限制,传统社会政府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相对于普通百姓的医疗需求,只能是杯水车薪。这折射出传统政治本质上视医学为巩固统治之手段,而不是政治行为所理应追求之目的。
“尊医重卫”精神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价值支撑。医务工作者、卫生健康事业工作者是国民健康、生活幸福的保障者。政府、社会、公民都应关心、关爱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医务工作者不断提高技能和道德水平,发挥医者道德伦理对社会整体道德建设的引领作用,加强尊医重卫的社会修养。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不断出台尊医重卫的法律、政策,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社会层面不断培育尊医重卫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坚定尊医重卫文化自信。个人层面不断践行尊医重卫的价值观,夯实社会和谐情感基础。多渠道、宽领域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氛围。善于从传统“上医医国”中寻找尊医重卫的历史素材和传统基因,不断促进包括“上医医国”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结语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面对本次疫情,中国党和政府果断采取措施,经过艰苦卓绝地努力,中国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基本控制疫情大规模蔓延的国家。在这场伟大“抗疫”战中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义无反顾地充当“逆行者”,展现出“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敢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医德,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仰,用一腔“精医报国”之志上演了“上医医国”的当代传奇。
立足新时代,重新审视“上医医国”这一古老而鲜活的话题,揭示“上医医国”给予中国医学、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这是本论文的初衷。“上医医国”作为医家信仰,自先秦以至当代,亘古长存,承载着中国医家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寄托着中国医家梦寐以求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诉求。在这一命题里,医者不仅是悬壶济世的仁者,而且也是引领治国、引导社会的道德标尺。
传统社会里,政府需要借助医学和医疗来彰显仁政,承载社会救济责任,这一过程实质也是医学政治化的过程。现代社会中,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已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行政职能和治理能力,国家介入公民健康呵护成为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医学与政治的对话从传统的“疾病干预”提升到“健康干预”,医学治理成为国家干预的重要手段。可以预测后疫情时代医学嵌入政治的力度必然增强,当抗疫成为国际议题时,也意味着医学政治化将跨越国界走向国际医学治理,国际医学治理成为当代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显著载体。“上医医国”在不同的时空中,架起了医学与政治、医者与治国的桥梁,不断演绎着医学与政治的对话。通过这一对话,不仅提升了医者的职业伦理和职业定位,而且也增添了政治的人本理念和人文色彩,从而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向着健康、和谐、美好的远景目标前进。
注释:
(1)形成于汉代的《礼记·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唐人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2)吴崑注《黄帝内经素问》,《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980册。
(3)陈桷《石山医案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65册,397页。
(4)王旭《兰轩集·送韩子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02册,844页。
(5)赵撝谦《赵考古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29册,657页。
(6)贝琼《清江文集·同寿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28册,505页。
(7)庄昶《定山集·为余生谢程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254册,278页。
(8)苏轼,沈括《苏沈良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38册,219页。
(9)宋史崧音释《灵枢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33册,377页。
(10)张杲《医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42册,368页。
(11)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原表》,《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742册,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