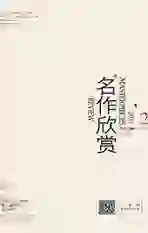神话重述的艺术
2021-02-23袁易
摘 要:文学经典的重述伴随着后现代价值下对经典文本及其价值的解构与重塑。阿特伍德重述古希腊经典神话史诗《奥德赛》创作出《珀涅罗珀记》,通过对叙事结构的调整,探讨了后现代视野下文学叙事除神话叙事的神圣性以及女性叙事对男性叙事文本再造的可能性,试图通过复调型叙事把话语权力赋予不同阶级的女性,尝试在经典文本中重建新的性别话语秩序。
关键词:《珀涅罗珀记》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叙事
一、从神话叙事到文学叙事
文学经典的重述伴随着后现代价值下对经典文本及其价值的解构与重塑。伴随经典解构与重塑的热潮,神话重述的写作潮流在21世纪之交盛行,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 Book)的邀请下参加了“坎农格特神话系列”(Canongate Myth Series),并以《奥德赛》(The Odyssey)为底本重新创作,于2005出版了小说《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
古希腊神话诞生于历史上人类的童年时代。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原始人类认识能力水平有限,面对大自然给予的有益恩赐和无情灾难,他们心生恐惧并开始敬畏自然,产生万物有灵的想法。马克思评价:“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a神话作为原始人类由内而外自发的行为产物,成为他们试图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一种方式,在客观认识能力匮乏的土壤上生长出了神话这朵富有想象力的花朵。进入古希腊时代,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古希腊理性主义兴起,但神话式叙事作为唯一的话语形式依然得到保留和延续。即使是古希腊时代的启蒙者也必须“被迫(compelled)赋予自己的观点以神话式表述”b。神话式叙事的传统制约了古希腊时代的叙述者,他们自觉又或是无意识地屈从于这种话语结构。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神话是一种具有功能性效用的形式,是从属于颂神的衍生物,也是一种必然也应然的话语结构。在原始思维下,神的世界是存在的,即使在古希腊文学中神的实体早已在英雄时代开始逐步隐形,但是神的精神一直在持久地指引着古希腊人的生活。在神话重述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浪潮消解权威、颠覆传统的思潮合流,文学创作被看作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是创作者感情与理性的结合物,而非是颂神的产物。原始神话式的思维模式与现代性的创作理念激烈对撞,神话重述势必要将神话文本中的神性抹去,将神话叙事还原为文学叙事。
阿兰·邓迪斯认为“神圣”是区别神话与其他叙述形式的关键:“其中决定性的形容词‘神圣的把神话与其他叙述性形式,如民间故事这一通常是世俗的和虚构的形式区别开来。”c神话是神圣性的叙事,构建的是一个充满神性的世界。神话中人物是一种人格化、神性化的具象符号,为实践神的意志和预言、赞颂神的权威而存在。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被符号化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古典英雄形象,他受雅典娜的指引去实现宙斯的寓言,最终回归家园。在神性世界中,人实现的一切伟大都需要神的协助,一切成功或是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神的操纵,是神性意志的体现。神话叙事构建的神性世界是神话神圣性的核心,而神圣化的人是反日常、超经验性的,是与现實中人的形象不相符的。神话重述不仅仅对原始素材进行再创造,它同时对再创作主体提出了如下要求:如何以现代性视野去审视原始神话式的思维模式?如何去处理神话叙事塑造的神性世界以切近当今的现实生活?
阿特伍德采取女性主义立场,通过视角的逆转召唤珀涅罗珀开口破除奥德修斯被建构出来的神性:“当然我其实是有点儿数的,关于他的圆滑、他的狡诈、他狐狸般的诡秘……他的狂妄。”d神性在奥德修斯身上消退,他被降格成一个具有缺点的普通人。他原先健美强壮的男性躯体有了缺憾,性格上的稳重变成了身体上短腿的缺陷。奥德修斯归家途中种种英雄事迹的神圣性也同样被消解,阿特伍德用戏谑的语气将“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变成“独眼的客栈老板”,将为生存而还击的战斗称作“不过是因为没付钱”;将基尔克的宫殿还原为“不过是家昂贵的妓院”,而奥德修斯“则吃了老鸨的白食”。阿特伍德通过这种还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神圣的冒险并不存在,这种神圣性只是奥德修斯编造的谎言。原始神话中的神圣世界的神性面纱被撕破,一切英雄事迹只不过是文学性话语复述而捏造的假象。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爱情的神圣性也不复存在,阿特伍德将奥德修斯变成了追求海伦的众多失败者之一,他与珀涅罗珀缔结的婚姻完全是“他与廷达瑞俄斯做了这笔买卖”。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之间不存在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只有纯粹妥协与利益的交媾。
在叙事结构上,阿特伍德引入由12名女仆组成的歌队(合唱团),她沿袭了“歌队的最大功能是代替幕”e的作用,用12名女仆歌队来划分不同的时空领域。阿特伍德在歌队的合唱歌词中试验了韵律、挽诗、流行歌、牧歌、船夫曲、民谣、舞台剧、人类学演讲、审判录像带和情歌包含歌曲、舞台剧、演讲、录像四种形式等10种不同风格,多样叙事风格的转变对文本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进一步消解,通过一种文体的狂欢化实现神话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向。
二、从男性叙事到女性叙事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进入到文学领域,女性主义者发现过去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男性中心主义的事实。一方面女性形象由于误读被简单地片面化,并根据男权社会要求的妇女道德分为道德模范和妖女两类形象。另一方面男性作家的男性叙事让女性在文本中被迫丧失话语权,延续现实生活的沉默状态。
荷马在《奥德赛》中以男性视角将男权社会对女性守节的标准附加在珀涅罗珀身上,他用审慎、忠贞来颂扬珀涅罗珀并且多次写到珀涅罗珀的哭泣。在男性叙事下,女性形象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她们必然是脆弱的并需要依靠男性获取力量来生存。《奥德赛》中珀涅罗珀知道自己的无力与被动,她需要祈祷奥德修斯的回归来摆脱求婚人的骚扰。《珀涅罗珀记》中珀涅罗珀的形象趋于饱满,她重获思维能力,拥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她清醒地意识到奥德修斯性格上的狡诈和虚伪,不再对于奥德修斯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开始质疑男权社会的不合理性,控诉男性的暴力和冷酷。而海伦也从荷马笔下被裹挟而走的争夺对象,转变为一个利用自己美貌支配男性的存在。她的追求者不再是控制她的主体,而是变成了她“身后那伙兴奋的跟班”。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到了话语的内部控制原则:作者赋予虚构语言统一性并保证文本隐含意义的可信。f文本意义受到了作者话语权力的制约。《奥德赛》是典型的男性作家主导下的男性叙事作品,它的叙事主体也必然被规定为男性。《奥德赛》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奥德修斯归家,另一条是特勒马科斯离家寻找奥德修斯。这两条主线的叙事主体都是男性,而作为女性的珀涅罗珀只能待在“奥德修斯的家”中。尽管她在不停地发声,但她的话语被剥夺,意志转而为奥德修斯服务,最终只是“一个训诫意味十足的传奇”,“一根用来敲打其他妇人的棍棒”g。《奥德修斯》中珀涅罗珀的职责是守护奥德修斯的财产,一方面指的是金银、牛羊、房屋、地位等世俗意义上的财产,另一方面又与珀涅罗珀本人的贞洁及婚姻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珀涅罗珀本身也属于奥德修斯的财产,因此她需要守护自己。出于这个意图,男性叙事下的珀涅罗珀是审慎的,尽管她小心翼翼地采取了编织裹尸布和强弓择偶等手段进行反抗,但实际上这只是男性意志借她的躯壳说话,珀涅罗珀依然处于“失语”状态。
女性主义文学想要获得话语权力,改变男性叙事中不平等的对话地位就必须主动争夺话语权。阿特伍德借助神话重述的机会,将性别、话语、权力三者在男性叙事中固有的联结打破,重新赋予沉默的女性话语权。阿特伍德采用一种戏仿的手法,把自己对于《奥德赛》(The Odyssey)的重构作品命名为《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隐晦地用珀涅罗珀来取代原作中奥德修斯等男性为核心的叙事中心。阿特伍德通过剥夺男性话语权,进行性别话语权力的再分配直接挑战了荷马文本中的古希腊男权社会,实现男性叙事向女性叙事的转向。在《珀涅罗珀记》的第一章“低俗艺术”中,珀涅罗珀自白:“而今既然其他人都气数已尽,就该轮到我编点儿故事了。”阿特伍德借此机会宣布《珀涅罗珀记》中男性话语的死亡,女性在文本中完全掌握话语权力成为叙事的唯一主体。阿特伍德并没有改变珀涅罗珀所处的男权社会的处境,虚构出一个女性乌托邦,甚至她在“合唱歌词:奥德修斯的审判”中强调: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个被男性话语支配的社会。阿特伍德设计女性话语放置在男权世界中进行批判,通过错位放置力图解构古希腊至今以男性话语为核心的主流叙事,凭借女性叙事的回归反抗取代男性叙事。
三、从独白型叙事到复调型叙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八章表明:“应该把歌队看作是演员中的一分子。歌队应是整体的一部分,并在演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珀涅罗珀记》全文一共29个章节,其中19个为死后珀涅罗珀的回忆,其余10个为12女仆组成的歌队的合唱歌词。阿特伍德将12女仆组成的歌队作为“古希腊歌队和萨提洛斯剧功能的混杂”h,代表了与珀涅罗珀不同的另一种阶级女性的声音。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复调小说理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i相较于独白型叙事作者对描写对象单方面的规定,复调型叙事中不存在某一个统一体。在《珀涅罗珀记》中珀涅罗珀作为上层女性占据了文本的主体部分因而掌握了主要叙述声音,12女仆只能以歌队的形式在间幕中发声。两类声音同属于女性立场,但又各自代表了一个阶级,都属于独立的主体。通过独立而又不融合的声音,阿特伍德打破了《奥德赛》独白型叙事中单一的、一致的叙事主体和全知的上帝视角,取而代之的是《珀涅罗珀记》中两个不同叙事角度的多声部合唱。
珀涅罗珀的回忆将自己与12女仆归为“同谋者”,他称12女仆为“我宫里最信任的耳目”,说“我们简直成了姐妹”。从珀涅罗珀的叙事角度,她与12女仆之间主仆控制关系淡化,通过淡化阶级的姿态营造出主仆互爱的表象并声称自己“从来不会伤害她们,不会刻意为之”。但12女仆在“合唱歌词:小孩儿的哀歌”中诉说作为女仆“孩提时起就要做苦工,从黎明到黄昏”的艰辛。她们的生活并没有珀涅罗珀所说的那么轻松,而作為主人的珀涅罗珀也并没有给予她们任何优待。由此可见,歌队与珀涅罗珀的关系并非如珀涅罗珀叙述的那种主仆互爱、关系无间。在另一方面,歌队的合唱对于珀涅罗珀的贞洁也产生了质疑:“据说珀涅罗珀谨慎贤淑,有上床机会可不含糊。”这与珀涅罗珀自述的忠贞相对立。此外,阿特伍德通过12女仆出演戏剧的形式杂糅进女仆之死的另一种解读:珀涅罗珀与欧律克勒亚为封住她们的嘴而故意指使奥德修斯吊死了她们,从而隐藏珀涅罗珀失贞的事实。两个完全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叙事主体互相矛盾的叙事,将原本《奥德赛》中清晰的故事真相模糊化,质疑了每个叙事主体的叙事真实性。
借助两种不同阶级的女性叙事,阿特伍德暗示着女性主义运动中不同阶层女性斗争目的和斗争性的差异。在珀涅罗珀的个人叙事中,她展现出对奥德修斯的品性、行为的清醒认识,尽管对奥德修斯不满与不屑,但珀涅罗珀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抗奥德修斯的权威。她不仅认为“拥有一个奥德修斯这样的丈夫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并且面对奥德修斯吊死女仆的暴行认为“死了就死了”,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祭祀,生怕“奥德修斯也会对我起疑心”。而相反,只在间幕中出现的12女仆却展现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敢于呼唤复仇女神对奥德修斯施展复仇。阿特伍德赋予了代表下层阶级女性的12女仆比以珀涅罗珀为代表的上层女性叙事更强有力的批判和斗争性。
四、结语
神话重述的艺术也是对神话经典拆解并再创作的艺术。阿特伍德通过神话重述消解了《奥德修斯》神话史诗世界的神圣性,将原本的男性话语权力交付于女性。几千年来在荷马笔下沉默的女性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批判父权社会和男性话语。阿特伍德不仅关心女性,更关注下层女性的生活。她通过歌队的形式将部分话语权力赋予了在神话中消失主体性的下层女性,让她们通过歌队的狂欢化合唱批判男权社会对她们的迫害,以极强的斗争精神与上层女性的软弱性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在现如今女权主义阶级分化、种族分化,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逐步发展的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背景下,阿特伍德借助《珀涅罗珀记》破除了神话叙事的神圣性和男性叙事对女性形象的固化,试图通过复调型叙事把话语权力赋予不同阶级的女性,尝试在经典文本中重建新的性别话语秩序。
a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1页。
b 〔美〕列奥·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c 〔美〕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朝金戈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d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韦清琦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e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罗念生全集·卷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f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g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2页。
h Margaret Atwood: “What a tangled web she wove”, in Times, 2005.
i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261页。
作 者: 袁易,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