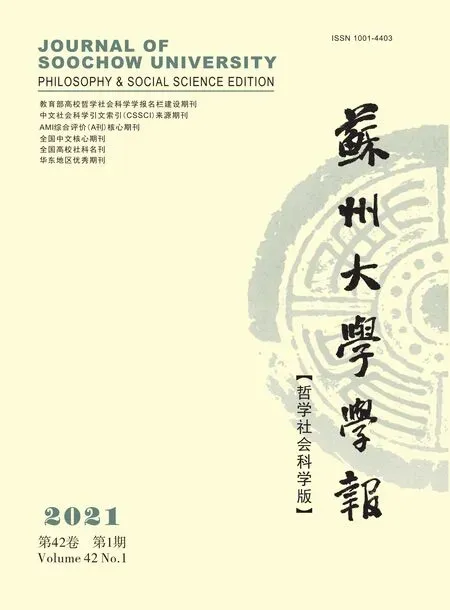汉音、魏响与别调:沈德潜对魏诗的分期与定位
2021-02-22王宏林
叶 飞 王宏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诗歌史上论及魏诗常以“汉魏”“魏晋”并称,论“汉魏”则重汉,言“魏晋”则偏晋,魏代诗歌常处于陪衬的尴尬地位,即便谈起魏诗也多以“建安风骨”代而论之。魏享国46年,加上曹操实际掌控汉廷生杀予夺大权的25年,前后70余年间,魏代诗歌在曹氏父子、建安七子、正始诗人的共同努力下,书写出独特而丰富的艺术形态。如果仅以“建安风骨”来代指魏诗,既不全面也失客观。魏诗的多元性,宋人严羽较早论及,其《沧浪诗话·诗体》云:“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1]203-205严羽的“三体”论已将魏诗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进行了区分。遗憾的是,其未能真正将黄初与建安区别开来,如同踏入真理领域的瞬间,倏忽退回。实际上,黄初以后,魏诗风格发生重大转型,曹植的转变显而易见,曹丕便娟婉约的诗风趋于定型。阮籍的诗歌创作多在曹魏后期,适逢司马氏当政,其《咏怀诗》兴寄无端,已有相当的玄学意味。沈德潜《古诗源》评曹氏父子曰:“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2]91评阮籍言:“嗣宗触绪兴怀,无端哀乐,当涂之世,又成别调矣。”[2]1在沈氏看来,三曹、阮籍的诗歌风格基本代表了魏诗的主要特征和总体风貌,沈氏以“汉音”评曹操,“魏响”释曹丕、曹植,“别调”论阮籍,是基于代表作家来考察时代整体风格的演进历程,其最大价值在于诠释了魏诗的多元性、丰富性,相对清晰地勾勒出魏诗的总体发展风貌。当前,学界对沈氏“汉音”“魏响”“别调”之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王澍《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黄志浩《也论“汉音”与“魏响”:“三曹”诗歌创作的历史定位》结合三曹的创作,对“汉音”“魏响”进行了阐述,但未能从诗学流变的角度把握两者的内蕴和时代特征,也没有注意到两者与“别调”的内在贯通性。王宏林《从齐驱并驾到异响竞流——汉魏诗歌的分野及其诗学意义》主要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魏诗新变特点的肯定及其诗学意义。[3]140总体来看,学界对“汉音”“魏响”的界定还不太准确、全面,对沈德潜以“别调”论阮籍所代表的正始诗歌,且将三者连缀起来考察魏诗演进脉络、整体风格的诗学理路几无问津,对魏诗三期衍进的诗学特征少有论及。为此,本文试通过考察沈德潜《古诗源》对魏诗的选评情况,诠释“汉音”“魏响”与“别调”的内涵,以期能够客观呈现魏诗的整体发展风貌,纠正传统诗学以“建安风骨”代指魏诗的偏颇。
一、赓续“汉音”之诗
清人陈祚明首倡“汉音”“魏响”,其《采菽堂古诗选》评曹操道:“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4]126-127陈祚明立足“格调”,揭示曹氏父子诗歌的主要特征和风格,对阐释魏诗内蕴有揭橥之功。沈德潜更进一步,易陈祚明的“全”为“犹”、“多”为“纯”,虽两字之差,却更能展现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在汉魏诗风转关过程中的特质与个性。而何为“汉音”,则需要结合沈德潜对曹操等建安诗人作品的选评加以探讨。
其一,文人乐府对“俗乐”的赓续。乐府是汉代诗歌的常用体裁,常被看作《国风》的承继与再现。沈德潜视汉乐府为诗歌的典范,其言:“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就五言中,较然两体,苏李赠答、无名氏《十九首》,古诗体也;《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类,乐府体也。”[2]1乐府是汉代诗歌的经典,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对曹魏诗人的影响不言而喻。沈德潜所谓“孟德诗犹是汉音”中的“犹”字颇有深意,较陈祚明的“全”字更能客观体现曹操诗歌的特征及其在汉魏乐府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作用。曹操现存22首诗歌中有20首为“相和歌辞”,分为相和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四类。相和曲有《气出唱》3首、《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陌上桑》,平调曲有《短歌行》2首,清调曲有《苦寒行》2首、《秋胡行》2首,瑟调曲有《善哉行》3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皆是依前曲所作,与汉乐府一脉相承。曹操诗歌与汉乐府的关系后人多有论及,明胡应麟《诗薮》云:“魏武‘对酒当歌’……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5]11此言甚是。传统四言诗在东汉末期已了无生气,在曹操大力创作下,再度焕发生机,颇有汉人乐府风范。胡应麟又言:“魏武《度关山》、‘对酒’等篇,古质莽苍,然比之汉人《东、西门行》,音律稍艰,韵度微乏,其体大类《雁门太守行》。《气出唱》三首类《董逃》,《秋胡行》二首类《满歌》。”[5]43胡应麟深谙乐府,对乐府的生成流变、风格句法颇有研究,这里以比较的方式揭示出曹操诗歌与汉乐府的渊源关系。明钟惺言:“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6]16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云:“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7]26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云:“《短歌行》犹是汉音。”[6]29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评《精列》道:“一起大气磅礴,与汉《铙歌》同调。”[8]131上述所论,虽各有侧重,指向却基本一致,认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多有吸收承传,有汉诗之遗风。陈祚明、沈德潜评曹诗为“汉音”,实为有见。
实际上,相和歌辞出于“街陌谣讴”,常被视为俗乐,其调多楚声,用丝竹乐器伴奏,声音委婉抑扬,与被视为正声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风格迥异。《宋书·乐志》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9]603史书对此多有记载,《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0]54《资治通鉴》亦云:“魏太祖起铜爵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11]4220隋文帝曾令音乐家何妥考定钟律,何妥上表曰:“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12]1714曹操诗歌“合乐而作”的特征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个人深厚的音乐素养息息相关。张华《博物志》载:“桓谭、蔡邕善音乐,冯诩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13]156曹操音乐造诣之高可见一斑。曹植所作《武帝诔》在颂扬曹操丰功伟绩时,不忘提及其父于军国大事之外孜孜于乐府创作:“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14]199总体而言,曹操依照古题乐府作新诗,曲调变化不大,保留了乐府诗用于演唱的传统,但也显露出渐变痕迹与开风气之先的迹象:诗歌主旨与乐府旧题脱离关系,体式已不再局限于五言和杂言,大量四言的出现使乐府诗的形式更加多样、更具活力。
总之,曹操乐府诗创作最大的意义是以文人乐府的手法继承了相和歌辞的俗乐传统,使汉乐府最质朴、最初始的风貌得以保存,也使文人乐府一开始就能雅俗结合而具有勃勃生机。
其二,“诗史”传统的肇始。“诗史”是唐人孟棨于《本事诗》中首次提出,并以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为范例。实际上,具有“诗史”特征的诗歌早在曹操作品中已有体现。沈德潜评《蒿里行》道:“此指本初、公路辈,讨董卓而不能成功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2]93在沈氏看来,以诗歌集中书写时事的笔法始于曹操。曹操现存诗歌以军旅战事、忧时忧世之作居多,多有“汉末实录”特征。《古诗源》所选录《薤露》《蒿里行》《苦寒行》诸篇最为典型。钟惺评《薤露》道:“汉末实录,真诗史也!”[15]124沈德潜曰:“此指何进召董卓事,汉末实录也。”[2]93“诗史”“实录”都意味着诗歌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历史现实,而沈德潜在钟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具体的人、事来解析诗歌历史背景和史实。清方东树曰:“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16]208将《薤露》《蒿里行》相连发论,着眼汉末时局,历史的真实感与即事感尤为强烈。如果说《薤露》《蒿里行》以广阔的视角反映了宏大的历史画面,那么《苦寒行》则以细腻的手法描摹出历史细节。建安十一年(206)春,曹操远征高干途中作《苦寒行》:“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2]93此六句先后用曲折的羊肠小道、颠摧车轮的山石、萧瑟的树木、寒冽的北风、夹路而蹲的熊罴虎豹来描述征途的险恶。艰苦的行军环境超出常人想象,若非身临其境,不可能有如此逼真的描写,相比古代其他军旅诗歌,曹操的细节描写颇有镜头感和画面感。《观沧海》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归途中登碣石山所作,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10]29此战之后,北方基本在曹操的掌控之下。在一派大好的政治军事情势下,曹操意气风发,澄清海内之志自然流露于诗中,沈德潜誉其有“吞吐宇宙气象”[2]92。此外,《短歌行》《土不同》《龟虽寿》《观沧海》《董卓歌词》《谣俗词》《秋胡行》《却东西门行》也属时事性较强的作品,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状况。所以,王土禛《古诗选·凡例》言:“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乐府题叙汉末事,虽谓之古诗亦可。”[17]1这种写实的风格,在建安七子的诗作中也有体现。他们的咏史诗、杂诗、军戎诗哀时伤世,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局面。初平三年(192)的李傕、郭汜之乱,对上层官员和底层民众而言都是深重灾难。王粲的《七哀诗》正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生动注脚:“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18]86与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情景相通,可以说,《七哀诗》和《薤露》《蒿里行》共同构成了董卓之乱的全景图。此外,缪袭的《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战荥阳》四诗反映了曹操的赫赫战功,是曹操早期创业的真实写照,具有诗史的价值。曹操、建安七子的部分诗歌把满目疮痍的历史画面真实呈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千载之下读来,无不令人动容惊魂。这不仅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一脉相承,也开创了古典诗歌集中书写“时事”的先河。
综合来看,曹操诗歌以文人乐府赓续“俗乐”,不仅使乐府诗合乐而作的特征得以保留,而且推动了乐府诗歌的雅俗结合。他与其他建安诗人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以诗写史”的实录特质,体现出叙乱悯人的人本情怀和现实主义追求,中国“诗史”传统实滥觞于此。曹操大力创作乐府带动了文人乐府的盛行,可谓“收束汉音,振发魏响”,堪称上一个时代诗风的承绪者,后一个时代诗风的开启者。
二、自铸“魏响”之诗
随着曹操、建安七子的谢世,曹丕称帝,曹植人生境遇的巨变,魏诗有别于“汉音”的新变要素更加鲜明。沈德潜所言“魏响”对廓清魏诗风貌、还原魏诗地位有着重要的价值。细而论之,大致体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淡合乐而重音韵。在曹操的影响下,曹植、曹丕也有着较高的音乐造诣。曹丕酷好音乐,“丝竹并奏,酒酣耳热”是其生活常景,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尝试以梵音制声,浓厚的音乐氛围与个人喜好为二人探索诗歌韵律提供了可能。不过,丕、植兄弟相对淡化乐府的合乐性,转而追求音韵和谐。刘勰言:“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19]103不诏乐师配曲,意味曹植对合乐演唱的淡化。明许学夷《诗源辩体》云:“子建乐府五言《七哀》《种葛》《浮萍》而外,惟《美女篇》声调为近。外惟《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白马篇》云:‘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数语,稍类乐府,余则谓之乖调矣。”[20]81清冯班《古今乐府论》云:“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6]168“乖调”语出《文心雕龙》,主要指曹植、陆机诗歌不同于此前依乐而作的乐府诗,是文人化的乐府。而曹植等人的诗歌不依乐填词,转向对诗歌韵律的探索,实领风气之先。《古诗源》中,沈德潜选曹丕7首诗,专就曹丕《燕歌行》用韵进行了点评:“句句用韵,掩抑徘徊。”此诗用阳部韵,一韵到底,感情婉转低徊,给人一种无尽哀愁之感。胡应麟言:“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始之,《燕歌》《白纻》皆此体。”[5]41清王尧衢曰:“此诗情词悱恻,为叠韵歌行之祖。”[6]75明清古诗选本中,很少以音韵论诗,但谈到《燕歌行》则是例外,明代陆时雍、钟惺、谭元春,清代吴淇、陈祚明、王夫之、王士禛等人点评此诗均论及音韵,可见《燕歌行》的音韵在诗歌史上的独特性与开创性。曹丕诗歌中,除了《燕歌行》这种句句押韵、《至广临于马上作》这类押偶句韵,多为不完全规则韵式,如《杂诗》(慢慢秋夜长)前十四句为偶句韵,基本为阳声韵中的阳部韵,但因“三五正纵横”中横字而变成阳庚合韵,后四句的偶句又回到阳部韵,奇数句则押密韵,形成奇句偶句交叉押韵的特点。同样,曹植诗歌也有不规则用韵的体现。沈氏评《弃妇篇》言:“篇中用韵,二‘庭’字,二‘灵’字,二‘鸣’字,二‘成’字,二‘宁’字。”[2]103-104这里指出了曹植一首诗重复用五韵的情况,在沈德潜之前,仅宋王观国《学林》、明谢榛《四溟诗话》曾指出《美女篇》一篇押二“难”字的问题。


《诗经》《楚辞》曹丕曹植阳声韵22.1%38.3%58.8%58.2%阴声韵44.9%40.2%34.2%36.0%入声韵21.6%21.6%7.0%5.8%
从《诗经》到丕、植诗歌押韵情况来看,阳声韵在诗歌中的比例不断递增,阴声韵在诗歌中的比例呈缓慢下降趋势,入声韵在丕、植诗歌中降低到《诗经》《楚辞》的三分之一。丕、植兄弟对阳声韵的偏好,使建安、黄初时期的诗风呈现出昂扬激越、婉转朗畅的格调。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魏诗歌,这种声韵传统在缓慢的演变中完成了诗歌在音韵方面的突破。然而,这种转变与突破并非一蹴而就,既是对两汉诗歌的传承,也是三曹等建安诗人孜孜以求的过程,折射出“汉音”“魏响”的演进轨迹。
第二,重抒情而淡叙事。相比曹操,丕、植兄弟诗歌抒情特质更加突出,宏大历史事实的叙述变得少见。许学夷曰:“盖汉人本叙事之诗,子建则事由创撰,故有异耳。较之汉人,已甚失其体矣。”[20]81所谓失体,应是诗歌功能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
在《古诗源》中,沈德潜选曹丕诗7首,都有点评,除《至广陵于马上作》外,均强调其诗歌的情感表达。评《短歌行》为“思亲之作”[2]94,此诗以比兴手法寄托对父亲的哀思,情深意婉。《寡妇》虽为代写,却感同身受。沈氏评道:“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寡居,为作是诗。”[2]96清张玉谷《古诗赏析》云:“就秋景说起,感时触物……曲达其深情,即隐坚其贞念也,何等宛至。”[22]197曹丕敏感而多情,在寒暑易时,人事更谢中触动情绪而兴发成诗。沈德潜评《善哉行》道:“此诗客游之感,忧来无方,写忧剧深。”[2]95评《杂诗》二首道:“二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感。”[2]95三诗婉转深致,表达出强烈的客游思乡、念亲怀远之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曹植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叙事成分较少。《古诗源》选录曹植作品29首,其中《朔风诗》《圣皇篇》《弃妇篇》《吁嗟篇》《当墙欲高行》《野田黄雀行》《当来日大难》《杂诗》《七哀诗》《情诗》《七步诗》等17首为纯抒情之作。沈氏评《圣皇篇》道:“处猜嫌疑贰之际,以执法归臣下,以恩赐归君上,此立言最得体处。王摩诘诗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深得斯旨。‘何以为赠赐’一段,极形君赐之盛,若夸耀不绝口者,然其情愈悲矣。”[2]102争位失败后,曹植受到曹丕、曹睿父子猜忌,屡遭贬谪流放,内心的愤懑压抑之情可想而知,碍于其时的处境,不便直言,所以才有这种隐曲的表达方式。沈德潜评《朔风诗》道:“结意和平夷愉,诗中正则。”[2]98评《吁嗟篇》道:“陈思之怨,为独得其正云。”[2]103肯定其怨情的表达符合雅正的传统。又评《弃妇篇》道:“怨而委之于命,可以怨矣,结希恩万一。情愈悲,词愈苦。”[2]103认为曹植以弃妇自喻,悲愤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却怨天而不尤人。《野田黄雀行》虽写“黄雀”,实以喻深陷牢笼之友,有心无力的悲愤感力透纸背。曹植还有多首以赠字为题的诗作,有的是劝慰朋友,勉励其振奋,如《赠徐干》《赠王粲》《赠丁仪》;有的则表达了送客远行的愁思,如《送应氏二首》。在《赠白马王彪》中,曹植备受压抑的愤懑、痛苦之情得到酣畅淋漓的抒发,情感时而激扬,时而低徊,激荡着感发人心的力量。曹植还善于在模拟汉乐府的过程中注入抒情要素,《美女篇》沿袭汉乐府《陌上桑》叙事手法的同时,增加了抒情的成分。前一部分极力描写美女之美,但结尾六句却变成了抒情之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2]101,美女不嫁之虑的叹息,正是曹植怀才不遇的写照。无独有偶,《白马篇》在描述游侠儿英雄形象之后,最后八句也以游侠儿的口吻道出了他奔赴国难的内心情感,充满着昂扬向上的感情色彩。正如明王世懋所言:“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24]774
第三,由慷慨激昂走向温婉轻靡。沈德潜评曹丕《燕歌行》道:“和柔巽顺之意,读之油然相感。节奏之妙,不可思议。句句用韵,掩抑徘徊。‘短歌微吟不能长’,恰似自言其诗。”[2]97曹丕长吁低吟,用语温婉蕴藉,“思断肠、不敢忘、沾衣裳、不能长”展示出少妇对丈夫的温顺、依恋之情,笔触十分缠绵细腻。诚如刘履《选诗补注》所言:“忧来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长,则可见其情义之正,词气之柔。”[25]23较之曹丕,曹植也不遑多让。钟惺言:“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6]131沈德潜评《吁嗟篇》道:“迁转之痛,至愿归糜灭,情事有不忍言者矣。”[2]103多次流放迁徙,使曹植的人生居无定所,政治理想几近幻灭,内心痛苦至极,如同诗中哀诉的那样:“流转无恒处,谁知我苦艰。”以“转蓬”自喻,隐衷尽显,凄楚动人。沈德潜评《怨歌行》亦言:“‘忠信事不显’,言忠信之心,不欲人知也,如周公纳祝词于匮中之类。”[2]100认为曹植以周公之事表达忠心,语言含蓄,风格也由激切趋于隽永。
曹丕、曹植这种温婉绵密的诗风与其个人经历有着重要的关系。曹植黄初前后的特殊人生遭际,使他的诗风从高华朗畅一变而温婉雅怨,情感由前期的高迈激昂、豪情四溢转向后期的悲愤低沉、忧郁伤感。曹丕的“公子气、文士气”贯穿其一生,贵为皇帝之后,诗风更加柔肠百结,轻靡细腻,情感基调极尽感伤、温婉,慷慨之音难觅踪迹。相对而言,黄初时期丕、植诗歌抒发的情感多为一己之情,其父曹操关注社会、关注民瘼的时政社会题材在他们诗中几无踪影,这也是兄弟二人黄初以后诗歌迥异其父的重要特征,更是汉魏诗歌分野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四,尚作用而远自然。所谓“作用”,即曹丕、曹植在语言上追求华辞丽彩。与自然率真的汉乐府和古朴质直的曹操诗歌相比,“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2]94,子建“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2]98。曹操身在军旅三十余年,曹丕、曹植虽生于乱世,成长环境则大异其父,“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的氛围造就了兄弟二人的“文士气”。曹植文才高华,诗歌辞彩富艳,兼善四言、五言,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明清古诗选本中入选诗歌数量名列前茅的诗人。沈氏评《名都篇》道:“《名都》《白马》二篇,敷陈藻彩,所谓修词之章也。”[2]100评《美女篇》道:“写美女如见君子品节,此不专以华缛胜人。”[2]101《名都》《白马》两篇辞藻精警,语言华丽,是以辞彩取胜的代表作,不专以华缛胜人的《美女篇》同样文采斐然,三篇诗作堪称曹植诗歌中词采华茂的典范之作。诚如胡应麟言:“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5]29胡应麟认为上述三篇诗歌不仅具有繁缛富丽的特征,还有句式工整、语言美赡的特点。曹丕主张“诗赋欲丽”,其诗也很好地体现这一价值取向,如《芙蓉池作》《黎阳作三首》。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华丽即曹丕所主张”,“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26]528沈德潜评曹丕《善哉行》道:“措语既工复活。”[2]95认为曹丕诗的语言既工整又生动流转。如许学夷所言:“子桓乐府七言《燕歌行》,用韵祖于《柏梁》,较之《四愁》,则体渐敷叙,语多显直,始见作用之迹。此七言之初变也。”[20]75-76亦如陈伯海所言:“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便转为字句、篇章的推敲,重视文采因亦成为文人的普通习性。”[27]74曹丕、曹植二人刻意求工,注重措辞的华丽严饬,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佳作名篇,流风所及,对邺下文人乃至六朝诗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曹植开始注重诗歌章法。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认为诗歌结构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19]570-571如以刘勰的启行、中篇、绝笔来审视曹植诗歌的章法布局,恰能概括其诗歌篇章结构特征。曹植身处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型的过渡阶段,对诗歌章法多有探索革新,开篇喜欢塑造一种大格局、大境界,给人一种大手笔之感。如沈德潜所评:“陈思最工起调,如‘高台多悲风’‘转蓬离本根’之类是也。”[2]108这里的“起调”,也是刘勰所言“启行之辞”。沈德潜点评《赠白马王彪》时,以诗歌章法来诠释作者的心理情感、诗歌主旨:“此章乃一篇正意,置在孤兽索群下,章法绝佳。”[2]107此章指该诗的第五章,前几章所写对京城的依恋、旅途的困顿、见景伤怀,在于铺垫,只为道出曹彰暴死,进而引发忧生之嗟、愤慨之情,曲折复杂的情感正是诗歌旨向、重心所在。评此诗第六章道:“此章无可奈何之词。人当极无聊后,每作此以强解也。”[2]107自己虽对命运无能为力、不能释怀,仍勉力安慰曹彪,情感相当压抑、曲折。评此诗最后一章道:“末章如赋中之‘乱’,几于生人作死别矣。”[2]107赋体结尾的“乱”,在于总括全篇,提振文章气势。本章透露出一种辛酸的悲愤,把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绪渲染得更加悲凉,给人一种英雄末路之感。总体而言,这三处点评是就全诗中篇、绝笔而言,加上对《杂诗》“起调”的探讨,沈德潜能够独辟蹊径地分析曹植诗歌的章法,颇具新意。
总体来看,曹丕、曹植两人在淡化传统乐府诗合乐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诗歌语言的音韵,这是诗歌走向文人化的必经之路。重情感抒发而淡化叙事,使汉乐府的叙事功用转向文人化的内心情感表达,使文学集体意识传统向个人主观意识转化。由尚“作用”而远自然,特意追求辞彩的藻丽、精心构造篇章句法,丰富了诗歌表现艺术,拓展了语言的张力,体现了建安时期慷慨激昂诗风向黄初、太和时期的温婉轻靡转变的过程。这是丕、植人生境遇在诗歌创作中的真实反映,也是“文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结果。这些新变元素共同构成了“魏响”的底色与内蕴,折射出“魏响”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三、“又成别调”之诗
阮籍诗歌表现出语言多义、思想隐晦、心理敏感复杂的特征,不同于三曹、七子等魏代诸多诗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的艺术风貌。沈德潜评阮诗“又成别调矣”[2]1,堪称独具慧眼。“别调”见于刘克庄词集《后村别调》,而何为“别调”,刘克庄并未具体说明。明姚希孟《媚幽阁诗余小序》云:“‘杨柳岸晓风残月’与‘大江东去’总为词人极致,然毕竟‘杨柳’为本色,‘大江’为别调也。”[28]604姚氏以婉约词为“本色”,“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的豪放词为“别调”。借用词之“别调”论诗,沈德潜似为首创,除以“别调”论阮籍之外,《古诗源》评六朝民歌也用到这个术语:“晋人《子夜歌》,齐梁人《读曲》等歌,俚语俱趣,拙语俱巧,自是诗中别调。”[2]3刘勰曾以“调”论阮诗:“响逸而调远。”[19]506其后,钟惺《古诗归》评阮诗:“愁怀达见,迫成异调。”[6]144可知,沈德潜对阮籍诗歌“别调”的定位可能受到刘勰、钟惺的启发。从沈德潜对阮籍诗歌的选评来看,“别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兴寓言与玄思意趣的融合。阮籍《咏怀诗》寄托了诗人独特而复杂的情绪,风格隐晦幽婉。颜延之谓“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沈德潜言“令读者莫求归趣”,都意在强调阮诗难以理解和把握。沈德潜《古诗源》入选阮籍《咏怀诗》20首,7首未予点评,7首以解说字词、典故为主,仅对其中6首主旨略有阐发,与颜延之“怯言其志”颇为相似。阮籍之前的曹魏诗歌多“指事而语”、畅而不隔,即便曹植后期的诗歌,虽多寓比、掩抑徘徊,但情感基调、诗歌主旨明确清晰,如《吁嗟篇》以“转蓬”形容自己飘荡无依的处境,《七哀诗》《弃妇篇》以弃妇自喻,即目之下,主旨自明。所以王夫之评《七哀诗》道:“可谓物外传心,空中造色。结语居然在人意中而如从天陨,匪可识寻,当由智得。”[23]180阮籍在正始年间的处境,与曹植在黄初以后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诗歌主旨表现出内在悲愤与外在超脱的反差,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和反差,导致诠释其诗歌旨趣、意蕴时会有隔离之感。有时是“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的壮志高迈,有时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凡庸自诩。在这种矛盾心态的交织纠葛之下,常常表现出无所适从的苦闷:“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沈德潜谓其“而远去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其位何,所以怆然心伤也”[2]122。面对昏聩堕落的曹魏集团,司马氏排除异己、严织罗网,阮籍常处于愤慨与不安之中。“夜中不能寐”而“忧思独伤心”,高压密网之下,以致“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残酷的现实使阮籍挣扎着寻求内心的平衡,或寄情于外物,或企冀以游仙稀释内心苦闷。“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景山之松成为化解诗人悲苦彷徨的寄托。“焉见王子乔,乘云翔北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神仙是诗人超脱危亡的寄托,因为现实的种种困苦,求仙得道不时出现在诗中,成为一种摆脱现实的希冀。相比曹氏父子游仙诗中与神共“游”的渲染描摹,阮籍更多的是对神仙的企羡。如“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这与曹植“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欢腾场景相比,颇显寂寥。场景描写的繁简寂闹,折射出诗人潜在的心理状态。对此,王利锁《试论阮籍咏怀诗的游仙描写与建安游仙诗模式风格的差异》作如是阐述:“建安诗人的游仙诗在抒情情调上包孕着浓重的现世人生价值追求的进取精神,即使与仙同‘乐’时他们也没有失去这种积极和主动,而阮籍的游仙坦露出的则是一颗孤独无援、痛苦难遣、明知不可行又不能不借此慰藉自己的悲苦心灵。”[29]102根本而言,曹魏诗人特别是三曹,游仙诗是他们高扬政治理想的“欢乐场”,阮籍的游仙诗则是他回避现实的“桃花源”,两种心理期待,呈现出迥异的“游仙诗”书写状态。清叶燮曾言:“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可不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30]193朦胧隐晦的诗意,激发后世对阮籍诗歌的兴趣和关注,正是其诗歌魅力所在。更为重要的是,82首《咏怀诗》作为组诗,集中反映了阮籍身处乱世,进退之间的矛盾纠葛,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摇摆。且“诸咏非一时所作,因情触景,随兴寓言。有说破者,有不说破者。忽哀忽荣,俶诡不羁”[2]122。所以沈德潜主张“《咏怀诗》当领其大意,不必逐章分解”[2]122。如履薄冰的心焦和企求超脱而不能的反差,给人一种疏离之感,造成难以把握的距离感,进而产生认知的困惑,陆时雍所谓“曲喻旁引,离合往复”[31]62正在于此。
与此相关,深厚的玄思色彩也是造成阮诗隐晦玄远风格的重要原因。《文心雕龙·论说》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19]327正始时期,玄学已与主流儒学思想争夺阵地,这在阮籍身上已经有所体现。“博览群籍,尤好《庄》《老》”的阮籍,常以“以庄周为模则”,其创作带有强烈的玄学气息,《清思赋》《大人先生传》着力营造逍遥游的境界,《咏怀诗》中也有相当的诗篇氤氲着这种气息。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诗人一度渴求“颜闵”与“荣名”的思想逐渐淡化,转而“乃悟羡门子”“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沈德潜评道:“有去之恐不速意。”[2]119但去留只是一种理论选择,现实却有诸多的身不由己。自然万物的变换是世事无常的外化,如“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棘”,山川草木、日月生灵是阮籍体认玄理、感悟玄思的载体,诗歌也将不可避免地投射出玄言色彩。钟嵘说阮诗“颇多感慨之词”,主要体现在结尾两句,或引入玄学话语,或升华性议论,大多带有玄学思辨色彩。钟嵘仅以感慨论之,恐难诠其实质。
阮籍有的诗歌以玄学话语收束全诗,如“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岂安通灵台,游养去高翔”,类似结尾多达20余处,直接引入老庄,是阮籍玄学思想的具化体现,给人以玄远之感。在有的作品中,阮籍通过议论来升华概括诗中之象,“北邻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哀叹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言乱世之中,不敢有鸿鹄之志,只求保全性命而已;“盛衰有须臾,离别将如何”是对繁华易逝的感慨。这些议论,是对具体物象的升华,体现一种普遍意义的认知,流露出玄学意趣。诗歌具体物象的玄学意蕴与诗歌结尾的玄学话语,成为阮籍诗歌区别于曹魏诗人的重要因素,也使因情触景,随兴寓言的诗语变得更加隐晦深幽。
第二,赋、比连用的创作手法。阮籍诗歌的隐晦幽深,并非语言的佶屈聱牙,而是潜在深层意义的难以把握。飞鸟、植物、冷秋等是《咏怀诗》中常见的物象,在描摹这些物象时,阮籍常常将赋、比连用,并不是常言之比、兴连用。正如《文心雕龙·比兴》所言:“日用乎比,月忘乎兴。”[19]602“比”用多了,就忘了“兴”。这种情况在曹植、曹丕等曹魏诗人中也比较常见,但阮籍恐怕不是忘了“兴”,其诗歌之“兴”不是朱熹所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是钟嵘所言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实际上,《咏怀诗》首句的物象景物很少有起兴作用,仅是全诗景物的一部分,也是诗歌情境的有机组成。《咏怀诗》(林中有奇鸟)描写的奇鸟凤凰,具有“饮醴泉、栖山冈、鸣九州、望八荒”的神奇行为,正是通过“赋”的陈述之法将凤凰的一系列动作展示出来。沈德潜评曰:“凤凰本以鸣国家之盛,今九州八荒,无可展翅,而远去昆仑之西,于洁身之道得矣。其如处非其位何,所以怆然心伤也。”[2]122凤凰是全诗的主体,并非“关雎”之于“君子、淑女”的关系,不具有“兴”的作用,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外化和比附,而“赋”是用来描述对凤凰的,“比”“赋”连用的过程中完成了凤凰形象的塑造,作者的怀抱也自在其中。《咏怀诗》(西方有佳人)也是如此,阮籍以“赋”的铺陈塑造了一位飘于云端的美人形象,寄托了作者的贤人寓意,是“赋”与“比”连用的又一体现。上述二诗中,凤凰、佳人是唯一书写主体,但有的诗则由多种物象共同构成书写主体: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2]120
首句中的“空堂”不具有起兴的作用,只是全诗的一个镜头而已,它与永路、旷野、高山、九州、孤鸟、离兽共同构成了寂寞、悲凉的画面,是为了比附作者内心的孤独与寂寥。很多人说阮籍的诗不好理解,恐怕不是文辞的原因,而是他们试图解构这些物象被赋予的潜在含义,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的确难以索隐钩沉。《文心雕龙·宗经》云:“《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19]22阮籍的诗歌大概也是如此,文辞一看即晓,但意旨却深奥隐晦。颜延之注阮诗言:“嗣宗生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32]322颜延之身处晋宋易代之际,最能以己之境度阮籍之况,考量当时的政治环境,阮籍也只能欲说又隐了。钟嵘说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33]151,是着眼于“诗外之旨”,追求“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歌韵味。阮籍将“赋”“比”连用,营造诗歌的画面和情境,为潜在的情绪、心理、思想寻求一种相适应、匹配的诗意介质,带有言外之意的玄学意味,必然会造成理解的困难、隔离。如果把颜延之和钟嵘的论述结合起来,也许就能破解阮籍诗歌内蕴指向的密码。因此,沈德潜立足于文学发展的流变,肯定了阮籍诗歌新变特征:“《十九首》后,复有此种笔墨,文章一转关也。”[2]122可以说,引“玄”入诗,或许是阮籍的有意之举,也可能是其时社会思潮熏染下无意识行为,但对此后盛行的玄言诗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阮籍的“别调”既不同于建安的慷慨激昂,也不同于黄初的温婉轻靡,而是玄学初兴之下的隐晦玄远。诗歌从重合乐向重韵律的渐变,是乐府诗向文人诗过渡转变的重要特征。与建安时期注重叙事、黄初之后偏向抒情的诗歌风貌相比,比、赋连用的表现手法,是阮籍诗歌更关注景外之象、言外之意、言外之情的现实需要。这些新变因素正是阮籍诗歌不同于建安、黄初诗作的表现,其背后则是时代风气和诗人个性特质双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
四、以“汉音”“魏响”与“别调”品评魏诗的意义
沈德潜以“汉音”“魏响”“别调”论魏诗,准确把握了魏代诗歌的本质特征与新变特点,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古诗源》中以“音”“响”“调”“韵”“声”论诗分别为70、14、15、16、44处,如此频繁使用这类术语来点评诗歌,在明清诗歌选本中相当少见,这与沈德潜的诗学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沈氏《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云:“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34]2音节正是沈德潜诗学理论重要一环,《古诗源》开篇即言:“康衢击壤,肇开声诗。”[2]1《击壤歌》等声诗具有合乐的特征,依靠配乐歌唱传达诗歌旨趣。《说诗晬语》亦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35]10声律音调对于诗歌的表情达意有着重要的作用,声律、音响能够传达出“言外之旨、韵外之味”。沈德潜对音节的重视既有承袭明七子格调论的原因,也有其为诗歌宗旨寻求外在表达方式的需要。就宗旨而言,其核心要义是“诗教”,这是贯穿其诗学体系的一条主线,也是他诗歌审美的终极指向。“‘诗教’为本,‘乐教’为用”[36]92,“诗教”“乐教”在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中被具化为宗旨和音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其诗歌审美的原则性主旨。在这一原则主导下,沈德潜将魏诗分为“汉音”“魏响”“别调”三种类型,既有对传统诗学话语的继承,又有诗学理念上的突破。
此外,沈德潜对魏诗的三期之分与其崇正主变的价值取向也有直接关系。崇正主变是沈德潜老师叶燮的诗学观念,叶氏《原诗》云:“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30]62如果说具有“汉音”特征的建安诗歌为正,那么“魏响”“别调”则为变,且是“变能启盛”的转捩点。“魏响”逐渐脱离音乐,变为徒诗,诗歌的音韵更加受到诗人关注,温婉轻靡的诗风成为黄初、太和时期的主流,对后世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傅玄对汉魏乐府的模拟,张华对曹植诗歌的有意摹仿,郭璞与阮籍、嵇康玄理的会通,陶渊明诗“源出于应璩”,无不反映出“汉音”“魏响”对两晋诗风的开启之功。进一步而言,魏诗对唐诗的繁盛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王粲的《七哀诗》是“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2]112,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标志着“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2]115,阮籍则开启了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的五古创作。可以说,基于崇正主变的诗学观念,沈德潜赋予“汉音”“魏响”“别调”承前启后的诗学地位,清晰地呈现了魏诗三期之分的总体特征,有利于以诗歌流变的角度来审视魏代诗歌衍变过程中多元诗学风貌,对于厘清魏诗诗学意蕴与时代特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