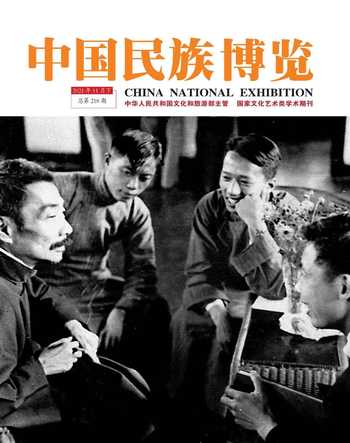传承与超越:唐代乐舞《霓裳羽衣曲》的民族审美话语
2021-02-15刘凯君
【摘要】中国古代乐舞在时代秩序演变中呈现出鲜明的延续性特征。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顶峰时期,其乐舞艺术更是以独特性的姿态成为典型代表。唐代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是由中原传统乐舞与西域龟兹乐舞相融合的产物,不仅代表着唐代乐舞文化的互通特点,也彰显着中华文化强大的吸收力与外显度。该乐曲所映射的时代氛围是其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体悟,进而以审美现代性的当代思维进行话语表达,从而实现对《霓裳羽衣曲》的内涵式解读与现实关照。
【關键词】传承与超越;霓裳羽衣曲;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2-196-03
【本文著录格式】刘凯君.传承与超越:唐代乐舞《霓裳羽衣曲》的民族审美话语[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2):196-198.
引言
《霓裳羽衣曲》作为唐代歌舞大曲的典型化乐舞作品,它是盛唐时期人们主体意识与审美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从该乐舞的演出内容与形式上看,其历史溯源可至《韶乐》传统,之后受西凉乐的影响并在道家思想的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时代氛围及超现实的乐舞作品,凸显盛唐时期的文化心理写照,体现出在前代文化传承基础上的精神超越。本文基于唐代乐舞《霓裳羽衣曲》的视角,对其历史传承、文化融合及民族审美进行内涵式剖析,进而在《霓裳羽衣曲》的内在文化意义中形成现实关照。
一、传统秩序中的风格范式延续
对唐代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的历史探寻需要先从《韶乐》传统谈起。《韶乐》作为歌颂舜美德且尽善尽美的乐舞,以国乐的性质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心灵交互。正所谓“《韶乐》一出,天下正”,《韶乐》的奏响是诗人歌唱、巫者蹈之、司向上天赞颂与祈祷等和合统一的艺术表现方式。歌舞大曲则是器乐演奏、歌唱、舞蹈等的多段体乐舞套曲。尽管两者在内容呈现上因时代不同而具有差异性,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均为诗歌、音乐、舞蹈等的综合性表达。同样,歌舞大曲的风格范式同样受到了汉代相和大曲边歌边舞结构形式的影响,其结构的完整性为唐代歌舞大曲的表演形式提供了模板参照。此外,从该乐曲的曲式结构上来看,《霓裳羽衣曲》的曲式结构由散序、拍序及舞遍三大段构成,西域龟兹乐的曲体结构包含歌曲、解曲和舞曲三部分,这也说明了两者乐曲结构的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看出,《霓裳羽衣曲》在其内容的选取维度上一脉相承于前代乐舞的表现形式,诗、乐、舞三位一体作为古代乐舞的专有“代名词”是建立在以劳动为本质属性的立场上生成的艺术化表现内容,这一点也遵循了舞蹈“劳动说”的起源论点,其内在结构较前代更为细化与明晰,体现出传统秩序中的延续性特点。与此同时,从表达功能来看,《霓裳羽衣曲》的功能散发同样沿袭着前代善与美的特点,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外延了对善与美的感性输出——脱离传统儒家学派尊崇现实性的原则,进而体现着虚幻状态下的美善表达。
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建构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扩大的关键时期,其在时代的分裂中逐渐形成民族间的互通与认同,族际间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文化意义,并通过转化实现了文化体系的形成,这使得魏晋南北朝呈现出精致化、体系化和个性化的审美自觉。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已经开始出现以道教为系统化存在的释道儒合流现象,各类艺术形式也都显现出不同思想的典型特征。唐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的大一统,并促使了民族文化进一步认同。与此同时,道教作为唐代国教,三教相互融合的现实性在唐代得到了快速发展,广泛影响着唐代乐舞艺术的产生。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的勃兴及民族文化的互通勾连,其历史文化及艺术风格的延续为唐代道教的繁盛、民族大一统及乐舞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从《霓裳羽衣曲》的思想文化背景来看,其舞蹈体式以道教的成仙长生为显著特征,充满了道教的意象与意境,体现出道家天乐思想的理想境界,这与《霓裳羽衣舞 》的“嫣然纵送游龙惊”有异曲同工之妙。“玉树长 漂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此乐舞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乐曲在空际回荡,仙子在瑶台曼舞这样一种神幻的意境,在乐舞文化上它们都具有奇特的想象力,都崇尚飘逸灵动的意境。[1]
二、古典精神中的异域风情融合
唐代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的创作是在“开元盛世”的盛唐时期所形成。《霓裳羽衣曲赋》中记载:“昔开元皇帝以海内清平,天下丰足,思紫府瑶池之乐制霓裳羽衣之曲。”时代的繁盛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乐舞的审美意识发生了转变,该乐舞的创作进一步深化了唐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从而成为具有典型化的乐舞艺术。这一时期不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在不断的深化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互通,由此呈现出的鲜明特质则是规模的扩大化与文化的多元性,与西域之间的紧密往来更是推动着当时文化的频繁交流。季羡林先生曾说:全国各个地方文化云集交融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古西域,中原的汉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都在此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外在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唐代这一时期人们对人生理想的高度追求。这种“跨界”性质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体现着唐代人们思维的超前意识与主动行为,展现出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古典精神。
从《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角度来看,其内容与形式的表达是中原传统与西域特色的交融。一是体现在乐曲制作与表达中,它以西域龟兹地区《婆罗门曲》为基础进行改编。音乐教育家杨荫浏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叙述到:在公元754年,玄宗皇帝命令将佛曲《婆罗门》命名为《霓裳羽衣》。《霓裳羽衣曲》的乐曲风格不仅包含中原文化温婉含蓄、秀丽清新的特点,同时还有西域文化中激昂奔放、热烈欢腾的典型特质,两者的相互融合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感。二是体现在乐舞的舞姿形态中,其中包含中原汉乐舞“小垂手”的基本体态,同时融入西域风情“胡旋舞”及龟兹乐舞中“绕腕”等的典型化动作。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中写到“拍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飘然旋转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若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以此来描述该乐舞鲜明风格化的舞蹈动作。三是体现在乐器的使用中,其中主要包括中原传统乐器钟、磬、筝、笙、箫、笛及西域特色乐器筚篥、箜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唢呐、钹、锣等。四是体现在乐舞的服饰装扮中,舞者服饰以点缀着羽毛装饰物的“羽衣”和带有闪光花纹裙的“霓裳”为主体。据白居易的诗,“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间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对创作者而言,在对两者文化属性的提取过程中其实质都是以“他者”视角展开的内容表达,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中找寻到同一性的融合点,从而形成完整的艺术作品。
整部作品鲜明的体现出异域文化融合下的审美特质。西域与中原文化看似迥然不同,但西域的胡乐风格与唐代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观念具有同一性。此外,唐代乐舞艺术的高峰构筑正是在源自对外来艺术的兼容并包与积极创新,《霓裳羽衣曲》的出现正是唐代乐舞典型化风格、标志性范式的集中体现,它彰显了唐代人们的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以及唐代社会整体的精神信仰。
三、时代嬗变中的民族审美感知
不同时代的历史轨迹烙印着属于自身特质的记忆范畴,而同一时代不同阶段同样展现着差异化的本质属性。《霓裳羽衣曲》在唐代的嬗变轨迹分为盛唐、中唐与晚唐三个阶段。盛唐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怀呈现出豪放的精神气质,该乐舞在整体的表现过程中凸显这一时期人们向往自由的审美追求。《杨太真外传》中记载:“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2]这一阶段的作品传播完全契合着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诉求,在宫廷“君臣共乐”的氛围中奠定了该作品的历史地位。中唐阶段的现实主义境遇呈现出朴实的人文状态,此时的表演也是由宫廷逐渐转向民间的多样化发展,展现出这一阶段人们平淡无华的现实际遇,这一阶段的作品传播剥离了宫廷雅乐的独一属性,开始转向民间集市的泛化表演,该作品的演出在现实主义的客观实在语境中表达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感悟。白居易在其《燕子楼三首并序》中写道:“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平实且灵动的《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的影响下不论从乐舞规模还是内容呈现已较之前有了较大差别。
晚唐时期的惆怅抑郁色彩是正统雅乐逐渐式微的具体化表现,肃穆庄严的乐舞风格成为这一时期典型化的表现特征,這一阶段的作品传播已经趋于凝定状态,在以伤感为典型化社会背景中与作品内容呈现出差异化特质,这也标志着《霓裳羽衣曲》在时代中转折的发生。这一阶段人们虽然仍在幻想盛唐时期的繁荣盛景,但现实状态使人们情感趋于平淡化,伴随着儒教势力的增强,《霓裳羽衣曲》进行了改乐处理。《新唐书》中记载:“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3]这种阶段的演变如同西方浪漫主义时期芭蕾艺术的发展演变一样,在社会现实的历史驱动中带动着人们对审美的诉求变化,因而在萌芽阶段、鼎盛阶段与衰落阶段的芭蕾作品反映着当时人们普遍的差异化审美追求。
纵观《霓裳羽衣曲》在唐代三个时期的演变,鲜明的体现出同一历史时期中不同阶段盛衰演变下乐舞艺术对人们内心精神诉求的重要指向作用,同时也彰显出古代乐舞及其精神在时代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以外,《霓裳羽衣曲》流传至五代十国是以“执板而歌”的形式简约化的进行表演,直至宋代仍有残存。南宋词人兼音乐家姜白石,于年在乐工的旧书堆找到了《霓裳羽衣》中的十八段器乐演奏谱,并取中序音节闲雅的一段填了歌词,名《霓裳中序第一》并加小序。尽管当代已无《霓裳羽衣曲》的存在,但其表现内容及文化价值始终是当代艺术效仿的典范。彰显民族精神品格与审美意蕴是一个民族不断延续的支撑,《霓裳羽衣曲》作为历史的产物,通过肢体语言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它以多样性的审美形态、异域性的审美风格和意向性的审美意识展现出唐代对乐舞艺术的审美品位与态度。由此,这不仅是唐代乐舞艺术顶峰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代表。
四、当代语境中的舞蹈语义革新
站在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唐代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在传承与发展中国舞蹈原有传统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当代古典舞的审美价值,通过对传统舞蹈中古典艺术精神的再理解来实现其文化语义的革新。一是民族审美形态的确立,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民族审美是在魏晋南北朝混乱的民族交融中进行整合后的全新体现,具有鲜明的大一统的浪漫主义情怀特质。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民族审美的阶级化差异达到最小状态,上层贵族与市集百姓对艺术审美的鸿沟逐渐弥合,呈现出同一性特点,这也是《霓裳羽衣曲》能够经历较长阶段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民族风格范式的体现,《霓裳羽衣曲》作为大曲类型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从内容提取、功能表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与稳定性,这对其文化内涵的解读能够形成系统性的逻辑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对《霓裳羽衣曲》的当代文化语义的革新首先需要清晰的认知其在历史中的演变规律与方式,在此基础上透过时代特征挖掘符合当代民族审美范式的艺术激活机制。一是在习俗表象的环境中进行艺术素材的再提取过程;二是通过对人文意趣的思维辨析,进而提炼身体构型中动作语言符号的表征进行审美现代性的艺术化处理;三是深度挖掘《霓裳羽衣曲》的内在情感表达,由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个体意识的突出,其情感内验的个体化实现了传统语境向当代化舞台创作的构建,从当代舞台化创作要素来看,情感的共通需要建立起传统意境与当代语境的互为关系,从而呈现出情感共识的审美体验,最终实现《霓裳羽衣曲》在当代语境中舞蹈语义的革新变化。
结语
中国古代乐舞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连续性与传承性中不断产生乐舞精品。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作为唐代典范性的乐舞艺术,它鲜明的体现出民族文化交融的本质特征。该乐舞的创作建构了传统文明的精神风貌,实现了中原传统文化与西域特色文化互联的价值认可与本源认同。在回归历史通道中认知传统社会秩序下《霓裳羽衣曲》传承的风格范式,进而通过回眸其内容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舞蹈的精神风貌与精神信仰,最终在回望《霓裳羽衣曲》的时代嬗变中构筑民族审美感知。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审美认知,同时也能够深化对中国传统舞蹈的文化思辨。
参考文献:
[1]闻慧莲,闻慧芳.唐代《霓裳羽衣舞》艺术风格及思想意境分析[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54-357.
[2]史官乐史.杨太真外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0.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2
作者简介:刘凯君(1994-),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助教,山西应用科技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教师,研究方向为舞蹈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