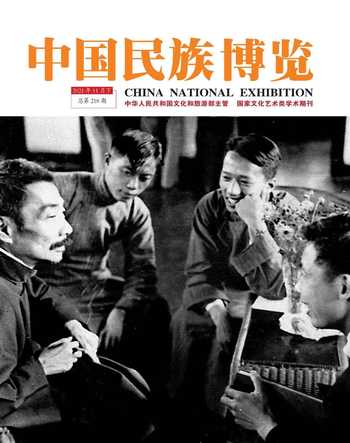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华人形象的迷幻性
2021-02-15巫冰宇
【摘要】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里,迷幻书写占据了重要地位,她利用迷幻书写的创作手法,描写了一系列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故事,刻画了典型而复杂的海外华人形象。从猎奇化、“妖魔化”、极致化三个方面来看,华人形象都呈现出迷幻性特质,这与严歌苓试图颠覆西方的话语霸权,同时又对西方文化想象产生了某种认同与妥协密切相关。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迷幻性;猎奇化;“妖魔化”;极致化情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2-193-03
【本文著录格式】巫冰宇.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华人形象的迷幻性[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2):193-195.
基金项目:2021年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谜幻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10220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Fantasy[1]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成为她独具特色的一种创作手法。Fantasy在中文里有多种翻译,综合考虑之下,文章用“迷幻”来概括。迷幻书写的含义是丰富的,通过对严歌苓作品的分析及她本人对Fantasy的阐释,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文章将迷幻书写的含义概括为:作家观察事物与人物时,结合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审美情趣进行虚构和再想象,着重捕捉并放大其荒诞、奇幻的特质,并将其置于一种极致化情境来建构故事情节,最终使作品呈现出浓重的荒诞、奇幻和神秘色彩的创作手法。
在迷幻书写这种创作手法的影响之下,严歌苓所创作的异域生活系列故事有很大一部分笼罩在迷幻的氛围下,即呈现出荒诞、奇幻与神秘的特征,这些故事中所刻画的华人形象也充满了迷幻性。结合迷幻书写的含义,下文将从猎奇化臆想、“妖魔化”臆想以及极致化情境下的华人形象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华人形象的迷幻性特质。
一、猎奇化臆想下的华人形象
祭天祭神、鸦片、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童养媳等古老中国的代表性元素在严歌苓小说中频繁出现,共同构建了严歌苓笔下的华人风情,展现出西方的猎奇化臆想下的东方形象——古老神秘、充滿吸引力的东方华人移民世界。小说《扶桑》最能展示这种原始的东方魅力,严歌苓在查阅一系列有关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历史资料之后,有意“再想象”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有着三寸金莲的女人、头顶粗黑辫子的男人、身怀绝技的中国侠士等都组合成了西方眼中神秘而奇幻的华人形象。12岁的白人男孩克里斯对中国妓女扶桑产生了入魔般的着迷,在他看来,扶桑的小脚、精致的发髻、猩红的绸衫乃至梳头、喝茶的动作全是遥远的东方古国的具象化,奇幻瑰丽,神秘颓废,充满迷幻的特征,他对扶桑的迷恋最初便是来源于这种神秘的东方情调。如果抹去那一层层异质文化的包裹,脱离那些令人着迷的东方元素,“他对她鬼迷心窍般的感觉不在了”。[2]不仅如此,克里斯眼中的扶桑总是以谜一样的微笑面对生活的苦难,永远让克里斯读不懂。在猎奇化臆想之下,扶桑既是荒诞的,又充满了奇幻美和神秘美。
同样的猎奇式臆想下的迷幻性在《魔旦》中也有集中体现,西方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误解与猎奇心理使华人戏子形象显得越发扑朔迷离、荒诞神秘。中国戏子的性别在他们眼中完全错乱,在舞台上分明是舞动水袖的古典俏丽的东方女子,舞台下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国男孩,为此,他们仿佛入魔一般,神魂颠倒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戏子的神秘导致了西方人狂热的迷恋,最后演变为前辈阿三在众多美国男子眼下活活被烧死以及奥古斯特对“金山第一旦”——阿枚的痴情爱慕。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戏剧传统在西方观众看来却是荒诞神秘的迷阵,这一方面是猎奇化臆想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难以避免的异质文化误读。在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华人形象显得愈加古典神秘、充满吸引力。
从《扶桑》中具有谜样的微笑、温顺隐忍的女主角扶桑,到《魔旦》中阴柔美丽的戏子阿三、阿玫,这些华人形象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作为西方社会后殖民主义式的欣赏物而存在,是神秘的东方大陆在西方社会的替代品,完美地契合了西方对东方的幻想,具有东方主义幻想所衍生的迷幻特征。然而,也要看到这一系列华人形象的迷幻性背后,其本质是一种猎奇式的臆想和幻象,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误读。
这种臆想与社会文化语境有关,它对作家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严歌苓于1989年辞别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写作硕士学位。在美国,她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系统地对西方小说的创作理论展开学习,长期接受着西方写作的训练。久居异乡的经历使严歌苓不可避免地受到被东方主义笼罩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熏陶,尽管她作为“边缘人”并未完全被西方话语同化,但是随着她不断接受着西方的文化价值判断,小说中已经“充分地渗透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期待”。[3]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接受和一定程度的内化,使得她的小说隐晦地表现出对西方文化想象的某种认同与妥协。
严歌苓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东方主义的内在认同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自我东方主义”。高鸿在《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中这样解释:“‘自我东方主义’是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延伸性理解,主要是指具有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和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创作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4]由于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与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作家个人教育经历、新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身份均存在关联,其小说中具有一定“自我东方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华人形象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呈现的迷幻性特质。
二、“妖魔化”臆想下的华人形象
除猎奇式臆想下,华人被西方想象为奇幻神秘、充满吸引力的形象,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也体现了东方主义幻想有意将华人“妖魔化”,这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臆想,不可避免会导致对异质文化的误解。以《橙血》中的玛丽为例,她自认为自己是高雅文明的象征,白人在她眼中是高贵的,而华人属于低劣的种族,因此她一直拒绝将品种优良的橙子卖给华人。她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到了华人手中都会被大批量复制,从而得到淹没般的繁衍,但她害怕的不仅仅是极品橙子因数量增多而价值贬低,更重要的是,她希望优良的物种一直持有优越感,不被低劣的种族占有。这种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对华人形象的“妖魔化”和对“黄祸”的忧虑、恐惧,其中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实质上也揭露了西方社会将华人“妖魔化”的虚构性和欺骗性。
18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华人为题材的“黄祸”小说曾一度充斥于西方,与《扶桑》中的大勇类似的华人恶棍形象被不断复制粘贴,被强加上东方种族的所有丑陋。这些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最终在文学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将华人彻底丑化。西方对华人的“妖魔化”不仅仅限于对大勇等个别人物的偏见,可以说一度上升到了对整个民族的丑化和敌对。《扶桑》的时代背景正是在美国西海岸排华运动推进、“中国威胁论”盛行之际,在白人眼中,华人谜一样的温良、谦恭乃至面对恶劣工作环境和低廉报酬时的宽容忍耐都令他们无法理解,继而为之震怒,无端激起误解和仇恨。当污蔑和丑化成为气候,他们便集体将华人视为这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认为华人奴性的忍让和谦恭将抢去自己的工作机会,这样的人种会悄无声息地吞没一切。甚至在年幼的克里斯心里,这种思想也根深蒂固,他早就默认华人是一个藏污纳垢的低劣人种,认为“这些拖着辫子的人把人和畜的距离陡然缩小,把人的价值陡然降低。这些天生的奴隶使奴隶主们合情合理地复活了……”[5]由此可见,华人的忍让哲学在西方彻底失败,反而被视为一种侵略。
从玛丽眼中的华人到西方人眼中的大勇和华工,西方对华人形象的“妖魔化”从未停止,他们将华人视作奇幻而丑恶、荒诞又低劣的人种,是一种“黄祸”。然而,这些强加的迷幻性、这些关于“黄祸”的臆想是无根据的,仅仅是由于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对另一种族的偏见。
严歌苓作为新移民作家,显然也认识到了西方对东方“妖魔化”的虚幻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想要颠覆这种刻板印象和根深蒂固的思想,如《栗色头发》中的“我”勇敢拒绝白人的追求、《橙血》中的黄阿贤不甘被控制、《扶桑》中的大勇身藏飞镖保护华人的利益都在试图解构这种东方主义,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消除偏见,力图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华人形象。但是,由于她多数的小说面向美国读者发行,决定了她不可能完全解构东方主义,反而不自觉陷入了东方主义的樊笼。
三、极致化情境下的華人形象
严歌苓作为新移民代表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华人移民生活充满复杂敏感的人生体验,华人形象则被置于极致化的情境中充满了迷幻性。在她书写的海外移民故事中,众多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后,因空间、环境、文化的多重改变以及在文化上相对西方的异质性不得不在异国成为种族、语言、性别等方面的多重“他者”,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即使他们扫除了生活习惯差异、语言障碍甚至是文化隔阂,面对西方的种族歧视和霸权意识,也不可能被彻底认同,始终逃不掉沦为“他者”的命运。这就使得他们在社会中不断被边缘化,时常处于极致化的情境之中,因此在心理上趋向于孤独、无助,在行为上充满了谜一样的荒诞色彩,呈现出迷幻性特征。
严歌苓善于筹划文字,在书写异域生活时,经常将华人置于极致化情境中建构故事情节,使其形象呈现浓重的荒诞奇幻和神秘色彩,“她能穿透现实生活层面向人的心灵深处迸发,把目光更多投向被抛出常规的情感体验。”[6]《抢劫犯查理和我》中,“我”被查理抢劫时的心理和行为显得有些荒诞不经,感受到的竟然是他外表的古典美以及声音的诗意般的轻柔,当再次与他相遇时,“我”不仅没有告发他,反而与他约会,并且亲眼目睹了两次他抢劫别人的过程。更为荒诞的是,“我”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他,对他的爱成为“我”一生中最不见天日的一个秘密。在这种超出常规的情境建构之下,“我”的心理和行为既是荒诞的,又充满了谜一样的色彩,体现出形象的迷幻性。
《失眠人的艳遇》中的“我”更是如此,对“我”来说,被边缘化导致了孤独的生命体验,这种孤独不再局限于心理层面,更是蔓延到了生理层面。“我”带有几分荒诞的意味,本想逃离原先的生活处境,去一片新的天地追求梦想,却在异国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无数个漆黑的夜晚辗转难眠,陷入了近乎癫狂的清醒。“我”不甘心只有自己处于疯狂的孤独难眠中,便开始热切地寻找另一份孤独,终于在遥远地一座高楼上分析了同样的彻夜明亮的灯。原以为有了孤独的相伴者,但是那个“我”认为的同样的失眠者——一个从未出过门、没人认识的男人,最后自杀了。“‘我’每夜里守望的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于默契,也许是一种荒诞的、自恋式的误读;‘我’一直渴求的平等的、心意相通的对话对象,竟也是这个国家的边缘人,甚至是个‘不在者’。”[7]最终,谜底揭晓之后,这一切只不过是荒诞又迷离的错觉,而产生如此错觉的“我”亦是荒诞的。
边缘化境地是导致严歌苓小说中人物处于极致化情境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海外华人所处的边缘化境地是双重的边缘化,一是中国移民“寄居者”在美国的土地上艰难求生,面临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力蔓延和扩散,使得在这一时期处于边缘“他者”地位的华人移民面临着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和焦虑,即种族和自我认同的边缘化。严歌苓刻意书写海外移民社会中的边缘华人形象,背后隐藏的是她作为海外华人对自我文化的思考。正如姜智芹在《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所说:“随着当代形象学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转向对自我文化的确认,借助他者形象这面镜子认识自我是形象塑造者的一个重要动机,无论形象创造者对他者文化持肯定还是批判的态度,无论是从他者文化中去寻求差异性还是同一性,其结果都可能是对形象创造者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和补充。”[8]
四、结语
东方在西方人眼中,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古老神秘、落后愚昧又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充满了荒诞奇幻与神秘色彩并存的迷幻特征。然而,这种形象不具有真实性,无疑是西方以自己为中心对东方的一种幻想。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论著《东方学》中指出,西方眼中的东方并非真实的东方,“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作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9]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形象塑造的背后是西方的文化霸权,是西方的一套权力话语。严歌苓小说中的华人形象正体现出这种东方主义幻想及其带来的迷幻特质,在猎奇化臆想之下,华人被视为古老神秘、充满吸引力的古老东方的代表,而“妖魔化”臆想又将华人视作奇幻而丑恶、荒诞又低劣的人物。这两种臆想都是严歌苓对东方主义幻想的又一重想象,是她结合历史资料和生活经历对西方眼中华人形象的一种虚构和再想象,刻意捕捉并放大了人物形象中荒诞奇幻的特征,使得华人形象笼罩在迷幻的氛围之下。除了这种虚构和再想象外,极致化情境的建构也是导致华人形象呈现迷幻性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极端的、非常态的环境中,人物最深处的潜藏苏醒,从而暴露出谜一般的、荒诞而神秘的特质。
华人形象所呈现的迷幻特征背后,隐含着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对自我文化的思考,她一方面试图揭露东方主义幻想的欺骗性,颠覆西方的文化霸权,消除偏见;另一方面,她又对西方霸权话语有所接受甚至已经内化,使得小说中华人形象隐晦地表现出对西方文化想象的某种认同与妥协,不自觉陷入了东方主义的樊笼。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165.
[2][5]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1,120.
[3]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J].华文文学,2003(5):34-40,61.
[4]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M].上海:三联书店,2005:109.
[6]刘艳.严歌苓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93.
[7]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J].华文文学,2002(4):63-69.
[8]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2.
[9][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1.
作者简介:巫冰宇(2000-),女,四川泸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