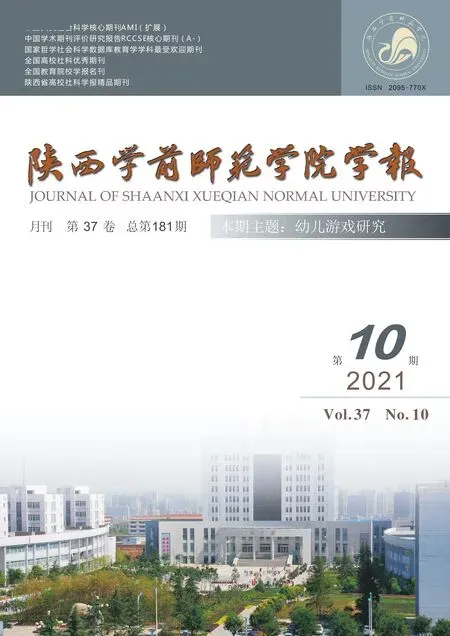关于儿童与游戏关系的再思考:从“游戏性”到“游戏力”再到“游戏的儿童”
2021-01-31胡福贞周雅君
胡福贞,周雅君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自有儿童开始便存在着儿童游戏,但游戏最初并不属于儿童。从游戏的本源来看,游戏到底是自主存在或是始于本能?游戏到底只是人性中的一种属性,旨在娱神娱己?还是一种教育与学习的工具路径?抑或甚至是游戏精神构成了人的本质?游戏同学习和劳动到底是一分为二还是交融互生?在发生学意义上看,游戏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但惟有人类的游戏能使人成为更好的人。从根本上说,游戏不仅是人的一种属性,更是儿童活动的基本特性。游戏活动是具体可感、受文化情况和资源等多种条件限制和规定的,但作为儿童精神世界的一个概念,“游戏”实则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代表着边界的超越、事实的反转、生命的自由和规则的突破。
一、长期以来儿童与游戏关系的二元悖论
(一)严肃与戏谑
文明之初,游戏被视为具有某种绝对性和神圣性的人类活动,它只代表神性的圆满绝对。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这样描述,“我以为人必须以严肃对待严肃的事,只有神才配最高的严肃。人被做成供神游戏的玩物,而那是人的最好的部分......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严肃的东西。尽管在战争中,游戏与文化——它们是我们认为最严肃的东西——都称不上严肃......生活必须作为游戏来过。玩游戏,做祭献,唱歌跳舞,这样,人才能抚慰神灵,才能免于敌人的侵犯并在竞争中获胜”[1]。可见,起初,游戏不属于“有限制的人”,更遑论尚未被发现的“儿童”。处于命运限制之中的人类以祭祀祈愿等游戏方式来娱神,从而摆脱厄运、获得佑护。群体游戏不单是关系到部族命运的大事,同时,游戏者亦有特定资格,是堪当部族家国重任、能与鬼神沟通的巫师圣者。
此后,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娱神”之大用的游戏仍在继续,同时,于劳作、争战之余的放松休闲里,游戏亦越来越多的蔚然成风。小到街头巷里的戏谑杂耍、田间地头的歌舞斗闹、闺阁庭院的斗花弄草,大到家庭大众的集体娱乐,特别是儿童世界的青梅竹马、玩泥巴、斗蛐蛐等,儿童世界的游戏日益增多,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源自成人、模仿成人游戏的玩法与器具,甚至有了专门为小儿制作的“小玩艺”如:风车、毽、鞠等;特别是在达官贵人之家,既看到了儿童玩耍、嬉戏的日常和正常视游戏性为儿童期的基本特征,认为婴幼儿期的本性“大抵童子之情,好玩、乐嬉戏而惮拘检”,允许、鼓励儿童嬉戏;但又视“嬉无益”,与学习、劳作对立,特别是7 岁以上的儿童游戏成为消极性发展意义的活动被否定和限制。此后经年,随着人们对儿童的认识逐渐科学化,日渐肯定了游戏之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游戏作为儿童的基本生存方式与教育的基本手段已被当下的人们普遍接受。但传统的惯习与现实的竞争尤其是教育学习压力的增大,关于“儿童与游戏的关系”便在严肃的娱神、认真的学习与戏谑的嘲讽、散漫的休闲张力中左右摇摆。
(二)边界与超越
在漫长的古代文明中,儿童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国家的后备军”“社会的生产力”,更多是受规训的“后来者”,或须接受既有社会的各种规定与边界,即使游戏被看到具有教育和学习功能后,成人们更多强调“教儿童游戏”或儿童只能玩规定的游戏作为社会教化,不容突破既有成规。游戏本是一种自主自发性的活动,却被严苛地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因此,作为儿童基本生活方式的游戏活动受制于特定教化功能,成为一种具有绝对约束力与控制力、有明显边界与规则的教化工具。
随着文明渐趋开化,教育者认识到“儿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的积极意义,故儿童游戏的创造性与超越性得到了积极回应。崔学古在《幼训》中明确指出了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而要进行儿童教育就需要充分尊重其身心自然发展规律,但不失教育性,绝不放任自流,工作中的儿童可以自主选择、自由活动,“大部分应该由儿童个别活动,由教师个别指导”[2]。儿童游戏是一个创造的世界,提供了超越现有存在方式的机会,儿童在这个世界中处于控制地位,游戏吸引儿童在于其自主性,是从意识世界里的边界到物质世界以外的自我超越。“儿童的游戏......对于世界是执著也是逃遁。他一方面要征服它,同时又要闪避它;它在这个世界上架起另一个世界来,使自己得到自己有能力的幻觉”[3],此时的现实世界、规则与束缚对于儿童来说早已消失,或置身之外,在游戏中的儿童,他们是具有无意识的超现实性。游戏便在适应儿童天性与传承社会规训的张力中不断增进儿童发展。假设在追逐游戏中,儿童在身体地积极参与中,不断通过协商和遵守规则维持着游戏,追逐过程带来的兴奋感同游戏规则提供的框架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点,这里可以体验各种情感,而没有“真实”世界中可能带来的后果。
(三)事功与精神
游戏所体现的事功与精神是指或偏执于特定的游戏目的,旨在要“玩出名堂”;或偏执于游戏的无目的性,强调不作准备,随意且散漫。自有文明开始便存在着游戏,其无论是娱神玩乐的方式,或是作为劳动生产工具的技能训练,亦或是如今作为儿童融身世界的交流方式,教师教学的辅助工具等,游戏都被视作依附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外在物质形式且具有特定功利性。当儿童游戏作为教学工具时,承载着特定教学目的,具有特定教化功能,是“将生命的体验与乐趣变为学习的目的与手段的一套工具和方法论”[4];是“通过设计、开发、管理合适的技术情景和资源,以促使学习者的生活体验与自身发展相融合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5]。所以便出现了“被游戏着的儿童”,过于重视游戏的工具性,甚至至于以“游戏力”来囊括儿童游戏的各个方面。
剖析游戏对于儿童生存、生活的实际价值,教育者发现了游戏有其自身合理化与合规律性的促进作用。杜威认为,“游戏不等于是儿童的外部活动。更确切地说,它是儿童精神态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标志。它是儿童全部能力、思想、以具体化的和令人满意的形式表现的身体运动、他自己的印象和兴趣等自由运用和相互作用”[6]。游戏也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精神性活动,在意识层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地,在这里,人们建构着他们自己的世界和周围人的世界,达成自身与周围世界的“神秘性统一”。人的最高本质与追求便是精神自由,当下人们不单重视游戏的功用特征,更强调彰显游戏精神,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游戏性精神是儿童精神特质最集中的反映和最充分的概括,游戏要求儿童具备“反事实”能力去构筑梦想世界和自由王国,德拉库尔解释道。儿童游戏便是超越日常劳苦抵达休闲幸福;超越能力局限抵达技能习得,进入精神忘我之境界。
儿童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既存在于物质世界,又有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因自身思维意识能力提高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儿童游戏不单是本能需求所推动或宗教仪式的化身,更不单是统治与教化的附庸,而是自发性与自觉性同被动、束缚与规训互为表里、共通共融,进而从认真到愉悦、从规则到自由,从物质存在到意识超越,实现游戏与儿童的关系指向共生与契合。
二、在时代变革中重新定位儿童与游戏
“前喻文化”“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人类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当代教育也随之呼唤变革。儿童游戏在个体发展与社会教化中的地位与性质亦随之变化。简单将游戏作为儿童社会活动之一,或是将其异化为教育工具,亦或是片面强调物质化游戏是当前将游戏纳入教育实践误区。为更准确把握儿童与游戏二者的关系,需要从作为儿童特质之一到作为教学路径再到作为儿童充分本质之一的有机结合,促进儿童从“被游戏”到“自主游戏”的主动转换。
(一)充分把握儿童游戏的丰富意蕴
现代人类的文化也已赋予了童年期以“游戏期”,认为“儿童的时代应该是游戏的时代”[7]。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它近乎本能、自发,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活动冲动、兴味与状态,儿童天生就是游戏者。游戏性是儿童通过游戏活动所体现的个人特质,其可以囊括儿童游戏的丰富意蕴;格瑞菲斯(Griffiths,1935)认为,游戏是童年期特有的活动类型,在这种活动中,儿童会形成对于周围环境的态度,这种以游戏活动为中介形成的态度会逐渐转变为个体的一种个性特征或品质,即“游戏性”[8]。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它就地取材,极富文化色彩,是从儿童自身兴趣出发,自愿选择游戏内容、方式与伙伴,自行制定游戏规则并随时改变,完全由儿童自身内驱力所控制,极少受制于成人或客观环境的约束,且在游戏中接受文化的规训与惩罚、传承与创新;正如胡伊青加所言,“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已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游戏的强制性摹仿”[9]。从心理学意义上看,它既是个体认知、情感与意志的囊括,又是集体无意识与群体关系的充分反映,儿童只有在游戏中才能完全称其为“儿童”,只有在游戏中才能看到其肆意解放与挥洒自我,只有在游戏中才能看到其性情的驰骋与潜力的释放,儿童游戏是因其自身而存在的活动,是为了能够享受做游戏时的快乐和喜悦而进行游戏;然而,游戏不仅仅是享乐,它对儿童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当然,若从文化学和政治学意义上我们也仍可以看到,儿童游戏既非附庸,亦非全然自创,它始终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儿童游戏是非功利性的,儿童游戏是单纯、毫无目的的,儿童游戏的目的就是为了愉悦心情、平衡心理、逃脱现实和宣泄情绪,可以说儿童游戏的目的就是游戏的本身;米舌莱指出:“游戏显然是一种无偿的活动,除了它本身带来的娱乐外,没有其他目的。”将童年视为成年的对立面这个角度看,儿童游戏作为一种发展机制,是形成成年生活所需技能的方式。如今教学异化现象仅仅看到游戏开发成为一项课程资源的表层现象,而未能触及游戏带给儿童的实在意蕴。体验性与虚幻性是儿童游戏的又一重要特质,游戏本身就是区别于现实生活的虚拟活动,儿童可以通过游戏感受其实际生活中面对的其他角色,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一切都是假想的状态下去实现生命的体验;西克森特米赫利普用英文单词“flow”(流畅、涌出等)一词来形容游戏中的情感体验,在游戏中,“在那一刻,自我、现实……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远远地遁去了,全副身心都被当前活动占据了……灵感迸发,思如泉涌”[10]。儿童在虚设的游戏空间里,书写着自身如诗一般的童年,幻想与创造也在其中尽情徜徉。
儿童游戏有其工具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从前者来看,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游戏是与儿童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学习方式,给以丰富的物体、形状、光线、色彩、言语等多方面的刺激以及频繁的互动交流,对幼儿的智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力、语言、意志、同理心、社会交往能力、心理健康、人格形成以及学业成就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1];游戏的本体性价值即是在哲学层面上认识到儿童与游戏的关系,促进儿童发展只是游戏的“副产品”,其真正价值在于满足儿童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即对自由的需要。近年来,游戏与幼儿园教学、课程之间的融合成为学前教育界的热点问题,二者间的有机整合也成为幼教改革的基本方向;随着教育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教师教学为中心”正逐步向“儿童自主为中心”迈进,时代对儿童游戏的急切呼唤,使得游戏从“与教学的二元对立”再到“教学游戏化”的有机融合,从儿童“被游戏”到“自主游戏”的主动转换是对当今社会所极力推崇的游戏化教学的呼应,在理论层面,“教学游戏化”“游戏化教学”“课程游戏化”等概念应运而生;在实践层面,各级各类幼儿园不断突破想象力的局限,拓展了传统幼儿园教育的边界。教学以教师为引导的基础上应尊重儿童的游戏自主、自发和自由性,在课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应珍视游戏融入教学活动的独特价值;在承载一定的教学目标与任务的同时发掘游戏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积极意义。让游戏成为儿童恣意遨游的场地,让游戏成为儿童生长的摇篮,让儿童在充满诗意的童年愉悦成长;充分把握儿童游戏的丰富意蕴是将其游戏性纳为儿童特质的一部分,也是游戏与儿童生命的契合。
(二)充分彰显儿童的游戏兴味和精神
儿童的时代就是游戏的时代,儿童本质上是天生的游戏人。福禄贝尔曾论述道:“(儿童)游戏是内在本质的自发表现,是内在本质出于其本身的必要性和需要的外向表现……所以游戏给人以欢乐、自由、满足,内部和外部的平静,同周围世界的和平相处。一切善的根源在于它、来自它、产生于它。[12]”儿童游戏是受自身需求所指、兴趣所使、天性所引,是其内在本质最真实的显现;无论是早期儿童游戏经典理论中的预演说、本能说或是剩余精力说,都例证了儿童游戏原生性与自发性的本质特征。游戏存在形式有二,其一为外化于物质活动的行为层面的游戏,其二为内隐于心理、非显像性的精神层面的游戏;片面、单一地理解二者,割裂了儿童游戏内涵的整体性与生成性。在现实生活中,仅仅将游戏作为为教育教学目的服务的手段,作为课程开展与实施的基本路径,作为课前儿童兴趣的兴奋剂是对游戏精神的漠视、压抑。事实上,游戏精神是儿童游戏的灵魂与精髓所在,是儿童在其一日活动中所体现的自由自主无目的性,积极主动性,真实体验性以及开放生成性[13]。杜威曾意识到游戏的精神远比其活动形式本身更具有教育价值。他说:“游戏的态度比游戏本身更重要,前者是心智的态度,后者是这一态度的现时的外部表现。[14]”毫无疑问,游戏活动成为儿童生活所指,成为儿童现实中难于表达、羞于言说的基本活动形式,游戏精神成为儿童全身心沉浸其中的动力和支柱;因此,“无论他是游戏着,工作着,还是进行着其它活动,往往都会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和心境来行事,以游戏的精神来观照外物和自己的活动”[15]。儿童那种浪漫主义的童话意识、天马行空的奇思怪想、轻松自在的玩笑幽默、泛灵主义的物理观念、荒诞不经的酒神逻辑、毫无掩饰的爱恨情仇、无拘无束的活泼天性等,都可看作是游戏精神在幼年时期的呈现[16]。不可否认,儿童生活的状态投射着其游戏精神;反之,游戏精神携带着儿童原发性的兴味,伴随社会文化的熏陶,以生成整体性的样态不断丰富儿童的生活。
在幼儿园的具体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误区,将儿童游戏的“形”“神”分离,不少教师在观念上仍有重上课轻游戏的倾向,或是重知识、重记忆、重纪律而轻过程、轻体验,或是有游戏无教学,即儿童游戏与教学“两张皮”。简单来说,前者只看到游戏的工具性属性,仅将其作为儿童发展的附着;后者过于强调游戏的重要性,甚至谈“教”色变,把游戏等同于自由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无计划的活动。儿童游戏的兴味与其游戏精神相辅相成,与其自身身心发展水平的个体性差异与特征共同决定了工厂式教学的弊端;“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将儿童游戏的“形”与“神”合而为一,既遵循儿童游戏天性,又认识到儿童作为学习与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创设宽松、迎合儿童兴趣的半结构性环境,保证足够的游戏时间,减少过渡干预与指导;既是对儿童游戏精神的重视,又是将儿童视为独立个体存在于周遭,需要通过自主性游戏适应社会并获得有效发展的强调。
(三)切实发挥游戏的育人功能
儿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然群体,有其自身规律的生理构造,系统的感知世界的方式,独特的行为活动,完整的语言表达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征,有其独特的生存文化与存在形式。就如生物学家格鲁司(K.Gross)所坚持的,不能仅仅认为是因为儿童的年幼,儿童才游戏,也应看到儿童是因为游戏,他才被赐予童年的生活[17]。因此,儿童正是通过游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意义并与世界交融。研究表明,早期儿童游戏对创造力起关键作用;利伯曼(Lieberman,1965)对93 名幼儿做了调查研究,发现游戏性与创造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游戏性越强的孩子,在发散性思维的测查中得分越高。游戏中宽松自由的氛围,为儿童创造了一个自在的天堂,抛开现实生活中重重规则的束缚,拥有自主权的儿童在游戏中尽情挥洒创造与想象,释放无穷的能量与精神。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维果茨基指出,游戏能够创造学前儿童的“最近发展区”,皮亚杰也根据儿童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提出了关于儿童游戏发展的三阶段:感知运动游戏、象征性游戏以及规则性游戏,儿童在求知欲和好奇心的趋势下,与外部环境、他人相互影响,不断探索与挖掘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世界,就像马斯洛和罗伊德写到的:“儿童早期是奠定智力发展的基础的令人兴奋的、有效的时期。游戏的过程正是智力发生的非同一般的、特殊的过程,这恰恰是游戏的作用之所在。[18]”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已充分证明,游戏是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活动,游戏场域中的儿童,其身心各方面的存在与发展充分彰显出儿童个性与社会性发展的一体化。游戏作为儿童与他人开始交往的起点,对于儿童社交能力、言语发展以及社会性提升有积极作用,儿童能够在游戏中逐渐克服“自我中心取向”,区分“他人”与“自我”的实在关系,学会运用自制的游戏规则约束自己与同伴;美国学者帕顿曾根据儿童在游戏中社会行为的发展,将儿童的游戏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独自游戏、平行游戏、联合游戏、合作游戏,从二者的关联与发展中也可以看出,儿童游戏行为的发展与其社会性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统一的[19]。
近现代学前教育社会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游戏的教化作用、切实实现幼教机构的价值始终是其基本主题。肇始于福禄贝尔的“儿童乐园”,到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到我国学前教育机构“蒙养院”的正式诞生,再从“蒙养园”到陈鹤琴先生创办的“鼓楼幼稚园”;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之内,游戏是儿童学习的基本方式已成为共识。《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作为我国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规,首次以法律成文的形式指出游戏为蒙养院保育教导四条目之首,也正是在文明渐趋开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看到了游戏之于儿童成长的有效价值;在《幼稚园课程标准》中提到,游戏包括发展身体的游戏、发展社交的游戏、发展言语的游戏等五种类型[20],鹤琴认识到游戏对儿童身体、社交等的促进。日本继对学前教育进行了健康、人际关系、环境、语言与表现五个领域的划分后,于《幼儿园教育要领》中体现出上述五个领域都应通过每日游戏来实现其教育目标,并强调教师要以游戏活动为中心进行指导,通过游戏和生活体验为儿童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奠基。英国作为最早为维护儿童权益进行立法的现代化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对儿童游戏权益也进行保护。《儿童权利公约》从保护、参与以及提供三个类别表明儿童能够通过游戏创造其自我保护,进而融入外界逐步社会化;儿童游戏提供了促进适应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可能性,脑科学研究表明,游戏效应的经验能够转化到与情绪、动机和回报有关的大脑系统中去,有利于提升儿童的积极体验(快乐和享受;情绪调节;学习和创造等);游戏作为儿童主要的参与方式与其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儿童在参与日常任务、工作和教育的同时进行游戏;提供权不仅仅意味着为儿童供应丰富的游戏设施并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它要求更广泛地考虑儿童权利以确保社会和物理环境能够支持儿童的游戏能力。
“游戏力”一词是当代应势而生的一个概念,强调游戏并非只是“玩得开心”更要“玩得有意义”,要通过特定的环境、装备与条件创造,使得游戏场同时也是学习场。源自科恩的“游戏力”致力于强调游戏者的心理联结,突出成人与儿童亲密关系下的游戏况味,而不是研究者将其推演至一种学习力,是每个活动者能自主自发参与其中、乐在其中的活动能力。尤其在当下教育游戏软件和人工智能冲击下的教育虚拟世界中,教育的游戏性或通过“游戏力”挖掘儿童游戏的育人价值,且与教育现代化推崇的“全人教育”相耦合,全人教育中的“全人”是指“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他们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人认知的方式行事”[21]。成人应该意识到儿童游戏的重要意义,尊重并保护儿童的游戏权利,任何促进儿童游戏的干预都必须承认其自身的特点,确保物理和社会环境有益于儿童的游戏,正确认识儿童游戏的性质与价值,避免把游戏视为无聊活动而不屑一顾的诱惑,避免因为恐惧游戏而限制游戏和儿童,避免为了更加工具性的目的而控制和喜欢游戏[22]。有关专家认为,全人教育致力于受教育者个人的认知与情感水平的最大提高,充分发挥个人的所有能力,使其走向理想的“全人”目标。这个目标具有“终极性”[23]。教师、父母等作为儿童教育的引路人,应保证儿童有适宜的机会与充足的时间进行游戏活动,并充分的信任,适当时机给予一定的干预与指导,相信儿童可以在游戏中实现其自身认知、身心、社会性等全面和谐发展。
从游戏最初作为限制在儿童之外的人类教化工具到被专门与儿童学习对立或是单一理解为教学辅助工具,当今时代如何重新探讨游戏与儿童的和合共生关系,真正成为儿童基本属性、切实能力以及本质特征是解决当下游戏异化困境的基础和本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