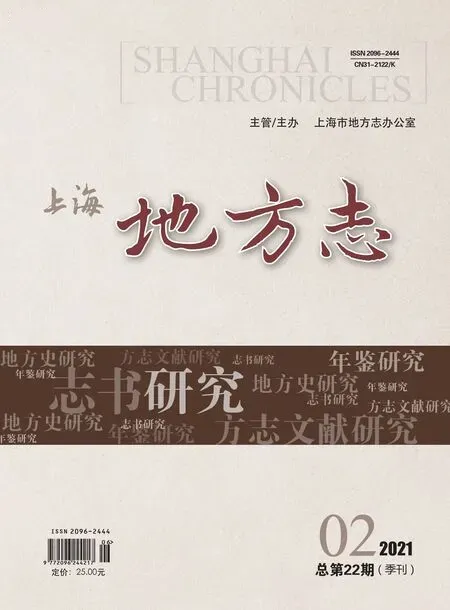中晚明时期名士陆树声禁奢思想探析
——以《乡会公约》为中心
2021-01-31刘鲜鲜
刘鲜鲜
风俗历来受到士人的关注,奢侈之风更是向来受到士人的重视,明代士人亦是如此。明代士人对待奢侈之风的态度可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从时间上看,相比于明初文献中对崇尚节俭的描述,明代中晚期尤其是万历及以后更多是对奢侈之风的忧虑。从地域上看,江南地区的奢侈之风在全国尤甚。而位于江南地区的松江府华亭县则是明清时期上海士人们活动最为活跃、最受人关注的地区。①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第13页。《乡会公约》便产生于明代奢侈风气较为严重的万历年间,而撰者陆树声(1509—1605年)亦是松江府华亭县人。②查阅地方志可知因明代松江府建制变动,陆树声后亦被认为青浦县人,但据[明]何三畏《云间志略》、[清]张廷玉《明史》等,可确定陆树声万历间生活在松江府所辖的区域无疑,故本文称其为华亭县人。目前学界对陆树声的专题研究较少,陆树声多作为例证出现在其他研究中,而专题研究也多集中在生平、文学成就、闲退思想方面。③陆树声作为例证的研究可分为五个方面:(一)制度方面,主要以陆树声与同窗能否留任翰林院为例,考察明代庶吉士制度,如董倩:《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社科纵横》1996年第4期;另其弟陆树德因兄长陆树声而改任他职的例子也为学者研究明代回避?制度提供依据,如杨华文:《明朝回避制度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二)文学作品方面,主要考察明代小品文的特点、文体以及自传文。如罗筠筠:《禅悦士风与晚明小品》,《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徐燕:《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苏娟:《中晚明自传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三)区域方面,主要考察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望族情况。如吴仁安:《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陈宝良:《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四)明代人物方面,主要在考察明代松江府华亭县的重要人物时,提及与陆树声的交往情况。如朱天曙:《“董陆因缘”考》,《中国书画》2005年第6期;李菁:《晚明文人陈继儒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五)社会生活方面,主要考察了明代的茶人集团、上海地区的私家园林、玩物与审美心态等。如吴智和:《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刘新静:《上海地区明代私家园林》,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3年;李玉芝:《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理论与现代化》2015年第5期。关于陆树声的专题研究:(一)生平方面,借助陆树声的画像赞等史料对其生平进行勾勒。毛文芳:《明代陆树声之画像自题析论》,廖可斌主编:《2006明代文学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二)文学成就方面,对陆树声的部分小说、诗歌、散文等进行研究。如康燕燕:《陆树声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王辛茹:《陆树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三)闲退思想方面,这是目前可见从历史领域对陆树声的闲退思想与其一生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张清逸:《陆树声(1509—1605)的闲退思想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国立”中央大学2016年。关于明代人“奢靡”概念的研究,如钞晓鸿从地方志入手,对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做了较详细的分类,颇有参考价值。①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士人的禁奢思想的研究,如陈彩云认为明清江南士绅的禁奢思想表现在上行下效与调和礼俗两方面,并从士绅间订立条约来相互约束、家训族规中强调禁奢复礼、乡约组织的风俗教化分析士人的禁奢实践。②陈彩云:《礼与俗的对抗——明清时期(1500—1800)江南地区的禁奢思想及其实践》,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6年。另外亦有对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崇奢思想的研究,常以对陆楫的崇奢思想进行研究,如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西安,1993年8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1994年。总的来看,对明代士人及江南士人禁奢思想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本文以陆树声的《乡会公约》为中心,结合相关笔记小说、时人文集等,探讨以陆树声为代表的中晚明江南士人在禁奢上的所思所想。
一、《乡会公约》撰写缘由及性质
陆树声(1509—1605年),字与吉,松江华亭人,学者尊称为平泉先生。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屡辞屡召。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94—5695页。最终在万历元年(1573年)辞去礼部尚书一职,归隐乡里,长期居住家乡华亭县约达三十二年之久。陆树声所著书存世的有《陆学士杂著》《善俗裨议》《乡会公约》《陆氏家训》及诗文集若干卷。④[明]何三畏:《云间志略》卷十三,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3编·第4辑》,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946页。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其子陆彦章(约1569—?)将存世著述刊行,即《陆文定公集》二十六卷,《乡会公约》便收录其中。⑤因《陆文定公集》二十六卷,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华亭陆氏家刊本收录的《乡会公约》或有内容错误之嫌,本文所用《乡会公约》版本为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的明万历间原刊本《乡会公约》一卷,特此说明。又陆彦章在《陆文定公集》卷末提及刊行内容,其中收录的《陆学士杂著》十种系陆树声生前手裒梓行。《乡会公约》作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即陆树声辞官还乡后。⑥[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5页。陆树声在《乡会公约》的开头部分便说明了撰写原因:一是近来乡郡人情往来时竞相追逐奢侈浮华之风,陆树声及同乡缙绅士友对此深感忧虑;二是距离松江府较近的南京刻版印行有益世道风俗之书,并对挽救世风产生一定影响。⑦[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1页。基于以上原因,陆树声便撰写了《乡会公约》,以期革除奢靡之风。
《乡会公约》应是以陆树声为代表的松江士人,在松江百姓尤其是士人之间约定禁奢的条例,且具有一定的乡约性质。学界对“乡约”概念的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如杨开道认为“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既包括约文也包括相当的组织。⑧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页。董建辉则认为“乡约”中包含着一定的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的维系才得以形成一种组织。⑨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常建华则把“乡约”定义为一种制度,且认为广义的制度指的是以里甲特别是里社为基础,结合社学、乡饮等制度,设立里老与旌善、申明二亭,以调节民间纠纷、实施教化为特征,而狭义的则是指设立约正宣讲六谕。⑩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朱鸿林认为“乡约”是一种有成文条款规范的地方基层自治制度,各地的乡约具有基本的共性和鲜明的特色,而且“乡约”的实施包括具体实施过和制定却未必实施的情况。⑪朱鸿林:《一道德,同风俗——乡约的理想与实践》,《读书》2016年第10期。可见,“乡约”可以指约文、组织或制度,而从目前所见史料,《乡会公约》更多是指“约文”。明代中后期的乡约往往还带有家训的意味,如成书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前后的《文雅社约》,便是曾任礼部尚书(任职自万历十二年)的沈鲤(1531—1615年)致仕后与同乡之人欲挽救风俗的社约,已有研究指出,《文雅社约》是具有乡约性质且欲成为各家各族的规训的社约。①陈时龙:《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清代亦有此种现象,著名理学家李光地(1642—1718年)为当地乡族规定的《同里公约》,不仅收录在其文集《榕村别集》,还收录在安溪湖头《李氏族谱》。②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乡会公约》也收录在陆树声的文集中,更明确地具有家训的性质。对于其具有的家训性质将在下文“陆树声禁奢思想的特点”进行论述。“乡约”的倡导者可以是地方官或士绅,但乡约的推行往往需要借助地方士绅的努力。从陆树声指出“每与缙绅士友谈及”“与同郡诸公约而行之”等③[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1页。,可知《乡会公约》更多是松郡士人倡导的,且为陆树声个人撰写的,兼具乡约与家训性质的条例。
二、《乡会公约》的内容
《乡会公约》的条例内容均是针对松郡的侈靡之风而提出的,主要从人际往来中名帖使用、投刺之风,宾主相见之礼,服饰穿着等方面做出规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以陆树声为代表的松江士人革靡从简的态度。
(一)名帖使用宜俭
《乡会公约》首先对人们拜谒结交时,用来通报姓名的门刺(即今天所谓的名片,明清时亦称名帖)进行了规定:在寻常的人情往来中,不论行辈先后,仅用单幅白帖。只有燕会、婚礼中的请期和时节庆贺时,才能使用全帖红签,而红帖只用在婚姻、嘉礼以及郡县官员刚上任时。陆树声对名帖的规定正是针对万历间名帖使用日趋奢侈的现状而提出的。
自汉以来,名帖已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明清时期更是盛行的交际工具,而且种类繁多。④王晓雷:《中国古代名刺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第6—38页。而使用的种类不同其代表的含义也不同。明代使用的名帖有红、白帖之分,又有单、全帖之别。红纸制成的称为“红帖”,白纸制成的称为“白帖”。单幅的称为“单帖”,横阔十倍于单帖并折为十面的称为“全帖”。按惯例,初次拜见时用红帖,以后便用白帖,遇到喜庆、节日,又要用红帖。遇到重大喜庆时则用全帖。⑤金良年:《姓名与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据《明文海》记载,单帖用于同辈间的相互拜访,京城大官只有在第一次交往时才用全帖,以后就改用单帖。遇到吉庆时,则用单红帖。⑥[明]蒋德璟:《笋江社申宁俭说》,载[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一〇九《说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80—1081页。转引自: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可见,全帖、红帖均表达恭敬、重大之意,但人情往来中的名帖却因时人追逐奢侈等而改变了以前交往的内涵。据明代学者皇甫录(1470—1540年)《近峰闻略》,“(正德初)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⑦[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三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7页。可知,名帖用红纸始于正德年间,且价格高于白纸,但人际交往中用价格昂贵的红纸似较流行。
嘉靖间士大夫使用的名帖还较为朴素,万历时使用较奢侈的红帖已较为流行。浙江人郎瑛(1487—约1566年)曾回忆少年时见到公卿交往所用刺纸多为白录纸,偶尔见到一二苏笺,已经感到奇异了。如今用纸不是“白录罗纹笺”,就是“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还要用“绵纸封袋”。这样的名帖上下通行,不用反而被认为是“不敬”。名帖上虽仅有五字,而“用纸当三厘之价”,可谓极其奢侈。①[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页。嘉兴人李乐(1532—1618年)也曾指出,嘉靖三十四年时官员上任只用白帖,不轻易用红帖。而“近来(万历间)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②[明]李乐:《见闻杂纪》卷二,“六十六”条,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188—189页。而且闽中士大夫在新官上任时,不论尊卑,均将“拜帖俱用大红”当成作贺的简约妙法,而且模仿此法的不易得罪人。③[明]李乐:《见闻杂纪》卷三,“九十四”条,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215页。使用红帖不仅是奢侈的表现,往往还存有僭越之意。清初松江人叶梦珠(1623—?)曾提到,以前松江平辈间的庆贺往来,只有新喜才用单红全柬,单红单帖仅京官才可使用。而同乡一孝廉在顺天乡试中举后,因用单红单帖拜客,便被人嘲讽为奢僭。直到崇祯末年,犹存此风。④[清]叶梦珠著,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明万历间永嘉学者姜准指出,名帖使用昂贵的红纸之风虽始于“京师勋戚之家”,官府小吏中即使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人,也纷纷跟风效仿,且“虽迩日变用折简,制遵复古,然红纸之用,未始因之除省,盖亦徒然而已!”⑤[明]姜准著,蔡克骄点校:《岐海琐谈》卷七《名刺用纸渐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姜准明确指出在人际交往中改用折简的方法,虽说明奢靡之风得到一定限制,但使用红纸的风气却未改变,也说明时人追求奢靡风气之盛。可知,名帖使用中的奢侈之风在万历间是较为广泛且较为严重的,《乡会公约》中第一条便对名帖使用宜俭做出规定亦可见陆树声的重视程度。
名帖使用时存在的奢侈之风也多为时人谈及。曾任福建巡抚的庞尚鹏(1524—1580年)在万历初年撰写的家训中,曾将“亲友往来,拜帖、礼帖、请帖、谢帖俱单柬,不用封筒”作为严禁奢靡的条例之一。⑥[明]庞尚鹏:《庞氏家训》“禁奢靡”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郭应聘(1520—1586年)在《兵部倡议崇质约言》指出,按照旧例,当地官差迎接新官到任、欢送官员升任以及其他祝贺事项多用红笺,他则倡议“今后俱用白柬,不宜参差。寻常往来,止投单红帖”⑦[明]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卷十五《兵部倡议崇质约言》,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可见,倡导禁止名帖使用中的奢靡之风,不仅是以陆树声为代表的松江乡郡士大夫的愿望,更是其他人对家人、官员的期望。
(二)投刺宜达情
相对于名帖使用宜简朴而言,陆树声指出投刺(即人际交往)应以表达情意为主。进而做出了以下规定:人们之间相互拜访的目的“主于叙情,亦藉以考问德业”,如果只是依照往例而频繁投刺得交往则不应提倡,并且约定“非有面谈属议不相拜访,亦不必答拜”,对于酬谢类的应酬也应罢除。⑧[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2页。
这种惯例式的投刺交往,宋代已有,明代更盛。太仓人陆容(1436—1494年)曾指出:京师的朝官在拜年时,不管相识与否,都要投帖。而这种只投刺、不拜访或者让他人代替送帖的现象在天顺(1457—1464年)以后较为普遍。直隶人张泰(1436—1480年)曾有诗批评这种投刺之风:“一刺来投一刺还,交情一日遍长安。直须不作虚文事,可使离群出世间。”⑨[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六,《丛书集成续编》第95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854页。华亭人何良俊(1506—1573年)以亲身经历指出循例拜客时的反常心情:“余以为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⑩[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页。转引自樊庆彦:《古代名片与明清社交》,《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可见,按照惯例的投刺拜客更多地为“虚礼”,显然不符合人们沟通感情的初衷。同时,陆树声还指出人情往来中的馈赠应以表达真挚的情谊为主,不应追求馈赠之物的薄厚。可见,相比于人情往来中的循例拜访、馈赠之物的外在形式,陆树声更看重表达人与人之间诚挚情谊的实质内容。
(三)主宾相见俱常礼
对于主人接见宾客时的礼节,《乡会公约》中也做出了规定:即平辈、身份地位相同的人仅行两拜的拜礼,只有卑幼尊长礼才行四拜的拜礼,而且在作揖谦让、举手时均不得过膝。表面上看,此条是对近来宾客相见时行“四拜”礼的纠正,实际上则反映了明中晚期宾客相见时尊卑失序、礼节繁琐的现象。据《大明会典》记载,明初规定民间士庶相见时,只有“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师范,奴婢见家长”,久别才“行四拜礼”,寻常近别只需“行揖礼”;对于其余亲戚,则“长幼照依等第”,久别“行两拜礼”,寻常近别“行揖礼”;平辈交往亦如此。①[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五十九《礼部十七》“庶人礼”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1015页。可知,明初的相见礼对尊卑极其重视。郭应聘亦曾指出四拜之礼“繁且过”,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过于繁琐且有碍传达情谊。②[明]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卷十三《会议仪节》,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陆树声强调宾、主相见时行恰当的礼节确是对当时浮华之风的纠正。
(四)服饰穿着宜简且真
《乡会公约》规定寻常往来时的穿着形式,即“不用冠带,约止常服或忠静巾服”③[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3页。。相比于《朱子家礼》主要从避免繁文缛节角度对丧葬服制进行了规定,明初更多从尊卑等级上对各类人群的衣冠服饰样式做出了严格的法令规定,但法令在明中后期则受到严重的冲击。此约定更多是从提倡简约、真率角度对士、庶服饰穿着尤其是士人做出的规定。
陆树声所谓的忠静巾源自忠静冠,忠静冠是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颁行的文武官闲居时所戴之冠,推行忠静冠的目的之一就是区别尊卑等级,很快受到士人的推崇与效仿,出现了一种类似忠静冠的巾式。嘉靖间人余永麟曾详细记载此事:“(世宗)制为忠静冠服,第其品职以别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迩来,又有一等巾,样以绸绢为质,界以蓝线绳,似忠静巾制度,而易名曰‘凌云巾’,虽商贩白丁亦有戴此者。”④[明]余永麟:《北窗琐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对于士人佩戴忠静巾的行为,朝廷一再明令禁止,“嘉靖二十二年,礼部言士子冠服诡异,有凌云等巾,甚乖礼制,诏所司禁之。万历二年,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静冠巾、锦绮镶履及张伞盖、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⑤[清]张廷玉:《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9页。此种现象并未得到较大改善。陆树声曾于万历初担任礼部尚书一职,对士人不应佩戴忠静巾的规定应较清楚。但他却倡议寻常往来可着忠静巾服,一方面可以说明忠静巾服在士人中间的盛行,另一方面应是华亭人范濂(1540—?)所谓的“习俗移人,贤者不免”⑥[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0页。。陆树声进一步指出提倡穿着忠静巾服的原因在于,既适用于接见客人的特殊场合,也适用于闲居在家的一般场合,这样就免去了“脱着拘窘之劳”,而且“近真率”。⑦[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3页。其实据范濂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云间据目抄》所载,此时松江地区的士人、平民等在巾帽、衣服上,不仅追求样式多样、新奇,更是极力追求奢侈的。⑧参见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第122—124页。而陆树声认为服饰穿着应遵循简便且体现人的真性情的原则,未尝不是对当时穿着上追求奢靡的反对,而他提倡穿常服或忠静巾服,亦或体现了对当时世风的一种妥协与折中的态度,而这更利于士人与平民接受并遵行。除此之外,陆树声还对特定时节的宴饮会聚上所摆列的果品、菜肴等的种类、数量进行了规定,总的原则是不应浪费、提倡节俭。
值得注意的是,陆树声与同乡徐阶(1503—1583年)、莫如忠(1509—1589年)、夏时(1514—1581年)、董传策(1530—1579年)在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间成立了讲习之会。①徐阶,字子升,号少湖、存斋,松江华亭人,曾官至首辅,隆庆二年(1568年)隐退归乡;董传策,字原汉,号幼海,上海人,曾任南京礼部侍郎,万历元年(1573年)被弹劾而被免官归乡,《明史·董传策传》记载董传策为松江府华亭县人,徐阶在为董传策所做的墓志铭中指出“其(即董传策)先自汴徙上海之竹岡”知董传策应为上海人;莫如忠,字子良,号中江,华亭人,曾任浙江布政使,约在隆庆三年致仕;夏时,字人正,别号阳衢,华亭人,曾任户科给事中,隆庆二年以疾归乡;陆树声在万历元年十二月归乡。故知讲习之会成立时间应在万历元年以后。而徐阶在给王畿作传时曾指出“……君(王畿)年八十犹不废出游……君顷过松,举卫武公事勖予毋以老自怠。予因联陆宗伯平泉数君为会讲习焉……”(见[明]徐阶:《世经堂续集》卷十《南京武选司郎中龙溪王君传》,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84页)。按徐阶所言,王畿最晚应在万历六年(1578年)年前后与他谈过建会一事。又因为王畿是在“夏五月”(见[明]徐阶:《世经堂续集》卷八《同志卷引》,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71页)拜访徐阶时提出联以成会的建议,再根据四人生卒,可知建会时间应不早于万历二年,最迟应在万历六年前后,但不晚于万历七年。徐阶在《同志卷引》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五人建会的缘起、目的、会约内容等。②世经堂续集》收录了《同志卷引》一文,据“《世经堂续集》者,太师徐文贞公归老东山之所作,厥孙肇惠君之所编次”知,《世经堂续集》中收录的文章均为徐阶自隆庆二年致仕至万历十一年去世期间所作。(见[明]徐阶:《世经堂续集》卷首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3册,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643页,因缺页故不能断定作序者为何人。参见姜德成:《徐阶与嘉隆政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兹录如下:
子(即徐阶)郡人平泉陆公、中江莫公、阳衢夏公、幼海董公,其所造诣皆卓然异于时流者也。如联以为会,月再举焉,交儆夹持之益岂少哉……予之老也,各为卷藏于家以寓戒,而属予引其端,且相勖志之成会约。
一、今举会,惟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自求有益。并不得谈朝廷政事、有司长短及乡人罪恶,违者众共责之。
一、会期以每月初八日、二十五日,巳而至,未而归。
一、会无定处,但随所便。
一、会日止具忠静冠服,一应礼节俱从简省。
一、会食止用水果二色,肴四品,添换腥、素各二味,点心二道,酒七行。饮毕,具汤饭而起食之,所余即以犒从者,不为另设,亦不与酒。③[明]徐阶:《世经堂续集》卷八《同志卷引》,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44册,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71—72页。
会约对谈论的内容做出了规定,即互相勉励德行与功业,规劝过失;随后又对会期、会所、会日穿着和礼节、会食做出了规定。从会约规定的内容可见其并不崇尚繁文缛节。万历十七年(1589年),其余四人均已离开人世,而从陆树声所做的《乡会公约》中对禁奢的要求仍可看出其与《同志卷引》中会约内容规定之相似。《乡会公约》应是以陆树声为代表的生活在中晚明时期的五位松江士人对家乡风气的忧虑及所做之努力。
三、陆树声禁奢思想的特点
《乡会公约》对人际往来中名帖使用、投刺,宾主相见之礼,服饰穿着等方面的规定均是由革靡从俭的总原则出发的,体现了陆树声的禁奢思想具有不满繁文缛节、重视真情,但不反对常礼的特点。
(一)不满繁文缛节,重视真情
陆树声对繁文缛节往往是不赞成的,如对于人情往来时投刺之风,如果仅仅为了答拜、酬谢,而且对于“其他亲递请帖及谢劳、谢酒之类,尤系烦劳”,这些在他看来是繁琐的礼节是希望能够罢除的。①[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3页。对于提倡穿常服或者忠静巾服,原因之一便是这样的穿着适用于多种场合,避免了局促窘迫的脱着之劳。
除了对于繁文缛节的不满,陆树声更看重的是真情。《乡会公约》中多次提到“情”在人际往来中的重要性。如在人与人彼此往来拜访之时“主于叙情”,而不是为了遵循故套的往来;在服饰穿着上,对忠静巾服或常服的提倡原因之一便是“近真率”;在人际交往馈赠时,更是对馈赠之物做出详细规定,且认为馈赠时是“主于达情”的,且主张“物薄情厚”。②[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3—4页。可见,陆树声的禁奢思想中是较重视真情的。
陆树声虽然不满繁文缛节,但是他不反对常礼的。《乡会公约》中几乎每条都指出条约适用于“寻常往来”,而且常常指出一般、特殊时节有一定的礼仪规范。如“宾至主人接见俱有常礼”“岁时燕会礼不能无”等。③[明]陆树声:《乡会公约》,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第3页。
(二)禁奢思想与乡约、家训形式结合
陆树声禁奢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其思想与乡约、家训的形式结合。前文已提到《乡会公约》为具有“乡约”性质的条例。同时,由《乡会公约》的撰写缘由可知,《乡会公约》不仅代表陆树声个人的禁奢思想,还代表着乡郡士人对禁奢的看法,而且《乡会公约》中对禁奢的具体规定是结合了乡人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可见陆树声将自己的禁奢思想与乡人的观念、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乡约”这一形式展现出来,为禁奢思想最大范围地为乡人知晓、认同、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陆树声除了通过“乡约”这一形式表达自己的禁奢思想,在所作的家训中也对其进行了强调。他在家训中指出:“宾、婚、丧、祭,当一依礼制。及称家有无,不可狥俗趋时,奢靡越礼。其详已著乡会约、善俗议中。”④[明]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二三《陆氏家训》,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华亭陆氏家刊本。“乡会约”即《乡会公约》,“善俗议”即《善俗裨议》,是陆树声应松郡官员之意从宾、婚、丧、祭礼方面对奢靡风俗作出的规定。⑤[明]陆树声:《善俗裨议》,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因《善俗裨议》或也存在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华亭陆氏家刊本错乱之嫌,故采用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原刊本。因本文以《乡会公约》为中心探讨陆树声的禁奢思想,故简要提及《善俗裨议》。《善俗裨议》从宾、婚、丧、祭礼方面出发,主张应革靡从简,对于繁琐的仪文应当去除,但应遵循常礼,大致与本文论述的陆树声禁奢思想上“不满繁文缛节,重视真情,但不反对常礼”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样一来,《乡会公约》就由之前“乡约”的性质而兼具了“家训”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子孙后代应如何禁奢,陆树声在家训中并没有大加论述,而是仅仅说在《乡会公约》中已经论述很详细了。《乡会公约》的原文并没有出现在家训中,陆树声在家训中也没有对禁奢做进一步的说明。陆树声此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会公约》或较通俗易懂,易于理解。亦可能是乡约与家训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⑥陈时龙:《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第140—142页。但陆树声主动将《乡会公约》纳入家训中,可见他认为《乡会公约》确切表达了自己的禁奢思想,亦可见对《乡会公约》的重视程度之高。
总之,陆树声的禁奢思想,体现了他对繁文缛节的不满,对真情的重视和对常礼遵从的特点。而结合乡约、家训的形式来展现其禁奢思想,则体现了陆树声期望禁奢思想能得到认可与推行。明代藏书家祁承爜(1563—1628年)将《乡会公约》列在“史部·礼乐·家礼”类,可知《乡会公约》对当时士人产生的影响。①[明]祁承爜著,郑诚整理,吴格审定:《澹生堂藏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结 语
《乡会公约》一书作于明代奢侈风气较为严重的万历年间,对人际往来、服饰穿着等做出具体规定。此外,撰者陆树声还将《乡会公约》融合进家训中,借助乡约与家训的形式展现了其禁奢思想,还与乡郡其他名望建会立约。不仅为其禁奢思想流传提供了可能,亦可略见明中晚期松江士人为禁奢所做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