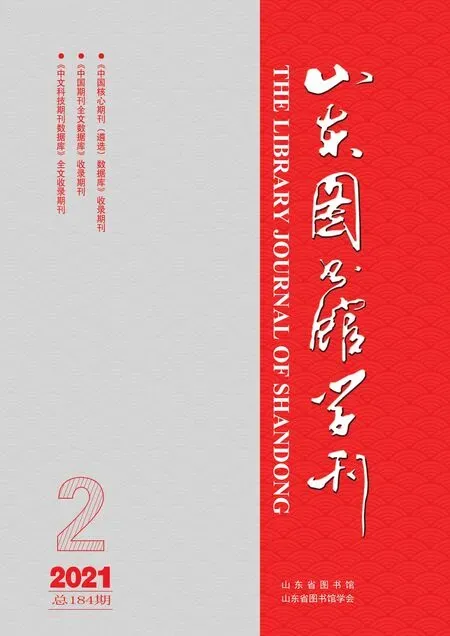目录学经史关系探析
2021-01-30徐定懿
徐定懿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编辑部,江苏南京 210095)
自从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对刘向、刘歆父子目录学上的贡献评价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自此,目录学研究大抵都围绕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一个思路上进行。然而,目录学中书目编排的经、史关系问题,并不仅仅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书目分类与学术溯源意义而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目系统中的经、史分类其实与经学史的历史脉络暗合。书目编排变化的历史,其实暗藏着经学发展、变化史。
1 目录学定位与经、史关系
首先应当从清末以来传统目录学的定位展开讨论。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对书目分类有这样的论述:“古今学术,其起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夫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后可行。故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原,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顾及。盖古之著目录者,皆在兰台、秘阁,职掌图书,故必兼计储藏之法,非如郑樵、焦竑之流,仰屋著书,按目分隶而已也。”[2]从此段论述可知,余嘉锡眼中的目录学究其根本是“以便人用”还要“兼计储藏之法”,用现代术语来说来说就是实用型学科,其目的是方便好用。关于七分和四部的关系,余嘉锡认为:“合而观之,七略之变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术数、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术数、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3]也就是说从七分到四部的变化完全是出于实用需要,因为史书增多,而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类书籍变少,相对应的,书目也就自然有了调整。
余嘉锡对目录学这种实用性学科定位的见解并非孤证,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对七分、四部有这样的评价:“世之言目录者辄喜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隋志》之四部非荀(勖)、李(充)之后裔,乃《七录》之嫡血乎?”[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从姚名达对目录学的定义就能看出其根源:“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5]姚明达认为七分、四部其实没有什么根本差异,四部于七分就是一脉相承。说到底,因为书目分类的实用需要,七分自然就过渡到了四部。姚明达的观点实际上与余嘉锡相通,相较于前文余嘉锡的观点更加彻底化:从七分到四部的变化,正是由目录学实用性学科的定位所决定的。
目录学的定义落脚为“专门学术”,这实则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历史境遇不符。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是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在以官簿为正统的目录学脉络中,目录学从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经学的意味非常浓厚,对于中国古代的官簿来说,首要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个“道”的载体,其次才是其学术价值,而且这个学术价值一直是出于不自觉的状态,并非是带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学科规范而带出的独立学术价值。
然而自晚清以来的目录学家多半是以学术考订的眼光来看待目录学。由于清末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学者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以西学为参照,以学科分类来规范目录学研究。如果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眼光来对传统目录学研究作一个总结的话,王欣夫引近人汪国垣《目录学研究》的一段话做了很好的界定:
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汇集群籍之名为一编,而标题其书之作者篇卷。或以书为次,或以书之体制为次,要皆但记书名。踵事而兴,则进而商确其体例,改进其部次。”这一类称为目录家的目录。二,“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后人览其目录,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之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难考索而得。”这一类成为史家的目录。三,“目录学者,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也。汉时诸经,本有今古文之不同,然艺文志必详加著录,非如此则异同得失,无所折衷。刘向必广求诸本,互资比较,乃得雠正一书,则旧本异本之重视,盖可知矣。”这一类称为藏书家的目录。四,“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也。如龙启瑞之《经籍举要》,张之雅之《书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版本,其目的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矇者,为用至宏。”[6]这一类称为读书者的目录。[7]
汪国垣将目录学划分为四种,分别是:目录家的目录学、史家的目录学、藏书家的目录学和读书者的目录学。这四种分类已经触及到中国古代目录学内在的非单一属性,书目绝非仅仅是一定规范的分类而已,目录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多重的意义。在汪国垣看来:作为目录家的目录学更多是为汇编方便,因此部次会本身就是可商榷且一直有改进的;作为史家的目录学则是为掌握古今学术源流承接,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藏书家的目录学则具有校雠意义,以汉代古文经与今文经为例,今古文不同,必广求诸本多方比对然后详加著录,这一过程就是校雠的过程;而读书者的目录学则具有治学途径的意义,这其实与史家的目录学有相通之处,目录学的背后是学术史,因此对治学有重要意义。这样的总结可以说是细致又有深意了。然而,这样细致的分类却都没有点明目录学受制于官簿背后的强大意识形态,不可能真的达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目的。可见,对古代目录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针对其具有汇编意义的一面,应当通过目录形式和内容的变化,理解目录学发生的经学背景乃至理解目录学承载官方意识形态的非学术性的一面。这样对目录学的研究才是回到具体历史语境对它本来面目的一种还原。
在进一步讨论目录学分类中经、史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经与史的含义作出归纳。首先是经字,《说文解字》中,经的解释为:“经,织纵丝也。”段玉裁对这个解释进一步注释为:“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8]成玄英疏《庄子·寓言》:“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中的“经”字:“上下为经。”[9]《汉书·五行志》中,颜师古对“还经鲁地”中的“经”解为:“经者,道出其中也。”[10]从以上对“经”的解释可以看出两点颇有意味:第一,经为纵。天在上,地在下,人居中,因此人要对天有所领会,与天要有所关联,那么这个渠道就是“经”。第二,道出于经。因为经是天与人的联系,所以天道也只能通过经向人显现。然后是史字,《说文解字·史部》,对史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1]《周礼·天官》中对史的解释为:“掌官书以治赞。”[12]《礼记·曲礼》中,孔颖达疏“史载笔”的“史”为:“史,谓国史,书录王事者。”[13]由以上对史的解释可见,“史”首先是职官,其次是事件,而且是关于国家王朝的事件。综上,经与天道更紧密,而史与人事密切。同时,与天道相关的经并不是高高在上,与人事没有关联的,它居于天道与人事之间,这是它“纵”的含义所确定的。
正是因为如此,对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既然他们以天子自居,那么经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为经是天道的载体。而史所关的人事不是一般事件,而是国家大事。那么经在先,史在后,因为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事,记人事也是为了谙天理。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排列的时候,就能看出一个明显的分野。经、史处于离王权中心近的位置,而子、集则处于离王权中心较远的地位。
2 汉唐时期七分、四部的形成
从目录学上追述经、史关系,大致可以《汉书·艺文志》为一个起点,同时,《汉志》作为流传下来可见的七分法文献,在目录学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据阮孝绪《七录序》,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别录》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篇幅比较多。《七略》是摘取《别录》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汉志》中如下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4]从《汉志》的七分来看,六艺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如果要以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来作一个对应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汉志》七分法没有史类,或者说史类归为六艺下的春秋略。查看春秋略下面的小序,是这样记载: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15]
春秋略的小序强调了这几点:一,汉离周不远,因此《汉志》使用的“史”更接近于史的原本意义。柳诒徵就曾指出:“古之有史,非欲其著书也,倚以行政也。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16]因此,史在原初更重要的乃是行政意义。也正是基于此,春秋略小序强调的第二点也就顺理成章了。二,礼。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也曾指出:“历夏商至周,而政务益繁,典册益富,历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职不得不分。然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17]而且还点明了:“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8]正符春秋略小序中所强调的“礼文备物,史官有法”“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里对七略四部的划分有这样的论述:“七略四部,名异而实同。荀勖、李充取六略之书合之为四。王俭、阮孝绪又取四部之书分之为七。观其分部之性质,实于根本无所改革。今以经史子集相沿较久,故仍以此为纲,其不同者皆分别归纳其中,以便观览。”[19]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史在最初“七分”起始阶段,就是从属于经的,没有客观记录历史的史,史这一部承载了国家行政意义以及“礼”的宏观内涵。
《汉书·艺文志》后具有转折性,且与《汉志》一样在目录学上具有及其重要地位的正史史志就是《隋书·经籍志》了。它采用了四部分类法,事实上在《隋志》之前《中经新簿》已开始了四部分类法: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20]
不过《中经新簿》对四部的排列是经、子、史、集。从《隋志》开始就采用了后世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从经、子、史、集到经、史、子、集的变化,反映出了官方书目不但具有收集、梳理文献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文献编排中体现出国家正统意识。文献的分类已经由不自觉的承载官方道统意识,过渡到自觉将这种意识贯穿文献分类的始终,且一直持续到清代。
《隋书·经籍志》经部录入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以及小学类文献,但在小学类文献的最后部分还录入了鲜卑号令一卷、婆罗门书一卷、外国书四卷以及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这类的文献。如果参照史部和集部的分类的话,似乎鲜卑号令归为史部或集部,婆罗门书、外国书以及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归为集部更合适。但《隋志》的书目分类并不只是检索分类的索引工具,在这个分类中隐含的是国家官方意志。鲜卑号令、婆罗门书、外国书涉及的是外邦,这与朝贡和王朝统治密切相关,而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则是代表国家一统的前代文献。因此从国家官方意志来看,经部目录收录的内容除了通常认为的经典和圣人之言外,还有一层含义是和王朝政权最密切相关的文献。前面所提的书目划分,被姚名达斥为有“分类之非,编目之误”[21],实质上《隋志》原本就不是按照姚名达依照的“严谨”标准来分类的。《隋志》的大序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经与史不同于子、集两部的地位以及它们同国家王权的亲近关系:“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22]“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23]虽然《经籍志》包含经、史、子、集四部,但大序中提到的“经籍也者”却只限于经、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史与子、集对国家政权来说完全不同的地位。
汉至唐作为本文探讨的目录学经、史关系的第一个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官簿、史志由开端到成熟的时期。奠定了目录学七分、四部的基本框架,在此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这一格局虽有被突破的时候,但都未能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七分、四部构成了中国目录学的主脉。而这一目录学上的主脉以及在其中占有极为重要位置的经、史关系,正与中国经学的发展伴随始终。从汉至唐这第一个分期来看,这个时期的经学从汉代立五经博士到唐代官修《五经正义》,用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的话来说,正好也是经历了从“经学昌明时代”到了“经学统一时代”[24]。与经学史相印证,目录学从汉至唐也可谓是处于其正统期。经部与史部的关系也从最初同属六艺略,到位列四部中的经、史二部。两者与古代王朝的国家意志始终最近,同时,经、史二部亦同源。在目录学的正统期,七分和四部都反应了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经学思想的内核,此时私家书目较少,且基本没有超出七分、四部范围都与“经学昌明”和“经学统一”相印证。
3 宋明时期目录学分类的变异
目录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宋明。中国古代都是隔代修史,因此《隋志》之后的《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都反应了宋明官修史志的状况。《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沿袭了从《隋志》以来确立的四部分类的传统,没有太大革新。《旧唐书》有《经籍志》,按甲、乙、丙、丁四部排列,对应于经、史、子、集。《新唐书》有《艺文志》,仍旧是按甲、乙、丙、丁四部排列,对应于经、史、子、集。《宋史·艺文志》也仍旧按经、史、子、集排列,但《宋志》著录重复、差误较多,故在所有史志目录中,《宋志》最称芜杂。《元史》更是没有《艺文志》和《经籍志》。不过,明正统时期,“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二十卷,其体例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五十橱,每书只著书名和册数,而不著撰人和卷数。”[25]《文渊阁书目》的出现,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作为历代官簿中为数不多的非四部系统(1)按:本文将四部和七分作为一个系统的不同阶段来看,在前文关于汉唐目录学部分已加以论述。的书目,它的非正统性正好对应于经学史上“积衰时代”[26],宋明性理之学的兴盛,无疑是经学史上最为离经叛道的时期,而恰恰最能体现官方正统思想的官簿也表现出了非正统性。二、《千字文》在《隋志》和《四库》中归为经部。按《千字文》排列书目,虽然后代斥为草率的评论不少,但若要论立场,却与其他正史官簿有相通之处,内里保留了经学正统性的核心。因此,宋明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变异时期,更需要关注的是私家书目的编排情况。原因有二:第一,从社会物质经济发展的外部情况来说,从宋代开始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刻书发达,书坊增多,私家书目渐盛。第二,私家书目受官方正统思想影响较小,因此在不少时候能超脱四部分类,而且宋明在经学史上原本就是疑古、叛逆的时代,非正统思想代表的私家书目,更能体现宋明的时代思想内核。
宋代极为重要的两部私家书目就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后来有人称目录学为晁、陈之学,足以表明他们二人在目录学方面的显要地位。《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都是采用的四部分类法。但如果细致比较又有所不同。《郡斋读书志》中,晁公武按照四部分类法将文献归类,经类分: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解经类、小学类[27]。相对于《隋志》,晁公武的经部分类中,没有谶纬类,也没有收录纬书。史类包含:正史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史评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里类、传记类、书目类[28]。相对《隋志》,《郡斋读书志》对“史”的分类有所不同,此外,另外一大区别是没有簿录类,《郡斋读书志》将《太平广记》收入子部小说类;将《河图天地》归为子部五行类。而《隋志》将同类的《河图》与《河图龙文》归为经部谶纬类。《郡斋读书志》集部,别集类收:《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而将《汉唐策要》《太平盛典》归为总集类。
《直斋书录解题》把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不标经、史、子、集,但实际还是按四部分类方法和顺序,列经类十种,史类十六种,子类二十种,集类七种。《直斋书录解题》没有大序,只有七个类目有小序,用以说明类目的增创和内容的变化。“语孟类”小序,叙述了增创之由。“小学类”小序,重新确定该类目的著录范围是“文字训诂”[29],“起居注类”小序重新确定该类目“与实录共为一类,而别出诏令”[30]。“时令类”小序,则叙述了这一类自“子部农家类”列于“史部”的原因:“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及里闾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是矣。今从之”[31]。“阴阳家类”小序,说明了恢复这一类目的原因,“以时日、禄命、遁甲等备阴阳一家之阙”[32]。“音乐类”小序,说明了不再将乐列为经部的原因:“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秦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而前志相承,遒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举,比亦悖呼”[33]。“诗集类”小序、“章奏类”小序,都说明其别为一类的原因是有单行本即“独行者”[34]。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的四部分类可以看到,虽然沿袭了四部的传统,但在收录眼光上,以及四部之下小部的归类上无疑是对正统四部分类有所打破的。以《直斋书录解题》来说,它列小序的出发点更多是为归类变化作出说明,而《汉志》和《隋志》序更大的作用在于载“道”。在这个意义上,私家书目更接近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目录学。
如果说宋代在目录学是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那么明代则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明代自《文渊阁书目》后,私家藏书多不恪守四部成规。来新夏将明私藏书目概括为“按四分法类略有增减的目录”和“打破四分法顺序的目录”[35]两类。下面以明代几部私家书目为例,来看视明代私家书目的特点。《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基本按经、史、子、集排列。卷中则分类有: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卷下则有: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术、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姓氏、佛藏、法帖。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卷中分类已经是对四部分类的不恪守了,而卷中分类中小学渊源等归为子杂,西厢记归为乐府,这诸种归类都是与传统四部分类不符的。《红雨楼书目》编写仍旧以四部为体例,不过子目有所增加,但其宋集部分的排编体例较有新意。宋集部分,用表格排录,上面一层为集的名称,下面一层为作者的别号和姓名,十分便于观览。《赵定宇书目》记录的赵定宇所藏的书目,“编写形式实际上是账簿式的,虽然也分了类,但类列极不精密。如开卷为:《天字号·史书》,而接下来则是《经类》《类书》《经济》等,并无规律可寻”[36]。从上述引证就能看出,在明代,私家书目破四部分类之风得到了发展。
通过对宋明书目的梳理,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即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叛逆期,也是经学史上的疑古期,经、史、子、集的关系变得松散了,经、史也不再具有强烈的承载国家意志、道统思想的意义。并且经、史之间也不再有因为在天道人事所构建的正统皇权网络中,有那样紧密的关系了。这正是汉唐与宋明目录学中经、史关系的区别所在。
4 清代四部分类的回归
清代目录学可分为两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对正统目录学的回归与集大成;第二个时期是晚清在西学影响下对目录学的经世致用的倡导和现代学科分类意识的引入,这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代表。
《四库全书总目》为我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在编排体例上,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是对录入《四库》的全部图书写出的提要。《四库全书》不论从规模上,还是编排体例上,都是对前代的集大成。而《四库提要》更是对前代目录学上有分歧的一系列问题作了一个总结。
《四库全书凡例》首先阐明了全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切目”[37],然后表明目录编排自《隋志》以下“择善而从”[38],比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归为集部,《四库》随《唐志》将“诏令”归为史部,随《汉志》将“奏议”归为史部。有意味的是,在明代以破四部分类为体例之后,《四库全书总目》不但能以四部分类为纲,而且能综合前代,包括明代书目体例,然后整合于四部体例之下,且体系周严。纵观古代整个目录学史,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但凡在正统期,比如汉、唐、清代,则目录分类明显重经、史。但凡在嬗变期,如宋、明,则经、史、子、集分类都有打乱,且无所谓强调承载道统,因此在对待经、史、子、集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轻重区分。《四库提要》也反应了这个规律。在“经部总序”中,除了勾勒出整个经学从汉至清的历史变化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长短得失,而且还特别强调了皇权和道统,在这一点上,也正如皮锡瑞所言,是“经学复盛时代”[39]。“经部总序”的首句是:“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40]。即是对皇权的强调;倒数第二句为:“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41]。公理换言之也就是道统,这种对“公理”的追求,其实也就是对道统的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在明代的叛逆与突破之后回归了正统,但同时,也成为一个绝唱,随着清朝的没落,晚清西学的大量传播,目录学再也不能固守于四部传统,经、史两部所立于官方正统的地位,为“实用”所突破,正如经学在经过清代最后的辉煌之后走向了没落一样。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这种变革时期的产物。
1875年,张之洞刊印《书目答问》,将典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在《书目答问》典籍分类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子部”。张之洞对该部分类作了较大调整。他在子部分类时说:“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42]。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提要》分类较为明显的差异之处。除此之外,《书目答问》四部分类变化最大的,是在子部的兵家类和天文历算类中,收录了从西洋翻译的书籍。也就是说,张之洞将当时西洋翻译而来的书籍,纳入了“四部”分类体系的“子部”分类中,将西学附属于了中学。比如在兵家类中,列举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刻本《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包括《克虏伯炮说》4卷、《炮操法》4卷、《炮表》6卷、《水师操练》18卷、《行军测绘》10卷、《防海新论》18卷、《御风要术》3卷等,并称赞这些西书“皆极有用”[43]。《书目答问》中,张之洞对经世致用十分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经部举家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觞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44]。对“实”与“实用”的强调已经远离了经作为天道承载,史作为天道下的人事体现的传统思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对子、集二部的极大重视,无疑就是对官簿重经、史的深刻反叛。由此,中国古代目录学走到了它真正不可回避的变革期,到如今传统目录学已经不可能存在于现实实践运用中。
5 结语
通过全文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目录学的沿革与经学发展内在理路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互为表里;一方面,目录沿革的历史也就是经学内部发展、变化的历史,而经、史关系无疑是目录学沿革历史中最为密切的一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目录学中各部的整体考量,能看出在代表正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官簿中史部首先乃是与经部最为紧密反映出与国家王权的亲近关系的,这不同于子、集两部,《隋书·经籍志》中的“经籍也者”就只限于经、史。不过经、史也各有所侧重,经与天道更紧密,而史与人事尤其是关于国家王朝的人事密切关联。总体来讲,如果在经学大背景下来审视古代目录学的经史关系,可以发现这样的变化曲线:但凡在经学正统期,比如汉、唐,目录分类明显重经、史。但凡在经学嬗变期,如宋、明,则经、史、子、集分类都有打乱,且无所谓强调承载道统,因此在对待经、史、子、集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轻重区分。而清代则既是经学最后的复兴期,也是书目分类上四部法集大成的时期;但同时到了清末,书目分类为“实用”所突破,正如经学在经过清代最后的辉煌之后走向了没落一样,书目再也无法恪守四部分类,经与史的特殊亲缘关系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