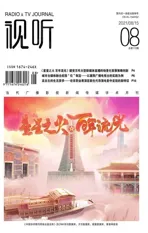“白光”审判下的存在之痛
——《被光抓走的人》的存在主义分析
2021-01-30唐恬
唐 恬
影片《被光抓走的人》虽以科幻元素号召观众,但是影片并未过多着墨于被“白光”带走的人们面临什么样的境遇,而是偏向于记述经历了“白光”审判后的现实世界,并给“白光”下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被光抓走的人才拥有真爱。这一特殊逻辑的预设,使影片中的现世之人被强行否定了真爱,原本对“真爱”的认知遭到挑战甚至转向虚无。作品不失荒诞地展现“后审判”下人们精神层面的虚无、焦虑、困顿。通过刻画一对中年夫妻、一个和丈夫正在离婚的妻子、一对年轻情侣和一个对发小有着同性恋情感的街头混混这四组不同人群的情感困境,追问“爱情”的存在如何被证明?被“白光”抛弃的人们如何超越自己“自为”地寻找“爱情”的标准和价值的支撑。本文从极端情境、矛盾冲突、表现手法三个方面来分析该片的叙事策略与主题表达。
一、极端情境:“白光事件”再现“上帝之死”
“上帝之死”是一个著名的哲学事件,是尼采借疯子之口传达出的惊人之语。海德格尔曾作解释:“上帝之死”并非仅是宗教领域的事件,“上帝这个名称——形而上学地思——代表超感性世界。按照柏拉图,超感性世界是‘理念’的领域。”①因此,“上帝之死”指的就是超感性世界的坍塌,就是理念领域、理想领域的一种瓦解模式。对整个哲学领域影响巨大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正是假设了一个超验的理想世界,将另一个更高级的世界当成追求绝对真理意志的理想“彼岸”,据此否认让人生活困苦的此岸世界,认为它是虚假而短暂的。但是上帝的死亡瓦解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体系,超感性世界没有了生命力,不再可以被依靠,人们的精神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状态。
影片中的“白光”是以一种“天灾”的姿态出现在故事中的,但是这种灾难带来的恐惧和危机感并非来源于它出现的那一瞬间,而是源于事件发生之后的“末日之感”。影片的镜头不遗余力地表现“白光事件”后人群的混乱、困惑和绝望。路边会有人打砸抢商店、街边犯罪率增加、新闻报道中世界各国都弥漫着疯癫与混乱。最为极端的代表人物是筷子在派出所遇到的社科院研究员,他借用“科学”的解释得出“被光抓走的人才是真爱”的结论,并宣判了自己和妻子“爱情”的死亡,以至于活活掐死妻子,前来自首。
影片中的“白光”如同“上帝降临”,台词反复强调了“白光”在人们心中代表“上帝”,如“老天爷来收人了”“被老天爷审判的我们不是真爱”等。事件中,“白光”强行带走了一部分人,却又抛弃了绝大多数人,这种被“上帝”抛弃后的精神状态和现代哲学史上的“上帝之死”让现代社会深陷虚无主义精神困境如出一辙,人们被强行剥夺了对超感性世界的依赖,意味着人们缺失了目的和方向,陷入了虚无。如萨特所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成为合法化。这样一来,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②因此萨特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人的痛苦源于他的自由是被逼迫的,他不得不“自为”地做出选择、承担责任,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价值和标准。
影片中,导演将这种危机聚焦于“真爱”这个概念中,借用“白光事件”的介入,颠覆原本真爱意义的传输链,在没有“上帝”和世俗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抛出人们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完成“真爱”意义的再建构、“真爱”是否可以得到证明等思考。电影正是通过这种极端情境的预设,推动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使每个人物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黄渤饰演的武文学,通过向他人说谎、伪造证据以及试图通过第三者来“报复”妻子,挽救自己所面临的爱情危机,对“白光”审判的结论持回避和反抗的态度;王珞丹饰演的李楠,在寻找消失的丈夫和他的“真爱”过程中,知晓了丈夫所展现的不同侧面,接受了人性的复杂和“真爱”的不稳定性;白客饰演的街头混混筷子,对自己的发小是一种游离于正统情感之外的同性情感,“白光事件”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于是他选择将这份隐蔽的情感外化为一种对“假想敌”的暴力,完成报复后,才如释重负地正视了自己的内心;李嘉琪饰演的刘佳一和她的男友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一种飞蛾扑火、不畏牺牲的状态,相比武文学逃避式的反抗,两个年轻人的反抗显得更为彻底,不论是“白光事件”前反叛父母而选择以死殉情,还是“白光事件”后用自杀来证明真爱,即使对真爱产生过自我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发出了“老天爷凭什么对我们进行审判?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样的抗争。
影片在挑战“真爱”指向“婚姻”的传统意义传输链的同时,又隐晦地进行了一次先锋性的探索。黄觉饰演的赵峰和他的妻子在美术馆里的活动颠覆了“婚姻”和“真爱”相对应的指涉关系,认为“婚姻”在爱情逝去的事实面前不过是一层“皇帝的新衣”,与其用“婚姻”来欺骗自己,不如正视事实重新赋予“婚姻”新的意义,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矛盾冲突:“存在遭遇”中爱情的冲突和失败
影片虽披着“软科幻”的外衣,但其内核是借助一个“外力”将司空见惯的情感问题放在极端情境中进行一场深入的“解剖”。导演曾表示,这个故事第一眼看起来是个悬疑的爱情故事,但真正想探讨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的故事。“认识自己”可以理解为人们如何借用爱情这种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他人的“注视”,使我由自为的存在转变成自在的存在,即变成一种被对象化的为他的存在。
在和他人的具体关系中,萨特提出了两种情况:“或者,我注定要迫使他人行使他的自由,以建立我的存在;或者,我注定要取消他人的自由,以震慑他人。”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人作为两者之间的主体,而我则被动地被他所爱,从而我成了他自由的限制;第二种情况中,我作为主体,他人作为我的对象,我要占有他的自由,把他的自由化入我的自由之中。于是这两种情况会形成对他人的不同态度:爱、语言、受虐色情狂或者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③。
在最接近片尾的段落中,导演通过武文学和小韩老师的对白,将“他人即地狱”的结论进行直白的引用,难掩导演对爱情是冲突的且注定是失败的思考。“他人即地狱”是从悲观的角度放大了和他人关系中冲突和对立的一面,是自为存在之间相互失衡的关系,这种失衡就成了剧情中随处可见的爱情危机。
萨特定义了爱情的三重可毁灭性以及导致爱情走向失败的因素,分别为“不满足感”“不安全感”和“羞耻感”。其中,李楠与丈夫、武文学与妻子的情感问题分别源于“不安全感”和“羞耻感”。
白领李楠寻夫的故事线中,李楠的丈夫胡建平是一种全程不在场的状态,他的人物形象很难被观众直观感知,导演陆续安排了一些和胡建平有着暧昧关系的女性角色出场,她们每一个人所描述的胡建平都是不一样的,给观众多维地展现出了一个难以简单定义的复杂形象。观众透过女性角色的“注视”,将胡建平看成是一个“对象”,观众便成为“对象”的主体,将胡建平变成一种“纯粹被沉思”的客体而统合于“我”的世界中,但是很快就会通过剧情的发展发现“注视”是相互的。不论是李楠在寻夫过程中所产生的陌生感和困顿,还是胡建平的情人执着于自我欺骗式的“真爱肯定”,李楠她们最终还是意识到自己同样也是一个“为他的客体”,他人是一种“我”不能驾驭、不能客观化的自由主体,而“我”却因为被迫接受他人的自由而无力守护自己的自由。这种相互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人成为“一种爆炸性的工具”,这种爆炸性又会使“我”突然体验到这个世界对“我”的抛弃,从而体验到我存在的异化,产生永久的不安全感。李楠夫妻间的危机正是如此,这是一种自我认识的过程。导演在访谈中提出,这段关系的故事并不是直接探讨爱情,而是探讨你在爱情这个过程中到底怎么看待自己。我们在爱情中,最终可能并不是说你对对方有多了解,而是你对自己有多了解④。
与其他角色在“白光事件”后的过激反应相比,武文学和妻子张燕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暗潮涌动的危机。导演用比较克制的长镜头来展现他们好似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但是两人之间的同框却总是巧妙地设置遮挡物将他们隔绝开,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疏离感。武文学作为一个强势的情感主导者,往往使张燕常处于一种被动的为他的存在。为了证明真爱、回避问题,他无视张燕的个体感受,执意利用她制造伪证以及公开夫妻之间的私事,直到赵峰和小韩老师作为入侵的第三者出现于两人之间。第三者注视让恋人的任何一方都体验到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的对象化,产生羞耻或骄傲,使感情发生异化⑤。他们夫妻之间的危机才被彻底揭露在台面上。
三、表现手法:叙事情节“荒诞化”处理
在表现手法上,该片将科幻背景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在这样的语境下,表演越现实,越具有代入感,故事就会越神奇,在叙事形式上呈现出一种“荒诞美学”的色彩。
例如导演在引入武文学和妻子张燕的夫妻关系时,加了一场机械化的、毫无激情可言的床戏,两个人虽做着亲密的举动,但是眼神举止、对话交流却都是琐碎日常情境下的状态,行为和情境相互割裂,构成了一种荒诞感;李楠寻夫的最终结果同样透着荒诞感和黑色幽默,在她和丈夫的情人找遍了他的“红颜知己”后,最终却被警察告知胡建平是在“白光事件”之前发生车祸掉入水中死亡,并没有被“白光”带走,他究竟对谁是真爱将是一个永远都沉在水中的谜团;武文学企图和暗恋他的小韩老师发生关系来报复自己的妻子,临了却慌乱不已想要逃离,特意避开电梯慌不择路地从楼梯往下走,却不想迎面撞上也选择从楼梯上来的小韩老师,氛围陡然走向滑稽;刘佳一和男友将爱情视为最高的追求,不惜以跳楼威胁父母证明自己的爱情,但是“白光事件”之后刘佳一立刻否定了自己的爱情,男友为了竭力证明对女友的爱意,在实行了强制性关系之后,因为一句“我能为你死!”就选择直接从楼上纵身一跃,结果并没有死亡而是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影片中这样的荒诞感无处不在。“荒诞”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荒诞表现的是人生存在的荒谬性和无意义。人对存在感到恐怖和无所适从,这种恐惧不是对对象的害怕,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理感受。人无法了解世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生命的意义也不复存在,生命仅仅成为肉体的存在,人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物品”,这就是存在的无根状态。加缪用“荒诞”来表述人与世界的关系,即“荒诞”是人与世界的断裂关系,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维系。加缪认为有五种因素使人意识到了“荒诞”:厌烦(日常生活的机械性使人对其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产生了怀疑,对存在状态提出疑问);时间(人对时光流逝的敏感);死亡(人意识到死亡);异己感(产生被遗弃于一个异己世界的感觉);有限性(人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⑥。
传统的世俗观念使婚姻呈现出一种机械的日常状态,厌烦让人不得不对婚姻提出质疑;极端情境的设定让所有人物处于一种异己的世界中,秩序混乱、和谐被打破;“被抓走的人是真爱”这样的结论将人物推向自我怀疑的境地,意识到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电影用荒诞的表现手法,象征性地突显了生活中的虚妄和荒谬,契合了作品对人和人、人的存在的思考,也彰显了人们精神家园的缺失、虚无主义的困惑以及自我存在的危机等主旨内涵。
四、结语
影片对存在问题的表达、情感问题的探讨都具有戏剧张力,但是在影片的后半段却明显为了一个形式上的“大团圆”而将剖析出来的情感问题搁置,在并未解决的情况下以一种强行和解、强行自我救赎的方式回归于机械日常,得出一个“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结论,与影片的前半部分自相矛盾;并且在电影的视听语言上缺乏与情节相对应的形式感,多以情节的推动为主。虽然在科幻类型电影上多了一些新形式的探索,但是在类型定位上进退失据,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科幻的元素单一,对于“白光事件”的处理过于草率和简略。不过,《被光抓走的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存在这一具有普遍价值主题的深刻探讨上可圈可点。
注释:
①马新宇.海德格尔与尼采论上帝之死的契合与分殊[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8-25.
②[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③吴华眉.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爱情观[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08):27-29.
④程橙.《被光抓走的人》导演董润年:“光”从何而来?又如何实现?[J].电影,2019(12):17-21+16.
⑤[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462.
⑥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文学化”[D].济南: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