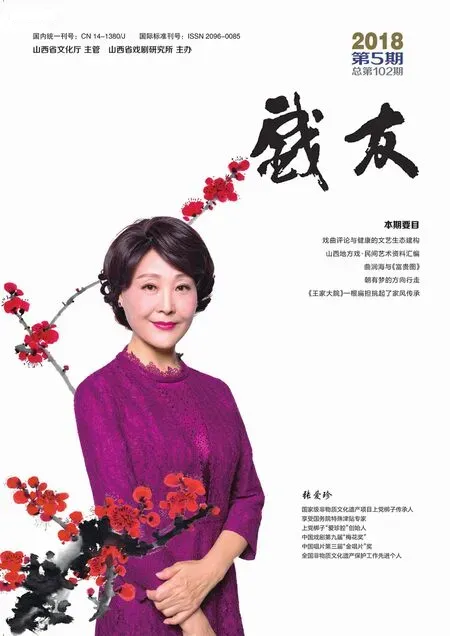生命之河
——《阳光下的红丝带》
2021-01-28王小东
王小东
当一个人的生命与你的健康联系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如何选择?谈之色变、避之不及,还是共同抗毒决不放弃?当面对与自身利益相关尤其涉及生死命题时,每一个人的选择也许都没有错,但郭保平的选择,却让中国人看到了人间至情,胸中大爱。这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山西省晋剧院重点打造的原创晋剧现代戏《阳光下的红丝带》就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纯粹的情感。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以郭保平院长为代表的医护人员力排众议救助爱滋病患的故事。在故事中,所有患者都被周围人孤立,甚至包括自己的母亲。他们流浪,他们有家难归。因为“脏病”,他们无法活在别人眼中,每一个患者都只能在郭院长的羽翼下避难。军军的死亡,让病患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也让周围人感受到生命之脆弱,他们终于开始思考生命,看到自己以外的生命。郭院长毅然辞职办校,留住这些年轻的生命,数十年如一日,郭校长也终于等到了那些孩子们成人成才的那一刻。
这部剧讲述的故事大胆且深刻,关于艾滋病,国人大多谈及色变,但《阳光下的红丝带》就将艾滋病不保留地放在阳光下剖析,我们看到了面对艾滋病时,我们自身的镜像:冷漠、决绝、事不关己。也感受到了病患的无助、心寒、绝望。这是一部有意义的剧作,编剧张俊海把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内心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刚开始的动摇和冷漠,之后生命的骤然离去,最后大家的守望相助,层层递进地展现了出来。通过这部剧,更呼应了从年初到现在以来,守护在抗疫一线的医务战士,传达着大家共同的初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时,也传递着广大基层党员的奉献意识和大局意识。
《阳光下的红丝带》中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在第一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部分,也就是王贵生过年难进家门,由杨文艳扮演的老母亲一句“一声声哭得我心裂碎”,肝肠寸断,唱出了老母亲左右为难、两面难舍的骨肉离情。王贵生一句句“开门呐!”喊出了王贵生作为儿子竟被母亲挡在门外的心寒与凄冷。陈永强表演的分寸把握、杨文艳的悲情演唱,两位演员如泣如诉,将这一感人至深的场面,难于抉择的人伦场景动心地表达出来。李明星、张芙蓉扮演的郭保平、慧琴夫妇在唱演部分也足够动人心弦。如“藏药”“露馅”“恐慌”等段落中,有节奏有层次的表演将他们各自丰富的内心感情外化于舞台,尤其是张芙蓉,炉火纯青的演唱更是将作为院长家属那种对于自身、对于病患、对于道义的三难境地生动表现出来。总的来说,李明星、杨文艳用唱功成功传情,张芙蓉、陈永强用行为表演征服观众。在作曲岳永明的音乐铺垫下,整部剧如画龙点睛,剧作、演员也有了依托。当然,整部剧目的成功演出离不开导演席凯的优秀调度功底,我在此祝贺他们。剧中的小演员们表现同样抢眼,他们来自太原市艺术学校,这次的登台对他们来说既是对所学的检验,也是一次珍贵的实践经历。在舞台上,他们对于同伴、对于自我、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在不短的唱词中得以展现。我想这部剧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演技上的提高,更是对于生命、善念、对于人之为人的一次深刻理解。
本剧有诸多眼前一亮的表现形式。在开场部分,一条“血河”铺在舞台上,所有爱滋病患翻腾在这条“血河”中,而他们在现实中经历的波涛可远不止舞台上的红绸“血河”。郭保平的“找药”这一部分,以舞蹈动作无声胜有声地生动展现出郭院长对艾滋儿童的关爱,与家人的斗智斗勇看起来调笑、滑稽,但实则蕴含着对于艾滋病人的无尽的无奈和怜惜,而这样的设计也恰好中和了全局比较悲调的氛围。另外一些怪兽装扮的演员上场做打,隐喻着无穷的病毒和死神,他们舞蹈化的表演既增强整个剧的可看性,也进一步形象化艾滋病毒。另外还有诸如抢救军军时剪影的运用,布景如树、小卖部的移动等,都展现了导演对于这类社会性、话题性强的剧目的创意运用。不过,该剧有些结构、情节还存在一些瑕疵,需要不断地磨炼、完善。
《阳光下的红丝带》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观照着弱势群体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救还是逃?面对艰难的选择,作为百姓,我们普世的情感价值有过动摇,但郭保平带领众医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部剧尽管题材敏感,也很难排,但却在艺术市场上打响了成功的一枪。对于青少年、对于曾经“冷漠”的你我,这部剧都极其有意义。它的成功上演是我们作为观众、作为父母、作为文艺工作者都很欣慰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多年以来,作为创排单位,山西省晋剧院不仅在保护、传承传统剧目上下功夫,更在不断应时推出新戏。而山西作为戏曲大省,能够保持这样的戏曲创作力,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在此希望省晋剧院能够多复排、加工优秀传统剧目,不断推出精品,引领我省戏曲发展,做好戏曲排头兵,不愧对山西戏曲大省的称号,也希望我们的小演员们通过多多参与这样的实践经历,积累人生和演戏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