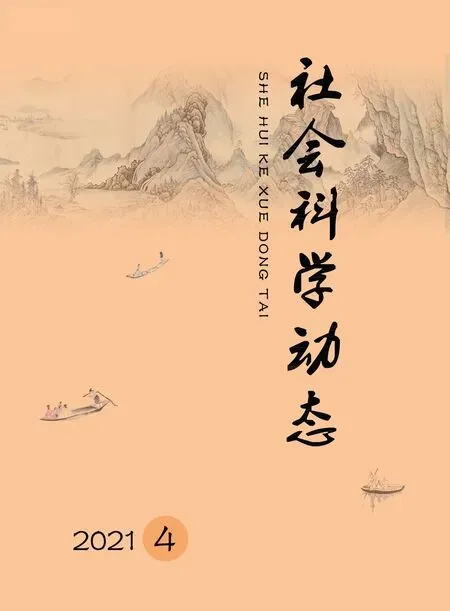熊铁基教授的执着与真诚
2021-01-27张艳国
张艳国
日前,范军师兄发来微信约稿,告知今年(2020) 是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的米寿,同门高兴之余,跃跃写稿,庆祝熊先生米寿之喜,也希望我参与凑乐。范军师兄知我与熊老师素有交谊,颇有渊源,有故事可讲,有人情可述,而我也欣然应允,愿为熊老师米寿略尽绵薄,喜上添喜。前些时,我在网络上拜读了校友戴建业教授的《喜乐熊先生》之后,就颇有共鸣,觉得我也可以说上一些什么与大家分享。静心一想,细细梳理,我在与熊老师几十年的交往中,他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育意义的是:他在待人接物、治教立学中所体现学者的执着与真诚,对我启发和影响尤巨尤深。
1985 年夏天,我从大学毕业入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史学编辑室伊始,就与熊老师开始有了来往。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从湖北籍老乡谢天佑教授的交谈中,就知道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熊铁基老师。谢老师告诉我,熊老师与既他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同学,又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研究班的同学。他们在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束世徵、李平心、戴家祥教授的精心指导下顺利完成学业,谢老师留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熊老师则回华中师院历史系任教。他们都专攻中国古代史,尤其主攻秦汉史,以此在史学界知名。谢老师对熊老师勤勉治学的态度很肯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样,我虽是后学,但与熊老师是名副其实的校友。因为有谢老师的介绍,上班后,我就很快地拜访了熊老师,由此建立了常态化联系。两年后,我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康同学恋爱,她毕业后我们结婚成家,偶有机会,我陪太太回她的母系母校走访师友,也会拜访熊老师。熊老师是康同学的中国古代史任课教师,熊老师的夫人李雪松老师是康同学的世界近代史任课教师。我经常听康同学关于她在大学读书时的回忆,特别喜欢听她关于老师授课的讲述。她说,熊老师和师母李老师都是敬业乐教、爱护学生的良师,但各有特点,令人难忘。熊老师讲课潇洒自如,洒脱发散,每次都带上一大摞文献古籍,总不忘结合史料讲,永远都惟恐没能讲尽知识点,生怕学生学得不深不细;李老师则线索清晰,条理清楚,娓娓道来,学生听后一下子就记住了。加上康同学与熊老师夫妇这一层师生关系,我后来与熊老师的联系更多、交往也就更加轻松惬意了。
熊老师一向待人热心快肠、乐于助人,蕴藏在他这样待人接物言行深处的情感,是炽热执着的,是真诚坚定的。1988 年初,华中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邹贤俊教授指导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就要毕业了。按照常情,应该是研究生本人的导师要更着急、更积极一些地思考和筹划学生的未来。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熊老师对于这位并不是自己指导的青年学生的关爱是火热的、无私的。其时,熊老师隔三差五向我了解《江汉论坛》历史编辑室的用人情况,刚开始,我并不知道熊老师有推荐人的意向。当时,我们编辑室已有两人,除我而外,在上年刚刚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挑选了一名优秀毕业生,加上何浩先生刚刚退下来,我们还请他看一段时间的稿子。按照当时的设岗情况,史学编辑室是不缺人的。当我把这一情况向熊老师沟通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拟向我推荐一名优秀的硕士毕业生。当时,因为我刚刚主持史学编辑室工作,加上年轻,没有经验,感到难度不可想象,简直是没有可能。但是,对于熊老师给我们推荐人才、支持我们工作的好意,我也不能推辞。但我心底里相信,这应该是没有戏的事情。因此,我的态度犹豫模糊。在一段时间里,熊老师经常来电话,甚或是从桂子山骑车来我们所在东湖之滨的办公室找我反复说,诚恳地请我支持。我终于被熊老师感动了,由态度犹豫转为坚定支持。我告诉他,编辑部和院里,我就说不上话了,成与不成,与我无关。熊老师对此,只是向我报以神秘而自信的微笑。此后,熊老师隔三差五来编辑部,不过,找人的对象换成了编辑部主任荣开明同志。熊老师之所以能够不厌其烦地找荣主任,一是因为他们是老熟人,交谊深厚,建立了和谐的作者与编者关系;二是因为他们是湖南老乡,常有联系,共叙乡情。据我观察,他们之间的沟通很长时间内都很不顺畅。但在当年五月末的一天,等到荣主任找我商量史学编辑室进人问题,而荣主任倾向于进人时,我意识到“关键的堡垒”已经被熊老师的锲而不舍、真诚执着攻下了。后来,这位青年学子顺利入职,发展得很好。
熊老师待人处事的执着真诚,并非此一孤案。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性评价。我的仙桃同乡、曾任康同学班主任的郑敬高教授在与我回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对熊老师的真诚帮助总是不禁唏嘘叹息、由衷感激的。郑敬高同志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从武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由此与熊老师成为同事。在郑敬高同志入职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熊老师经常到青年教师的筒子楼转悠,“察看”小郑同志在干些什么?开始一段时间里,小郑老师很不适应,甚至感觉很不好。但过了一段时间,小郑同志觉得这是熊老师善意的监督和督促,便由不适应变得很配合了,主动向熊老师汇报读书体会,主动与熊老师进行学术交流,在教学科研中,他们成为亲密的合作者。在华中师大历史系工作期间,小郑同志感觉很愉快,与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配合很好,而他自己也进步很快,慢慢变得很自信、很主动积极地从事各方面工作。虽然他已经从华中师大调离多年了,但只要我们一谈到他在与熊老师他们共事的日子,他总是充满幸福的深情和对往日的依依不舍。如何回答戴建业校友在文中的“熊先生喜乐之问”?我认为,熊老师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是执着而真诚的,因此,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一定洋溢着无尽的喜乐!
在史学研究中,熊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执着和真诚的。1987 年春夏之际,熊老师来编辑部史学编辑室几次,同我和何浩老师交流。先是他向我们介绍他正在做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七五”规划项目“汉唐文化史研究”,并交流当时学术界“文化热”的进展,以及他对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看法。然后是他就研究设想、运用的理论与方法、所借鉴的主要学术资料和史料,与我们进行比较深入地互动,对于一些心得体会,熊老师讲得兴奋不已,以至于像上课一样畅达,我听得津津有味,何老师不时插话点评,场面十分融洽而热烈,堪称作者与编辑互动的经典。最后,他在确知我们对他的研究感兴趣,得到“有新意、有价值、有前途”的肯定性评价后,就兴冲冲地拿了几篇文稿来供我们挑选一篇,作为向杂志社正式地投稿。客观地说,这样与编辑深度交流,投稿是很有成功率的。根据我刊发稿特点和办刊风格,我们最后选取了其中一篇《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轨迹》文章予以发表,而其他两篇《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发展——汉唐文化史研究之一》文章,则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表①。这组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重视。发于我刊的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秦汉史》全文转载,并被《史学年鉴》介绍。等到几年后,他的《汉唐文化史》②出版了,他也不忘记亲自骑着自行车送几本到编辑部来,荣主任、何浩老师和我各有一本,熊老师还亲手签上大名,一边向我们表示感谢,一边笑着说送我们“请指正”。他投入在秦汉文化史研究之中的炽热执着,他在研究中寻求友谊和支持的真诚坦率,他在与我们的交往中善始善终的严谨严整,深刻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给我留下的印象难忘、使我深受教益,这是显而易见的。针对有的作者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教养和文化气质,何浩老师还几次认真地以熊老师的“汉唐文化研究”与我们的交往交流为例,进行对比和点评,使我增强了人生和业务的双重感悟。我们被熊老师的真诚与执着感动着,因此,我们由被动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和他的研究之中,到自觉自愿地支持他的工作,等到他的这部专著出版后,我们就积极组织院内历史学者撰写书评并及时发表③。这篇书评对熊老师关于汉唐文化史的研究作了积极地肯定性评价,认为这种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深入探讨,“将有利于推动文化史学科研究的进展”。熊老师的执着与真诚,换来了杂志社同他真诚地进行同情共感、互动合作。由此看来,这就不能仅仅简单地看做只是熊老师的一种生活态度了,而应该将此看做是熊老师的一种具有深厚底蕴的工作方法,看做是一种做事成事的人生智慧。
1992 年春,我与武汉出版社商定选题,计划主编出版一本“史学家自述其史学研究经验、方法和史观”的大书,在启动计划并组织一批史学家参与时,得到全国范围内史学家的赞同、支持和响应。在湖北省内选择史学家参与时,我想到了熊老师,并积极与他联系。在向我了解参与名单之后,他犹豫了好一段时间才答应下来。后来我才明白,他起初的犹豫不决,既是一种对师长辈史学家敬畏的真诚,也是一种出于职业敬畏的谦虚。这正如他在文中的真实真情地流露:“我现在该不该写这样的东西,犹豫了一番:原因之一,是本书的作者不少是我的师长(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教授、夏东元教授,——作者注),我不该和他们平起平坐;原因之二,有人说我也算‘功成名就’了,可以写。一是表明我的师长们后继有人,二是我的经历和体会或者对部分青年的学习多少有点启发。这样,我怎么想(当然也还是比较认真的想) 就怎么写出来,如实地写,不过,这个‘实’也不是完全可靠的,首先是记忆不一定准确,写的并非真正的‘实’,其次是观点和看法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是此时此刻我的一些想法。”他在文末还有“附记”,读来也觉得真情感人:“此文预约很久了,此次恩师吴泽教授从教治学六十年及八十华诞的纪念活动,我专程赴沪,利用途中这几天时间,有特别意义的完成此文。”对老师的感恩感激,反思不忘所来的路,跃然纸上,这不是一种真情实感,又是什么?唯有真情,才能感人动人。时隔近三十年了,他的这种真诚坦荡依然是浓烈的,依然十分感人!除了情感浓烈之外,其中还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吧!熊老师答应参与本书后,认真撰稿,一丝不苟,期间还数次与我交流、切磋。他说,他在最后一部分要写一段与主题无关的文字,希望我不要删去。接到稿件后,我深深地被作者倾注的真情实感和对于史学研究的执着追求所感动,我觉得大有益于史学研究事业,我怎么舍得删除这段精彩的文字呢!在名为“学无止境”的第十章,他说道:“这里最后谈一个‘学无止境’的问题”,“好在我还人老心不老,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毕竟是老,又仍然是和书本打交道,所以对‘活到老学到老’、‘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之类的格言,就有些切身的体会了……这就要求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恐怕还要到死。”④这些年来,熊老师无一日懈怠,坚持“学无止境”、“学到老活到老”,带研究生、教书育人,写论著、留下智慧结晶,精气神十足,忙得不亦乐乎!据我所知,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深受陶染,而母校历史系正是将他的这种精神情操视为学院的“宝贝”!今天,我们一起重温这些温馨的故事,可以从中获得人生经验的启发,把它积累转化成一种向上向善的文化,予以光大,泽惠后学。
内心的执着与真诚,是一种人性的坚定和坚韧,待人接物的执着与真诚,则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生命活力与激情。从本质上说,执着是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真诚是一种经由长期积累而由内向外抒发的善良。人生的执着与真诚,这既是一种自己坚定地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也是一种深藏于自身的处事为人方法,它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所具备的那些特性、特点和特征, 《语》 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⑤; 《书》 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⑥熊铁基先生对人对事的执着与真诚,对于他自己立业立言来说,这是极其难得的;对于后学作为精神文化滋养来说,这也是极其可贵的。这些可贵的文化内容,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是对人具有闪光智慧,因而是具有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最后,祝愿熊铁基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注释:
① 熊铁基: 《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轨迹》,《江汉论坛》1987 年第11 期;《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发展——汉唐文化史研究之一》,分别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7 年第 4 期、1990 年第 3 期。
② 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 年版。
③ 参见雷家宏:《简评〈汉唐文化史〉》,《江汉论坛》1993 年第6 期。这是有关该书几篇书评中的第一篇,也是其中最早的一篇。
④ 参详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载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 页。
⑤ 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 页。
⑥ 《尚书·周书·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