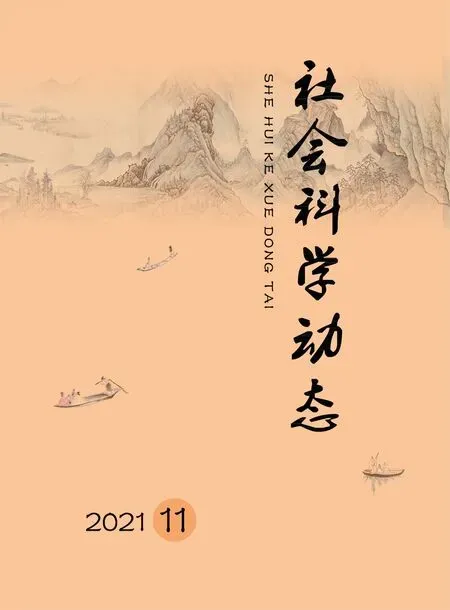潜邸时期的忽必烈与佛教徒
2021-01-27岑宇凡
岑宇凡
蒙元史学界有关忽必烈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相对而言,受限于史料,对他早年经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①目前对于“潜邸”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忽必烈招纳贤才,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如何学习汉法、行用汉法,并以此作为蒙古统治阶层开展“汉化”进程的论据。②如李治安先生在《忽必烈传》 中为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划出了六大群体,其中宗教僧侣群的代表人物包括八思巴、海云、萧公弼等。他认为“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但对忽必烈的个人宗教信仰,对日后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响颇大”③。笔者认同李先生的判断,即八思巴、海云等人对后来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吐蕃有巨大影响,有必要对潜邸时期忽必烈身边的宗教人士群体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从窝阔台至蒙哥汗执政时期,即所谓的忽必烈“潜邸”时期,忽必烈与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这一时期忽必烈的宗教观。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宗教的特殊性,不宜简单地把与忽必烈有过往来的佛教人士(尤其是那些高僧大德) 都视为他的幕僚。如禅僧海云,早在窝阔台汗时期就受到蒙古汗廷的召见,在蒙古治下的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在蒙古汗权转移到拖雷一系之后,海云仍受到蒙哥汗的信任。蒙哥即位之初就命海云“掌释教事”④,忽必烈亦曾请他前去,向他“问佛法大意”。⑤年轻的忽必烈对于海云甚是礼敬,《佛祖历代通载》称:“王(忽必烈) 以珠袄金锦无缝大衣奉以师礼。王固留师,师固辞。”⑥海云本人并未长期为忽必烈服务,不应视为忽必烈的幕僚。同样,八思巴也不宜简单地归为忽必烈的幕僚,尽管二人关系密切。在宗教意义上,八思巴甚至是忽必烈的师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潜邸时期忽必烈与佛教人士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归纳和分析,探讨早年经历对忽必烈日后宗教政策的影响。
一、忽必烈与有影响的汉地高僧
就目前可见的材料来看,忽必烈最早接触的应是汉地禅僧,其中又以海云及其弟子最为典型。除海云一系外,忽必烈与雪庭福裕等禅僧也有交往。以下就海云印简和可庵智朗师徒的事迹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海云印简
学界已经有不少关于海云印简的研究。⑦海云(1202—1257) 是金蒙之际著名的禅僧领袖,属于北方临济宗,他在前四汗时期汉地佛教界地位尊崇。元人王万庆称“太宗合罕皇帝、蒙哥皇帝,咸有命海云为天下僧众之首”⑧。已经有学者对海云印简禅师相关文物遗迹进行了考察。⑨有关海云的史料,最重要的是元人王万庆所撰的《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 (也称《海云碑》)和《佛祖历代通载》 中的记载。据邢东风校勘的《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⑩,其内容与《佛祖历代通载》卷21 所记的海云事迹大致相合。考虑到这两份文献对于海云的生平事迹记载较为详尽,因此本文对海云生平不再赘述。以下就海云与忽必烈的交往的史料进行分析。
据《佛祖历代通载》:
壬寅,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师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种种法要,开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时秉忠书记为侍。郎(引者注——疑为“即”) 刘太保也。复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师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备于佛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尘许,况一四海乎。若论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离心。而人不知天之与人,是其问别。法于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释迦氏之法,于庙堂之论,在王法正论品,理固昭然。非难非易,唯恐王不能尽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⑪
海云对忽必烈的影响,在于他最早向忽必烈建议“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倡导仁善、爱民、用贤等思想。壬寅年(1242)时,蒙古汗位尚未转移到拖雷一系,忽必烈的地位亦没有后来那么显赫。年轻的忽必烈尽管有雄心壮志,身边却没有足够的贤才。他向海云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体现了他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广阔雄心。当海云辞别之际,忽必烈还专门向他询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海云则回答道:“信心难生,善心难发。今已发生,务要护持专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见三宝有过。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⑫海云长期活跃于蒙古宫廷,向黄金家族宣扬佛法,受到蒙古贵族的尊崇。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治国理政的精要与崇奉佛教联系起来,在面对忽必烈的询问时,既给出可行的执政理念,同时又宣扬佛法广大,增加忽必烈对佛教的好感。前引“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的做法被海云都归入“佛法”中,向忽必烈点明了治理汉地的纲要,并将其归入佛法,有利于增加忽必烈对佛教的信赖。海云把仁善、爱民等品质划入佛教的“信心”和“善心”,告诫忽必烈“务要护持专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对于塑造年轻宗王忽必烈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师(海云) 既辞行,有一恶少年肆言讪谤,以佛法不足信。王闻之,乃召其人,训以大人之言,复以刑法罪之。专使白师。师回启曰:‘明镜当台,妍丑自现。神锋在掌,赏罚无私。若以正念现前,邪见外魔杀之可矣。然王者当以仁恕存心乃可。’王(忽必烈) 益敬焉。”⑬萧启庆先生把实行仁政、关爱百姓、任用贤才等作为忽必烈“汉化”的论据,称“他们(引者注——指潜邸旧侣) 启迪了忽必烈的汉化思想,尽力协助他重建汉地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并且进一步压制蒙古本位主义的反动而创建元朝。”⑭笔者认为,这个总结符合历史实际。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忽必烈的行为同样遵循了海云的教诲。汉地儒士劝诫忽必烈“止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等爱民的思想,海云很早就以讲解佛法的方式告诉过忽必烈。海云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有助于忽必烈了解汉文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忽必烈对佛教的认可。
海云死后,忽必烈下令在大庆寿寺之侧建塔,并命令王万庆为海云撰碑文。⑮海云有关“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的论述,为忽必烈日后崇奉佛教奠定了基础。
(二) 可庵智朗
可庵智朗没有专门的传记,但对于他的事迹,周清澍、党宝海两位先生已经做了归纳整理。⑯智朗是临济宗禅师海云的弟子,也是忽必烈的亲信、元朝早期重臣刘秉忠(1216—1274) 学佛时的师傅。据王博文《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载:“海云传可庵朗、龙宫玉、赜庵儇。可庵传太傅刘文贞公、庆寿满。”⑰赵孟頫页《临济正宗之碑》也称:海云有“大弟子二人,曰可庵朗、赜庵儇。朗公度荜庵满及太傅刘文贞”。⑱海云印简和可庵智朗师徒在元代地位很高,他们死后,部分舍利安放在燕京庆寿寺(北京双塔寺),直到明代仍被供奉。成书于明代的《帝京景物略》 称:“今寺(双塔寺) 尚有海云、可庵二像, 衣皆团龙鱼袋。”⑲
《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记作《护必烈大王令旨》)之碑立于甲辰年(1244) 二月,其中提到智朗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表明他曾在此前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向蒙古贵族传授佛法。海云印简和可庵智朗师徒当是忽必烈最早接触到的一批中原人物,并且受到忽必烈的尊崇。而他们的弟子刘秉忠则成为了忽必烈招揽人才和崇奉佛教的助手。据党宝海先生对《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的研究,其汉文部分很可能出自刘秉忠之手。周清澍先生指出:“忽必烈最早对中原关心的是佛教, 通过僧侣的引见, 才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⑳海云印简、可庵智朗等汉僧在漠北与忽必烈的交流,增加了这位宗王对汉地的了解。对忽必烈本人而言,海云印简、可庵智朗、刘秉忠等人的帮助和交流引起了他对佛教的崇奉,也增加了他治理天下的经验。
二、忽必烈幕府中的佛教徒
有关忽必烈即位之前的幕府人员,萧启庆先生曾对“潜邸旧侣”进行过考察。㉑萧启庆先生指出“潜邸旧侣”对忽必烈有巨大影响,重在关注他们对忽必烈行汉法、接受儒家思想的推动作用。应当指出,这也是元人比较常见的看法。如赵孟頫页称:“(靳德进) 且言世祖潜邸,延四方儒士,谘取善道,故能致中统、至元之治。”㉒《元史·世祖本纪》也称:“岁甲辰(1244),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㉓
通过梳理海云印简和可庵智朗师徒对忽必烈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的做法与海云的教导是一致的。最早在忽必烈幕府中服务的佛教徒就是刘秉忠。据《元史·刘秉忠传》:“(刘秉忠) 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倶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㉔可见,刘秉忠自壬寅年(1242) 起留在忽必烈身边服务,为忽必烈招揽人才、扩充幕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熟悉汉地情况的刘秉忠,为忽必烈提供了招揽中原人才的便利。㉕据萧启庆先生研究,经刘氏援引入忽必烈潜邸的,包括张文谦、李德辉、马亨、王恂、刘秉恕(其弟)、张易、李俊民等。㉖刘秉忠还曾于1253 年推荐刘肃、脱兀脱、李简、张耕治邢州,促成了“邢州之治”。王磐所撰《文贞刘公神道碑铭》称:
燕闲之际,每承顾问,辄推荐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宜见录用。由是弓旌之所召,蒲轮之所近,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至无虚月,逮今三十年间,扬历朝省,班布郡县,赞维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荐之余也。㉗
由此可见刘秉忠对忽必烈的巨大帮助。值得说明的是,刘秉忠“虽居左右,而犹不改旧服,时人称之为聪书记”,直到至元元年,才因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上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并“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赐第奉先坊”㉘。史料表明,刘秉忠从进入忽必烈幕府直到至元元年,20 多年中都是以“聪书记”的身份辅佐忽必烈。王磐说他“晚娶无子,以犹子兰璋为嗣”㉙,可知他此前长年未婚娶,应是长期保持着佛门弟子的身份。《元史·刘秉忠传》说他“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并且直到他去世的至元十一年,“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尝筑精舍居之”㉚,依然保持着佛门弟子的生活习惯。王磐所拟的铭文中,有“不坐官府,不趋朝行。褐衣蔬食,禅寂倘佯”的说法,也可见一斑。㉛
我们不宜把倡导仁爱、实行仁政都简单地划归为儒家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佛教慈悲情怀的体现。王磐所撰《文贞刘公神道碑铭》:“上神武英断。每临战阵,前无坚敌而中心仁爱,公尝赞之。以天地好生为德,佛氏以慈悲济物为心,方便救护。所全活者,不可胜计。”㉜刘秉忠劝诫忽必烈仁爱,既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他作为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心。
忽必烈幕府中另一位佛教徒是张易。由于涉及刺杀阿合马被处死,张易在《元史》中无传,也没有留下行状等专门记叙其生平的材料。20 世纪40年代,唐长孺先生首先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撰《补元史张易传》,对张易的生平进行了考察。㉝此后,袁冀、白钢、王颋等学者也对张易生平以及刺杀阿合马事件进行了研究。㉞近年,毛海明、张帆通过史料梳理指出王恽《秋涧集》中提到的“元仲一”即张易,推进了张易生平事迹的研究。㉟尽管围绕张易生平尚有许多问题不清楚,但张易为佛教徒这一史事,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前文提到刘秉忠向忽必烈举荐了张易。刘致为姚燧编写的《年谱》 中提到“右丞则前书记张公也。本姓鲁,父名聚……父为人所杀,其母负公行丐于市。至郝太守家,有张孔目者无子,携去,养以为子,因冒张姓。长祝发为僧。及遇知世祖皇帝,得所攀附云”。㊱张易字仲一,除了“张仲一”的称呼外,前辈研究者认为《元史》中提到的“张启元”也是张易。㊲毛海明、张帆前揭文推测“启元”是张易的法号,并考证张易在1253 年受到忽必烈的正式聘请,1254 年初前往忽必烈军营,那时忽必烈正率军出征大理。㊳与刘秉忠相似,张易在忽必烈幕府担任书记。有关张易在忽必烈幕府中的事迹和地位,毛海明、张帆前揭文已经做了细致的梳理,指出张易虽然入幕较晚,但地位较高。㊴
《至元辨伪录》记载开平佛道辩论裁定道士失败之后,“有一道士潜隐名性(引者注——疑为“姓”),不胜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岁,驾言寿永,以倾僧人。上(引者注——此处指忽必烈) 召问曰:‘尔既多年,当初宋上皇时僧有何过,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往来,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说谎人也。’使寮佐张仲谦、元学士穷考年数。乃三十余岁,本刑(引者注——疑为“邢”) 州人也。上怒其不实,始则配塗役夫,终竟喂了豹子。”㊵毛海明、张帆前揭文推测材料中的“元学士”就是张易。㊶《至元辨伪录》未提到“张仲一”,但从刘秉忠也在佛教阵营中参加此次辩论的史实来看,这一推断比较可靠。《至元辨伪录》完成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那时张易已因阿合马案被忽必烈处死,编纂时有可能不提及他,只在此处留下了模糊的称呼,亦合情理。
三、忽必烈与藏传佛教僧人
藏传佛教在蒙古贵族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从藏文史料看,忽必烈先后接触了藏传佛教多个教派。据米玛次仁对《贡塘寺志》的研究,忽必烈是蔡巴噶举派的施主,与贡塘寺有着供养关系。㊷王妃察必在赞扬八思巴的时候也提到,先前蔡巴等老僧们不如八思巴知识渊博。㊸噶玛噶举派噶玛拔希也曾受到忽必烈的迎请,但他最终拒绝了忽必烈要求他留在身边的邀请,前往甘州一带传教。㊹对于藏传佛教的几个派系,忽必烈均有过接触,最后决定皈依萨迦派宗教领袖八思巴。
藏传佛教僧人中,对忽必烈影响最大者是八思巴。㊺按陈得芝先生的梳理,八思巴19 岁的阴水牛年(1253),他应召到忽必烈驻地六盘山谒见。初次应对时,八思巴因谏请忽必烈不要向吐蕃地区摊派兵差未被采纳,心中不悦,遂请求返藏。忽必烈本已准许, 后听从王妃察必之言再次与八思巴会谈。八思巴对答的吐蕃史事,经查证史书和派人入藏调查被证实,于是察必请他传授了喜金刚灌顶,忽必烈在察必的劝说下接受灌顶。 《萨迦世系史》这样记载:“当法王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1253),薛禅汗请求传授灌顶,封其为帝师,并赐给刻有‘萨’字镶嵌珍宝的羊脂玉印章。此外,还赐给黄金、珍珠镶嵌的袈裟、法衣、大氅、僧帽、靴子、坐垫、金座、伞盖、全套碗盏杯盘、骆驼及乘骡、全套金鞍具,特别是赐给上述的各万户及法螺等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㊻
忽必烈率军出征大理时,八思巴去凉州为法主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忽必烈从大理班师时,给八思巴颁发了一道令旨(被称为“蕃字札撒”) 并赏赐白银、茶、锦缎等物。
宪宗七年(1257),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宪宗八年(1258),23 岁的八思巴作为佛教一方的首领参加了在上都宫殿举行的佛道辩论会,取得了辩论的胜利。藏文史料在谈到此事时这样记载:“(八思巴) 前往王宫举行佛法之时,见有信奉太上老君之教、修行神仙之道士多人,沉溺邪见,害人害己。于是,遵照皇帝之命,八思巴与多年修习道教的道士辩论,折服了所有的道士,使他们出家为僧,持佛教正见。”㊼此后忽必烈率军进攻南宋,渡江围鄂,最终因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于己未年闰十一月辛未日(1259 年12 月17 日),率领部分军队北返,闰十一月己丑日(1260 年1 月4日) 抵达燕京,随即着手准备称汗。㊽中统元年(1260) 四月,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同年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㊾这不仅体现了他和八思巴之间及其紧密的联系,也有争取佛教势力以及稳定西藏的用意。
四、忽必烈的宗教观
忽必烈年轻时在漠北,首先接触到的是汉传佛教,其中又以临济宗影响最大。他和其他蒙古贵族一样,对高僧大德十分尊崇。早在1242 年,忽必烈就向海云请教佛法,并询问佛法中是否有安天下之法。海云把治国理政的精要与崇奉佛教联系起来,告诉忽必烈“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这既为忽必烈提供了一定的执政经验,又宣扬了佛教,给年轻的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随海云的子聪(刘秉忠) 则受到忽必烈的青睐,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是忽必烈集团中的中流砥柱。在刘秉忠的辅佐下,忽必烈积极招徕汉地贤能,逐渐组成了一个忠诚可靠、人才济济的幕府集团。忽必烈仁爱待人、求贤若渴的态度,不仅仅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尊奉佛法的表现(是一种由经海云阐释的、能“安天下”的佛法)。尽管在吸收汉文化、任用汉人方面,忽必烈有过波折,但在崇奉佛教方面则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向汉地僧人请教佛法,还积极向藏传佛教学习,最终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在礼奉高僧、修建寺庙等方面,忽必烈一直是以佛教的保护者和弘扬者的面貌出现的。在他主持的开平佛道辩论中,他裁决佛教徒取得胜利,勒令道士削发为僧,退还侵占的寺产,并焚毁诋毁佛教的“伪经”。
在宗教管理方面,忽必烈沿袭了蒙古国的传统,保护一切宗教,让他们为皇室、国家祈福,既崇奉佛教,也保护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也任用道士为自己服务。在和八思巴相处方面,既符合佛教礼仪,尊为帝师,又注重维护大汗权威,利用宗教巩固皇权。在政治上,忽必烈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符合海云的阐释。因此,可以多角度地看待忽必烈爱民、行仁政、用贤才的事例,它的动因并不仅仅是忽必烈的“汉化”,也不仅仅来自于忽必烈身边儒士的影响。从宗教的角度看待,会得出新的认识。
忽必烈并非一个完全虔诚某种宗教或学说的人,他对于各种宗教甚至方术都不排斥。对于宗教,他评判的主要依据为是否名副其实,其言论是否可靠,对于经常“灵验”的宗教比较信任,反之对于自我吹嘘、夸大效果则比较反感。壬寅年(1242) 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三教高下时,海云曾称:“诸圣之中吾佛最胜。诸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㊿忽必烈信任佛教,与海云向他倡导的能“安天下”的佛法行之有效密不可分。海云曾告诉忽必烈,“我释迦氏之法,于庙堂之论,在王法正论品,理固昭然。非难非易,唯恐王不能尽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51]后来忽必烈确实经常向汉地士人贤才求问古今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海云“佛法最真,唯僧无诈”的说法,至少对忽必烈而言并非空洞无用、吹嘘自夸之语。他身边的儒士群体向他提供的儒家学说,也因为有助于治国理政而得到忽必烈的采信。刘秉忠本人更是因为善于阴阳术数,得到忽必烈的重用。《文贞刘公神道碑铭》载:“(刘秉忠) 享年五十有九。讣闻,上嗟悼不已,语群臣曰:‘秉忠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危,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预闻也。’”[52]刘秉忠“占事知来,若合符契”的本领,深受忽必烈的赞赏。尽管这种阴阳术数并非出于儒释道等影响较大的宗教或学说,但由于经过长期的检验,忽必烈仍然十分信任。
潜邸时期,最能典型反映忽必烈宗教观的事件就是开平佛道辩论和焚毁道藏。[53]开平佛道辩论之后,蒙哥、忽必烈下令焚毁除《道德经》以外的全部道藏。[54]至元十八年(1281) 忽必烈颁布的焚毁道经的圣旨称:“戊午年(1258) 和上先生每折证佛法,先生每输底上头,教十七个先生剃头做了和上,将先生每说谎做来的化胡等经并印板,教烧毁了者。随路观院里画着的、石碑镌着底八十一化图,尽行烧毁了者,么道。”[55]蒙哥、忽必烈最终裁断“焚伪经四十五部”[56],对这批应予焚毁的道经的定性,正是强调“说谎做来的”。前引《至元辨伪录》提到忽必烈对某道士处以严酷的惩罚,“始则配塗役夫,终竟喂了豹子”[57],理由也是此人说谎。
开平佛道辩论之后,蒙哥汗下令焚毁含有诋毁佛教和吹嘘道教的内容的道藏,这一决定也得到忽必烈的支持和贯彻。尽管忽必烈在开平主持佛道辩论时裁决道士败落,但这并没有导致他对道教的片面反对。忽必烈即位之后,对于各种宗教的说辞,仍经实践检验才崇信。至元十三年(1276),随着江南地区的初步平定,忽必烈召正一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觐见。 《元史·释老传》 载:“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58]王一清原为南方人,蒙哥汗在位时前往北方传教并积极为蒙古效力,后来又随忽必烈进攻鄂州并死在那里。[59]从元军初定江南忽必烈即召见张宗演并“命主领江南道教”来看,张可大、张宗演父子很受忽必烈重视。除去要笼络江南道教势力为元朝服务之外,张可大灵验的预言显然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忽必烈“神仙之言验于今矣”一语,表明了他对张可大的敬佩,以及这种重视灵验的宗教观。而对于夸大异能、故弄玄虚的道经,至元年间仍发布了几道焚毁“伪经”的圣旨。成文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 的《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载:“上(忽必烈) 曰:‘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之未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60]可见忽必烈也注重现实影响,并利用这种实践检验减少政策的阻力。
海云印简对佛法的解释契合了忽必烈的需求,对忽必烈日后的行为有着不小的影响。经海云的阐释,崇奉佛教与治国爱民、招贤纳才并行不悖。这一点启发我们,不宜简单地把潜邸时期的忽必烈思想和活动限定在“行汉法”、学习吸收儒家文化这一个层面。海云、八思巴等高僧与忽必烈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君王与臣民的关系,从宗教的角度分析更为恰当。
总体来说,忽必烈的思想既表现出崇奉佛教的一面,又表现出宽容各种宗教的一面。忽必烈对于各种宗教,主要秉持一种朴素的检验意识,如果一种宗教或学说能言行一致,得到现实的验证,他就予以保护和信任,如果一种宗教或学说夸大不实,则予以打击和惩戒。他对于佛教的崇奉,与海云所传授的“佛法”在实际政治中有助于治理天下有关。开平佛道辩论对道教的打击,主要是基于道经不实,而不是对道教所有派系和论述的全面否定。
注释:
①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载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版;舒正方:《在潜开邸思大有为于天下——潜藩漠北时期的忽必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周清澍:《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1 期;党宝海:《〈朗公开堂疏〉与忽必烈蒙古文手迹》,载李治安主编:《庆祝蔡美彪教授九十华诞元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607—619 页;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65 页;有关忽必烈与汉族儒士的交往,参见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6—166 页。
②㉑㉖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 113—143、113—143、122 页。
③ 李治安: 《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 页。
④《元史》卷3《宪宗本纪》。
⑤ ⑥ ⑪ ⑫ ⑬ ㉗ ㉙ ㉛ ㉜ ㊿ [51] [52] [55] [56] [60] [元] 念 常 :《佛祖历代通载》 卷21,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49 册,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年版,第704、704、704、704、704、706、706、706、706、704、704、704、707、708、709 页。
⑦ 蒋九愚:《海云印简禅法思想探析》,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584—600 页。
⑧[元]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对于此碑,今人邢东风进行了校对和整理,参见邢东风:《海云印简禅师相关遗迹漫谈》,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570 页。
⑨⑩ 邢东风:《海云印简禅师相关遗迹漫谈》,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553—583、570—583 页。
⑭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载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43 页。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于“汉化”有不同的界定。萧启庆先生所讨论的“汉化”,是指“两个民族或群体长期接触而导致文化上从属群体放弃其原有文化并全面接受文化主宰群体的文化,与后者融为一体,不可区分”。
⑮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钦承护必烈大王令旨,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望临济为十六世”。邢东风:《海云印简禅师相关遗迹漫谈》,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570页。
⑯ 周清澍:《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1 期;党宝海:《〈朗公开堂疏〉与忽必烈蒙古文手迹》,载李治安主编:《庆祝蔡美彪教授九十华诞元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607—619 页。
⑰ [元]王博文:《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元碑已不存,录文转引自刘友恒、李秀婷:《〈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浅谈》,《文物春秋》2007 年第5 期。
⑱ [元]赵孟頫页:《松雪斋文集》卷9《临济正宗之碑》,《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沈伯玉刊本;据《佛祖历代通载》卷22 所收赵孟頫页《临济正宗之碑》,该文写于至大二年。
⑲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3 页。
⑳ 周清澍:《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1 期。
㉒ [元]赵孟頫页:《松雪斋文集》卷9《靳公墓志铭》。
㉓㊾ 《元史》 卷 4《世祖纪一》。
㉔㉘㉚ 《元史》 卷 157 《刘秉忠传》。
㉕ 唐长孺先生较早注意到了刘秉忠在忽必烈进用汉文人过程的作用。参见唐长孺:《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原载《学原》 1948 年第2 卷第7期,后收入唐长孺:《山居存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503 页。
㉝ 唐长孺:《补元史张易传》,载《山居存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1—531 页。
㉞ 袁冀:《试拟元史张易传略》,收录于袁冀《元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4 年版,第126—139 页;白钢:《论元初杰出政治家张易》,《晋阳学刊》1988 年第3 期;王颋:《变止宫门——张易生平及阿合马被杀事件》,载王颋:《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82—95 页。
㉟㊳㊴㊶毛海明、张帆:《元仲一即张易考——兼论元初名臣张易的幕府生涯》,《文史》2015 年第1 辑。
㊱ [元]刘致:《(姚燧) 年谱》至元四年条,参见姚燧:《牧庵集》附录,《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 册。
㊲ 参见唐长孺、白钢、王颋前揭文。
㊵[57] [元]祥迈:《至元辨伪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 册。
㊷米玛次仁: 《蔡巴万户历史考——以藏文文献〈贡塘寺志〉为中心》,《藏学学刊》2014 年第1 期。
㊸㊻㊼ [元] 阿旺·贡噶索南: 《萨迦世系史》,陈庆英、周润年、高禾福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7、111、122 页。
㊹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 《西藏通史·元代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6 页。
㊺ [意]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张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5 页;张云:《忽必烈处理藏传佛教政策的分析——以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为核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5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2—69 页。陈得芝先生专门对1251—1253 年之间八思巴、忽必烈两人的活动进行了梳理,见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㊽ 《元史》卷4《世祖纪一》。本文的公历日期换算参考洪金富编:《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 年版。
[53] 有关开平佛道辩论请参见周清澍:《论少林福裕和佛道之争》,《清华元史》第1 辑,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8—73 页。
[54] 一般认为蒙哥、忽必烈要求焚毁的是除《道德经》以外的全部道藏。张云江则认为至元十八年(1281) 焚毁道经的命令只是焚毁道藏中部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的著作,而非除《道德经》外的全部道藏。参见张云江:《元初华北地区佛道论争事迹考辨》,载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4 页。
[58] 《元史》卷202《释老传》。
[59] 有关王一清的活动请参见樱井智美:《〈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元史论丛》第10 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年版,第363—372 页;刘晓:《元代皇家五福太一祭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