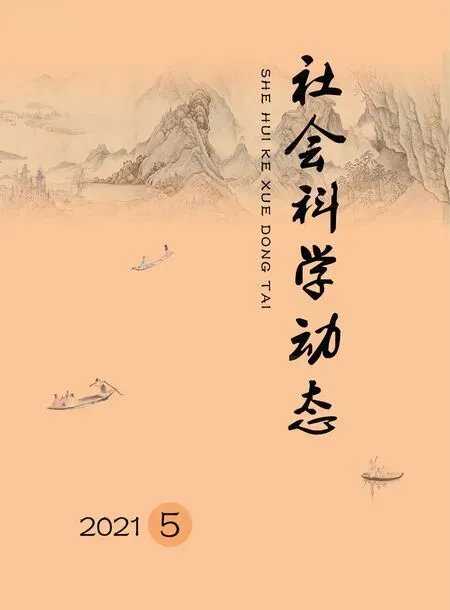戈夫曼的行动理论:基本假定与分析要素
——基于SIAC 图式的修正
2021-01-27王晴锋
王晴锋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以下简称戈夫曼)以拟剧论为学界所熟知,他可谓20 世纪下半叶最负盛名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目标是推动面对面互动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他将该领域冠名为互动秩序,并采取微观分析的研究方法。①在戈夫曼看来,社会分析的首要对象是日常生活中真实行为的结构及其组织。②戈夫曼以敏锐的洞察力聚焦于通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者被熟视无睹的事物,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或微不足道的行为,从而揭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和互动秩序的微观运作逻辑。面对面互动涉及一系列的条件,诸如,行动者能够彼此感知的共同在场、信息的接收与发送、即时性的过程监控以及共享的情境定义等。戈夫曼主张对互动秩序进行非帕森斯式研究,为此,他提出了一套用于分析面对面互动系统的核心概念与术语,以此探讨人们对自身、他人和现实的认知,包括何谓真实的感知及经验的限度等,并且逐渐形成关于互动秩序的系统化理论。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的微观行动理论,先是大致勾勒出他关于面对面互动的一般性论述,主要涉及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法则,然后引出菲利普·曼宁(以下简称曼宁)总结的关于戈夫曼行动理论的SIAC 图式,本文的重点是在曼宁图式的基础上提炼出CEIT模型,以期深入探讨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基本假定与分析要素。
一、 面对面互动法则: 促成与限制
戈夫曼研究的是“世俗互动”③,他的著作大多是探讨公共场所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在戈夫曼那里,个体是具有某种态度、立场或姿态的实体,他在认同或反对某个组织/机构之间占据着某个位置,并随时准备通过改变参与卷入的方向以恢复均衡。④社会行动者往往设法保护和维持整全的自我,因此他们参与的互动也应该符合自我的旨趣。大体而言,戈夫曼社会学里的个体具有三重性,即他是自决的、应激性的(动物行为学意义上)和社会性(仪式意义上)的存在。互动的先决条件和自我的需求限制着互动的属性以及进程,这些限制性条件也可以被理解为互动的基本规则。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那些频繁出现的特征根源于社会生活的某些普遍性条件,而互动规则亦源自于社会,它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按照戈夫曼的理解,面对面互动领域主要关注的是互动的“交通规则”,而不是人们为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结果如何。互动规则相对独立于个体,类似于语言与语法、句法之间的关系一样,每一位个体都需要学习行为的语法规则,从而使其行为举止恰如其分,符合情境与社会的特定要求。倘若个人不遵从这些规则,那么将可能危及他们整全的社会性自我。这些规则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关于特定情境中如何行事的说明;第二种是对行为期待的背景预设;第三种是统摄其他一切规则的规则,即要求表明行为背后的通情达理和可说明性,戈夫曼将这一要求称为“言辞适切的条件”。⑤行动者希望通过操控互动秩序的规则来达到特定的互动效果,正是这些情境操控者使互动的基本法则变得明晰可见。
谈话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形式。戈夫曼的谈话分析图式包括局外人,这表明他的阐释不仅仅针对聚焦式互动,而且也囊括了更广泛的社会情境。戈夫曼认为在分析谈话时,区分熟人与非熟人颇为重要。共同在场的他人可能无法理解熟人之间的谈话,因为他们无法解码那些谈话中缺损的信息,而熟人能够通过带入互动情境的共享记忆和知识填补这些信息空洞。熟人之间的谈话具有既成的和可辨识的对话结构和框架,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先前的话轮、主题和身份共享以及特定情境中即时性生成的谈话指涉。“作为普遍的规则,社会情境中相识的人需要理由规避彼此进行面对面参与,而不相识的人却需要理由开启面对面参与”。⑥在相识的个体之间,相互给予社会性认可的意愿可以避免个体被有意识地忽视;而在不相识的个体之间,适当地抑制开启新交遇(encounter)的恳求则不致于使个体遭受各种不合时宜的主动示意或请求。换言之,陌生人之间发生互动需要适当的理由或借口,故而存在各种开启互动、获取信息的途径,较为典型的是请求“免费供给”,诸如,询问时间、吸烟借火、借座(有空着的座位但仍要询问能否就坐)等。这些行为很可能并非目的本身,询问时间的人可能自己有手表,借火者可能有打火机,而借座者完全可以坐在别的位置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引出进一步的互动序列。互动参与者犹如“信息储存筒”,每一位潜在的询问者“能够通过某种访问序列允许进入文档”。⑦这些都是面对面互动的一般性法则,其背后的潜在原则是个体向他人开放自己(表明自己可资利用)但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
任何互动规则都包含着不同的自然框架或社会框架。例如,下棋者在走棋时需要通晓博弈规则(社会框架),而下棋者在作出移动棋子这样的操作时则涉及细微的身体运动框架(自然框架)。下棋的规则和戈夫曼隐喻地提出的“车辆交通”规则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对参与者目的管控的理解,后者没有规定行程、目的地以及为何前往,而仅是对行程的实现过程施加某些限制。在《公共场所的行为》里,戈夫曼探讨了管理人们共同在场行为的公共秩序,它与社会秩序相类似。互动过程中参与者不断呈现的眼神、姿态、话语等是“态度和参与的外显标志”。⑧在特定的社交场合,个体的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都需要与所参与的情境和活动保持协调一致。因此,戈夫曼认为,互动研究的对象“不是个体及其心理,而是共同在场的不同个体行为之间的句法关系”⑨,也即这些“态度和参与”的社会组织形式。戈夫曼还运用语言学的隐喻来分析互动的“句法关系”,认为语言交流包含三个部分,技术的、契约的和社交的语言交流,它们构成了细微的礼貌、谦恭和尊重。⑩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行动者随时准备接收各种情境信息并作出有效反馈,通过印象整饰和面子工夫维护个人外表或保全面子,并在主要卷入与次要卷入之间进行适当的卷入配置等,这些都构成了面对面互动的重要内容。同一个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有彼此寒暄、交谈的权利和义务。当与他人共同在场时,个体会有意无意地提供关于自身的信息,诸如,性别、年龄、阶级、健康状态以及种族等,其中很多信息是在无意中传达的。有些表意性的情境道具相对固定,它们的状态在互动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某些关于个体的呈现形式反映了缓慢变化的或者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属性。而有些行为是迅速变化、转瞬即逝的,如,谈话过程中应激性的言语和身势表达等,它们同样提供了有关行动者自身的信息。包含特定角色丛与行为举止的互动关系将会产生独特的社会现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展演重大戏剧行动的场域、一种存在的阶段、一台意义的引擎以及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成体系的世界”⑪。涂尔干认为,有一种外在的、社会性的力量约束着个体的行动,而在戈夫曼看来,这种制度性约束仅是社会约束的其中一种形式,另一种是互动性约束。在面对面互动系统中,关联性原则与非关联性原则是共同维持情境定义的重要原则。从表面上看,这些关于“专注管理”的规则似乎是社会生活的非实质性要素,它们仅仅是关于礼貌、规矩和礼仪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脆弱的规则,而不是外部世界不可撼动的特征,才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坚实感。⑫
二、 曼宁的 “SIAC 图式”
由于戈夫曼研究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事物,因此他经常不被认可是社会理论家。但是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戈夫曼是一位系统性的理论家,他关于互动秩序的分析可以整合到社会秩序的理论传统中。曼宁亦认可戈夫曼在理论建构方面作出的努力,指出他关注构成面对面互动的规则和基本假设,进而探讨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理论。1951 年,帕森斯在《社会系统》 (The Social System)一书里将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化为若干要素或进程,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以及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这也是社会系统的功能必要条件,分别对应着经济、政体、文化和社会四个亚系统,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AGIL 模式。帕森斯的理论后来遭到美国左翼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判,认为其浮夸、过度抽象并且无法进行经验检验。⑬受到帕森斯提出的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的AGIL 模式启发,曼宁指出,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的互动系统研究也存在四个基本假定,它们分别为“情境适当”(Situational Propriety)、“参与卷入” (Involvement)、“易接近性” (Accessibility)以及“礼节性忽视”(Civil Inattention),即所谓的SIAC 图式,这是戈夫曼关于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阐释图式。日常互动中的人们在维持自我独特身份感的同时忠实地遵循着SIAC 图式,不同社会情境里的面对面互动之所以能够朝着有序、可预期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重要的假定。鉴于很多读者对SIAC 图式并不熟悉,而且该图式也是本文的重要对话点,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解释。
(一)情境适当
情境适当和情境失当这对概念源自戈夫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情境适当涉及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如何行动的实践知识,包括姿态、谈话用语、身体距离以及各种细微的生活礼节等。与情境适当对应的是情境失当,即个体的行为不符合或无法满足特定情境的要求,它体现了微观互动领域的结构性压力。行动者一旦无法表现出应有的实践能力,很可能被他人认为是“异常”或“失能”,此时行动者会通过各种补救性措施挽回失误,如,找各类托辞,说自己疲乏劳累、笨拙不堪、很不礼貌等,从而让共同在场者及时地将他重新纳入原有的互动道德体系。戈夫曼用情境适当的概念批评了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精神病学领域用非生理性的指标诊断精神疾病,即根据外在的行为表现作为判断个体“精神是否正常”的依据。这些精神病学家将某个社会、文化无法接受和难以容忍的行为归类为“精神病”范畴,使之与“正常行为”“正常人”分离开来,并对其施加监控与规训,从而维持“正常”社会的“纯净”“健康”与“和谐”。由此,戈夫曼揭示了精神疾病的社会建构性:
很多精神病行为是由于未能遵守面对面互动行为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由某些评估性的、审判性的或者监管性的群体制定,至少由它们来实施执行。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病行为应该被称作一种情境失当。⑭
在戈夫曼看来,这些所谓的“精神病人”实质上是缺乏某种成员资格能力,而这种成员资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建构的。情境适当背后是这样一种理念,即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嵌入在特定的情境里,若对行动发生于其中的情境一无所知,那么也无从知晓该行动的意义。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某种疯狂的举动或不雅的言语在另一种情境里是可以被完全理解和接纳的。因此,不能仅用行为表征作为判断心理病症的依据。戈夫曼认为,精神病学成为一种极具压制性而又难以反抗的国家治理术,它已经弥漫式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有人都难以逃脱它审视的目光。精神病学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具体代理人,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权威身份公开介入私人的精神生活并进行粗暴干预,这再次体现了知识/专家与权力/制度之间的合谋。
(二)参与卷入
戈夫曼在《公共场所的行为》里指出,“卷入参与是个体对于某些在他身边发生的活动给予或拒绝给予关注的能力”⑮,它表达了行动者特定的目的或意图。在这之前,戈夫曼在他的博士论文《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里指出,互动过程有时会产生“欣愉感”,这有助于行动者在社会聚集场合的参与活动。自然地投入并参与互动是一种需要拿捏得当的行为艺术,参与者不能唐突地对他人正在进行之中的谈话进行插话,并确保不会破坏整个谈话氛围。个体的行动需要恰到好处地满足他的卷入义务,但是他又不能仅仅为了履行这些义务而行事,因为这样做会使他将注意力“从谈话主题转移到如何应对自发性卷入的问题”⑯。社交场合的个体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他们“会强烈地感到必须表明自己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当前的事件,他拥有的能够进行互动的自我不能被淹没”⑰。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须规避某些疏离性的举动,诸如,对互动之外事务的全神贯注、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等,这些因素都会使参与者分心,转移对当下互动的注意力。因此,参与者“不仅仅只是在过程中表达一种投入,同时还表达了在投入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微妙平衡”⑱。
戈夫曼区分了支配性参与和附属性参与。在支配性参与中,特定的社交场合迫使或责成个体承认某些加诸在其身上的要求;而附属性参与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它是支配性参与的一些次要的、补充性的参与,且行动者可以随时退出。同一项活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参与者那里,它的参与属性和地位甚至可能发生逆转。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时刻不停地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参与,交替进行着支配性参与和附属性参与行为。附属性参与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它赋予高度社会化行为中的个体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表明即使是结构化的互动行为也存在各种缓解和释放张力的隙缝,从而使惯例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情境充满一定的灵活性。每一次日常生活中的互动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参与介入,行动者在任何互动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投入,即符合社会规范和角色期待的适当参与,互动参与者则根据不同的“卷入结构”调整参与程度。倘若在特定的情境中投入程度不当,那么参与者可能因此受到制裁。当个体处于某种互动情境并需要向在场的他人表明自己的行为卷入程度时,他也可能掩饰自己真实的参与状态。行动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人际互动系统存在“参与防护盾”的设置,它确保个体在不同的场合能够选择恰当程度的参与。譬如,当父母吵架时,孩子在旁边故意打开电视机,当做没听见;又如,当拥挤的公交车上有小偷正在行窃时,旁边的乘客若无其事地看着手机,装作没看到。在社交场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偷听别人谈话的人,他们也需要刻意地表现出漫不经心、专注于其他事情的模样。参与卷入还涉及“过度投入”的情况⑲,即互动卷入过度,行动者过多地承诺或承担互动义务,这种情况也会影响互动的正常进行。
(三)易接近性
通常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会对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促使他们躲在安全的“保护性气泡”里,以捍卫自我的领地。然而,除了这种对互动而言是疏离性的特征之外,行动者还具有易接近性的特征,否则社会互动将难以为继或可能面临崩溃。对所有熟人或得到承认的陌生人而言,在场的个体都是“可接近的”或是“可获得的”。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行动者不排斥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并以礼相待,同时也期待他人能够如此行事,即所谓的“礼尚往来”。个体往往用微笑、眼神接触等善意的身势语交流来表达这种易接近性。个体层面的这种易接近性体现了涂尔干式的社会团结,这也类似于齐美尔所说的“社交性驱动力”,使离散式存在的个体产生信赖感,并趋于形成互动。然而,易接近性也使个体面临着各种不希望得到的关注,如陌生人的问路、乞丐的乞讨以及形形色色的搭讪等,此类行为违犯了人际互动的礼节性忽视原则。礼节性忽视原则能够恰当地处理公共场所对陌生人的尊重和冷漠之间的关系,它包含着身体上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和行为上的自由选择。人际间交往得以可能的另一个条件是行动者对周围的人和事物具有持续不断的反思性监控能力,他们能够及时判断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及时地筛选互动对象并甄别易接近性的程度。
在公共场合,“自我谈话”被视为是一种情境失当行为,因为“警告他人这样一种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即在所有在场者中预先存在一种共同维持的相互可理解的基础”⑳。同时,它也违反了易接近性原则,由于自言自语者是自我封闭的,对他人而言是不可获得的,这实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自我卷入”,它对人际互动中的主体间性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动参与者必须避免所有形式的自言自语,或者认为它们都是无关紧要的或是毫无意义的。戈夫曼认为,某些场合的自言自语,确切地说是那些下意识脱口而出的词汇,是非常重要的沟通形式,它们可被用来向共同在场的他人解释自己的失误或反常行为。这种情境下的自言自语,其实有它特定的表演对象,即那些共同在场的行为观察者。在这里,戈夫曼讨论的是那些诸如“哎呀”“啊哟”等表示惊讶、懊恼等语气词,即所谓的“溢出性叫喊”。“溢出性叫喊”表明,行动者对现实世界暂时失去控制,同时也向共同在场者表明他遇到的失控仅仅是一个小问题,他完全有能力进行应付;而且这些失误或失控不足以表明他是有行为缺陷的,正常的解释框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当发生行为失当时,倘若个体缺乏这些“溢出性叫喊”来进行自我调解和解释,那么,他可能被共同在场的观察者视为没有能力处理日常事务的不合格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即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下意识脱口而出的言语,此时它们或作为情绪性的自我宣泄,或作为自我暗示,这种情况下它们是与自我进行的对话,并向自我解释自己的失当行为。总而言之,这些貌似自发流露的本能性反应其实具有高度的社会关联性,尤其是它们具有保持面子和自我的功能。
(四)礼节性忽视
礼节性忽视的常见实例是电梯间里的人们相互避免目光接触,他们或低着头盯着脚下,或注视着电子屏上显示楼层的数字。礼节性忽视表明,空间设置会对互动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倘若个体打破礼节性忽视的潜在规则,轻则让共同在场者感觉不舒服、惊慌失措、担忧或恼怒,重则招致人身攻击乃至暴力冲突。例如,美国社会在废奴运动之前,对黑人的“忿恨瞪视”是引发族群暴力的原因之一。礼节性忽视是面对面互动的基本特征,从表面上看,它是易接近性的对立面,但在实质上体现为仪式与道德的维度。礼节性忽视不是人际间的冷漠,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声明,表明个体对于同一情境中的他人是可获得的和易接近的,这也体现了对共同在场的他人的仪式性尊重,充分给予对方不想开启互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境中,个体彼此处于互动的临界值状态,互动行为随时可能触发,也可能不发生。因此,在微观人际互动中,礼节性忽视与易接近性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共同阐释着互动系统的特征及其可能性。
以上我们探讨的情境适当、参与卷入、易接近性和礼节性忽视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戈夫曼研究面对面互动系统的基本假定,即SIAC 图式,它们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不同“时刻”。㉑宏观的社会结构需要与这些不同的时刻或关于微观细节的假定保持协调一致,否则会影响空间结构的正常运作。譬如,曼宁认为,很多城市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设计的都市景观几乎不包含使用或生活在这些都市空间里的人们,仿佛他们是无足轻重的局部和琐碎之物。城市规划的很多失策和不尽如人意之处都是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SIAC 图式,倘若从人际互动的礼节性忽视和卷入结构等角度出发来衡量这些都市空间设计,它们大多显得呆板僵硬、毫无生气。如同传统社会学家一样,这些都市规划者由于过于熟悉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则,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如果日常生活空间的设置无法帮助人们从容自如地维持这些互动规则,那么社会世界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预期的场所。㉒
三、 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基础: CEIT图式
曼宁的SIAC 图式提炼了戈夫曼关于人际互动的四个基本假定,进一步系统化了戈夫曼的行动理论,使之成为一个理想型的行动阐释图式,可运用于分析一般性的互动行为。然而,仔细推敲曼宁的行动假定图式,它仍然存在某些缺憾,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曼宁的SIAC 图式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它未能充分包含互动系统的冲突性要素,而冲突、失调、失衡以及相应的调适是戈夫曼研究面对面互动的重要维度。功能主义的痕迹明显体现在关于情境适当这一基本假定,曼宁对它的择取和解释具有强烈的价值评判取向,因而无法有效地充当互动系统的基本构成原则。我们认为,行为与言语中出现的情境失当与情境适当同样构成互动系统的基本面。其次,从更高的抽象层次或模型建构的简洁性而言,易接近性和礼节性忽视可以并入参与卷入的范畴,它们都是参与或投入互动的同一面向。再次,与功能主义取向相一致,SIAC 图式仅探讨维持互动的诸要素,完全忽略互动的防御与补救机制。也就是说,它探讨的仅仅是戈夫曼所提出的仪式性互动,而未能涵括策略性互动等其他互动形态,因此限制了该图式的理论解释范围和效力,也未能充分反映戈夫曼较为完整的行动观念。互动的防御与补救机制是互动过程的重要构成,对此,戈夫曼探讨了很多日常互动中的失态或失常现象以及相应的补救措施。最后,SIAC 图式对行动者类型缺乏区分。譬如,在涉及谈话互动时,它没有区别“正式听话者”和“非正式听话者”;又譬如,礼节性忽视原则主要运用于陌生人,熟人之间则很难运用这项原则。
总之,曼宁提炼的关于戈夫曼的行动理论过于强调人际互动的仪式性,这些因素对行动系统而言都是促成性的。本文在前面论述面对面互动系统的规则时已经指出,互动规则既具有促成性的一面,也具有制约与限制性的一面,互动系统及互动秩序的正常运行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下维系的。SIAC图式的四个基本背景假定或规则本身是以表明“个体行为是通情达理、可理解的”这一根本性要求为基础的,曼宁认为这正是“言辞适切”的条件。由于戈夫曼将谈话视为互动的原型,因此曼宁也将“言辞适切的条件”视为互动系统的一般性条件,视其为关于互动背景的“假定之假定”。我们认为,关于行动理论的建构应遵循客观性、简洁性、普遍性和含括性等原则,尤其是纳入潜在的冲突要素。互动系统内部充满张力,时刻面临着各种风险,它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且即使是对仪式的考量,过度仪式化与仪式化不足一样,都无法持久地维系互动系统。因此,有必要重构戈夫曼关于行动理论的基本假定。
我们认为,“共同在场”(co-present)是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发生面对面互动的物理条件,社会情境效应也随之产生。同时,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行动者需具备基本的“表意性与感知性”(expression-perception),这种能力是个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根本条件。我们同样认为,参与卷入是互动系统的重要构成,但我们对它的理解与曼宁有所不同,SIAC 图式的四个因素事实上都可以纳入参与卷入这一要素。最后,我们认为领地性是戈夫曼行动理论不可缺失的组成,它与参与卷入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概言之,共同在场、表意性与感知性、参与卷入以及领地性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CEIT 模型”,它是我们理解的戈夫曼关于微观行动理论的基本假定与分析要素,下文我们对这四个假定/要素分别进行探讨。
(一)共同在场
戈夫曼对“共同在场”的定义是:“人们之间必须足够近,近到无论他们做什么都能够被他人感知到,包括对他人的体验,并且近距离到这样的程度,即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他人注意时,这也能够被他人察觉”。㉓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理解的“共同在场”主要包含四个要素。第一,“在场”主要是指身体在场,这是物理条件对互动产生的约束,并产生相应的互动属性。面对面互动是一种参与者身体在场的共时性互动,因身体在场而生成的社会情境是戈夫曼的行动理论的重要前提。第二,在场者的身份是陌生人,戈夫曼研究的互动世界基本由陌生人构成,它只偶尔出现朋友关系。第三,共同在场的个体彼此之间是直接“可获得的”,而且个体主动使自身处于他人“可获得”的状态,吉登斯将这种个体状态称作“在场的可获得性”。㉔第四,当互动参与者共同在场时,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交互作用关系。在共同在场的互动进程中,行动者彼此揣摩并适时调适自己的行为,彼此之间的相互感知将产生行动的互依性。这种交互性也促使行动者之间达成默契,每个人都信任对方采取的行动,因此不必投入大量的精力不间断地进行相互监视。总之,面对面互动的参与者是共同在场的,他们之间构成一种“次级关系”,而不是初级关系或初级群体。
(二)表意性与感知性
面对面互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参与者之间的认知与判断。由于个体与共同在场的其他参与者和旁观者之间进行的是表意性沟通,因此必须关注公共场所表意性的沟通行为及其规则。互动参与者是符合一定资质的行动者,他们具备普遍的表意、感知和认知能力,这涉及互动信息的发出与接收、理解与反馈等。倘若没有信息的表意和感知,一切形式的互动将无从谈起。行动者的表意性涉及信息的中介属性,身份与地位、情绪感受、意图和能力等个人信息通过它传达给在场的他人。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对行为与事件作出反应时,他们的眼神、表情与姿态等都包含着各种暗示与意义。不仅如此,说话的语调、反复和停顿等也传达出特定的表意性。就面对面互动而言,个体行动者的表意性与感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也是行动者表演能力的施展。
首先,个体本身是重要的信息源,它主要以两种方式表达信息:给予(give)与流露(give off)。㉕在聚集(gathering)或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个体通过意志性的行动(即意义共享的符号行动)给予信息,信息提供者需要对其所提供的信息负责。而信息的流露则是不由自主的、无意图的,信息提供者本人无法选择,它是行动者的在场和行动不可避免的产物。信息的给予存在相关动机,背后有明确的施动者;而信息的流露是额外的或剩余的信息,它所提供的内容及产生的后果是行动者无法预料的,而且不同的接收者会有不同的解读,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行动后果。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出于行为者的本意,而是共同在场的互动参与者如何理解信息,即认为它是意图性的抑或是本能性的。
其次,表意性信息具有反身性,并且具体化为身体符号(信息的身体化)。个体通过“稽查”和“监控”他人的表意性信息,推断其行为背后的意义。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能理解他人的行为活动,将它视为其行事能力的证明。用框架的术语来说,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发生在初级框架内,它是以能动者自身的经验为基础的,戈夫曼称之为“指导性作为”。㉖在指导性的行为中,个体同时监控着自身的行为与自然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运用初级框架指导自己的行为过程,并试图理解与自然事件不同的他人行为。
最后,个体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不断地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感知能力。共同在场的情境促成了信息的反馈机制,在面对面互动中,行动者通过身体操控和姿势摆放以及对他人信息的理解传达这种胜任能力。互动参与者起着表意性信息的收发器的功能,“每一位信息给予者自身是接收者,而每一位接收者同时也是给予者”。㉗行动者的感知能力是实现和维系面对面互动的基本条件。
(三)参与卷入
参与卷入包括易接近性。与曼宁的理解不同,这里所说的参与卷入包括补救性仪式等互动过程中的纠错机制和防护措施。首先,参与卷入表现为一种互动义务,即卷入义务,它是行动者开启和维系互动的促成性因素,公共场所有些陌生人占据着暴露的或开放性的位置,如警察、门卫等,这使他们能够顺畅地开启互动。其次,参与卷入意味着互动的约定性。戈夫曼认为,对运作共识的道德承诺是互动的基本规则。一旦运作共识遭到破坏,那么互动秩序可能面临崩溃。再次,参与卷入包含着互动过程中补救、道德的维度,也即互动系统普遍存在道德性与仪式性。最后,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除了仪式性互动与策略性互动等有意识的行为之外,还存在自发性卷入现象。这表明社会行动者并非总是理性、算计的,而且也未必都是仪式性的,它甚至还可能是无意识的,如同印象管理中信息的发出或流露所表明的。
个体有时会全神贯注、不由自主地卷入某项活动,此时他在心理上没有任何自我抑制,并通过选择性地忽略周围干扰或无关的事件而心无旁骛地卷入当下的互动,这种情况便是自发性卷入现象。自发性的卷入行为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即自然卷入。自发性卷入是非反身性的,或前反身性的。在自发性卷入的过程中,行动者受意识控制的程度较低,而且卷入本身并非首要的关注对象。自发性卷入现象表明,面对面互动进程中个体的表达并非完全受意识控制,虽然个体可能持续关注印象管理,但并不一直如此。戈夫曼认为,个体无法彻底脱离自发性卷入的自然发生,或者说自发性是个体经验存在的本质特征之一。自发性卷入这个概念驳斥了博弈、仪式以及拟剧等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行动特征。然而,许多从表面看来是自然的表意行为也可能不是自然的,这种自发性卷入是伪装的。人为地制造自发性卷入的表象会对“错误卷入的反射性后果产生阻尼效应”,同时也会对个体产生“疏离效果”。㉘与自发性卷入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正常的表象”。㉙行动者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努力呈现出这样一种表象,即他并不试图对自己或他人的形象进行操控和管理,从而赢得共同在场的他人信任并在互动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四)领地性
领地性主要涉及自我边界,它是每位互动参与者周围具有的无形的空间范围,个体在该空间范围内享有独占权。因此,领地性的含义与参与卷入中的易接近性是相对立的,领地性意味着独占、私密和排他。互动的领地与区域不是无条件彻底开放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在错综复杂、迅速变化的社会情境里,互动系统必须设立相对明晰的边界。而按照曼宁的SIAC 图式,行动者最多只有矜持和礼貌,没有拒斥和反对,这样的行动者在互动系统中将因礼仪的繁复而穷于应付,最终使行动系统陷于瘫痪。在戈夫曼的社会学里,互动系统是筛选性的,它有边界、门槛和规则,它不仅限制系统外的行动者,而且有一套合理的选择系统,并非所有行动者都会被无条件地接纳。对此,戈夫曼曾援引齐美尔的观点,后者认为,行动者周围存在“理想领域”,“虽然在不同的方向其大小不同,并且因个人所包含的关系的不同也会存在差异,但是该领域不能被渗透,否则个体的人格价值将被摧毁”。㉚因此,互动参与者需要运用规避仪式与之保持特定的仪式距离,确保其神圣的个人空间不受任意侵犯。戈夫曼还采用“互动膜”的隐喻㉛,这种膜发挥着过滤器的功能,选择性地过滤或阻止某些外部因素进入,从而使行动者全身心地专注于当下的互动;同时它也具有边界保护的功能,不至于同时发生的互动系统之间产生冲突。总之,领地性涉及自我的保存、面子以及私利性等。
共同在场、表意性与感知性、参与卷入以及领地性这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基本图式,它可以被简称为“CEIT 模型”。戈夫曼互动理论的前提是身体性的共同在场,互动参与者具有基本的表意和感知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行为时刻进行着大量的细微变动或者次级调适。互动系统是相对开放的,共同在场的情境性特质会生成促进互动的约定性,因而参与卷入既是行动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但是,特定的互动系统并非向所有个体完全开放,无关的个体不能像经过公共通道一样随意进出。互动的领地性意味着边界、筛选和保持距离。总之,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系统内部存在一种推拉力量,譬如,易接近性与自我的领地、自发性卷入与义务性卷入、轻松愉悦与紧张焦躁以及博弈与仪式等,它是在一种动态的张力过程中保持平衡的。
四、 讨论与总结
戈夫曼对互动行为的理解整合了亚当·斯密、查尔斯·霍顿·库利、乔治·米德和古斯塔夫·伊克海塞等人的行动理念。㉜斯坦福·莱曼和马文·斯科特以拟剧论的笔调勾勒出了戈夫曼关于行动者的肖像:
戈夫曼的行动者,如同马基雅维利那里的君主一样,他们的生活颇为注重外表。他忙于日常例行的印象管理,有条件时展现自身的优势,演砸了则尽其所能进行挽救。他的日常生活由各种互动仪式构成,利用恭敬与风度,保全他自身和他人的面子,抑制可能毁坏游戏乐趣的行动,当场合需要时变得亲密,当接近可能是不明智时则保持距离,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充分意识到公共场所的行为要求。㉝
拟剧论视角下的印象管理、策略性互动中的博弈、仪式性互动里的恭敬与风度等,都体现了戈夫曼笔下行动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在《沟通行动理论》一书里,哈贝马斯论述了目的论行动、规范性管控行动以及戈夫曼的拟剧行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几乎无视戈夫曼分析面对面互动的仪式框架,认为拟剧论强调行动者通过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增强自我,个体行动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或策略性特征。在哈贝马斯看来,拟剧行动主要涉及行动者面对观众时的主观世界,戈夫曼也因此未能意识到言语行动(如谈话)本身具有弥合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之间鸿沟的潜质。总之,哈贝马斯认为,拟剧行动是“寄生性的”,它们有赖于“目的导向性行动的结构”。㉞另一方面,曼宁提出的SIAC 图式因其功能主义取向则过于强调戈夫曼关于互动研究的仪式性。我们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戈夫曼而言过于理性主义,曼宁的SIAC 图式又显得过于道德化,而本文提出的“CEIT 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两者之间的理论立场。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本文努力尝试的关于戈夫曼行动理论的重构不是设法调和微观互动过程与宏观社会结构,而是关于他的行动理论图式的进一步整合与完善。戈夫曼的社会理论无需我们去做微观—宏观、行动—结构之间的联结与耦合,因为他已经进行了充分诠释。
戈夫曼毕生研究微观互动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尤其是挖掘日常人际互动过程中那些貌似微不足道的方式和表达的重要性,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权宜性的概念或分析性的解释。从这些细致入微的分析中,戈夫曼试图抽取和分离出那些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并赋予面对面互动以结构与意义。戈夫曼的互动社会学试图建构出一种理想类型,即纯粹的“互动人”假设,他摒弃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历史和个性等因素,从而提出统一的分析框架。戈夫曼试图将面对面互动世界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析性领域并追求一般化的解释框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他的理论雄心丝毫不亚于帕森斯。然而,戈夫曼没有像帕森斯那样最终提出明确的理论图式。因此,曼宁通过整合戈夫曼社会学的某些关键要素,提炼出SIAC 图式,它们包括情境适当、参与卷入、易接近性以及礼节性忽视,但是该图式过于以功能和秩序为导向,导致它的解释力匮乏,因而有必要重新引入互动的张力,这样方能恢复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原貌。在曼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CEIT 模型”,具体包括共同在场、表意与感知、参与卷入以及领地性等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行动理论的基本假定和分析要素。
注释:
① Erving Goffman,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1), p.2.
②㉖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p.564, p.22.
③Paul Creelan, The Degradation of the Sacred: Approaches of Cooley and Goffman, Symbolic Interaction, 1987,10(1), p.29.
④⑩⑲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Anchor Books, 1961, p.320, pp.328-329, p.311.
⑤㉒ 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25, p.27.
⑥⑮㉓㉗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Free Press, 1963, p.124, p.43, p.17, p.16.
⑦ Erving Goffman, Felicity’s Cond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 89(1), p.47.
⑧⑨⑭⑯㉑㉘㉚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p.1, p.2, p.141, p.115, p.3, p.126, p.62.
⑪⑫㉛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1,p.26, pp.80-81, pp.65-66.
⑬ James Chriss, Habermas, Goffman, Communicative Action: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4), p.546.
⑰⑱ Erving Goffman,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Ph.D.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p.274, p.274.
⑳Erving Goffman,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85.
㉔Anthony Giddens, 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in P.Drew, A.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p.276.
㉕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1959, p.2.
㉙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238.
㉜ 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35-36.
㉝Stanford Lyman and Marvin Scott,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0, p.20.
㉞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