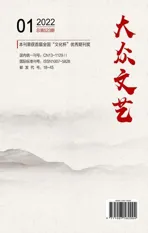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五中的内涵与主张
2021-01-27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72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作者对诗歌进行自施疏凿,正本清源之作,他以自成一体、言说成理的评诗原则,来区分泾渭,表达欣赏、批评、禁忌等等态度,起总结之效,亦深藏对未来诗歌发展方向的愿想。其中第二十五首“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是以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两首诗为讨论对象展开的文学批评,关于此首论诗诗的研究较为冷清,且历代以来少有的辨析和解释也分歧别出,未能达成基本的统一认识。
郭绍虞先生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中对“乱后玄都失故基”一诗说明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此诗表面上远离了“疏凿微恉”,但并非浅显地吟咏感慨,而亦指向作者对诗歌的评赏原则;接着,郭绍虞从刘禹锡此二诗生发出的影响最深远的怨刺话题入手,指出元好问通过这首诗,重点意图在讨论诗歌中的讥刺应否,并列出此诗位于“俳谐怒骂”与“女郎诗”二首之后的顺序作为辅证;再次,他引入苏轼对刘禹锡诗歌的创作接受和学习现象,并指出此诗位于论苏、黄诗各首其间,推论此诗不止咏刘,更旨在论苏;最后,郭绍虞引用了前人以元好问论诗之时,金未亡灭的历史事实来判断寄托与否的论证,否认了元好问在此诗中有自伤身世的寄寓。以上郭绍虞的谈论角度,可归纳为四点,即元好问在此诗中对诗歌讥刺的讨论;评价苏诗的立场;是否自伤身世;是否有失论诗宗旨,此四点亦可基本概括前人对此论诗诗的争辩话题,故本文以这四点为脉络,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
一、对讥刺的态度
郭绍虞因刘禹锡的看花诗语涉讥刺,推测元好问通过论刘禹锡的具体二诗,生发出在普遍的创作诗歌经历中,诗人“作诗应否讥刺之问题”的见解,而由于谈论讥刺的主旨,则此论诗诗紧列“俳谐怒骂”与“女郎诗”两首之后的顺序实属自然,能以此论据否定宗廷辅认为的这首“似应次东野一首之下”的排序失次说。郭绍虞对此诗重在语论讥刺的推论具有启发意义,其倾向元氏不赞同作诗讥刺的立场。后人对此观点更有发展和辨析,明确元好问对诗歌讥刺究竟是何种具体态度。如刘泽首先以“讽谕朝政、发洩愤慨”的看花诗给诗人招致贬谪祸害的历史后果,指出元好问是在评点看花诗的怨刺失度、无效之用,且认为元好问还想通过批评看花诗的错误模式,来树立写讽刺诗的范例,表达了元好问对“温柔敦厚传统诗教”的继承和推崇。陈长义对元好问论诗深意的理解更进了一步,指出元好问更认为“‘怨’要分清是非正谬”,才能有益于世。他从解释“乱后玄都失故基”的“乱”字具体何指着手,展开论述,他富有创建性地推翻了以往用“战乱”解释“乱”的常见指向,将这里的“乱”认为是“永贞革新”,即刘禹锡作看花诗的由来,“唐顺宗时期二王结党擅权”的永贞事件,唐宋以前的传统史学观点觉得这是一次小人的结党乱政,所以陈长义认为元好问将二王掌权视作“乱”行,切合当世之人的普遍认同,那么“乱后”即指唐宪宗监国之后对王叔文集团的清理与平息,而刘禹锡曾附丽二王,并因二王倒台写下怨讽情绪明显地表达不满的看花诗,则他在创作风格和政治立场皆违背了元好问的原则,因此,陈长义指出,元好问在本诗中既批评又惋惜了刘禹锡这类的有才有志之士们“蹈道不谨”,怨刺错指是非,导致无益于世。洪迎华亦将元好问在诗中的情绪解释为双重含义,不过内容与陈长义的看法有所差异,他从元好问主张温柔敦厚之旨的诗学思想和别裁伪体的写作意图,解读出元好问确有对刘禹锡讽刺失当的批评态度,又由“枉”字的徒然意,推出元好问对诗中怨刺于事无补、无益的伤感和悲悯情怀。
关于此首论诗诗中的怨刺,郭绍虞的综论具有启发意义,之后刘泽、陈长义、洪迎华等人进一步明确了元好问对诗中怨刺的态度,他们主要通过元氏一贯的论诗倾向,和在此文本中对看花诗的悲憾情绪,认为元氏是在以无功无用来批评怨刺失当,且前人主要讨论出“怨刺的方式太过直露”和“怨刺的内容错指是非”两类元好问认为的“怨刺失当”,则反之可以推断元氏亦在提倡一种温柔敦厚的创作形式、谨慎冷静的创作心理。
二、如何更及论苏
郭绍虞由苏轼对刘禹锡的创作接受,和此论诗诗排列位置推论元好问更旨在论苏,他指出苏轼初学刘禹锡,与刘禹锡有着相似的以“即事感兴之作,易为人摭拾陷害”的文学风格和人生遭际,并且此论诗诗出现在苏、黄各首之间,亦可知与论苏意图的关联。刘泽亦从苏轼的传承和论诗诗顺序入手,认为元好问以刘禹锡因看花诗发述怨刺而招祸,来批评初学刘禹锡的苏轼“嬉笑怒骂之失的”。
苏轼对刘禹锡的学习接受,宋人已多有讨论,尤其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载,“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指明苏轼对刘禹锡诗中怨刺的继承。洪迎华细致地通过分析相关讽刺诗的具体文本和创作背景,归纳了苏轼与刘禹锡在创作动机、仕途遭际和性格特征上的相似之处,且苏轼作品中对刘禹锡看花诗的引用或评论,诗词加起来有十一首之多。那么可以知道苏轼在写书写讥刺方面受刘禹锡的影响之大,二人有着相似的对讥刺话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及书写讥刺后相似的人生路径与曲线,并且,前人对刘禹锡看花诗和苏轼讽刺诗的主流认知是不认同,因“语涉讥刺”既有违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教观,也无益保全自身、平坦仕途、实现理想,所以,推论此首论诗诗中,元好问表面在论评刘禹锡以怨刺闻名的看花诗,但更深一层指向了学刘禹锡而讥刺观点、历程相似的苏轼,以刘喻苏的说法基本能够成立。然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元好问的这首诗虽表面咏刘,实际论苏,都呈现出作者的不认同态度,他却并非是针对两位诗人来给予绝对的批评,而更侧重于对一种文学现象、创作风格,即怨刺失度,发出告诫与警示。
三、是否自伤身世
郭绍虞不认同此首论诗诗存有作者自寓兴亡之感,他直接引用了大段《雪桥诗话》中的论述表明态度。杨钟义在《雪桥诗话》中,用遗山论诗之时金未覆灭的历史证据,推论其不应在这首诗中寄此自况情绪,反对朱介裴之前说。陈长义亦认为元好问完全是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来面对刘禹锡的看花诗,就诗论诗,没有将个体遭际所带来的情绪寄托其中。他将“乱后玄都失故基”中“乱”解读为“永贞革新”,将整句大意表达为,“永贞以后,王叔文集团遭到清除,被逐出朝廷,他们原来所依倚的唐顺宗已成过去,再也没有在朝把持朝政的根基了”,且认为“只堪悲”的“悲”,是元氏对刘禹锡等人“蹈道不谨”的惋惜和遗憾,不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命运,而“枉问”显有批评意味,并不是悲悯情绪的喷涌。而从诗歌中品味出自伤身世深意的,主要有周本淳、刘泽。周本淳因无法用充足的理由将“乱”对应成刘禹锡经历过的具体战乱,便认为“乱后玄都失故基”一句是无的放矢,不如指向元好问的借题发挥,更说得通,于是周本淳将“乱后”一句理解为不具指的“国亡家破”意,“看花”句则蕴含了亡国后的自伤身世之悲,全诗表面论刘,实则抒怀,充满黍离之悲。刘泽不认同周本淳的具体解说,认为他的观点不符合《论诗三十首》整体的逻辑,也未能对“乱后”一句的含义细究清楚,虽然如此,刘泽自己的阐释同样最终说明元氏在此诗中有自伤身世的情感寄托,他将“乱”具体解读为金宣宗贞祐四年的潼关战乱,即非统指“国忘家破”,也不针对刘禹锡所在时空的兵祸,而是元氏有感于刘禹锡的遭遇产生的联想事件,充满伤古怀今之哀思,所以尽管刘泽肯定元好问这首诗不离议论诗宗旨,但认为它明显地包含有想象与抒情的特征。
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对元好问是否在此诗中有自伤身世的判断依据,是如何认知首句中“乱”字的指向,否定元氏自寓兴亡之感的郭绍虞、杨钟义和陈长义,都坚定地认为元氏论诗之时金朝尚未亡国,便无从谈起“乱后”。的确,无论是从《论诗三十首》结构的系统性,宗旨的明确性考虑,还是从如何更合理、更自然地解释“乱”字具体所指的角度,较严谨的判断结果是元好问在此首论诗诗中并没有寄托家国悲怀,持相反观念的周本淳和刘泽对“乱”字的阐述,都没有能给出直接和充分的证据,所以在暂时还没有鲜明地历史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不管陈长义关于“永贞革新”的推理是否成立,总之,将“乱”划分为刘禹锡时代的动荡事件,认为元氏并未涉及此身经历,是更贴切文本内容和思想表达的观点。
四、是否有违论诗宗旨
郭绍虞认为元氏此首论诗诗虽似只就刘禹锡看花诗而言,但绝非仅为吟咏感怀之作,其中疏凿微恉的思索和论见并未缺失,元氏没有违背于组诗第一首中表明的论诗宗旨。刘泽秉持着《论诗三十首》结构完整性、主旨明确性的原则论述这首诗,他以元氏的论诗宗旨、批评标准及所论文本在组诗结构系统中的位置和功能,来解释诗歌次序和谈论元氏对讥刺、苏诗话题的主张。陈长义也是从组诗内容的完整性、思想的贯通性入手辨析文意,所以认为自许“诗中疏凿手”的元好问,绝不会写出一首对所论文本“无的放矢”而重在抒怀的论诗诗。持不同意见的有何三本,他认为元好问的这首诗论人为主,有感于刘禹锡的遭遇,发生叹惋,而未论及其诗,有失论诗宗旨。
关于元氏是否在这首诗中违背了论诗宗旨这一话题,论争激烈,然参与此话题讨论的前人对《论诗三十首》的“论诗宗旨”的定义实则趋向统一,由组诗首诗“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和末诗“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可明显地感知到,元氏论诗的意图在“疏凿”诗歌,背景是“书生论量”,故前人对论诗宗旨的认知基本同意郭绍虞的判断,即“就诗论诗,非由愤激,更无寄托”。而正因为前人对议论本位的论诗宗旨的统一认同,那么是否违背论诗宗旨的争议,实则是元氏究竟在此诗中是重以议论还是重以抒情的问题。本文倾向于元氏一以贯之了论诗宗旨,并未因抒怀破例。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此诗失次问题,这首论诗诗的位置不符合论诗对象的时代顺序,那么无论是出于“借唐论宋”的考虑,还是以紧邻“俳谐怒骂”诗来表达对怨刺论旨的强调,或是其他合理的猜测,总之皆源自议论需要,是为了论诗目的在铺张布局,若认为元氏重在咏怀,便难以解释这种突兀的排序结果。其二,是元氏身世与家国哀思间的矛盾,郭绍虞曾多次重申,在作者论诗之时金未亡灭,其“兴亡之感实无所施”,由此历史证据可得之,元氏确实不太可能在重大的战乱兵祸之前就“大动干戈”地借唐人之诗,深切地来表达悲伤、遗憾之情,甚至不惜突兀地调整论诗顺序,并且,刘禹锡的看花诗以讥刺闻名,而非家国哀情,若作为寄托兴亡之感的载体和起因,则不够典型,若作评判讥刺所用,则更具不可替代性。
五、结语
综合梳理前人对元氏在此首论诗诗中对诗歌讥刺话题、对苏诗态度、是否自伤身世与是否违背论诗宗旨四点的理解,无论是从事件的基本逻辑合理性,还是诗人的背景遭际和论诗态度,《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五的主要目的应是在批评怨刺失当这种文学现象,且以刘、苏为具体实例引发这一讨论,仍遵循了论诗宗旨,并无作者更多身世悲情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