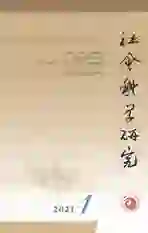内外有别:风险社会背景下村庄疫情防控逻辑
2021-01-26王毅杰卜莲秀
王毅杰 卜莲秀
〔摘要〕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村庄带来了一场严峻考验。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村庄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反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仍受质疑,具有“严防死守”与“意识淡薄”两副面孔。本文通过西部Y村的研究发现,村庄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内外有别”的逻辑,对外采取各种硬核的措施与规则,而对内维系传统的人情与面子。之所以采取差别化的应对方式,是村民基于“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判断。疫情之下,“风险”成为影响内外之分的关键因素,个体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结构。在风险社会,尤其当重大疫情来临时,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与衍生性,“内外有别”不仅是简单的伦理与规则,更是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关键词〕 村庄;疫情防控;风险;内外有别;自我保护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54-08
〔作者简介〕王毅杰,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卜莲秀,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11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健康与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贝克用“风险社会”这个词来专门描述现代社会的特征。①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也进入了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②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农村疫情防控是整个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单位是村庄。村庄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反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有效应对疫情,村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硬核防控措施,如小喇叭循环宣传、封村堵路、卡点劝返等。但其防控的有效性仍受到质疑,在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中,能看到许多关于农村疫情防控意识淡薄的评论,马良灿、张雅光等学者也指出了这一问题。③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一方面,村民自发参与封村堵路等疫情防控,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们出门不戴口罩、经常串门以及大规模集聚等。
实际上,在农村的疫情防控中,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防控面貌,一面是村民与村干部积极参与防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面则是村民与村干部“消极”的防控行为。首先,我们需要弄清农村疫情防控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其次,追问为何会呈现出对立的防控面貌,與村庄差序化的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最后,探究其背后深层次的缘由,挖掘农村社会风险防控的保护机制。
本文以Y村为例。Y村位于西部边缘山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由5个村民小组组成,700余户、近3000人。疫情期间,外省返乡人员200余人,其中湖北返乡与探亲人员10余人。面对疫情,村民积极参与防控,自发参与堵路、卡点劝返等。截至目前,村庄无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2020年1月至3月,正是国内疫情严重的时期,第二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该村的疫情防控中,全程参与入户排查、卡点值守以及流动人口登记上报等,这不仅让我们有幸为疫情防控做出一定贡献,也给我们收集资料提供了便利。本文所说的村庄疫情防控主体不只是基层干部,还包括村民。在“群防群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疫情防控中。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虽已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国外疫情仍严峻,已经蔓延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风险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面对极大的风险。近半年,境外输入仍存在,国内局部地区疫情也出现“反弹”。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现今,风险防控已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农村作为风险防控的薄弱地带,应受到更多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检验农村风险防控的一个窗口,本文期望通过考察2020年西部Y村疫情防控的真实过程,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挖掘村庄风险防控的保护机制。疫情防控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我们重点考察疫情高发期的村庄防控情况,也关注到疫情后期及其常态化时期的情况。
二、村庄差别化的疫情防控
村庄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功能单位,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堡垒。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村庄采取了硬核的防控措施。村庄硬核的防控措施是如何运作的?其真实性如何?在Y村,我们发现硬核防控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村庄外来人口。在对内的防控上,仍未打破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与面子,甚至维护乡土规则的运行,但对村内的外省返乡人员并非一视同仁。
(一)外部防控:硬措施与硬规则
外部防控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与关键。为阻隔外部风险,疫情防控期间,Y村采取了多种措施,最硬核的当属封村堵路。封村堵路本身并不算新鲜,在2003年非典肆虐之际,很多村庄都实行了这种措施。
2020年1月底,正是疫情扩散之时,Y村村民与村干部把与周边村相通的5条小路用泥土、树枝等堵上,仅留一条通往外界的主干道。即使在2月底,村里接到撤销卡点的通知,也没有立即疏通被堵的道路。对于这种做法,大家都十分支持。参与堵路的村民刘先生表示,“只有把所有路都堵上,才能防止外面的车辆进来,堵上才是最安全的。”尽管知道政策上不允许,但是村支书认为这是最能保证村庄安全的做法。
卡点劝返也是村庄应对外来人口的硬核措施。疫情期间,Y村设了5个劝返点与1个卡点,成立了5支群防队伍60余人轮班值守。卡点与劝返点主要是为了劝返外来人口,Y村在劝返外来人口上态度十分强硬,即使是送生活物资的车辆也不让进入。在第二作者所在的卡点,曾遇到送奶粉与尿不湿的外来车辆,尽管司机坚称自己从未回家,还是被拦截在村外,最终只能把物品放在卡点处,村民自己来取。
Y村还发生了一起全力追踪外来车辆事件。2月下旬,一则浙江省车辆进入村中的消息传开,群防队伍开始挨家挨户排查,并通知各家各户,一旦发现该车辆,及时上报。虽然后来发现该车辆并未进入村中,只是途经了村外的公路,但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实际上,在对外的防控上,村庄“严防死守”,有着十分硬核的措施与规则,形成了一种封闭式治理。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通过集体排斥外来人口的方式保护村庄内部的安全。④那么,在内部的防控上,又有何不同呢?
(二)内部丧事的举办:人情与面子
乡土社會是一个讲究人情与面子的社会。⑤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描述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⑥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人情”可作为社会交易的资源。它不仅有金钱、财货或服务等具体的物质层面含义,还有抽象的情感含义。⑦疫情之下,村庄人情与面子等内部规则并未完全被打破。
在Y村的疫情防控中,人情与面子的运作体现在卡点放熟人、不上报本地返乡人员以及参加集聚活动等多方面。其中丧事最充分展示了这点。在Y村,如果有人去世,需要守夜、举办酒席、抬棺与埋葬仪式等,这些环节都需要街坊邻里的帮助。
1月24日,村里王先生猝然离世,阴阳先生把葬礼定在月底。当时, Y村所在县的确诊病例为本省最多,村里也开始排查外省返乡人员,并宣传坚决禁止乱办滥办酒席、推迟婚庆活动、殡仪馆暂停集中治丧、民间简办丧事等规定。针对村中王先生的丧事,为了避免大量人员集聚,村干部对家人进行了劝导,希望不要请客收礼。不过,在“人情”与“面子”的运作下,王先生的丧事依然照常举办了。
首先是被默认的请客收礼。请客收礼是农村丧事酒席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使在疫情之下,这一规则仍未被打破。作为一种默认的文化规则,其运作只是更加隐秘。中国人对于这种默认规则有更强的领悟、体会、联想以及经验。⑧王家在村干部的劝导下,答应不请客收礼,只是宴请当地关系好的亲属。但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默认丧事仍按照以往村中规则,私下都在讨论吊唁、送礼与帮忙事宜。王先生的子女也表示虽然父亲在疫情期间去世,但仍希望为他举办一个风光的葬礼。
其次是亲属邻里的照常参与。王先生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邻居自他去世起,就到他家帮忙。每天有20多位女性煮饭做菜,3位或4位男性守夜,另有一批在场打牌喝酒的人。在31日的酒席上,据参加的村民说,王先生家中集聚了300多人,摆了30多桌;外村的兄弟家和女儿家还各买了一只羊来祭奠。为何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还有那么多村民来参加?村民易先生提到,“我儿子讨媳妇的时候,他家来了,还是要去一下。他家亲戚都是附近村的,没有从远处来的人,是安全的。”与易先生一样,很多村民之前都与王家有礼节来往。而亲属更多的是基于义务来参与葬礼,“我岳母的哥哥,肯定要去的,在这种时候,人少更要去帮忙。要是没人去帮忙,都无法抬上山。”由此看出,疫情之下丧事中的人情仍存在,作为熟人社会里默认的文化规则,即使在知道不能集聚的情况下,很多村民还是参与其中。
最后是村干部的默许与理解。村干部对于丧事酒席上的人员集聚都知情,表示理解。村长提到,“大过年的,又有疫情,遇到这种事情,也是没得办法,把人送上山都需要很多人帮忙。我们不可能去赶人,那太没得道德了,要被人家戳脊梁骨。都是当地人,没有远处来的,不然我们也怕,各个路口都是守着的,放进来的都是他家本地亲戚朋友,而且湖北那边来的都隔离了。”村支书表示疫情防控政策已经宣传到位了,没有必要去赶人,毕竟以后还要和村民打交道。村干部作为村庄土生土长的人,在政策执行中,仍会按照乡土规则办事,这与以往的研究相符合。
那么,疫情期间,村民对“自己人”都一视同仁吗?
(三)村内人的村外待遇:被严防的湖北返乡人员
一般来说,本村人与本村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流动性大大增加,村庄内部逐渐划分出留守村民与外出村民,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变迁。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之际,也正是农民工返乡之时。为应对疫情,各村庄都需要实时掌握流动人口信息情况,2020年1月至3月,各村内部逐渐清晰地划分出了“武汉返乡人员”“湖北返乡人员”“外省返乡人员”“本省返乡人员”“本地返乡人员”。相对于本地返乡人员,疫情期间,村中的外省返乡人员,尤其是湖北返乡人员,成为村中严防的“外来人口”,本村村民自然而然与之划开了界限。
对于湖北返乡人员,墙上都被拉上“此户有湖北返乡人员,请勿接触”的横幅,一律要求居家隔离14天。熟人社会中,即使不拉横幅,大家都清楚具体情况,会自觉地不去接触他们,并刻意保持距离。村里小卖部的张阿姨提到,“我家上面那家他儿媳妇就是从湖北来的,来我家这里买东西必须要戴口罩才能进来,他们也很自觉的,每次来买东西都是戴起口罩来的。”从湖北返回的唐女士表示,“自从我们返回村里,从来没有人来我家串门,都已经过了14天的隔离期了。”
在Y村,看到了“内外有别”的差别化防控方式。对外采取了各种硬核措施,严防死守;而对内讲究人情与面子等规则,在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场300多人的葬礼酒席,但也不是对所有的村内人都一视同仁。接下来,本文将回答:为什么村庄在疫情防控上会内外有别?疫情之下的内外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了解村庄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弄清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如何思考与行事的。
三、安全的“自己人”与危险的“外人”
疫情防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这个系统无可避免地镶嵌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⑩因此,如果想弄清为什么村庄会采取内外有别的防控方式,就需要了解乡土社会结构与文化。在乡村社会,人们习惯性地把人分为“自己人”与“外人”,并区别对待。“自己人”意味着知根知底,是安全、可靠、值得信任之人,往来遵循人情与面子等规则。而外人意味着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不可信、不可靠的,是有待深入了解和认识的,交往遵循契约规则。研究发现,内外有别的防控逻辑与村庄如何看待“自己人”与“外人”相关,在村民的认知中,“自己人”是安全的,而“外人”是危险的。但还需要注意到,疫情之下的内外之分不仅仅依赖于关系亲疏远近的判断。
(一)疫情之下的村庄“自己人圈”与“外人圈”
村民如何判断“自己人”与“外人”呢?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把本村村籍身份作为唯一标准。在村民的认知中,外来人口往往指那些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人,附近其他村庄的人是可以被当作本地人,并获得更多信任,有些还能发展为自己人。B11“自己人”与“外人”的划分还得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说起。何为差序格局?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B12
亲疏关系, 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即乡土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划分“自己人”与“外人”。广义上讲,相对于村外人,村内人都是“自己人”,并有着“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基本判断,安全交往圈更可能与“自己人圈”重合,风险圈更可能与“外人圈”重合。常态运行的社会是这样,但疫情之下,个人、群体和机构都因风险而被组织、被监控和被管理。风险成为影响“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甚至可能是决定关系亲疏远近的最大砝码。常态社会中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呈下降之态,“自己人圈”与“外人圈”的边界出现了变化,村庄“自己人”也会受到“外人”待遇,村民对湖北返乡人员的严防证实了这点。该村村支书就表示,“我们村肯定没有,都认得哪家是什么情况,主要不要去湖北返乡人家,还有防着外面的人。”
在Y村,的确没有发生确诊病例与疑似病例,所以在村庄内部,当时作为高风险人群的湖北返乡人员往往与村外陌生人一起被划分到“风险外围圈”。疫情之下,每个人的“安全核心圈”可能是不一样的,但“风险外围圈”却是相似的,即湖北返乡人群与外来人口。家庭生活是中国文化的社会根基,它限定了社会信任的范围,经验和熟悉不再是信任的保证。B13从湖北返乡的唐女士表示,自从自己和丈夫回家后,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和亲朋好友都不会来自己家,甚至避免相见,“像陌生人一样”。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疫情之下,人们的交往与信任缩小到低风险的村内人。村民被禁锢在某个圈子中,其核心交往圈有缩小的趋势,即“自己人圈”缩小了,“外人圈”扩大了。原有的人际交往圈出现了变化,原来的“自己人”出现陌生化的情况,即使在村庄内部也划分出“安全核心圈”与“风险外围圈”。关于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结构的一项研究中也发现,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呈现出明显内核与外围两级分化的结构。B14疫情之下,这种两级分化的结构更加明显。
(二)“风险外围圈”的防范与“安全核心圈”的维系
再进一步分析发现,疫情防控中的人情与面子规则主要发生在“安全核心圈”内。硬核防控主要针对“风险外围圈”。即村民在防范风险外围圈的同时,也在维系自己的安全核心圈。
Y村丧事的成功举办与各主体维护自己的“安全核心圈”相关。村民选择是否参与有着风险的判断,很多人因其在自己的“安全核心圈”才参与。在他们的判断中,王家没有外来的亲戚,在酒席上不可能遇到外来人与疫区返乡人员,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村民李先生提到,“王家亲戚都是周边的,没有从很远地方来的,都是安全的。”同样,村干部之所以默许,也是基于风险逻辑与关系逻辑的考量。如村干部所说,“都是当地人,没有远处来的,不然我们也怕,各个路口都是守着的,放进来的都是他家本地亲戚朋友。”因此,各方都在维系着原有关系。村干部想维护正常的干群关系,不愿意破坏村庄原有的丧事规则;亲属不愿破坏亲属关系;邻里不愿破坏互帮互助的规则;即使关系不亲密但是“欠礼”的人也不愿破坏礼尚往来这一乡土规则。
所以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各方都在用一套内部规则维护着村庄安全的人际交往圈,即他们在防范外部风险的同时,也在维护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内部关系。如果行事规则跨越了边界,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三)“跨界”矛盾:误识风波
村庄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内外有别”的逻辑,即对“风险外围圈”防范、“安全核心圈”维系的并存逻辑。那么,如果破坏这一逻辑,会如何呢?
某天下午,村里的楊某和值守的张某因拦车问题发生了冲突。事件的起因是杨某骑车经过卡点处,被两个代替母亲值班的孩子误拦。而这时应同时值班的张某回家了,不知此事,回来听说后,便叫杨某来取车。但杨某拒绝了,认为拦了车就应该负责守着,并叫张某替他守一晚上,如果丢失了,也是张某的责任。张某自然不愿意,不断催其来取车。不久,杨某来到卡点处,与张某争吵起来,开始只是围绕为什么拦车的问题争吵,之后逐渐上升到打骂的程度。杨某还叫来自己的几个哥哥,将张某打伤。势单力薄的张某叫村干部来调解。在了解事件的原委后,村干部认为是杨某的错,应该支付张某的医药费。但杨某觉得不该拦自己的车,大家都是本村人,截留了自己的车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并扬言不会放过张某。
这起事件是Y村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唯一冲突事件。其中,可看到内外识别发生错误,会引起矛盾,破坏村庄原有秩序。杨某与张某的矛盾仅来自一场误识风波,两人在村中没有任何恩怨,也未发生过矛盾。在这场风波中,不是张某拦截的车,为何杨某却纠缠他呢?原来在此卡点,杨某是第一个被拦住不让车辆通过的本村人,杨某觉得十分没有面子,但是又不能冲两个孩子发火,只能以张某不帮其守车为由出气。按照村内“自己人”的防控逻辑,杨某作为村内的熟人,且非外出人员,值守人员应该给其面子。拦截杨某的车,不仅损害了杨某的面子,也表明对杨某的不信任。从该案例中,也可看出,“内外有别”的规则使疫情防控政策更具弹性。
村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关键的是在这个社会中,有着一群被特定历史塑造的、具有独特面貌的人,这些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结构,在其中人们通行的伦理和规则是“内外有别”。B15内外有别的疫情防控是村民基于“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判断。但在风险社会中,“内外有别”仅是一种不变的伦理与规则吗?
四、内外有别: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乡村社会是个内外有别的社会。内外有别的伦理与规则不仅表现在疫情防控中,而且表现在村庄应对外来危险的各个方面。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衍生性。农村作为风险防控的薄弱地带,防疫体系极不完善,这决定了内外有别的伦理与规则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与行事准则,实际上也是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一) 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内外”的动态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一大特征,而流动性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疫情随时有扩散与反弹的可能。为应对风险,村庄对“自己人”与“外人”的划分也处于动态之中。
乡土社会中个人的自我边界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和动态性,“自己人”与“外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具有很强的情景性和自我中心性,当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内外之界限也发生变化。B16疫情之下,人们信任与交往的边界圈子是随着疫情风险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高风险时期,村民交往与信任缩小到低风险的村内人,风险逻辑甚至支配了关系逻辑。而在疫情后期,即低风险时期,“自己人圈”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风险不再是影响人们人际交往圈的重要因素,回归到正常的村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调研中,湖北返乡的唐女士一家在疫情严重时期受到了“外人”待遇,被村民严防。但在疫情低风险时期,街坊邻居也都参加了她弟弟的婚礼,他们一家重回村庄“自己人圈”。在村庄熟人社会,风险排斥是短期性的,并不会导致长期的人际隔离,常态化防控时期的村庄社会关系一如既往。
疫情之下的“自己人”与“外人”的边界变动表明,差序格局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其中也蕴含着个人的能动性,个人会利用差序格局的伸缩性来规避风险。实际上,这也是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表现,不过这种理性化与经济利益无关,而是与生命安全相关。关系理性会驱使人们计算维持与拓展关系的得失,自我在其中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决定着交往圈的大小。B17当然风险在其中所占比重与关系亲密程度相关,关系越亲密,风险因素在其中引起内外之分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村庄整体来看,“内外”的动态性表现为村庄的封闭与开放的改变,即随着风险的变化,村庄的封闭与开放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高风险时期,疫情威胁的不只是个体的生命,而是整个村庄的生存安全。在此情况下,村庄通过封闭式治理来应对风险。但随着风险等级的降低,村庄也会调整自己的边界,对外越来越开放。如果疫情出现反弹,村庄又会再一次封闭。从经济边界和社会边界来看,疫情之下的村庄都是较封闭的。但是这种封闭性与维护村庄的经济利益无关,而与村庄的生命安全相关。以往研究主要讨论的是村庄的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但在风险社会中,尤其在重大疫情下,不得不考虑村庄的风险边界。经济利益在风险社会被贬值,遭受生命意义上的剥夺。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受到风险边界的影响,甚至村庄的风险边界决定了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的封闭性与开放性,而并非常被提及的经济利益。
当然,村庄的封闭与开放不仅与外部风险相关,也与村庄自身的特质相关。一项研究显示,团结型和分裂型村庄较封闭,分散型村庄较开放。B18但在重大疫情面前,村民的集体生存意识被激发B19,不管什么性质的村庄,都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即使是当前,村民仍然认同于村庄,并对村庄有许多要求。B20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那些既不共享村庄社会规范、又不承担义务的外来者的排斥,对于维系熟人社会的存在是必要的。B21作为一种“集体话语”、记忆和体验形式的村庄,会产生强有力的历史和传统惯性,在现代社会,它仍是个体风险抵御的庇护来源。B22
(二)风险的衍生性与“内外”的调节性
在风险社会,风险一旦出现,就必然会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互作用,并产生一种社会放大效应。B23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带来健康安全风险,而且在疫情发展和应对过程中,衍生出诸如生活保障风险、社会信任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风险等。B24这说明在风险防控中,我们不仅要应对单一的健康风险,还要关注次生风险。对于村庄来说,疫情不仅威胁着村庄安全,也对村庄内生秩序造成冲击。这就要求村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既要应对外部风险,也要维持内部秩序。内外有別的防控方式具有一定的调节性,是有利于应对疫情风险与次生风险。
内外有别的防控实现了人情与制度的平衡,减少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冲突。从疫情防控政策来看,一些地区禁止村内集聚活动,甚至串门等,但这些与乡土规则相冲突。在风险面前,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村民既有规避风险的需求,也有维持原有交往圈子的需求。如果在内部防控中,政策执行过激,没有很好地区分“自己人”与“外人”的边界,会引起矛盾与冲突,破坏村庄内生秩序。内外有别的防控既把风险阻隔在村外以及村内的“外来人群”中,也减少了村庄次生风险的发生发展,减少了个人焦虑感,避免了关系孤岛的形成。
但乡土社会规则并非完全与国家疫情政策背道而驰,其中也有很多契合之处。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村庄治理与国家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上,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国家倡导适当的封城封村方式,这与村庄封闭性的特征不谋而合,而乡土社会内外有别的规则也是传染病防治隔离技术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国家与村庄之间,国家有效治理依赖社区的非正式机制B25,内外有别的防控方式正满足了这一条件。
总之,内外有别的防控逻辑既有效应对了风险的不确定性,也维护了村庄的内部秩序,满足了个人与集体的需求,实现了村庄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一。内外有别的规则是村庄在风险社会的一种保护机制,其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文化。我们对于这种保护机制并不陌生,孔飞力的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和缓解内部社会紧张,民众会将陌生的、来历不明的以及没有社会关系的流浪者视为村庄秩序的威胁。在村民眼中,这类人都是陌生的“外人”,他们通过排斥,甚至是清除的方式来保护村庄安全。在风险面前,“外人”被当作替罪羊以缓解威胁和矛盾,强化自身团结,实现内部秩序的维系。B26